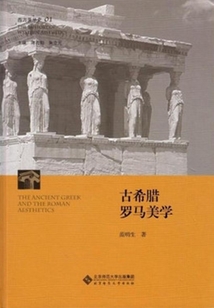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導論(1)
二十年以前,當我們還在醞釀編寫一套《西方美學史》(七卷本)之際,我們對這套書的未來面貌,還只有一個大致的輪廓,而并無清晰的藍圖。而今天,當我們終于把當初的設想變為七卷本的專著時,除了心情的激動和對已經歷的甘苦的淡淡回味之外,對西方美學的歷史發展,在總體上似乎也有了較之過去更為深切的認識和體會。當然,這只是我們這個寫作群體的一些粗淺看法,并不一定正確。因為面對同一歷史,人們完全可能也完全可以作出不同的闡釋,美學史亦不例外。
一、關于《西方美學史》(七卷本)的寫作宗旨
我們的老祖宗喜歡凡事必先“正名”,這里姑且沿用這一慣例先對本書書名“正”一下“名”。
首先,這是一部美學史著,其學科定位當是美學。但是,在西方,美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歷史并不長,從1750年鮑姆加登發明“美學”(esthetik)一詞,把美學從哲學中獨立出來至今,亦不過兩個半世紀。所以,嚴格地說,本書并不完全是學科意義上的美學史,而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美學思想史,即在美學學科誕生后,回過頭來把凡符合美學學科范圍的哲學家、理論家、批評家的有關思想都看作美學思想,加以歸納梳理,作出歷史的描述。正因為是寫美學思想史,而非嚴格學科意義上的美學史,所以其范圍相對寬泛一點,既包括歷代哲學家思想中涉及美學和藝術的內容,也包括嚴格說來屬于文學藝術理論的思想、觀點、學說。這一點跟我國一些中國美學史論著十分相似。當然,本書主要還是按照作為哲學的分支學科之一來理解美學和美學思想的,所以,除了明白無誤的美學理論、思想外,一般說來,只有具有某種哲學背景的文藝理論才進入我們敘述和寫作的視野。否則美學史就與文論史或批評史完全等同合一了,而這與我們的初衷不合。
其次,這是一部西方美學史,這就有個“西方”的范圍如何界定的問題。雖然我們沿用了朱光潛先生“西方美學史”的老書名,但在當今世界經濟日趨“全球化”的今天,“西方”的含義已有若干變化,如“西方七國首腦會議”,把東方的日本也包括了進去,這“西方”顯然就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地理概念,而幾乎等于“發達國家”的含義了。又如我們現在講“西方”,主要講歐洲、北美,而把地理上同屬西半球的中、南美洲排除在外;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又把同屬歐洲的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排除在“西方”門外,這里“西方”概念又不僅有經濟發達之意,還具有意識形態色彩了,其詞義與“資本主義世界”相近。這導致美學史寫作上一種奇怪現象:蘇聯美學家撰寫西方美學史時常把俄羅斯美學排除在外,而中國美學家寫西方美學史時則把沙俄時代的美學納入其內,卻把社會主義的蘇聯時期的美學排除在外。造成這種對“西方”概念認識和使用上的模糊和混亂自然有復雜的歷史、文化和意識形態上的原因,但卻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既成事實。
本書是把“西方”作為一個大范圍的地理(域)和文化雙重意義的概念來理解和使用的,具體說來,基本上繼承了朱光潛和中國其他美學家們的理解和使用。第一,從地理上說,我們把“西方”看成與亞洲等東方民族和國家相對應的地區來說的,主要指歐美。第二,從文化上說,“西方”主要指發源于古希臘的歐洲文化及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以后西歐文化在北美的傳播、延續和發展。中、南美洲等在文化上與西歐不屬同一系統因而不在我們的研究范圍之內。第三,對于俄羅斯和東歐各國的美學,我們采取了折中的辦法:將19世紀俄羅斯美學納入“西方”范圍,在第五卷中用了較大的篇幅專門予以介紹;但對蘇聯時期的蘇聯、東歐美學則基本不涉及,只寫到對20世紀西方美學影響很大的少數美學家與美學學派,如俄國形式主義、布拉格學派、巴赫金、英伽登等。這在安排上固然不太統一,卻也是無奈的選擇,一方面沿襲了前輩和已有的西方美學史的寫作慣例;另一方面是對蘇、東美學缺少資料的搜集與準備,即使想寫也心有余而力不足。
還需要說明的是,本書是一群中國學者眼中的“西方”美學史,此“西方”對于我們來說,不言而喻是屬于與中國傳統文化具有重大差異的另一系統的文化。我們在寫作時既常常感覺到中西文化之間有著某些根本的一致性或共同處,否則兩種文化之間的相互理解與溝通根本不可能,中國學者也就根本不可能理解和寫作西方美學史了;又時時感覺到中西文化之間的巨大差異乃至鴻溝,中國人與西方人從生活、生存方式到思維、理解方式,直至語言、表達方式,都有著重大的區別,這也導致中西美學在入思和言說等各方面的許多不同特點。我們寫作時,比較注重分析、揭示“西方”美學不同于中國美學思想的特殊性。當然,這一半是由于我們作為中國學者的文化基因所致,并非純然特意為之。
最后,這是一部西方美學通史。所謂通史,自然既不同于專史或專題史(如美論史、美感論史、藝術哲學史、審美觀史等),也不同于斷代史(如古希臘羅馬美學史、中世紀美學史、文藝復興美學史等),而是貫通古今的歷史。具體來說,就是把從古希臘至20世紀末,時間跨度達2600年之久的、美學思想演變的歷史,貫通起來寫,努力揭示其發展的軌跡和演進的規律。
據此,我們寫作時努力注意兩點。一是寫史一定要有歷史的觀念。不能把各個時代的單個美學家及其代表作、美學思想簡單地按年代先后敘述、編排起來,而忽視其內在的歷史聯系。在我們看來編年史不是真正的歷史著述。因此,我們每一卷都注意發現和概述各個時代重要美學家、美學思想之間的歷史承續、沿革、論爭、否定、創新等錯綜復雜的關系,盡可能清晰地勾勒出各個時代美學思想的發展脈絡和歷史軌跡。至于這種勾勒和描述是否科學,是否準確地揭示了各時代美學思想演進的歷史真相,則有待于讀者的評判了。至少我們主觀上是盡了努力的。二是寫通史一定要真正“通”起來,就是說一定要把古今貫通起來寫。具體來說,雖然我們各卷是由不同作者分工寫作的,但分工并不分家,人人都要有全局、整體觀念,都要把自己所寫的部分放在2600年美學思想的漫長歷史中來觀察、思考,而不能與整個歷史割斷。這里涉及的方面很多,既有各時代、各卷之間的前后銜接(如古希臘羅馬美學與中世紀美學間的承續、連接),又有前代美學家對后代美學家的影響(如柏拉圖對新柏拉圖主義乃至對黑格爾、叔本華的影響)和后世美學家對先輩的繼承或批判的分析,還有各個時代之間或同時代美學思想、思潮、流派之間的比較(如羅馬古典主義與17世紀法國新古典主義之間的異同、結構主義與解構主義的比較等),如此等等,每卷作者都要考慮到古今貫通這一層,都要在西方美學“通史”中把握和敘述自己分工所寫的那一部分內容。
此外,本書雖然是美學史,但因為美學在西方既是哲學的一個分支,又與藝術創造實踐和審美趣味、風尚息息相關,還同文學藝術理論密切聯系,所以美學史同整個思想文化史緊密相連、不可分割。更確切地說,西方美學史在一定意義上是整個西方文化史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有機組成部分。我們不可能離開整個西方文化史孤立地理解、說明西方美學史;同樣,我們也無法設想,如果排除了西方美學史,還怎么可能理解、闡釋整個西方文化史。因此,我們寫作時力圖一方面在文化史的大格局中把握美學史,而不是孤立地就美學談美學,把美學史從文化史中游離出來;另一方面又由美學史切入,透過美學史的敘述而展示文化史的風貌。一句話,著眼于文化史而落腳于美學史。
那么,本書是如何勾勒西方美學演進的歷史軌跡呢?我們認為,對整個西方美學的歷史發展,可以從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思路、在不同的層面上加以概括和描述。
朱光潛先生的《西方美學史》基本上是按歷史上大時代的劃分來組織素材的,它分為“古希臘羅馬時期到文藝復興”、“17、18世紀和啟蒙運動”、“18世紀末到20世紀初”三大部分。但這只是表層結構,其深層結構是三條重要線索。第一條也是最根本的線索在朱先生看來是,“美學發展史在大體輪廓上歸根到底,總是跟著社會史走的。就歐洲來說,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這三大階段中的美學觀點各有明顯的區別,都帶著社會經濟基礎的烙印。這是必須首先牢牢掌握的一條線索”。[1]這一條是從唯物史觀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這一基本原理推導出來的,即美學史跟著社會史走、社會發展史最終決定美學史。這自然是一條顛撲不破的馬克思主義真理,但在我們看來,這一條線索不但對美學,而且對一切思想意識、精神文化都適用,因此對美學史的寫作來說,似顯得過于寬泛、過于一般化。
也許朱先生意識到了這一點,又提出與美學較為接近的另兩條對立的線索來“統”整個西方美學史,這就是以古希臘的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兩大哲學家、美學家為代表的“兩種性質不同的對立線索”:
……他們所代表的一方面是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的對立線索,另一方面是浪漫主義與現實意義的對立線索。這兩種對立線索又是錯綜復雜的:我們不能庸俗化地在唯心主義與浪漫主義以及唯物主義與現實意義之間畫出等號,盡管在歷史上消極的浪漫主義曾和唯心主義結合在一起,而現實主義大半曾和唯物主義結合在一起。[2]
但是,在今天看來,朱先生所概括的這兩條互相對立的主導線索,似乎并不十分切合西方美學發展的實際;把一部西方美學史概括為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之間對立斗爭的歷史,進而使肯定的價值評判主要向唯物主義和現實主義方面傾斜(這一價值標準暗含在兩條對立線索的概括之中),顯然是過于簡單化且有失公允的。當然,這應當看作中國那個特定時代過于政治化的社會環境和思想氛圍在朱先生思想中留下的烙印與痕跡。況且,在具體闡述西方美學史上的許多美學家的美學思想時,朱先生也并未處處緊扣這兩條主線,倒是時常有意無意地偏離這兩條主線而作出深刻精辟的論述。
本書分卷基本上承襲了朱先生的《西方美學史》,第一卷為古希臘羅馬時期的美學,第二卷為中世紀至文藝復興時期的美學,第三卷為17、18世紀美學,第四卷為德國古典美學,第五卷為19世紀美學,第六、七兩卷為20世紀美學。如把這一分期(分卷)也看成本書的表層結構的話,那么,本書的深層結構,大致上可以概括為:三個階段、兩條主線。三個階段是:本體論階段,認識論階段和語言學階段;兩條主線在特定意義上為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本書基本上是按此思路展開論述的。下面試分述之。
二、西方美學發展的三個階段
把西方美學史分為本體論、認識論、語言學三個階段的基本原則是跟著哲學史走。原因很簡單,這既符合西方美學發展的實際,又符合西方視美學為哲學的一部分或分支學科的主導觀念。西方哲學從發端起,就孕育、包容著美學思想和觀念,古希臘各派哲學家以至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大家的美學思想都是從其哲學思想中派生、推演出來的,都是其哲學思想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缺少了其美學思想,其哲學思想就殘缺不全,無法理解;同樣,離開了其哲學背景,其美學思想也就變得突兀孤立,難以闡釋。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20世紀。20世紀美學雖然出現了諸多劇變和“轉向”,從古典主義美學形態走出,經過現代主義,走向后現代主義,但美學與哲學的密切關系仍然未變,有時美學甚至直接就是哲學,而哲學有時又以美學形態來表達。誠然,一些后現代主義思想家不但主張消解美學,也主張消解哲學,他們的入思和言說方式也確實與傳統哲學、美學大不相同,但細究其入思路徑,其消解哲學、美學的主張,仍未能最終擺脫西方歷來美學與哲學一體化的傳統。如法國思想家利奧塔的后現代哲學的核心是“讓我們向統一的總體性(totality)開戰”[3],即向傳統哲學追求的普遍性:統一性、整體性和極權開戰,以實現后現代性對現代性的顛覆。沿此哲學思路,利奧塔對西方傳統文化、主要是18世紀啟蒙運動以降的理性主義文化進行解構,他認為,理性文化的實質就是崇拜話語(詞語),也就是對欲望的僵化,欲望于是只有在藝術和審美的感性形(figure)中方能得到健康的實現。在他看來,只有顛覆理性主義話語文化,用藝術和形象來拯救感性欲望,才有可能根本上拯救西方文化。對此,有的西方學者精辟地概括道:“利奧塔希望使形象進入和塑造話語”,“其目的是用形象的語匯來打破抽象的理論話語,用采取越軌的文學策略的新語匯來摧毀霸權話語”[4]。由此可見,利奧塔的后現代主義美學思想仍與其顛覆傳統的后現代哲學一脈相承,血肉相連。
既然西方美學的歷史發展基本上是跟著西方哲學的歷史發展走的,所以,國內外哲學界不少人把西方哲學分為本體論、認識論和語言學三個階段的觀點,也大體適用于西方美學史。
下面,我們試分別對這三個階段作一概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