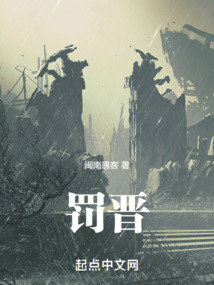最新章節(jié)
書友吧 4評論第1章 ,太安二年
太安二年,公元303年。
三月入尾,春末夏初,北方余有幾許殘寒。
通往鄴城的幾路官道上,處處可見軍旅開拔的行蹤,大到千人百騎,小到三五十一股,隊(duì)列有序,向著郡境南部調(diào)動(dòng)。
兵將們神情氣志多顯高漲,似乎對即將到來的戰(zhàn)事躍躍欲試。
距離鄴城西南十五里的北杜驛,一輛雙駕馬車在七、八騎士的扈從下,踏塵而來,車轅積滿干泥,輿身更是濺沾了無數(shù)泥斑;隨同的騎士們,亦是人與馬,雙雙宿積風(fēng)塵。
八日前,洛水失堤,淹沒了向北的一片官道,致道路淤結(jié)。連日趕路,也不顧上收拾車身,這才顯得邋遢不堪。
不過,驛站小吏隔著老遠(yuǎn)見了,仍不敢怠慢,殷勤的跑出了驛院門來迎。蓋因這輛車乃皂蓋朱轓,制為中兩千石官員專用。
陪車的仆人掀開車簾,車上竟走下來一位弱冠青年,著禪袍,披素色斗篷。
盡管說當(dāng)今朝綱亂象,帝權(quán)薄輕,臺司將軍幾乎任性敕封,但以弱冠之年行兩千石者,仍屬罕見。
驛站自小吏到仆役,無不小心謹(jǐn)慎,生怕這又是哪一家的王公貴族。
“給外面的騎士備一些水,再給馬用一些好料。”仆人上前向驛吏交代,他手中捧著一方錦盒,跟著驛吏一同來到后廚。
錦盒打開,里面盛著的是一枚陶碗。
士族子弟外出,必不會(huì)與平民共用食器。
那青年則自顧自走進(jìn)了驛站內(nèi),尋一處角落的坐榻落座。
驛站小吏和仆役,看茶喂馬,分頭行事,不敢有誤。
此時(shí),驛站內(nèi)尚有幾名軍漢坐在另一邊用食,刀、弓放在身側(cè),長槍則依在墻沿,其中一人還背著信壺,看樣子是為長途旅奔的軍驛騎兵。
他們對青年的出現(xiàn)視而不見,如今官制混亂,派系林立,無論士、民、軍,皆各奉主府,而無視國綱。
“剛才說到哪兒了……對,就是上個(gè)月,長沙王無緣無故處死了河南尹李世容、郎中令卞玄仁,還收捕了馮侍中。”一名體毛豐盛的軍漢說道。
他一邊喝著粟飧(sun)的酸湯,一邊壓低身形,神情故作嚴(yán)峻。
“這離齊王殺右光祿、裴尚書才過去幾年啊?”另一名軍漢答話道。
“嗐,誰能記得清楚這些呢,頭些年里,洛中數(shù)月一變,上一道檄文還沒傳到,下一道檄文又發(fā)出來了。”
“今次成都王調(diào)兵,怕就是因?yàn)殚L沙王濫殺無辜的事吧?”
“你可別亂說?就我知道的,義陽南蠻張昌賊聚眾嘩變,在荊州鬧得不可開交,成都王此次發(fā)兵,乃拜表南征張賊。”
“可我怎么聽說,河間王也從長安發(fā)兵了?”
“皇家的事,用得著你操心嗎?”
角落的青年默然聽著,他心中當(dāng)然清楚,所謂長沙王誅河南尹、郎中令,捕侍中,看似是濫殺無辜,實(shí)則卻是因?yàn)楹娱g王司馬颙(yóng)忌長沙王司馬乂(yì)獨(dú)權(quán),暗通河南尹在內(nèi)的幾位朝官,試圖暗殺司馬乂。
然,東窗事發(fā),遂被司馬乂先手誅之。
八王之亂,司馬家從親王到外戚,仿佛五石散磕過頭了一樣,集體性失了智。所有人的動(dòng)機(jī)、行為,甚至人設(shè)的轉(zhuǎn)變,都毫無正常邏輯可循。
這大概就是上層建筑的“視界”吧。
這般朝野敏感的話頭,若換作其他時(shí)期,豈容這些大頭兵私下竊議?
無他,猶是八王之亂遷延至今,國威已遭動(dòng)搖。禮樂既崩,便無法度。
“兄長,你就跟弟透個(gè)底兒,此番咱們當(dāng)真是要往荊州去么?”那軍漢仍有幾分好奇,忍不住向大胡子追問道。
大胡子神秘一笑,不疾不徐喝完了碗里的酸湯。
“這么跟你說吧,我這壺里的信,告的就是那張昌賊已克下樊城,新野王殉國了。”他先賣了一個(gè)關(guān)子。
“嗐,這么說,咱們真得南下荊州了。”先前那軍漢有些苦惱,繼而嘆息道,“兩地可有千里之遠(yuǎn),這一去,也不知什么時(shí)候才能歸家。”
如今在魏郡集結(jié)的軍隊(duì),有成都王所轄的王國兵,也有成都王領(lǐng)大將軍治下的外軍,還有臨時(shí)被征召起來的州郡兵以及各雜號將軍的治兵。
除外軍與國兵之中的部分上軍是為職業(yè)軍人之外,大部分國兵的中下軍、州郡兵實(shí)則都是農(nóng)兵性質(zhì),有家有地,自然不愿發(fā)外遠(yuǎn)征。
“聽我說完嘛。”大胡子話鋒一轉(zhuǎn),笑瞇瞇的又道,“除樊城戰(zhàn)事之外,荊州司馬陶士衡的援軍也已經(jīng)克復(fù)襄陽了。”
“是嗎?自家的兵處置自家的事,這才像話嘛!”軍漢欣然說道。
“瞧著看吧。總之,這次不是去荊州,就是去洛都。”大胡子說著,抹了一把粘在胡子上的酸湯,又在褲腿子上蹭了蹭。
“也罷,高低洛都要比荊州近不少。”軍漢點(diǎn)頭說道。
角落的青年聽到這里,臉色不禁流露出了幾許憂慮,這些軍漢所議成都王發(fā)兵之事,正是他惴心近半個(gè)月的事。
歷史上,成都王司馬穎假伐義陽南蠻張昌于荊州境內(nèi)的叛反,集麾下大軍二十萬南下。
事實(shí)上軍隊(duì)還沒集結(jié)完畢,荊州司馬陶侃便已經(jīng)平定了賊事。
爾后,司馬穎便直接改道,率兵徑赴洛陽,與河間王司馬颙一并,討伐掌控洛都的長沙王司馬乂。
此一役,雖說長沙王最終兵敗被殺,但過程中司馬穎與司馬颙饒是經(jīng)歷了不小挫折,若非最后在洛都的東海王司馬越突然反水,偷襲了司馬乂,只怕還得再熬上一番磨礪。
其中,司馬穎損失尤為慘烈,首戰(zhàn)大敗,損兵近七萬、折將十六員。
彼時(shí),指揮這一仗的人,乃司馬穎新征入府不久的陸機(jī),輔之事后遭到舊部諸將讒陷,陸機(jī)遂被司馬穎夷三族。
青年之所以惴心憂愁,無他,正因?yàn)樗闶顷憴C(jī)的長子陸蔚,待到數(shù)月之后,父親兵敗陷誣,自己與昆仲陸夏、叔父陸云、陸耽,皆將坐罪受戮。
此時(shí)的陸蔚之所以能未卜先知,是因?yàn)樗且幻┰秸摺?
兩個(gè)月前,他還是后世的一名老社畜,只因天寒地凍幫領(lǐng)導(dǎo)送文件時(shí),不慎摔倒,后腦觸地,不成想醒來之后竟穿越到了西晉末年。
豈不說這是個(gè)什么年代?可謂禮法崩潰,腐朽至極,用不了幾年還將人畜不分。
再說這穿越附身之人,倘使能提前三、五十年,那自當(dāng)是一份直通上流的貴身。
只可惜三國歸晉,吳郡陸氏已近山河日落,又且僅僅只剩下不足一年的時(shí)間,更是還將經(jīng)歷門庭滅絕的重大變故。
前路不可不謂之堪憂!
半年前,遭遇流邊的陸機(jī)一門,獲大赦返回洛都,不久后父親陸機(jī)應(yīng)司馬穎辟召,由洛都北上入鄴城,出“穎府”大將軍參軍。
至于他,卻因動(dòng)身之前突然大病了一場,在洛都遷延數(shù)月,痊愈之后即換得了全新靈魂。當(dāng)務(wù)之急的頭等大事,便是速赴鄴城,阻止即將發(fā)生在父親陸機(jī)身上的不幸。
這時(shí),軍漢們用完食水,提槍攜弓便徑自出門上馬而去。
目下年代,公人往來官驛,吃喝住宿皆為免費(fèi),看上去是一件難能可貴的社會(huì)福利。然而,這福利的背后,卻是由驛站吏、役及左近百姓們擔(dān)下所有開銷。
營運(yùn)驛站,本是當(dāng)?shù)乜たh征發(fā)的一種徭役。
而在不久之后的東晉,甚至還會(huì)出現(xiàn)更為荒唐的征役,郡縣一級公府,除丞、史、尉非公府自辟的吏掾,其余吏掾一律屬于出役,不僅沒有俸祿,甚至還要倒貼,真正做到了絕亙古、止通今的“付費(fèi)上班”。
陸蔚飲了一些水,不多時(shí),一直守在門外的仆人快步進(jìn)到了屋內(nèi)。
“大郎君,鄴城方向來了車,似是二郎君來迎了。”仆人躬身說道。
“嗯。”陸蔚點(diǎn)了點(diǎn)頭,起身往驛站外走。
仆人自是好生收起了剛才陸蔚使用的陶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