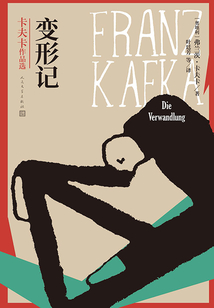最新章節(jié)
書友吧 3評論第1章 編者前言
弗蘭茨·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在西方現代文學中有著特殊的地位。他生前在德語文壇上鮮為人知,但死后卻引起了世人廣泛的注意,成為美學上、哲學上、宗教和社會觀念上激烈爭論的焦點,被譽為西方現代派文學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論年齡和創(chuàng)作年代,卡夫卡屬于表現主義派一代,但他并沒有認同于表現主義。他生活在布拉格德語文學的孤島上,對歌德、克萊斯特、福樓拜、陀思妥耶夫斯基、易卜生、托馬斯·曼等名家的作品懷有濃厚的興趣。在特殊的文學氛圍里,卡夫卡不斷吸收,不斷融化,形成了獨特的“卡夫卡風格”。他作品中別具一格甚至捉摸不透的東西就是那深深地蘊含于簡單平淡的語言之中的、多層交織的藝術結構。他的一生、他的環(huán)境和他的文學偏愛全都網織進那“永恒的謎”里。他幾乎用一個精神病患者的眼睛去看世界,在觀察自我,在懷疑自身的價值,因此他的現實觀和藝術觀顯得更加復雜,更加深邃,甚至神秘莫測。
布拉格是卡夫卡的誕生地,他在這里幾乎度過了一生。到了生命最后的日子,他移居到柏林,試圖擺脫不再屬于卡夫卡的布拉格。不管怎樣,跟他的同胞里爾克和韋爾弗相比,卡夫卡與布拉格保持著更長時間和更密切的聯系。在這個融匯著捷克、德意志、奧地利和猶太文化的布拉格,卡夫卡發(fā)現了他終身無法脫身的迷宮,同時也造就了他永遠無法擺脫的命運。
實際上,隨著卡夫卡命運的終結,一個融匯了捷克—德意志—奧地利—猶太文化的布拉格精神也宣告結束。像所有的藝術家一樣,卡夫卡也是他那個時代的產物;社會現實、家庭環(huán)境、個人身體狀況以及其他具體的因素,決定了他的命運和創(chuàng)作。他處在一個歷史發(fā)展的末期:隨著哈布斯堡王朝日薄西山的掙扎,布拉格的德語文化走向衰敗,但作為藝術家的卡夫卡并沒有去獵取當時時髦的風格,借以表現現實的經歷與感受,而是賦予表現那種末日現象以卡夫卡式的形式,一種并未使他生前發(fā)表的為數不多的作品能夠產生廣泛影響的形式。如果卡夫卡在他絕大多數作品和札記里表現了絕望和徒勞的尋求的話,那么這無疑不只是猶太人命運的寫照,而更多溯源于哈布斯堡王朝面臨衰亡和自我身心的絕望,也就是處于社會精神和文化危機中的現代人的困惑。
卡夫卡的一生是平淡無奇的。他出生在奧匈帝國統(tǒng)治的布拉格,猶太血統(tǒng),父親是一個百貨批發(fā)商。卡夫卡從小受德語文化教育,1901年中學畢業(yè)后入布拉格大學攻讀德國文學,后迫于父親的意志轉修法學,1906年獲得法學博士學位。大學畢業(yè)后,先后在法律事務所和法院見習,1908年以后一直在一家半官方的工傷事故保險公司供職。1922年因肺病嚴重離職,幾度輾轉療養(yǎng),1924年病情惡化,死于維也納近郊的基爾林療養(yǎng)院。
卡夫卡自幼愛好文學。早在中學時代,他就開始大量閱讀世界文學名著,尤其對歌德的作品、福樓拜的小說和易卜生的戲劇鉆研頗深。與此同時,他還涉獵斯賓諾莎和達爾文的學說。大學時期開始創(chuàng)作,經常和密友馬克斯·布羅德一起參加布拉格的文學活動,并發(fā)表一些短小作品。供職以后,文學成為他惟一的業(yè)余愛好。1908年發(fā)表了題為《觀察》的七篇速寫,此后又陸續(xù)出版了《司爐》(長篇小說《失蹤的人》第一章,1913),以及《變形記》(1915)、《在流放地》(1919)、《鄉(xiāng)村醫(yī)生》(1919)和《饑餓藝術家》(1924)四部中短篇小說集。此外,他還寫了三部長篇小說:《失蹤的人》(1912—1914)、《審判》(1914—1918)和《城堡》(1921—1922),但生前均未出版。對于自己的作品,作者很少表示滿意,認為大都是涂鴉之作,因此在給布羅德的遺言中,要求將其“毫無例外地付之一炬”。但是,布羅德違背了作者的遺愿,陸續(xù)整理出版了卡夫卡的全部著作(包括手稿、片斷、日記和書信)。1935至1937年出了六卷集,1950至1958年又擴充為九卷集。這些作品發(fā)表后,在世界文壇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從上世紀四十年代以來,現代文學史上形成了特有的一章:“卡夫卡學”。
無論對卡夫卡的接受模式多么千差萬別,無論有多少現代主義文學流派和卡夫卡攀親結緣,卡夫卡不是一個思想家,不是一個哲學家,更不是一個宗教寓言家,他只是一個風格獨具的奧地利作家,一個開拓創(chuàng)新的小說家。原因有二:其一,在卡夫卡的藝術世界里沒有了傳統(tǒng)的和諧,貫穿始終的美學模式是悖謬。一個鄉(xiāng)下人來到法的門前(《在法的門前》),守門人卻不讓他進去,于是他長年累月地等著通往法的門開啟,直到生命最后一息,最終卻得知那扇即將關閉的門只是為他而開的。與表現主義作家相比,卡夫卡著意描寫的不是令人心醉神迷的情景,而是平淡無奇的現象:在他的筆下,神秘怪誕的世界更多是精心觀察體驗來的生活細節(jié)的組合;那樸實無華、深層隱喻的表現所產生的震撼作用則來自那近乎無詩意的,然而卻扣人心弦的冷靜。卡夫卡敘述的素材幾乎毫無例外地取自普普通通的生存經歷,但這些經歷的一點一滴卻匯聚成與常理相悖的藝術整體,既催人尋味,也令人費解。卡夫卡對他的朋友雅魯赫說過:“那平淡無奇的東西本身是不可思議的。我不過是把它寫下來而已。”其二,卡夫卡的小說以其新穎別致的形式開拓了藝術表現的新視角,以陌生化的手段,表現了具體的生活情景。毫無疑問,卡夫卡的作品往往會讓人看出作者自身經歷的蛛絲馬跡,尤其是那令人窒息的現代官僚世界的影子。然而,卡夫卡的藝術感覺絕非傳統(tǒng)意義上的模仿。他所敘述的故事既無貫穿始終的發(fā)展主線,也無個性沖突的發(fā)展和升華,傳統(tǒng)的時空概念解體,描寫景物、安排故事的束縛被打破。強烈的社會情緒、深深的內心體驗和復雜的變態(tài)心理蘊含于矛盾層面的表現中:一方面是自然主義地描寫人間煙火、七情六欲、人情世態(tài),清楚、真切、明晰;另一方面是所描寫的事件與過程不協(xié)調,整體卻往往讓人無所適從,甚至讓人覺得荒誕不經。這就是典型的卡夫卡。卡夫卡正是以這種離經叛道的悖謬法和多層含義的隱喻表現了那夢幻般的內心生活——無法逃脫的精神苦痛和所面臨的困惑。恐怕很少有作家在他們的作品中把握和再現世界的時候,能把世界上從未出現過的事物的奇異,像他的作品那樣表現得如此強烈。卡夫卡的美學成就就是獨創(chuàng)性和不可模仿性的完美結合。
卡夫卡的世界是荒誕的、非理性的;困惑于矛盾危機中的人物,是人的生存中普遍存在的陌生、孤獨、苦悶、分裂、異化或者絕望的象征。他的全部作品所描寫的真正對象就是人性的不協(xié)調,生活的不協(xié)調,現實的不協(xié)調。從第一篇作品《一場斗爭的描述》(1903)開始,他那“籠子尋鳥”的悖論思維就幾乎無處不在。在早期短篇小說《鄉(xiāng)村婚禮籌備》(1907)中已經得到充分體現。主人公拉班去看望未婚妻,可心理上卻抗拒這種聯系,且又不愿意公開承認。他沉陷于夢幻里,想象自己作為甲蟲留在床上,而他那裝扮得衣冠楚楚的軀體則踏上了旅程。他無所適從,自我分裂,自我異化,因為他面對的是一個昏暗的世界。夢幻里的自我分裂實際上是拉班無法擺脫生存危機的自我感受;人生與現實的沖突是不可克服的。
在卡夫卡的文學創(chuàng)作中,中短篇小說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他那寓言式的短篇之作是世界現代派文學中獨一無二的經典(比如《在法的門前》《在馬戲場頂層樓座》《小寓言》等)。許多中短篇小說,無論從主題還是表現手法上都為他的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提供了深厚的鋪墊。短篇成名作《判決》(1912)是卡夫卡對自我分裂和自我異化在理解中的判決,是對自身命運的可能抗拒。許多批評家把《判決》與其后來寫的著名長信《致父親的信》相提并論,視之為卡夫卡審父情結的自白。實際上,《判決》是作者心理矛盾感受的必然,并不是現實的模仿。小說中的人物更多則表現為主人公格奧爾格·本德曼內心分裂的象征。在一個春光明媚的星期天上午,本德曼寫信給一個遠在俄羅斯的朋友,告訴他自己跟一個富家閨秀訂婚的消息。這個朋友是個光棍漢,流落他鄉(xiāng),與世格格不入,一事無成。訂婚標志著本德曼的幸福和成就,也就是這個世界令人尊敬的人生價值。而這位朋友的存在則成為幸福和成就的障礙。小說中,父親象征著某種無比強大的力量,由于他的介入,本德曼被從輝煌的成就世界里分離出來,父親稱他既是一個“純真無邪的孩子”,又是一個“卑劣的人”。本來的命運就決定他是一個與現實世界格格不入的、捉弄生活的故事敘述者,因此父親判他去“死”,本德曼欣然接受。接受良知賜予的、與現實世界不相融的生存,便意味著隨遇而安的本德曼的死亡。他懷著對父母的愛投河自殺,告別了追求功利的現實世界,存在的是一個漂流他鄉(xiāng)的陌生人。
1915年發(fā)表的《變形記》是其中篇小說的代表作。小說主要從主人公的視角出發(fā),描寫了在家庭與社會的壓迫下人的異化現象。如果《判決》中的本德曼是在自我分裂中尋求自身歸宿的話,那么,《變形記》的主人公在自我異化中感受到的只是災難和孤獨。一天早晨,推銷員格雷戈爾從不安的睡夢中醒來,發(fā)現自己變成了一只甲蟲。他掙扎著想從床上起來,但是,變形的身體和四肢無論如何也不聽使喚。他擔心失去工作,不能再掙錢養(yǎng)家,感到十分恐懼。格雷戈爾變成甲蟲之后,他厭惡人類的食物而喜歡吃腐敗的東西;他總是躲在陰暗的角落里或倒掛在天花板上。然而,他仍然保持著人的心理,能夠感覺、觀察、思考和判斷,能夠體會到他的變形使自己陷入無法擺脫的災難與孤獨中,生理和精神上的雙重痛苦日夜折磨著他。格雷戈爾被視為“一切不幸的根源”,連憐憫他的妹妹也要無情地“把他弄走”。自此,他不再進食,被反鎖在堆滿家具的房間里,在孤獨中變成了一具干癟的僵尸。格雷戈爾死后,全家人如釋重負,永遠離開了那座給他們帶來不幸的公寓。在郊外春意盎然的陽光下,父母親突然發(fā)現,自己的女兒已經長成一個身材豐滿的美麗少女,他們的心中充滿了夢想和美好的打算。
卡夫卡在這篇小說中用寫實的手法描寫荒誕不經的事物,把現實荒誕化,把所描寫的事物虛妄化。人變甲蟲,從生理現象看,是反常的、虛妄的、荒誕的;而從社會現象上講,又是正常的、可能的、現實的。卡夫卡在這里追求的不是形似而是神似。他以荒誕的想象、真實的細節(jié)描寫、冷漠而簡潔的語言表述、深奧莫測的內涵,寓言式地顯示出荒誕的真實、平淡的可怕,使作品的結尾滲透辛辣的諷刺。
《在流放地》(1919)是卡夫卡的第二部中短篇小說集,其中的同名短篇小說是備受讀者青睞的名篇。它在主題上與長篇小說《審判》緊密相連。在這篇小說里,作者以近乎自然主義的寫實手法,描寫了殺人機器執(zhí)行死刑那慘無人道的過程,而不容改變的執(zhí)行與被判刑人莫名其妙的罪行在讀者的接受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怪誕的對立。小說敘述者通過對殺人機器身臨其境的觀察而成為“不公正的審判和非人道的執(zhí)行”的見證者,通過荒誕的細節(jié)描寫使讀者自始至終感到難以擺脫的難堪:不僅是這篇小說“令人難堪,而更多是我們共同的時代和我這個特別的時代十分難堪,過去是,現在依然如此”(卡夫卡)。時代的罪責問題構成了這篇小說表現的主題。
繼《在流放地》之后,卡夫卡又發(fā)表了短篇小說集《鄉(xiāng)村醫(yī)生》。其中的同名短篇和《一份致某科學院的報告》屬于卡夫卡最受關注和最晦澀的作品之一。《鄉(xiāng)村醫(yī)生》的主人公夜里聽到求診的門鈴,要冒雪去好遠的村子搶救病人,可是檢查的結果卻是病人沒有病。小說層次多樣,情節(jié)怪誕,隱喻豐富,在似真似幻的夢境里,鄉(xiāng)村醫(yī)生經歷了許多離奇古怪的事情;他“承受著這個最不幸的時代的冰凍,坐著塵世的馬車,駕著非塵世的馬,迷途難返”,結果只有上當受騙的感覺。這里更多表現的是在人的內心深處產生作用而又不可名狀的力量。它們驅使鄉(xiāng)村醫(yī)生遵循治病救人的目的,可他卻常常感到無能為力。主人公最終停滯在孤獨無助的境地,他在現實中的孤獨感變成了各種各樣的幻覺和夢境的映像。學界對這篇小說有多種多樣的闡釋,當然讀者也有各種各樣的解讀。
像《鄉(xiāng)村醫(yī)生》一樣,《一份致某科學院的報告》也是卡夫卡最有爭議的作品。小說主人公是猴子紅彼得。它應一個科學院的要求,要它對其當猴子的歷史做出回答。這就是紅彼得致科學院的報告。它被從非洲捉來以后就關在籠子里,并且在其中“只有這樣一個感覺:沒有出路”。于是,它下定決心要通過模仿人而發(fā)展成人。這是它惟一可能的出路。它時刻有意回避“自由”這個概念。紅彼得最終成為一個受到廣泛青睞的雜耍藝術家。它始終把孜孜不倦地學習當作最重要的事情,并且在此期間已經達到了一個歐洲人的平均教育水平。紅彼得穿著像人一樣,住在豪華賓館里,遠近聞名,有社會地位,收入豐厚,過上了一種小市民的生活,最終實現了從籠子里找到出路的目的。《一份致某科學院的報告》是一個充滿寓意也令人費解的譬喻,作者以離經叛道的怪誕方式暗示出失去自由的現代人的生存問題。
《饑餓藝術家》是卡夫卡在其生命末期發(fā)表的一部短篇小說集。值得一提的是兩篇以藝術家為題材的作品,即《饑餓藝術家》和《女歌手約瑟芬或耗子民族》。前者是卡夫卡十分鐘愛的一篇作品,其主題是不安、絕望和徒勞地尋找“可吃的食物”和“可呼吸的空氣”。饑餓藝術家之所以在馬戲團的鐵籠里把饑餓當成“藝術”,是因為他在這個世界上無法找到適合他的食物,也就是他厭惡一切通常的食物。所以,饑餓對他來說是“這個世界上再簡單不過的事情”。他要把自己的饑餓藝術表現到極致,可是他卻被追求刺激的大眾和馬戲團的監(jiān)督人員徹底忘記了。最終他像《變形記》中的格雷戈爾一樣,尸體如同廢物似的被弄出了鐵籠子。取而代之的是一頭小豹子,它在里面立刻覺得很愜意,因為適合它胃口的食物很豐富。這里展現的是一個對立的象征,它既是對藝術家,也是對普通人生存危機意蘊深邃的寫照。而卡夫卡彌留之際發(fā)表的《女歌手約瑟芬或耗子民族》與《饑餓藝術家》在許多方面有相似之處。這篇小說似乎更多是作者命運多舛的藝術生涯的譬喻。
在作者生前未發(fā)表的眾多中短篇小說中,值得一提的是《中國長城建造時》和《地洞》。短篇小說《中國長城建造時》具有深刻的象征寓意和諷喻韻味。卡夫卡借用對中國長城分段建造過程的描寫,象征性地展現了現代人在一種捉摸不透、不可企及的權力機制統(tǒng)治下一切努力的徒勞。作為參加長城建造的敘述者在敘述的第二部分插入了一個膾炙人口的傳說“皇帝的圣旨”,從一個非同凡響的敘事視角凝練和拓寬了小說所表現的主題。
中篇小說《地洞》寫于作者逝世的前一年,可謂是《變形記》的姊妹篇,其構思更加抽象和怪誕,情節(jié)更加離奇和陰郁。小說的主人公是一個人化的動物,為了保存食物和維持生命,它精心營造了一個地洞,然而對于這個地洞的安全性卻始終表示懷疑。它被一種“神經質似的恐懼”折磨得寢食難安。無論它在地洞哪兒,始終憂心忡忡,總覺得已經陷入一種巨大的危險之中。與此同時,敵人卻從某個地方悄悄地往里鉆穿洞壁,咄咄逼近。于是,它惶惶不可終日,忽而躥到地面上,忽而又鉆進地洞里,似乎什么地方都不安全,它“能夠信賴的,只有我自己和我的地洞”。它一會兒把食物集中在一起,一會兒又將食物分藏在各處,但無論怎樣都不能使它放心。有一天,它在洞里突然隱約聽到有挖掘的聲音,而那聲音越來越像出自一頭大動物。從此,它陷入了更加恐懼和不安的境地,好像末日即將來臨,每時每刻都在準備著應對緊急情況的發(fā)生。可以說,《地洞》借用對人化的動物的描寫,以象征的手法,淋漓盡致地表現了現代人無所適從的精神危機。
本書收錄了卡夫卡生前發(fā)表和未發(fā)表的全部中短篇小說,意在向我國讀者展現卡夫卡中短篇小說創(chuàng)作的全貌,使讀者進一步欣賞和認識這位獨具風格和魅力的世界文壇大師,并從中得到新的閱讀感受。但由于我們水平有限,疏漏難免,敬請批評指正。
編者 韓瑞祥 仝保民
2014年6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