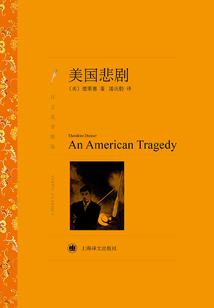
美國(guó)悲劇(譯文名著精選)
最新章節(jié)
書(shū)友吧 3評(píng)論第1章 譯本序(1)
美國(guó)夢(mèng)的殉葬品
德萊塞繼承了各個(gè)時(shí)代和各個(gè)國(guó)家的小說(shuō)家的傳統(tǒng)而集其大成,20世紀(jì)任何美國(guó)作家都無(wú)法與之倫比。作為生活紀(jì)實(shí)者,德萊塞可與托爾斯泰、菲爾丁、巴爾扎克等作家相媲美。
美國(guó)著名批評(píng)家
喬治·斯奈爾
從小說(shuō)家的首要任務(wù)是描繪出一幅既可信而又有重要內(nèi)涵的想象中的社會(huì)畫(huà)面來(lái)說(shuō),德萊塞是美國(guó)的巨人之一,是美國(guó)僅有的屈指可數(shù)的巨人之一。小說(shuō)在敘述中一次又一次嚴(yán)厲地抨擊社會(huì),深深地沉浸在人的痛苦里,并把人們?cè)诳駸釙r(shí)下意識(shí)的各種無(wú)定形的欲望深挖出來(lái),這一切都使我深為感動(dòng)和震驚。……《美國(guó)悲劇》的畫(huà)面波瀾壯闊,氣勢(shì)磅礴,完全可以說(shuō)是一部杰作。
美國(guó)著名評(píng)論家
歐文·豪
20世紀(jì)20、30年代美國(guó)文學(xué)揭開(kāi)了一個(gè)新時(shí)期。這是美國(guó)小說(shuō)的黃金時(shí)代,這二十年間,群星燦爛,異彩紛呈,顯現(xiàn)出空前繁榮的壯觀。當(dāng)時(shí),西奧多·德萊塞(1871—1945)異軍突起,馳騁文壇,獨(dú)領(lǐng)風(fēng)騷;他既是20世紀(jì)美國(guó)文學(xué)中第一位杰出的作家,也是美國(guó)現(xiàn)代小說(shuō)的先驅(qū);在美國(guó)文學(xué)史上,他不帶偏見(jiàn)地率先如實(shí)描寫(xiě)了新的美國(guó)城市生活,厥功奇?zhèn)ァK麚碛性S多忠實(shí)的追隨者,其中甚至包括他的同時(shí)代人舍伍德·安德森(1876—1941)等名家,他們都在他的周?chē)聣殉砷L(zhǎng),受到讀者們的青睞。這個(gè)新秀群落不斷地推出力作,使20、30年代成為美國(guó)文學(xué)史上最富有成果的時(shí)期,他們中間,諸如辛克萊·路易斯(1885—1951)和多斯·帕索斯(1896—1970)等名家無(wú)不深知德萊塞為他們未來(lái)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開(kāi)辟了道路。此時(shí)剛開(kāi)始文學(xué)生涯、后來(lái)成為“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人物的司各特·菲茨杰拉德(1896—1970)甚至譽(yù)稱(chēng)德萊塞是當(dāng)代美國(guó)的最偉大的人物。
1930年路易斯在榮獲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的莊嚴(yán)儀式上的答詞中,還向全世界昭示了德萊塞在美國(guó)文學(xué)史上的偉績(jī)。作為獲此殊榮的第一個(gè)美國(guó)作家,路易斯在答詞中宣稱(chēng):德萊塞才是理應(yīng)榮膺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的更佳人選。他說(shuō):“德萊塞常常得不到人們的賞識(shí),有時(shí)還遭人忌恨,但跟任何別的美國(guó)作家相比,他總是獨(dú)辟蹊徑,勇往直前,在美國(guó)小說(shuō)領(lǐng)域里,為從維多利亞時(shí)期和豪威爾斯式的膽怯與斯文風(fēng)格轉(zhuǎn)向忠實(shí)、大膽和生活的激情掃清了道路。沒(méi)有他披荊斬棘地開(kāi)拓的功績(jī),我懷疑我們中間有哪一位——除非他心甘情愿去坐牢——敢把生活、美和恐怖通通描繪出來(lái)。”因此,美國(guó)評(píng)論家認(rèn)為,德萊塞忠于生活,大膽創(chuàng)新,突破了美國(guó)文壇上傳統(tǒng)思想禁錮,解放了美國(guó)小說(shuō),給美國(guó)文學(xué)帶來(lái)了一場(chǎng)革命,并且把他跟福克納、海明威并列為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美國(guó)僅有的三大小說(shuō)家。[1]
德萊塞又是美國(guó)文學(xué)中第一位來(lái)自底層社會(huì)、非盎格魯—撒克遜血統(tǒng)的重要作家。本來(lái)美國(guó)作家中出身貧寒并不罕見(jiàn),畢竟都屬于美國(guó)社會(huì)內(nèi)部的“自己人”。然而,德萊塞是出生于印第安納州特雷霍特市郊的一個(gè)德國(guó)移民家庭,顯然是一個(gè)地地道道的外人。他秉性剛烈,桀驁不馴,曾經(jīng)自嘲為“以實(shí)瑪利,一個(gè)流浪漢”[2],意謂化外之民,備受歧視。德萊塞的父親是一位虔誠(chéng)、古板、平庸無(wú)能的天主教徒,當(dāng)年為了逃避兵役流亡到美國(guó),婚后生下了十幾個(gè)子女,不幸經(jīng)常失業(yè),而且胸襟狹隘,執(zhí)迷不悟,對(duì)待子女猶如暴君,以致大多數(shù)子女淪入不正經(jīng)的生活,甚至墮落。只有保羅·德萊塞除外,他原先僅僅是個(gè)闖江湖的滑稽藝人,后來(lái)成了流行歌曲作家,紅極一時(shí)。在他弟弟西奧多·德萊塞心目中,不消說(shuō),是成功的榜樣。德萊塞的母親,秉性溫柔,克勤克儉,是來(lái)自賓夕法尼亞州的、具有斯拉夫血統(tǒng)的孟諾派的新教徒。德萊塞8歲時(shí),目不識(shí)丁的母親為生活所迫,帶著他和其他3個(gè)幼小孩子離開(kāi)了家庭,在中西部從一個(gè)市鎮(zhèn)流浪到另一個(gè)市鎮(zhèn)。因此,子女們經(jīng)常被迫輟學(xué)。他們一家人始終過(guò)著極其窘困而又遭人非議的生活。德萊塞的童年,飽嘗貧困無(wú)知之苦。那段辛酸的生涯,后來(lái)他全都寫(xiě)進(jìn)了《美國(guó)悲劇》的開(kāi)頭幾章里去。
1887年,他初次獨(dú)自來(lái)到了芝加哥,先后在餐館和五金公司干粗活,盡管如此,他還是被這個(gè)充滿興奮和刺激的大城市生活所吸引。1889年,他在一位好心的中學(xué)老師慷慨資助下進(jìn)入印第安納大學(xué)念書(shū),無(wú)奈次年即輟學(xué),到芝加哥某地產(chǎn)公司和家具公司當(dāng)收賬員,整日價(jià)挨門(mén)逐戶去收錢(qián),使他接觸到底層社會(huì)各種人物和陰暗面,為日后創(chuàng)作積累了豐富素材,也決定了他的創(chuàng)作中的悲劇意識(shí)和自然主義色彩。正如舍伍德·安德森所指出的:“大概世上自古以來(lái)存在過(guò)的一切抑郁、陰暗和沉重,在他筆下都有所反映。……他神情沮喪,他不知道該如何改變生活,因而他描繪生活一如所見(jiàn)——真實(shí),毫不偽飾。”1892年,德萊塞進(jìn)入了報(bào)界,開(kāi)始記者生涯,先后在芝加哥《環(huán)球報(bào)》、圣路易斯《環(huán)球—民主報(bào)》和《共和報(bào)》任職。那時(shí)節(jié),新聞工作往往成為許多作家練武之地。德萊塞在芝加哥還目睹了一邊是花天酒地,一邊是赤貧如洗的強(qiáng)烈對(duì)比。他親眼看到貧窮如何受人鄙視,偽善如何暢行無(wú)阻。于是,德萊塞執(zhí)意要對(duì)他目睹的現(xiàn)狀進(jìn)行道德評(píng)價(jià),這不僅是十分自然,而且從主觀上來(lái)說(shuō),就是他思想、感情和認(rèn)識(shí)的開(kāi)端,從而引導(dǎo)他去構(gòu)思創(chuàng)作自己的小說(shuō)。1895年,德萊塞寓居紐約,正式從事寫(xiě)作,同時(shí)編輯雜志,經(jīng)常往來(lái)于芝加哥、圣路易斯、托萊多、克利夫蘭、匹茲堡各大城市之間,視野較前更為深廣地接觸到當(dāng)時(shí)現(xiàn)實(shí)生活中各個(gè)不同的層面,親眼目睹了貧民窟、酗酒、色情、兇殺、拐騙、搶劫……使他更進(jìn)一步深刻認(rèn)識(shí)到美國(guó)的現(xiàn)實(shí)是一種“殘酷的、不公道的現(xiàn)實(shí)”,是一個(gè)“毀滅的過(guò)程,而幸福只不過(guò)是幻想而已”。由于這些真相沒(méi)法在報(bào)刊上反映出來(lái),德萊塞就鐵了心,拋棄了新聞?dòng)浾叩墓ぷ鞫_(kāi)始寫(xiě)作,來(lái)揭發(fā)社會(huì)上不公平的事情。
德萊塞全憑個(gè)人天賦與勤奮,自學(xué)成才。說(shuō)實(shí)話,他的審美能力壓根兒沒(méi)有經(jīng)過(guò)系統(tǒng)的培養(yǎng)。從青少年時(shí)代起,他只要有機(jī)會(huì)接觸到書(shū)籍,就會(huì)廢寢忘食,埋頭閱讀。在幾部自傳體的作品中,他情不自禁地追憶往昔讀書(shū)的樂(lè)趣。比如說(shuō),他在奧索小鎮(zhèn)圖書(shū)館里曾經(jīng)讀過(guò)莎士比亞、歐依達(dá)、《湯姆·瓊斯》、勞拉·瓊·利比、華萊士的《本·赫爾》、狄更斯、卡萊爾,還有笛福的《摩爾·弗蘭德斯》,都給年輕的心靈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最有意思的是,人們一直把德萊塞尊稱(chēng)為現(xiàn)實(shí)主義或自然主義的大師,但德萊塞本人卻一概加以否認(rèn),一再聲明年輕時(shí)他“壓根兒沒(méi)讀過(guò)左拉的書(shū)”。事實(shí)上,對(duì)德萊塞的創(chuàng)作具有決定性影響的,卻是巴爾扎克。德萊塞在《自述》中回憶道,讀了法國(guó)偉大的現(xiàn)實(shí)主義作家巴爾扎克的作品,對(duì)他說(shuō)來(lái),不啻是一場(chǎng)“文學(xué)道路上的革命”。他說(shuō),在相當(dāng)長(zhǎng)一段時(shí)間里,“我簡(jiǎn)直跟巴爾扎克以及他筆下的人物一同吃飯、一同睡覺(jué)、一同做夢(mèng)、一同呼吸,腦子里裝的是他的想法,眼里看到的是他描繪的城市。”后來(lái)在匹茲堡卡內(nèi)基圖書(shū)館里,他覺(jué)得巴爾扎克“突然給我打開(kāi)了一道吸引我走向生活的新的大門(mén)”。德萊塞繼續(xù)寫(xiě)道,“這才是個(gè)有眼力、有思想、有感受的作家,通過(guò)他,我看到了如此廣闊的景象,簡(jiǎn)直使我驚訝得目瞪口呆——通過(guò)法國(guó)人的眼睛,我看到了整個(gè)巴黎,整個(gè)法國(guó),整個(gè)生活。”德萊塞認(rèn)為,“巴爾扎克的哲學(xué)推理有點(diǎn)夸張,但卻十分出色;他處理各種重大社會(huì)、政治、歷史以及宗教問(wèn)題都是從容不迫,得心應(yīng)手;他憑借自己的天才,顯示出好像對(duì)各種問(wèn)題都有直接而又無(wú)可辯駁的知識(shí);這一切就像天才和預(yù)言家的真本領(lǐng),深深地吸引著我,使我著了迷。但愿我也能具有這樣一種洞察力!”殊不知就在德萊塞對(duì)巴爾扎克欽佩得五體投地之時(shí),他“卻不知不覺(jué)地對(duì)自己所處的世界獲得了一種新的、形象的認(rèn)識(shí)”,十分驚異地發(fā)現(xiàn),“在這里(美國(guó))竟和那里(法國(guó))一樣,都有可資描寫(xiě)的事物”。換句話說(shuō),年輕的德萊塞早已下了決心,要用巴爾扎克式的方法來(lái)描寫(xiě)美國(guó)生活。以上這些自述,對(duì)我們了解德萊塞從事文學(xué)創(chuàng)作之前的思想基礎(chǔ)是極為重要的。此外,他還如饑似渴地研讀過(guò)史蒂文森、大仲馬、托爾斯泰、愛(ài)倫·坡、司各特、薩克雷、哈代、歐文、霍桑、顯克微支等名家的作品,深深地被這些文學(xué)大師塑造的人物所感動(dòng),從而產(chǎn)生了急欲表現(xiàn)美國(guó)形形色色的社會(huì)生活的創(chuàng)作激情。由此可見(jiàn),盡管有人說(shuō)德萊塞文學(xué)修養(yǎng)欠佳,事實(shí)上,他早已成竹在胸,充分作好了創(chuàng)作準(zhǔn)備。
20世紀(jì)初,德萊塞的頭一部長(zhǎng)篇小說(shuō)《嘉莉妹妹》在美國(guó)文壇上一出現(xiàn),就產(chǎn)生強(qiáng)烈反響。由于作者在小說(shuō)中通過(guò)外來(lái)妹嘉莉的發(fā)跡與高級(jí)經(jīng)理赫斯特伍德的敗落,對(duì)當(dāng)時(shí)流行的社會(huì)道德傳統(tǒng)標(biāo)準(zhǔn)提出了直接挑戰(zhàn),使這位默默無(wú)聞的年輕作家與他筆下的女主人公嘉莉妹妹“全都成了世界文學(xué)中的人物”。正如路易斯贊揚(yáng)《嘉莉妹妹》“像一股強(qiáng)勁的自由的西風(fēng),席卷了株守家園、密不通風(fēng)的美國(guó),自從馬克·吐溫和惠特曼以來(lái),頭一次給我們悶熱的千家萬(wàn)戶吹進(jìn)了新鮮的空氣”,另一方面也使作者多年來(lái)一直受到責(zé)難和攻擊。因?yàn)槟菚r(shí)美國(guó)正經(jīng)歷著一場(chǎng)急劇的社會(huì)變革,從自由資本主義過(guò)渡到壟斷資本主義,同時(shí)也是整個(gè)美國(guó)文學(xué)沉湎于理想主義的時(shí)代,許多作家熱衷于描寫(xiě)人生的樂(lè)觀方面,正如豪威爾斯所說(shuō)的“生活中笑盈盈的一面,那正是美國(guó)的特色”,小說(shuō)被視為消遣品,作品中往往充滿虛無(wú)縹緲的理想或浪漫色彩,而對(duì)生活中的現(xiàn)實(shí),主要是貧富兩極分化,掠奪者與被掠奪者之間的生活懸殊,以及種種丑惡現(xiàn)象,則根本熟視無(wú)睹。德萊塞在《嘉莉妹妹》中卻如實(shí)揭示了美國(guó)社會(huì)生活的陰暗面,結(jié)果作者不斷受迫害,小說(shuō)竟被列為“禁書(shū)”,不準(zhǔn)在美國(guó)出版。盡管如此,德萊塞還是堅(jiān)持認(rèn)為:“生活就是悲劇,……我只想按照生活的本來(lái)面目來(lái)描寫(xiě)生活。”他“寧愿餓著肚子跑到紐約格林威治村來(lái)寫(xiě)幾部反映真實(shí)的小說(shuō)”。他就憑著那股傻勁,鍥而不舍地堅(jiān)持著,“一年接一年,寫(xiě)出了他的生動(dòng)有力的小說(shuō),描寫(xiě)被壓迫的婦女,暴露巧取豪奪的美國(guó)金融家,或是剖析中產(chǎn)階級(jí)下層的各種慘痛的悲劇”。這些小說(shuō)包括德萊塞的其他四部被公認(rèn)的第一流作品,即長(zhǎng)篇小說(shuō)《嘉莉妹妹》(1900年)、《珍妮姑娘》(1911年)、《金融家》(1912年,“欲望”三部曲之一)、《美國(guó)悲劇》(1925年),以及《巨人》(1914年,“欲望”三部曲之二)、《“天才”》(1915年)、《堡壘》(1946年)、《斯多噶》(1947年,“欲望”三部曲之三),總計(jì)長(zhǎng)篇小說(shuō)八部,短篇小說(shuō)集四部,戲劇詩(shī)歌各二部,特寫(xiě)、散論、政論七部,留下了巨大的、珍貴的文學(xué)遺產(chǎn)。
美國(guó)文學(xué)界早先對(duì)德萊塞的文體時(shí)有爭(zhēng)議。誠(chéng)然,他寫(xiě)得不那么文雅精致,有時(shí)行文滯重。但是,正如不少評(píng)論家所指出,他的作品中并不是全然如此。在很多情況下,德萊塞的描寫(xiě)是極其成功的。事實(shí)上,有不少章節(jié)他寫(xiě)得嚴(yán)謹(jǐn)緊湊,文采斐然。就以《美國(guó)悲劇》為例,盡管小說(shuō)容量龐大,頭緒紛繁,但在很多章節(jié)里,作者還是完全能寫(xiě)出簡(jiǎn)潔,乃至于優(yōu)秀的華彩樂(lè)段來(lái)。比如,本書(shū)第三卷第十三章描寫(xiě)克萊德案發(fā)后在伯父家中引起一場(chǎng)激烈的爭(zhēng)論,德萊塞在短短的篇幅之中敘述得清晰、洗練,而又富于層次感,要不是大手筆,是斷斷寫(xiě)不出來(lái)的,本書(shū)第二卷,主要描述克萊德與貧家女、闊小姐之間的三角戀情,不消說(shuō),德萊塞又成了一位能干練達(dá)、循循善誘的新聞?dòng)浾摺5氯R塞在《美國(guó)悲劇》結(jié)尾處幾個(gè)場(chǎng)景的描寫(xiě),更有一種能言善辯的韻味。德萊塞特別擅長(zhǎng)塑造人物,像嘉莉妹妹、珍妮姑娘、克萊德、赫斯特伍德和考珀伍德等都已成為美國(guó)文學(xué)中的典型。特別重要的是,德萊塞善于通過(guò)大量的細(xì)節(jié)來(lái)展現(xiàn)人物的社會(huì)背景,使他的小說(shuō)不僅具有生活真實(shí)感,而且還生動(dòng)地再現(xiàn)了一個(gè)歷史時(shí)代。歷經(jīng)半個(gè)多世紀(jì)的論爭(zhēng)、研究和比較,德萊塞在美國(guó)文學(xué)史上的重要地位,越來(lái)越被評(píng)論家和廣大讀者所確認(rèn)。1990年,美國(guó)評(píng)論家理查德·林杰曼認(rèn)為:“德萊塞是美國(guó)小說(shuō)家中最富有美國(guó)氣魄的……有過(guò)一個(gè)時(shí)期,他就是美國(guó)文學(xué)中惟獨(dú)一位堪與歐洲文學(xué)大師們相提并論的美國(guó)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