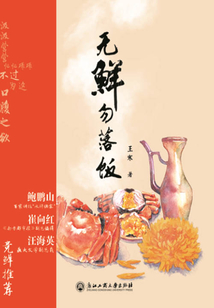最新章節(jié)
書友吧 3評論第1章 靠海吃海
章太炎夫人湯國梨喜歡吃蟹,有“不是陽澄湖蟹好,人生何必住蘇州”的句子,我喜歡吃海鮮,也想鸚鵡學(xué)舌說上一句:“不是此地海鮮好,人生早已住杭州”。
蘇州的朋友出差來看我,我盡地主之誼,請他吃海鮮。在海邊的夜排檔,他喝多了酒,在我面前咿呀咿呀地開唱,“獺狐(太湖)美呀獺狐(太湖)美,美就美在獺狐(太湖)水,水上有白帆哪,啊水下有紅菱哪,啊水邊蘆葦,水底魚蝦肥。”我說你別啊啊的,我順手拿起兩根筷子,敲打著酒杯,念出一首我們當?shù)氐拿裰{《月節(jié)魚名》,“正月雪里梅(梅,指梅童魚),二月桃花鯔,三鯧四鰳,五呼六淡(呼,呼魚,淡,彈涂),八月白蟹板,九月黃魚加篰,十月田蟹呷老酒,十一月湖里鯽,十二月帶魚熬菜頭吃勿息。”——意思再明白不過了,你“獺狐”再美,無非是紅菱呀湖魚湖蝦,咱們這里,有雪里梅,有桃花鯔,還有黃魚花,口福比你們多多了。
江南的江鮮、河鮮、湖鮮和海鮮,都值得一夸。但我以為,最值得夸的是海鮮。
對一個愛好吃的人來說,人生之福,很大程度體現(xiàn)在口福上。所謂口福,就是味蕾上的幸福指數(shù)。
江南人味蕾上的幸福指數(shù),那是相當高。
江南諸城,盛產(chǎn)海鮮的地方不少,像寧波、舟山、溫州、臺州等地,都以產(chǎn)海鮮著稱,海鮮是這些地方的主打美食。當?shù)厝艘话愣寄茼樋谡f上二三十種海鮮的名字,那些大腦內(nèi)存大的吃貨,一開口就能排得出上百種海鮮名。這并不奇怪,浙江有綿延千里的海岸線,魚類和貝殼類水產(chǎn)品有五百多種。說到海鮮,海邊城市的人滋生出洋洋自得的情緒,那也是順理成章的事。
江南海鮮多,吃法也多。有熟食法;有生食法——龍蝦、象鼻蚌、金槍魚就適宜生食;有腌干法,腌制成黃魚鲞、瓜筒、梅子鲓、白大鲓、龍頭鲓、鯊魚鲞、鰻鲞、烏狼鲞、墨魚干、彈涂干、淡菜干、蝦干,各種小雜魚則會被曬干成烤頭(小魚干);有糟醉法,加酒糟做成糟鰳魚、糟帶魚、醉泥螺、醉蟹、魚生、血蚶等——海邊人在四五月常把細帶魚絲加紅糟白曲腌制,封在缸內(nèi)待過三伏天后取食,也有的將脫水的帶魚等糟腌的,稱之為糟帶魚;還有制糊磨醬的,像蝦醬、蟹醬、辣螺醬等。
關(guān)于這些地方的海鮮,天南地北的食客都作過評價,歸納起來就是一句話:形狀見所未見,吃法聞所未聞,口味倒是一致,就是一個“鮮”字!南宋江南浪子戴復(fù)古就在詩中寫道:“每思鄉(xiāng)味必流涎,一物何能到眼前。”想起家鄉(xiāng)的海鮮,這位老兄竟然會口水橫流。
各地方言中,都有一個字叫“鮮”。“鮮”原指食物的新鮮和味道鮮美,但在我們這里,這個“鮮”別有含義,主要表現(xiàn)為得意忘形,不知含蓄,同時還含有一點顯擺、賣弄的意思。它類似于杭州話里的“纖”,北京話里的“燒包”,東北話的“得瑟”,但我覺得無論是“纖”“燒包”,還是“得瑟”,表現(xiàn)力都不如這個“鮮”字強。比如我們的方言里,形容一個人得意揚揚,就用“鮮答答”,讓人想起海鮮剛撈上來時,新鮮透骨,渾身滴著水的樣子。把“鮮”字用在人身上,委實生動形象不過。
海鮮海鮮,就圖個鮮字。但是,以我的眼光來看,光一個鮮字還不夠。我認為,吃海鮮有三重境界:一曰鮮美,二為肥美,三則甜美。我們這里的人對海鮮的最高評價,就是“鮮甜”二字。這種評價,很是讓一些人想不明白,說海鮮“鮮”是可以理解的,怎么會甜呢?我懶得跟他們爭辯,如果他們到沿海城市走上一遭,吃到過剛打撈上來的小黃魚梅童魚等小海鮮,他們一定會對我們以“鮮甜”這個詞形容海鮮心服口服。
我們南方人味蕾敏感而細膩,看餐桌上有無鮮物,不看紅肉,而是一看時令的菜蔬,二看桌上海鮮有多少。因此,海邊人有“無鮮勿落飯”的說法,也是,餐桌上若沒幾樣海鮮,叫人咋吃得下飯呀。
江南的海鮮里,有黃魚、青蟹、對蝦、海參之類“大牌”,這些海鮮太出名了,跟內(nèi)陸地區(qū)的人提這些,顯得我們有些得瑟。江南地雖不大、但海鮮很博,長得稀奇古怪的海鮮很多——什么像鳥一樣長著翅膀的尖嘴“飛魚”,魚假虎威的“巖頭老虎”,跟石頭一般形狀一樣顏色的“石頭魚”,滿身疙瘩像癩蛤蟆的“蛤蟆魚”,細細長長的“釘頭螺”,從巖石表皮揭下來的“佛手”,名字好像是上海灘斧頭幫起的而肉質(zhì)卻極細嫩的“斧頭魚”,名字倒胃口一吃不松口的“瀨尿蝦”,一身硬殼尾巴像把劍、據(jù)說是比恐龍還早的、抱個小孩站上去可以讓它馱著爬的鱟……這些個海鮮,別說外地朋友沒見過,就是本地人未必全叫得出名,就說那個鱟字,就完全可以難倒個文學(xué)博士。嗨,就說到這兒吧,說多了就真的有賣弄之嫌了。有機會,還是請你到海邊的大排檔吃吃我們的海鮮吧。
這些海鮮,別看模樣長得怪,名字起得兇,其實,它們都具備一兩門“獨門絕技”,或擁有致命殺傷性武器,如河豚;要么懂“奇門遁甲”,遇上危險會放煙幕彈,如墨魚;要么有森嚴壁壘的防御體系,如各種海螺。
很多外地人,愛上海邊的這些城市,都始于這些的海鮮。這跟愛上一個人,再愛上一座城,是同樣道理。有位寧波朋友,找了位南京姑娘,兩人為婚后定居哪座城市而犯難,寧波朋友帶南京姑娘吃遍了寧波的海鮮,以美味的海鮮攻下了南京姑娘的心。
作家朋友龔澤華也是被海鮮誘惑,心甘情愿一輩子把家安在了海邊小城。他大學(xué)畢業(yè)后,與班里五六位同學(xué)一起被分配到我們這里,從省城杭州到海邊小城市,心理落差相當大,不過,好吃的龔老師說,“接連幾天用臉盆煮黃魚和螃蟹來吃,就誰也不愿離開這里了。黃魚肉香,是一種過齒難忘的香。那時街上黃魚堆如小山,我們是天天吃,吃不厭,黃魚撈面,黃魚鲞肉……還有螃蟹,活的,那肉白如羊脂,清煮來吃,又鮮又甜,大家覺得日子過得神仙似的,到什么地方也享不到如此口福!”
龔澤華有位生意場上的朋友,是臺灣人,因為鐘情我們這里的海鮮,索性把廠子建在這里,吃遍了當?shù)厣习俜N海鮮,過了一陣子想家了,想回臺灣了。龔澤華跟他說,你嘗夠了鮑魚、海參、魚翅、海卵、石斑、血蛤……可還沒嘗農(nóng)家海鮮呢!這位臺商朋友一聽還有農(nóng)家海鮮,口風馬上變了,說回去不回去還可以再商量。
東北朋友到我們這里來,跟我提起他們那里的小雞燉蘑菇、豬肉燉粉條,說東北的美食如何如何的,我啥也不說,帶他到我們海邊的大排檔,點了一桌菜,全是稀奇古怪的海鮮,什么辣螺、佛手、斧頭魚、棺材蟹、紅綠頭……服務(wù)員每端一道菜,我就大聲地報一道菜名。光聽這菜名,立馬就把他給震住了!
在海邊人的眼里,那些沒海鮮吃,或者吃海鮮過敏的人,都是些“可憐的銀”。某位曾在我們這里當一把手的領(lǐng)導(dǎo),食海鮮過敏。坊間傳聞,說他因為不能吃海鮮,原擬任舟山市長,后改到一個山區(qū)的地級市當市長了。在嗜海鮮的海邊人眼里,若海鮮不能吃,做人的樂趣可是要打些折扣的,說得嚴重點,那是“一眼眼”意思也沒有的。
海鮮對海邊人的貢獻,不僅僅是滿足海邊人的口腹之欲,還給他們帶來一種世俗又市井的快樂,同時,又會讓海邊人滋生出對家鄉(xiāng)的自豪感和對人生的滿足感。而后者,才是最重要的。
我可以負責任地說:寧波、臺州、溫州都曾入選中國最具幸福感城市,如果沒有這些味美的海鮮,市民的幸福感,怕是要打些折扣的。
這話有點上綱上線,不過,不要緊,但凡靠海吃海的江南人,都會理解的。誰讓咱們這兒的海鮮那么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