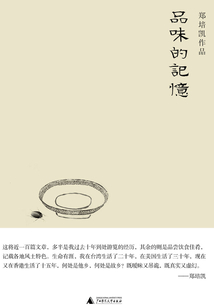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自序:美食與他鄉
北京的一位編輯整理了我昔日的文章,選出飲食與游覽相關的將近一百篇,要輯成一本書,在大陸出版。他建議,書名《何處是他鄉》,能引起讀者的興趣,問我合適不合適。我想,這些文章,多半是我過去十年到處游覽的經歷,其余寫的是品嘗飲食佳肴,記載各地風土特色。的確,寫的都是他鄉引起的感懷,只不過一提起“他鄉”,就想到“故鄉”。這種情感認同的對立概念,既曖昧又吊詭,既真實又虛幻,曾經困擾了我幾十年,經常引發潛伏在心底的錯綜復雜的思緒與聯想。
我出生在青島,正逢國共內戰烽火連天之際,幾個月后隨父母逃離山東,在上海暫住了八個月,才剛滿一歲,就跟著國民政府到了臺灣。我在臺灣生長,從幼稚園、小學、中學,到大學畢業,都生活在臺北南區的新店溪畔,對河堤邊上綠油油的稻田、田里蹦跳的青蛙、環繞著圳渠翩翩飛翔的蜻蜓、溪畔石塊下隱藏的小魚小蝦,都有深切的鄉土之情。然而,父母從來都念叨著故鄉在山東,總是說臺灣沒有可口的水果,雖然出產南國的香蕉與鳳梨,哪比得上煙臺蘋果、肥城桃、萊陽梨?他們懷念山東的山水,時常回憶青島的海灘與棧橋,也回憶我出生的場景,告訴我出生在青島萊蕪路山坡上一棟德國人建造的洋樓里,出生那天積雪盈尺,司機在汽車輪胎上系了鐵鏈,才從山下請了醫生來接生。我家在臺灣的戶口名簿,籍貫寫的是父親的祖籍,山東日照。我離開臺灣之前的身份證,籍貫也是這個與我沒有直接關系的祖籍。父母總是說,將來落葉歸根,還是要回山東的,回青島也好。因此,我這個臺灣外省人的故鄉觀念,一方面是根深蒂固的山東,另一方面卻覺得故鄉有如海市蜃樓,是美好的向往,卻也是永遠無法駐足的他鄉。倒是感到臺北很親切,是我生活了二十年的鄉土,空氣污濁卻很實在,雖然是父母的他鄉,卻是我熟悉的環境。來往的親戚朋友,學校的老師與同學,甚至是巷口的鄰居,光著膀子送煤球(后來送煤氣筒)的老張,都讓我覺得,管他是故鄉還是他鄉,自己在臺灣這片土地已經生了根。
我一九七〇年到美國留學,去到心目中很明確的“他鄉”。當時的想法很單純,只想努力進修,得到博士學位,學業有成,就可以離開他鄉,回到雖然有點曖昧卻讓我感到故鄉親切的臺灣。因緣際會,參加了保衛釣魚臺運動,捍衛國土主權,抗議美國把釣魚臺移交給日本,卻做夢也沒想到,居然被臺灣當局當做不聽話的左派學生,列入黑名單,撤銷了護照,斷了我的回鄉之路。就這么滯留在美國,加入美國大學教授行列,一教二十多年,培植他鄉的桃李。有很長一段時間,我總覺得自己是流落海角天涯的游子,遙望故國山川風起云揚,卻回不去。山東故鄉早已斷了根,臺灣則是有家歸不得。心情郁悶之時,不禁想到《浣紗記》寫伍子胥,害怕政治迫害會連累家族,把兒子托給東齊的鮑牧,硬生生父子離散,有這么一段唱詞:“料團圓今生已稀,要重逢他年怎期?浪打東西,似浮萍無蒂。禁不住數行珠淚,羨雙雙旅雁南歸。”
在美國前前后后加起來,一共生活了三十年,成家立業,也結交了不少好友與同事,到了后來,對他鄉與故鄉的分界,逐漸模糊了。這種心境的改變,與年歲增長有關,有時會拿《金剛經》的話,為自己解說:“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生命有涯,我在臺灣生活了二十年,在美國生活了三十年,現在又在香港生活了十五年,何處是他鄉,何處是故鄉?我思故我在,我在故我思,何處非故鄉,何處非他鄉。
于是,就跟編輯說,“何處是他鄉”意思很好,但是,作為書名,未免太“大路貨”,而且讀者也不容易理解我是如何解脫了“他鄉”的困惑。他鄉、故鄉,對我而言已經沒有什么區別,書中談的多是游歷和美食,索性題為《品味的記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