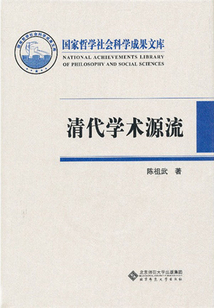
清代學術源流
最新章節
- 第89章 后記 就清代學術史研究答客問(3)
- 第88章 后記 就清代學術史研究答客問(2)
- 第87章 后記 就清代學術史研究答客問(1)
- 第86章 附錄 詮釋學案之嘗試(2)
- 第85章 附錄 詮釋學案之嘗試(1)
- 第84章 《清儒學案》之余波(2)
第1章 前言
承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不棄,2010年初,責任編輯同志致電寒舍,囑祖武選編近若干年所撰學術論文,以《清代學術源流》為題結集,奉請該社出版。謬蒙盛誼,喜愧交并。祖武深知,雖已屆望七之齡,然在學史、治史的道路上,無非起步伊始。所知不過滄海一粟,要認真去學習的功課還太多太多,又遑論東施效顰,忝然出版文集!好在近二三十年間,祖武關于討論清代學術史的習作,皆在不同場合,以不同形式發表,業已接受過方家大雅的指教。因而此番結集,或可作為學史歷程的一個階段性記錄。其間的偶然所得及諸多失誤,對今日及往后的年輕朋友,抑或不無些微助益。秉持此一宗旨,于是便有了奉獻給各位的這一冊不成片段的集子。如果幸能再獲四方高賢撥冗賜教,祖武不勝感激,謹預致深切謝忱。
以上,算是本書的編選緣起。2004年8月,應《人民日報》理論部之約,祖武曾就清代學術史研究寫過一篇短文,題為《清代學術研究的三個問題》。六年過去,重讀篋中舊文,似乎所言尚無大謬,謹冠諸卷首,權充本書前言。
近一二十年間,關注清代學術的學者日益增多,并不斷有研究成果問世,顯示了良好的發展前景。關于清代學術研究,筆者以為,劃分清代學術演進的階段、清理《清史稿·儒林傳》之訛誤和發掘《清儒學案》的文獻價值,是值得關注的三個問題。
劃分清代學術演進的階段
清代學術,以對中國數千年學術的整理、總結為特點,經史子集,包羅宏富。260余年間,既隨社會變遷而顯示其發展的階段性,又因學術演進的內在邏輯而呈現后先相接的一貫性。以時間為順序,大體上可以分為3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為清初學術,上起順治元年(1644年),下迄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順治、康熙兩朝,是奠定國基的關鍵時期。就一代學術的發展而言,清初的80年,是一個承先啟后、開拓路徑的重要階段。其間,才人輩出,著述如林,其氣魄之博大,思想之開闊,影響之久遠,在中國古代學術史上是不多見的。清初學術,既有別于先前的宋明學術,又不同于爾后的乾嘉漢學,它以博大恢弘、經世致用、批判理學、倡導經學為基本特征。正是在以經學濟理學之窮的學術潮流之中,清初學術由經學考辨入手,翻開了對傳統學術進行全面整理和總結的新篇章。
第二個階段為清中葉學術,上起雍正元年(1723年),下迄道光十九年(1839年)。雍正一朝為時不長,實為清初學術向清中葉學術演進的一個過渡時期。清中葉學術以乾嘉學術為主體。王國維先生曾以一個“精”字來概括乾嘉學術:“國初之學大,乾嘉之學精,而道咸以來之學新。”乾嘉學術,由博而精,專家絕學,并時而興。惠棟、戴震、錢大昕主盟學壇,后先輝映,古學復興蔚成風氣。三家之后,最能體現一時學術風貌,且以精湛為學而睥睨一代者,當屬高郵王念孫、王引之父子。至阮元崛起,身為封疆大吏而獎掖學術,以道光初《皇清經解》及與之前后問世的《漢學師承記》、《漢學商兌》為標志,乾嘉學術遂步入其總結時期。
第三個階段為晚清學術,上起道光二十年(1840年),下迄宣統三年(1911年)。嘉慶、道光間,清廷已內外交困。面對漢學頹勢的不可逆轉,方東樹、唐鑒等欲以理學取而代之,試圖營造一個宋學復興的局面。然而時代在前進,不惟漢學日過中天,非變不可,而且宋學一統也早已成為過去,復興藍圖不過一廂情愿而已。晚清學術,既不是漢學的粲然復彰,也不是宋學的振然中興,它帶著鮮明的時代印記,隨著亙古未有的歷史巨變而演進。70年間,先是今文經學復興同經世思潮崛起合流,從而揭開晚清學術之序幕。繼之洋務思潮起,新舊體用之爭,一度成席卷朝野之勢。而與此同時,會通漢宋,假《公羊》以議政之風愈演愈烈,終成戊戌維新之思想狂飆。晚清的最后一二十年間,“以禮代理”之說蔚成風氣。先秦諸子學的復興,更成一時思想解放的關鍵。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學說挺生其間,以之為旗幟,思想解放與武裝抗爭相輔相成,腐朽的清王朝無可挽回地結束了。然而,立足當世,總結既往,會通漢宋以求新的學術潮流,與融域外先進學術為我所有的民族氣魄相匯合,中國學術依然沿著自己獨特的發展道路執著地求索,曲折地前進。
清理《清史稿·儒林傳》之訛誤
《清史稿·儒林傳》凡4卷,前3卷入傳學者共284人,第四卷依《明史》舊規,為襲封衍圣公之孔子后裔11人。前3卷為全傳主體,以學術好尚而區分類聚,大致第一卷為理學,第二、第三卷為經學、小學。入傳學者上起清初孫奇逢、黃宗羲,下迄晚清王先謙、孫詒讓,一代學人,已見大體。各傳行文皆有所依據,或史館舊文,或碑志傳狀,大致可信。因此,數十年來,幾輩學人研究清代學術史,凡論及學者學行,《清史稿·儒林傳》都是重要的參考依據。
然而,由于歷史和認識的局限,加以書成眾手,完稿有期,故而其間的疏失、漏略、訛誤又在所難免,從而嚴重影響了該傳的信史價值。僅舉數例,以見大概。
卷一《陸世儀傳》,稱傳主“少從劉宗周講學”。據考,陸氏雖于所著《論學酬答》中表示,劉宗周為“今海內之可仰以為宗師者”,卻并無追隨其講學的實際經歷。惟其如此,乾隆年間全祖望為陸世儀立傳,說陸氏因未得師從劉氏而“終身以為恨”。又傳末記陸世儀從祀文廟,時間也不準確。傳稱:“同治十一年,從祀文廟。”其實,陸氏從祀,事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四月,五月十六日飭下禮部議復,從祀獲準已是光緒元年(1875年)二月十五日。
又如同卷《顏元傳》,稱“明末,父戍遼東,歿于關外”。“戍”字不實。據考,顏元父至遼東,系明崇禎十一年為入關清軍所挾,非為明廷戍邊。一字之訛,足見撰傳者之立足點所在。
戴震為乾隆間大儒,影響一時學風甚巨。在《清史稿·儒林傳》中,戴氏本傳舉足輕重,不可輕率下筆。然而此傳則疏于考核,于重要學行似是而非。傳稱“年二十八補諸生”,不確。據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洪榜《戴先生行狀》、王昶《戴東原先生墓志銘》,均作乾隆十六年(1751年)補諸生,時年29。此其一。其二,傳稱“與吳縣惠棟、吳江沈彤為忘年友”,亦不確。惠棟、戴震相識于乾隆二十二年,戴少惠27歲,確為忘年之交。而沈彤已于乾隆十七年故世,終身未曾與戴震謀面,“忘年友”云云,無從談起。疑系張冠李戴,將沈大成誤作沈彤。其三,緊接“忘年友”后,傳文云“以避仇入都”。倘依此行文順序,則先有與惠、沈訂交,隨后傳主才避仇北上。其實大謬不然。戴震避仇入都,事在乾隆十九年,三年后南旋,始在揚州結識惠棟、沈大成。于此,戴震事后所撰《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沈學子文集序》,說得非常清楚。
他如對呂留良、譚嗣同、梁啟超、章太炎等人視而不見,拒不入傳,則已非疏失可言,而是腐朽的歷史觀使然。有鑒于此,清理《清史稿·儒林傳》之訛誤,爬梳史料,結撰信史,已是今日學人須認真去做的一樁事情。
發掘《清儒學案》的文獻價值
清代史料,浩若煙海,一代學術文獻足稱汗牛充棟。以文獻長編而述一代學術,前輩學者早已建樹篳路藍縷之功,其間業績最為卓著者,是徐世昌主持纂修的《清儒學案》。
《清儒學案》的纂修,始于1928年,迄于1938年中。這部書雖因系徐世昌主持而以徐氏署名,實是集體協力的成果。全書凡208卷,入案學者計1169人。上起明清之際孫奇逢、顧炎武、黃宗羲,下迄清末民初宋書升、王先謙、柯劭忞,一代學林中人,舉凡經學、理學、史學、諸子百家、天文歷算、文字音韻、方輿地志、詩文金石,學有專主,無不囊括其中。它既是對清代260余年間學術的一個總結,也是對中國古代學案體史籍的一個總結。唯因其卷帙浩繁,通讀非易,所以,除20世紀40年代初容肇祖、錢穆等先生有過評論之外,對其做專題研究者并不多見。
同《清史稿·儒林傳》相比,《清儒學案》的入案學者已成數倍地增加,搜求文獻,排比成編,其用力之艱辛也不是《清史稿》所可比擬的。盡管一如《清史稿》,由于歷史和認識的局限,《清儒學案》的歷史觀已經遠遠落伍于時代,疏失、錯訛亦所在多有。然而其文獻價值則無可取代,應予以充分肯定。今日學人研究清代學術史,《清儒學案》實為不可忽視的重要參考著述。
《清儒學案》承黃宗羲、全祖望二家開啟的路徑,采用學者傳記和學術資料匯編的形式,述一代學術盛衰。這樣一種編纂體裁,或人自為案,或諸家共編,某一學者或學術流派自身的傳承,抑或可以大致反映。然而,對于諸如此一學者或流派出現的背景,其學說的歷史地位,不同時期學術發展的基本特征及趨勢,眾多學術門類的消長及交互影響,一代學術的橫向、縱向聯系,尤其是蘊涵于其間的規律應當如何把握等等,所有這些問題又都是《清儒學案》一類學案體史籍所難以解答的。一方面是學案體史籍在編纂體例上的極度成熟,另一方面卻又是這一編纂體裁的局限,使之不能全面反映學術發展的真實面貌。這種矛盾狀況,足以說明學案體史籍已經走到了盡頭。
進入20世紀以后,隨著西方史學方法論的傳入,融會中西而有章節體學術史問世。梁啟超先生挺然而起,倡導“史界革命”,完成《清代學術概論》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結撰。以之為標志,學術史編纂翻過學案體史籍的一頁,邁入現代史學的門檻。
祖武治清代學術史30余年,以讀清儒著述為每日功課。不間寒暑,朝夕以之,幸有所得則為文敬請四方同好指教。多歷年所,成篇居然數以十計。此番應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之約,從中遴選20余篇結集,旨在據以窺知有清一代學術之演進歷程。承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組織專家評審,將此一不成片段的集子納入成果文庫。鞭策鼓勵,感激至深,謹向規劃辦公室并各位評審專家致以崇高敬意和由衷感謝。
承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盛誼,尤其是責任編輯劉東明同志受累,精心編輯,精心校對,精心出版,本書方能有今日之面貌,謹致深切謝忱。
陳祖武 謹識
2010年12月8日初稿
2011年11月20日改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