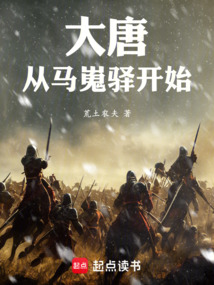最新章節
- 第38章 李隆基:真假秦王,一鑒便知
- 第37章 潼關潰兵!敵軍前鋒將至!
- 第36章 李倓:陛下,小心父老遮留
- 第35章 麒麟兒,汝當勉勵之
- 第34章 秦王冊立,鹿死誰手?
- 第33章 封爵秦王,開府儀同三司!
第1章 建寧王,李倓(求收藏,求追讀)
天寶十五載,六月十三。
月光如華,清冷冷照著黑燈瞎火的金城驛站。
驛站內,又餓又累的李唐皇室成員,再也顧不上什么尊嚴和體面,一個個橫七豎八地躺在破草席上,鼾聲如雷。
所有人都睡著了。
唯獨皇孫李倓拄刀隱在黑暗中,望著掛在柳梢上的銀月,一口口用力咀嚼著胡麻餅,像在咀嚼骨頭。
這胡麻餅是他拿著刀從楊貴妃的外甥手里搶來的。
陡然穿越大唐,一路追隨皇帝倉皇奔逃,腹中空空如也,忍饑挨餓的困頓早已讓胸中郁結的怒火瀕臨爆發。
偏在此時,楊貴妃的外甥竟仗著外戚權勢,要強奪他手頭僅有的一點吃食。
若換作原主,怕是早已懾于楊家那滔天權勢,只能把這口惡氣硬生生咽進肚子里。
旁人也都篤定他會如此,畢竟圣人對楊家的寵幸更甚于東宮,太子對楊國忠的忌憚不亞于李林甫。
太子已是如此,更遑論只是根本不受皇帝待見的建寧郡王李倓呢。
只是任誰也未曾料到,此刻的李倓,內里早已換了乾坤。
當他怒目圓睜,猛地抽刀架在對方脖頸上時,周遭目睹這一幕的人無不駭然失色,大氣都不敢出。
胡麻餅保住了,但雙方就此結下了生死之仇。
那一刻,幾乎所有人都在為他默哀,唯獨李倓自己心中哂笑——
想他死?
不可能的,明天就是六月十四,歷史上著名的馬嵬驛兵變便是發生于這一天。
屆時,莫說楊貴妃這個外甥,便是集萬千寵愛于一身的楊貴妃本人,最終也不過落得個三尺白綾縊死馬嵬坡的結局。
至于其余楊氏外戚,同樣無法幸免,無論男女老少,盡皆被屠滅。
按李倓原本的盤算,原是打算靜候馬嵬驛兵變的到來。
屆時無需他多費手腳,自能坐收漁翁之利。
若實在按捺不住此刻的怒氣,等事到臨頭時,揮刀劈砍幾下泄泄憤,也并非不可。
可計劃終究趕不上變化。
眼看夜色漸濃,李隆基卻突然傳下口諭,竟命李倓今夜值守宿衛,還特意強調“若有貽誤,軍法處置”。
這道突如其來的命令,像一塊巨石砸進平靜的湖面,瞬間打亂了李倓所有的盤算。
原本只需蟄伏等待的他,猝然被推到了風口浪尖。
宿衛之責,看似是皇命所托的體面差事,可在這人心惶惶的逃亡路上,前路未卜,禁軍情緒浮動,稍有差池便是掉腦袋的罪過。
更何況,這道旨意來得蹊蹺,若是其中沒有楊貴妃的影響,打死李倓都不信。
李倓越想越震恐。
在這個皇權至上的年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絕不是空泛的口號,而是刻在律法骨血里的鐵則。
更別說,李隆基本就有過一日連殺三子的無情。
皇子尚且如此,他一個不受寵的皇孫,又算得了什么?那句“軍法處置”,字字帶著著殺機。
李倓覺得若不早做準備,或許根本等不到馬嵬驛之變,他就會被李隆基一杯鴆酒賜死。
李倓囫圇吞咽著胡麻餅,不一會,一張餅便入了肚。
吃了個半飽,正欲接著吃第二張餅的時候,停住了,怔怔盯著手中餅,他突然想起,自己父親、當朝太子好像也餓著肚子,要不要給他留著?
當然,這不是他孝心發現,而是值此危難之際,有能力救他一命的只剩下了東宮太子。
若太子拼死硬保,李隆基也得考慮一下影響。
只是太子會保他嗎?
很難說。
畢竟歷史上的建寧王李倓,本就死在肅宗的鴆酒之下,只比楊貴妃等人多活了一年而已。
李倓并沒有思考太長時間,不管日后如何,當下的難關才是最致命的、最緊要的,他必須在太子面前刷一波孝心。
即便眼下用不著,日后他聽信讒言想鴆殺自己,回想當今,也得考慮一下會不會人心向背。
收起僅剩的胡麻餅,李倓目光四下梭巡。
雞蛋不能放在同一個籃子里,這是自古不變的真理。
李倓自然也懂得這個道理。
他盛放雞蛋的另一個籃子,便是爆發于明日的馬嵬驛兵變。
歷史上的馬嵬之變,并非什么驚天動地的政變,甚至可以說,它不過是禁衛六軍宣泄心中不滿的一場嘩變。
它沒有波詭云譎的權謀爭斗,也沒有勢均力敵的血腥拼殺。
有的只是“看你不爽很久了,今日不除掉你,實在難平心頭之氣”的憤懣與憎恨。
不過,歷史就是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具體如何還得實事求是。只有深入了解禁軍情況,才能更好、更容易達到目的。
正想著,一個人影披星戴月急匆匆趕來。
“殿下。”
來人身材健壯,虬結的肌肉好似磐石,額頭微凸,下有兩條臥蠶濃眉。
“敬軒,你來的正好,來,”李倓將其引至僻靜處,望了眼陷入黑暗的驛站,斟酌問道:“今日我拜托你的事可有眉目?”
此人名為張敬軒,乃左龍武衛一個旅帥。
旅帥乃禁軍中層將領,隸屬校尉,下轄二十隊正,每隊領兵五十。
只是龍武軍建制不全,至今未能補齊,每旅下轄最多也就兩三個隊,遠不如其他禁軍。
張敬軒出逃時負責馬匹調度,因此得罪楊氏,被李倓救下后,調到了后衛軍。
聽李倓問話,張敬軒欲言又止。
李倓眉頭微蹙,探詢道:“有阻礙?”
與貴妃外甥發生沖突后,他便委托張敬軒暗中觀察禁軍情緒,此刻見其一副驚愕態度,心道可別出了什么幺蛾子。
“殿下……”
“說了多少次,私底下稱我‘三郎’便好。你我之間,不拘小禮。”事關重大,李倓希望兩人關系越親近越好。
張敬軒撓了撓后腦勺,做了好幾番心理建設,臨到嘴邊最后還是沒能喊出“三郎”。
“罷了,不強求你了。”李倓笑了,“只是,你要在心里記住,你我之間乃兄弟情義,而非臣屬。”
“誒,殿下恩情,臣沒齒難忘。”張敬軒咧嘴一笑,“殿下”二字喊的誠懇意切。
“說吧,可有眉目?”李倓摩挲著刀柄,沉聲問道。
提到“禁軍情緒”張敬軒臉色微變,急切道:“殿下,當早日離開此地!”
李倓眼前一亮,暗道有戲,隨即追問:“禁軍果真情緒浮躁?”
“何止情緒浮躁!”張敬軒壓低聲音:“若非殿下提醒,臣至今不敢相信這是禁軍將士。”
“臣發現,將士們脾氣越發暴戾乖張,粗言穢語常掛嘴邊,這也就罷了。其中更有甚者,常因為一點小事而刀兵相向。”
“就在方才,臣部屬就有兩人因為半塊燒餅而刀刃向己,若非臣阻擋及時,必有一人倒于血泊。”
“殿下,臣曾經戍過邊,見識士卒嘩變。每當嘩變前夕,士卒們就如當下的禁軍,情緒會變得異常狂躁,直到某一刻徹底爆發。”
李倓這才發現張敬軒胳膊上裹著一條紗帶,鮮血染出一片猩紅。
他沉默片刻,問道:“依你之見,禁軍估摸什么時候徹底會嘩變?”這才是李倓所在意的事。
張敬軒思忖了片刻,搖搖頭,“事關重大,臣不敢妄下判斷。”
旋即,他又誠懇勸說:“殿下,嘩變的士卒就是失去控制的瘋牛群,為了發泄心中的憤怒會不顧一切殺死他們所認為該死的人。”
“您當早做準備啊!”
李倓陷入了沉思,他不擔心自己會成為禁軍發泄憤怒的目標,而是思忖怎么利用好這股情緒,為自己攫取更多的利益。
到了這個份上,他若任機遇白白流走,恐遭天譴!
“啊——”
院墻外,突然傳來一聲凄厲的嚎叫,而后又響起鞭撻聲與喝罵聲。
“你這個該死的賤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