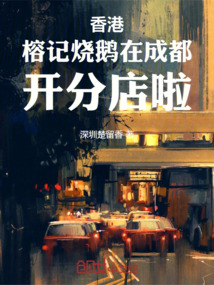最新章節(jié)
書友吧第1章 金子包著的炭火
維多利亞港的夜晚,像布滿繁星的銀河系。
成都的黃昏,像塊用舊的抹布,黏糊糊甩在太古里的玻璃幕墻上。
呂梁偉剪彩的金剪刀還在電視里閃光,李老饕的筷子已戳破盛大的泡沫。
當(dāng)荔枝木的煙熏味撞上錦江的水汽,周先行才發(fā)現(xiàn)——
香港百年老店的招牌,在麻辣味的成都夜里濺不起半點(diǎn)油星。
暮色沉進(jìn)錦江時(shí),周先行正站在“榕記”新店三樓臨街的休息室里。透過冰冷的落地玻璃望下去,太古里精巧的仿古建筑群亮起一片片浮華的金光,像從香港太平山頂俯瞰維多利亞港的星光。只是這里沒有咸腥的海風(fēng),空氣里飄浮著一種復(fù)雜的氣味,花椒、牛油、辣椒面被午后的暑氣蒸騰起來,鉆進(jìn)他挺括的亞麻襯衫領(lǐng)口。
他身后墻上的電視,本地財(cái)經(jīng)頻道還在循環(huán)播放兩天前開業(yè)典禮的高光片段。屏幕里,呂梁偉那張被歲月格外優(yōu)待的臉笑得意氣風(fēng)發(fā),手腕輕揚(yáng),特制的金色剪刀優(yōu)雅剪斷猩紅綢帶。綢帶墜地的瞬間,精心安排的干冰煙霧“嗤”地涌出,鎂光燈追逐著在場(chǎng)捧場(chǎng)的幾張重量級(jí)熟面孔——商會(huì)的孫會(huì)長(zhǎng),分管文旅的秦主任,還有專程飛來的香港商會(huì)副會(huì)長(zhǎng)。煙霧繚繞中,曹百里一身靛藍(lán)色定做西裝,油頭梳得一絲不茍,對(duì)著鏡頭侃侃而談榕記的歷史與新篇。他身側(cè),許艾洲安靜地站著,表情是精心計(jì)算過的低調(diào)謙和,只有偶爾劃過鏡片的閃光,顯出那點(diǎn)掩不住的精明。畫面切給VCR,李嘉欣溫婉的臉出現(xiàn)在巨大屏幕上:“預(yù)祝阿Joe(周先行英文名)新店生意興隆,我盡快去成都品嘗呀!”她的聲音透過高級(jí)音響流淌出來,甜美得有些不真實(shí)。
盛大的喧囂被厚玻璃阻隔在外。這間小小的休息室,是周先行為自己留的喘息之地,港島店鋪里那間窄小的、滿是油煙氣的老閣樓的幻影,在這里被無限放大,包裹著昂貴木料和真皮沙發(fā)散發(fā)出的嶄新氣味。
他閉上眼,想再嗅一嗅記憶深處的味道。海貨市場(chǎng)的咸腥,銅鑼灣密集人流蒸騰出的汗味,老榕樹下牛雜的霸道濃香。是父親站在掛爐前沉默又堅(jiān)定的汗?jié)癖秤啊?杀乔焕镱B固地盤踞著那股味道——復(fù)雜、強(qiáng)悍,帶著植物辛香和動(dòng)物油脂在高溫下融合后特有的攻擊性。成都的味道。
門被象征性地輕敲兩下,曹百里不等人應(yīng)就擰開了門鎖,閃身進(jìn)來。他臉上的招牌笑容像是焊上去的,手里拿著一臺(tái)平板,屏幕上密密麻麻的柱狀圖顏色刺目。
“Joe,爆了!真·爆·炸!”他聲音里的興奮像帶著火花,幾步跨到窗邊,指尖在屏幕上飛快滑動(dòng),“開檔到現(xiàn)下,堂食等位超過120號(hào)!外賣訂單接到系統(tǒng)快宕機(jī)!呂哥的號(hào)召力,李小姐的影響力,你看看這流量!錢!”他指了指最新一條攀升的曲線,“剛沖上點(diǎn)評(píng)網(wǎng)成都區(qū)域熱度第一!甩開第二名幾條街!”
他頓了頓,深吸一口氣,笑容里摻進(jìn)一絲不容置疑的決斷:“但這熱度,來得快,涼得也快!我們要趁熱打鐵再燒一把!蔡瀾先生那邊,我托了七拐八彎的關(guān)系,終于搭上了他的助理。人家口風(fēng)很緊,只說蔡生近期沒空檔。我下午送了兩只剛出爐、皮最靚的燒鵝過去,蔡生他老人家就好這口地道老味,吃了自然曉得我們幾斤幾兩!只要他肯動(dòng)動(dòng)金口……”曹百里做了個(gè)敲擊鍵盤的手勢(shì),眼神銳利,“點(diǎn)評(píng)網(wǎng)的熱度第一算什么?我們要的是文化金身!百年老店的金字招牌,加上蔡生的‘懂食’認(rèn)證,這才叫通殺!”
周先行轉(zhuǎn)過身。窗外太古里巨大的LV燈箱廣告恰好亮起,白花花的光芒瞬間填滿房間,將他身上那件素色亞麻襯衫照得雪亮,卻也在他眼底投下更深的疲憊的陰影。“曹生,”他的聲音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嘶啞,像被成都這初秋不該有的干燥抽走了水分,“根基是什么?根基是爐里的火候,是那一刀下去皮肉酥脆分離的聲音。外頭那些人,”他眼神朝樓下喧囂的人潮示意,“沖著誰的鏡頭來的?”
曹百里臉上的笑容只僵了一瞬,立刻更加燦爛。“當(dāng)然沖著呂哥靚仔,沖著李小姐的臉蛋!但這有什么問題?我們賣的是燒鵝,只要鵝入了他們口,舌頭和胃不會(huì)騙人!蔡瀾的金口玉言,就是給他們的舌頭加的保險(xiǎn)!”他指尖重重戳著屏幕上代表“流量來源-明星效應(yīng)”的高聳紫色柱狀圖,“你看這高度!沒這個(gè)引子,酒再香也飄不出這條巷子!”
“飄進(jìn)誰的巷子?”周先行的目光落在遠(yuǎn)處高樓縫隙間露出的、被霓虹映得發(fā)紫的一小截渾濁天空,“又為了留住誰?”
門再次被推開,這次顯得倉促許多。許艾洲站在門口,一絲不茍的襯衫上沾了點(diǎn)濺上的油漬,他眉頭緊鎖,目光快速掃過周先行和曹百里:“周總,曹總。下面出了點(diǎn)小狀況。”他沒有廢話,聲線在強(qiáng)裝鎮(zhèn)定下壓著一絲緊繃,“李老師來了。沒預(yù)約,就坐在正對(duì)出菜口那張方臺(tái)。一只整鵝剛端上去。”
許艾洲口中的“李老師”,曹百里反應(yīng)慢了一拍,周先行的心卻猛地往下一沉。在成都本地,能讓許艾洲稱呼為“李老師”的人,只有一個(gè)——李老饕。美食圈里一條低調(diào)而劇毒的舌,舌下壓著一支筆。
休息室里的暖意瞬間抽干。周先行甚至來不及交代一句,推開曹百里,大步流星沖出房間。樓梯窄而陡,他只三兩步就旋了下去,心跳在耳邊鼓噪。通往大堂的門簾猛地掀開,一股更洶涌、更喧囂、更濃郁的氣浪撲面而來,辛辣的香料味、蒸騰的肉脂香氣、數(shù)百人同時(shí)用餐的低語嗡鳴和杯盤碰撞聲,混雜著冷氣的機(jī)械低吟。這氣味和聲浪織成一張無形而堅(jiān)韌的網(wǎng),兜頭罩下,讓他呼吸驟緊。
他一眼就看到了靠里面那張方桌旁的身影。只一個(gè)人,瘦長(zhǎng),微微佝僂,穿著件洗得極干凈卻半舊的藏藍(lán)色滌卡上衣。面前一只淺口大圓盤里,盛著一只烤制完美、呈誘人琥珀蜜色的燒鵝,腹部被剖開,鵝腹內(nèi)的釀料閃著油光。這人就是李老饕。他低著頭,正用一根銀亮細(xì)長(zhǎng)的探針,小心地刺探著鵝胸最肥厚那塊皮下的肉質(zhì)。動(dòng)作帶著一種近乎宗教般的專注和審視。
周先行的腳步在距離桌邊兩步處停住。他身后,曹百里和許艾洲也跟了上來,三人像一排沉默的礁石,硬生生截?cái)嗔耸晨屯鶃淼某彼7讲胚€在附近推杯換盞、歡聲笑語的一桌年輕人,像是被無形的手掐住了脖子,嬉笑聲戛然而止。整個(gè)大堂似乎在這一剎按下了消音鍵,無數(shù)或好奇、或茫然、或帶著興奮窺探的目光,蛛網(wǎng)般悄無聲息地纏繞過來。
桌上那只金黃流油的燒鵝,在明亮的射燈下仿佛一件藝術(shù)品。李老饕緩緩收回探針,對(duì)著燈光仔細(xì)看了看針尖,微不可察地?fù)u了搖頭。他的目光終于抬起,越過焦糖色的鵝身,落在周先行臉上。那雙眼睛藏在深度老花鏡片后面,顯得渾濁,卻又銳利得像兩把小錐子。
李老饕沒說話,只是慢慢伸出筷子。那是雙看起來極為普通的竹筷,被他蒼老的手握著,卻有種千鈞重的分量。筷子尖夾住了一塊鵝腿肉——那是鵝身上肉質(zhì)最細(xì)嫩、皮最厚實(shí)的精華部分。
時(shí)間仿佛被粘稠的油脂浸透了,拖曳得緩慢而凝重。筷子夾著那塊金黃的肉,穩(wěn)穩(wěn)地送到他嘴邊。周先行全身的神經(jīng)都繃到了極致,似乎連空氣的震動(dòng)都能清晰捕捉。他盯著那塊肉,看著李老饕嘴唇微啟,咬住。
牙齒與酥皮接觸。
“咔……”
那一聲微乎其微的碎裂聲,如同最高審判官落下的驚堂木,在驟然凝滯的空氣里敲出一片令人窒息的漣漪。
李老饕閉上了眼睛,下頜輕輕蠕動(dòng)了一下。一秒,兩秒……整個(gè)喧囂的大堂死寂一片,只有不知哪個(gè)角落空調(diào)風(fēng)口吹出的細(xì)微風(fēng)聲,舔舐著人們的耳膜。終于,他極其緩慢地睜開眼,渾濁的鏡片后,眼神里沒有任何失望或憤怒的火光,只有一片深不見底的、冷冰冰的平靜。那平靜比最爆裂的怒容更讓人心悸。
他放下了筷子。
動(dòng)作很輕,在鋪著白色餐布的桌面上幾乎沒有聲響。但這一放,卻仿佛在每個(gè)人的心上投下了一塊巨石。曹百里臉上的血色瞬間褪得一干二凈,方才的興奮潮水般退去,只剩下慘白。許艾洲鏡片后的眼睛驟然縮緊,嘴唇抿成一道冷酷的直線。
“周老板,”李老饕終于開口,蒼老的聲音不高,但每個(gè)字都帶著一種磨礪過的金石質(zhì)感,奇異地壓過了大堂所有的殘留噪音,清晰無比地灌入每個(gè)人耳中,“你這燒鵝……”他頓了頓,手指指向那盤只被動(dòng)了一小部分的鵝肉,“炭火氣太重了。”
他聲音平淡得毫無起伏,像是在陳述一個(gè)毋庸置疑的事實(shí):“去年臘月在港島軒尼詩道,老榕樹下,嘗過尊父的手藝。那鵝味,是清潤(rùn)鮮甜。皮是脆,酥,咬下去一口油香,但不膩口。肉呢?嫩滑得,在舌尖一轉(zhuǎn)就化開。”
他抬起眼皮,鏡片后的目光如淬了冰的針,扎在周先行臉上,手指毫不客氣地戳向盤中那只無辜的鵝:
“這一只?炭煙味沖鼻!把鵝肉本身的鮮甜都蓋沒了,只落下一個(gè)‘猛’字!是燒給趕路的苦力吃的么?”他拿起桌上的濕毛巾,慢條斯理地擦了擦嘴角,仿佛要擦掉某種不堪的氣息。
“周生,”他對(duì)上周先行瞬間繃緊的嘴角,話語一字一頓,“榕記的金字招牌,貴在‘本真’二字。你帶了秘方帶了師傅,可帶得動(dòng)這成都的風(fēng)物水土嗎?”他渾濁的眼神掠過窗外濃得化不開的夜色,“在港島老榕樹下,你賣的是‘真’。在這里,你賣的是呂梁偉的臉面?還是李嘉欣的招牌?”
幾句話落音,整個(gè)大堂落針可聞。無數(shù)道目光灼灼地聚焦在周先行身上,帶著探詢、好奇和一絲絲獵取新聞般的興奮。隔壁桌一個(gè)打扮時(shí)髦的年輕女子甚至偷偷舉起了手機(jī)。
周先行覺得自己全身的血液都在沖撞著太陽穴。李老饕的話語像重錘,一下一下砸在他苦心經(jīng)營(yíng)的堡壘上。他深吸一口氣,胸中的翻騰幾乎沖垮他的理智。然而,十?dāng)?shù)年浸在廚房油煙氣里的定力在最后一刻死死拽住了他。他臉上肌肉抽動(dòng)了一下,硬生生將那股幾乎焚毀一切的怒氣壓成喉嚨深處一塊滾燙的烙鐵。
“李老師……”他開口,試圖微笑,嘴角扯動(dòng)得卻異常僵硬,“真·火眼金睛。成都天候不同,這荔枝木的火氣也比港島那批要猛三分。排氣上,還在一點(diǎn)點(diǎn)調(diào)試。”他努力讓每一個(gè)字清晰平穩(wěn),“多謝指點(diǎn)!我立即叫廚房再烤一只最靚的鵝腿,您再試過?”
“試?”李老饕輕輕笑了一下,搖搖頭,動(dòng)作帶著一種看透世事的疲憊。他拿起旁邊自己的磨禿邊緣的大麥茶水杯,呷了一口。“不是一只燒鵝的事。”他放下茶杯,杯底在桌子上輕輕一頓,發(fā)出清晰的聲響,“周老板,你要搞清楚,你賣的到底是百年老店的招牌味道,”他蒼老的手指抬起,指了指頭頂天花板——仿佛虛空中懸掛著呂梁偉、李嘉欣乃至曹百里眼中那虛幻的光環(huán),“還是那些明星帶來的浮光掠影?”他渾濁的眼睛透過鏡片,緊緊鎖住周先行,“味道不正,再多的浮光掠影……也不過是紙包著一點(diǎn)點(diǎn)可憐火星。終究是要熄滅的。”
“嗡……”
話音剛落,大堂里那持續(xù)不斷地、為這場(chǎng)盛大開業(yè)增添逼格的輕音樂,毫無預(yù)兆地停頓了一秒。然后重新響起時(shí),換成了另一首更加輕柔舒緩的鋼琴曲。這突兀的切換聲,在死寂的空氣中如同一聲震耳欲聾的嘲笑。
后廚窄小的辦公室,空氣幾乎凝成了實(shí)體。白熾燈管發(fā)出嗡嗡的電流聲,明晃晃地照亮每一寸空間,也照得角落里那只剛被周先行扔下的半只燒鵝格外刺眼。燒鵝的皮依舊金黃,可惜腹部被剖開后露出的肉塊泛著灰白,像是某種不祥的征兆。
“一個(gè)老不死的舌頭,就讓你們驚成這樣?!”曹百里的聲音拔得極高,帶著一種壓抑不住的尖利和破音。他煩躁地在原地打轉(zhuǎn),昂貴的皮鞋踩在冰冷油膩的地磚上發(fā)出吱嘎聲響,仿佛被困住的猛獸。“滿堂賓客,媒體鏡頭多少?偏他要在今日,要在那個(gè)位置!”
他猛地停住,直勾勾地瞪著許艾洲:“你請(qǐng)他來,就是專程砸場(chǎng)的?”
“我請(qǐng)?”許艾洲的聲音終于繃不住了,冰冷的鎮(zhèn)靜裂開一道銳利的口子,“他李老饕想坐哪,輪得到我安排?那張臺(tái)緊鄰出菜口,動(dòng)靜看得一清二楚!根本就是聞著味踩著我們痛點(diǎn)來的!”他鏡片后的目光鋒利地轉(zhuǎn)向一直沉默得像塊石頭杵在門邊的周先行,“周生!人家明話說了!問題不在鵝,在煙!”他伸手指著窗外,“這城市上頭的空氣,和我們老榕樹下的,是兩種天地!這木頭,這爐膛里的火氣,沒人比你更清楚!”
許艾洲頓了頓,喉結(jié)艱難地滾動(dòng)了一下,放低了聲音,卻字字砸在實(shí)處:“風(fēng)口浪尖上了!蔡瀾的鵝送過去人家收不收都兩說!本地平臺(tái)呢?我剛才進(jìn)來前掃了一眼,已經(jīng)有兩篇‘點(diǎn)評(píng)’冒出來了!標(biāo)題我都不敢念給你聽!現(xiàn)在,立刻,馬上!我們必須要讓李老饕改口!必須讓他發(fā)文澄清!或者——”他語氣陡然一轉(zhuǎn),帶上了一種近乎殘酷的冷靜,“把他那張老臉,釘死在‘不懂裝懂、蹭熱度’的恥辱柱上!拿他‘不懂新派融合’做文章!”
煙灰缸被一股蠻力掃落到水泥地上,“哐當(dāng)”一聲巨響!殘留的灰燼和煙頭砸開了冰冷的灰色地獄。
周先行抬起頭。燈光慘白,將他臉上的陰影雕刻得異常深刻,只有眼底深處一點(diǎn)掙扎的光焰,如同風(fēng)中殘燭般跳躍不滅。“炭火氣?”他反問,聲音沙啞得如同被粗砂紙打磨過,“那是……是焦土味!是我周家?guī)状跓熁鹄锇境鰜淼幕昶牵 彼偷刂赶虼巴鉂獾没婚_的漆黑深夜,像是要指向某個(gè)不存在的遙遠(yuǎn)所在——“那邊,老榕記的掛爐里燒的荔枝木,是浸了咸海風(fēng)的!從樹根芯到木紋理,都被那股子海鹽氣腌透了!那煙火燎出來,是……是清冽的!像初春早上的露珠滲入心脈!”
他猛地一拍辦公桌,那半只無辜的燒鵝被震得跳了一下。“這里呢?燒的是川西壩子雨澆不透的硬木!火性就是這壩子夏天的日頭!猛!烈!壓得住!這煙火味……它就該更粗、更重!”汗水順著周先行的鬢角往下滑,“我開大排氣,就是想留住鵝肉那點(diǎn)清甜的底子!想讓它不辜負(fù)這片天地的硬氣!李老饕懂個(gè)屁!他只知道港島風(fēng)輕云淡!”他聲音里的怨毒幾乎化為實(shí)體,“那些明星……那些流量……他們是錦緞!是包裝那老榕樹根底下沉淀下來的本味!你告訴我,炭火氣蓋過鵝肉香?是木頭變了嗎?是這個(gè)城市根本容不下一點(diǎn)點(diǎn)從海那邊漂過來的舊魂?”
他一步踏到窗邊,動(dòng)作大得帶倒了桌上一只馬克杯,殘存的冰涼茶水潑了他一手也渾然不覺。他猛地推開那扇布滿油膩指紋的舊鋼窗。剎那,洶涌的夜風(fēng)猛地灌入,裹挾著這個(gè)龐大都市午夜后獨(dú)有的復(fù)雜濃烈氣味——?jiǎng)偸帐谢疱伒陜A倒的油膩鍋底殘?jiān)⑸钜谷栽谶\(yùn)作的垃圾清運(yùn)車的腥氣、街邊燒烤攤孜然辣椒面燎過后的煙火余韻、濃烈得化不開的晚香玉氣息、混雜著遠(yuǎn)處建筑工地深夜仍不肯停歇的金屬敲擊沉悶回響,所有氣味聲響糾纏翻滾,野蠻地沖撞著室內(nèi)凝固空氣里那一點(diǎn)渺茫的荔枝木余煙。
周先行深深吸了一口這濃烈得令人窒息的空氣,冰冷的茶水滴在他袖口上,暈開一小片深色。
“這成都的夜氣……”他望著這片被無數(shù)霓虹切割拼貼的龐大夜色,每一個(gè)字都像被夜風(fēng)吹得搖搖欲墜,“容得下萬國宴席,容得下百味橫流……”他的聲音沉下去,化作風(fēng)中幾不可聞的嘆息,“就真的……容不下一只老榕樹味道的燒鵝么?”
曹百里盯著桌上那半只冷卻變硬的燒鵝,看著它在慘白燈光下透出死尸般的灰敗光澤。許艾洲的目光則落在周先行那只被茶水打濕、袖口微微發(fā)皺、此刻緊緊抓住窗框的右手上,指節(jié)因?yàn)檫^度用力而泛出絕望的蒼白。
窗外的夜風(fēng)攪動(dòng)著濃得化不開的渾濁空氣,隱隱傳來深夜貨柜車呼嘯碾過路面的沉重嗚咽,一聲、又一聲,如同這座城市的沉悶心跳,無情地碾壓著他們那點(diǎn)微弱的火光。那風(fēng)中糾纏不休的辛辣余味,霸道地浸染著每一個(gè)角落。
榕記百年招牌里沉淀的老魂,終究撞上了這麻辣洶涌的錦江大水。
第一朵潑在金色招牌上的冷水,終于落了下來,燙得人皮開肉綻,寒氣徹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