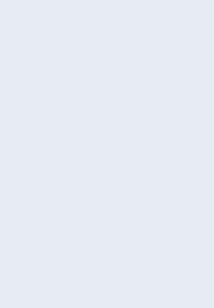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 4評論第1章 趕集(1)
【序】
這里的“趕集”不是逢一四七或二五八到集上去賣兩只雞或買二斗米的意思,不是;這是說這本集子里的十幾篇東西都是趕出來的。幾句話就足以說明這個:我本來不大寫短篇小說,因為不會。可是自從滬戰后,刊物增多,各處找我寫文章;既蒙賞臉,怎好不捧場?同時寫幾個長篇,自然是做不到的,于是由靠背戲改唱短打。這么一來,快信便接得更多:“既肯寫短篇了,還有什么說的?寫吧,伙計!三天的工夫還趕不出五千字來?少點也行啊!無論怎著吧,趕一篇,要快!”話說得很“自己”,我也就不好意思,于是天昏地暗,胡扯一番;明知寫得不成東西,還沒法不硬著頭皮干。到如今居然湊成這么一小堆堆了!
設若我要是不教書,或者這些篇還不至于這么糟,至少是在文字上。可是我得教書,白天的工夫都花費在學校里,只能在晚間來胡扯;扯到哪兒算哪兒,沒辦法!
現在要出集了,本當給這堆小鬼一一修飾打扮一番;哼,哪有那個工夫!隨它們去吧;它們沒出息,日后自會受淘汰;我不拿它們當寶貝兒,也不便把它們都勒死。就是這個主意!
排列的次序是依著寫成的先后。設若后邊的比前邊的好一點,那總算狗急跳墻,居然跳過去了。說真的,這種“歪打正著”的辦法,能得一兩個虎頭虎腦的家伙就得念佛!
蒙載過這些篇的雜志們允許我把它們收入這本里,十分的感激!
老舍一九三四年,二月一日,濟南。
【五九】
他分明是給一家外國人作仆人的。他拉著那兩個外國小孩,趕過我來,告訴他們,低聲下氣的央告他們:踢他!踢他!然后向我說:你!你敢打我?洋人也不打我呀!然后又向那兩個小孩說:踢!踢他!看他敢惹洋人不敢!
張丙,瘦得像剝了皮的小樹,差不多每天晚上來喝茶。他的臉上似乎沒有什么東西;只有一對深而很黑的眼睛,顯出他并不是因為瘦弱而完全沒有精力。當喝下第三碗茶之后,這對黑眼開始發光;嘴唇,像小孩要哭的時候,開始顫動。他要發議論了。
他的議論,不是有系統的;他遇到什么事便談什么,加以批評。但無論談什么事,他的批評總結束在“中國人是無望的,我剛說的這件事又是個好證據”。說完,他自動的斟上一碗茶,一氣喝完;閉上眼,不再說了,顯出:“不必辯論,中國人是無望的。無論怎說!”
這一晚,電燈非常的暗,讀書是不可能的。張丙來了,看了看屋里,看了看電燈,點了點頭,坐下,似乎是心里說:“中國人是無望的,看這個燈;電燈公司……”
第三碗茶喝過,我笑著說:“老張,什么新聞?”
出我意料之外,他笑了笑——他向來是不輕易發笑的。
“打架來著。”他說。
“誰?你?”我問。
“我!”他看著茶碗,不再說了。
等了足有五分鐘,他自動的開始:
“假如你看見一個壯小伙子,利用他身體氣力的優越,打一個七八歲的小孩,你怎辦?”
“過去勸解,我看,是第一步。”
“假若你一看見他打那個小孩子,你便想到:設若過去勸,他自然是停止住打,而嘟囔著罵話走開;那小孩子是白挨一頓打!你想,過去勸解是有意義的嗎?”他的眼睛發光了,看看我的臉。
“我自然說他一頓,叫他明白他不應當欺侮小孩子,那不體面。”
“是的,不體面;假如他懂得什么體面,他還不那樣作呢!而且,這樣的東西,你真要過去說他幾句,他一定問你:‘你管得著嗎?你是干什么的,管這個事?’你跟他辯駁,還不如和石頭說幾句好話呢;石頭是不會用言語沖撞你的。假如你和他嚷嚷起來,自然是招來一群人,來看熱鬧;結果是他走他的,你走你的路;可是他白打了小孩一頓,沒受一點懲罰;下回他遇到機會還這樣作!白打一個不能抵抗的小孩子,是便宜的事,他一定這么想。”
“那末,你以為應當立刻叫他受懲罰,路見不平……那一套?”我知道他最厭惡武俠小說,而故意斗他。
果然不出我所料,他說:
“別說《七俠五義》!我不要作什么武俠,我只是不能瞪著眼看一個小孩挨打;那叫我的靈魂全發了火!更不能叫打人的占了全勝去!我過去,一聲沒出,打了他個嘴巴!”
“他呢?”
“他?反正我是計畫好了的:假如我不打他,而過去勸,他是得意揚揚而去;打人是件舒服事,從人們的獸性方面看。設若我跟他講理,結果也還是得打架;不過,我未必打得著他,因為他必先下手,不給我先發制人的機會。”他又笑了;我知道他笑的意思。
“但是,”我問,“你打了他,他一定還手,你豈是他的對手?”我很關心這一點,因為張丙是那樣瘦弱的人。
“那自然我也想到了。我打他,他必定打我;我必定失敗。可是有一層,這種人,善于利用筋肉欺侮人的,遇到自家皮肉上挨了打,他會登時去用手遮護那里,在那一刻,他只覺得疼,而忘了動作。及至他看明白了你,他還是不敢動手,因為他向來利用筋肉的優越欺人,及至他自己挨了打,他必定想想那個打他的,一定是有些來歷;因為他自己打人的時候是看清了有無操必勝之券而后開打的。就是真還了手,把我打傷,我,不全像那小子那樣傻,會找巡警去。至少我跟他上警區,耽誤他一天的工夫(先不用說他一定受什么別的懲罰),叫他也曉得,打人是至少要上警區的。”
他不言語了,我看得出,他心中正在難受——難受,他打了人家一下,不用提他的理由充足與否。
“他打人,人也打他,對這等人正是妥當的辦法;人類是無望的,你常這么說。”我打算招他笑一下。
他沒笑,只輕輕搖了搖頭,說:
“這是今天早晨的事。下午四五點鐘的時候,我又遇見他了。”
“他要動手了?”我問,很不放心的。
“動手打我一頓,倒沒有什么!叫我,叫我——我應當怎樣說?——傷心的是:今天下午我遇見他的時候,他正拉著兩個十來歲的外國小孩兒;他分明是給一家外國人作仆人的。他拉著那兩個外國小孩,趕過我來,告訴他們,低聲下氣的央告他們:踢他!踢他!然后向我說:你!你敢打我?洋人也不打我呀!(請注意,這里他很巧妙的,去了一個‘敢’字!)然后又向那兩個小孩說:踢!踢他!看他敢惹洋人不敢!”他停頓了一會兒,忽然的問我:“今天是什么日子?”
“五九!”我不知道,為什么我的淚流下來了。
“嘔!”張丙立起來說,“怪不得街上那么多的‘打倒帝國主義’的標語呢!”
他好像忘了說那句:“中國人沒希望”,也沒喝那末一碗茶,便走了。
【熱包子】
她確是灑脫:自天子以至庶人好像沒有和她說不來的。我知道門外賣香油的,賣菜的,永遠給她比給旁人多些。她在我的孩子眼中是非常的美。她的牙頂美,到如今我還記得她的笑容,她一笑便會露出世界上最白的一點牙來。
愛情自古時候就是好出軌的事。不過,古年間沒有報紙和雜志,所以不像現在鬧得這么血花。不用往很古遠里說,就以我小時候說吧,人們鬧戀愛便不輕易弄得滿城風雨。我還記得老街坊小邱。那時候的“小”邱自然到現在已是“老”邱了。可是即使現在我再見著他,即使他已是白發老翁,我還得叫他“小”邱。他是不會老的。我們一想起花兒來,似乎便看見些紅花綠葉,開得正盛;大概沒有一人想花便想到落花如雨,色斷香銷的。小邱也是花兒似的,在人們腦中他永遠是青春,雖然他長得離花還遠得很呢。
小邱是從什么地方搬來的,和哪年搬來的,我似乎一點也不記得。我只記得他一搬來的時候就帶著個年青的媳婦。他們住我們的外院一間北小屋。從這小夫婦搬來之后,似乎常常聽人說:他們倆在夜半里常打架。小夫婦打架也是自古有之,不足為奇;我所希望的是小邱頭上破一塊,或是小邱嫂手上有些傷痕……我那時候比現在天真的多多了;很歡迎人們打架,并且多少要掛點傷。可是,小邱夫婦永遠是——在白天——那么快活和氣,身上確是沒傷。我說身上,一點不假,連小邱嫂的光脊梁我都看見過。我那時候常這么想:大概他們打架是一人手里拿著一塊棉花打的。
小邱嫂的小屋真好。永遠那么干凈永遠那么暖和,永遠有種味兒——特別的味兒,沒法形容,可是顯然的與眾不同。小倆口味兒,對,到現在我才想到一個適當的形容字。怪不得那時候街坊們,特別是中年男子,愿意上小邱嫂那里去談天呢,談天的時候,他們小夫婦永遠是歡天喜地的,老好像是大年初一迎接賀年的客人那么欣喜。可是,客人散了以后,據說,他們就必定打一回架。有人指天起誓說,曾聽見他們打得咚咚的響。
小邱,在街坊們眼中,是個毛騰廝火[1]的小伙子。他走路好像永遠腳不貼地,而且除了在家中,仿佛沒人看見過他站住不動,哪怕是一會兒呢。就是他坐著的時候,他的手腳也沒老實著的時候。他的手不是摸著衣縫,便是在凳子沿上打滑溜,要不然便在臉上搓。他的腳永遠上下左右找事作,好像一邊坐著說話,還一邊在走路,想象的走著。街坊們并不因此而小看他,雖然這是他永遠成不了“老邱”的主因。在另一方面,大家確是有點對他不敬,因為他的脖子老縮著。不知道怎么一來二去的“王八脖子”成了小邱的另一稱呼。自從這個稱呼成立以后,聽說他們半夜里更打得歡了。可是,在白天他們比以前更顯著歡喜和氣。
小邱嫂的光脊梁不但是被我看見過,有些中年人也說看見過。古時候的婦女不許露著胸部,而她竟自被人參觀了光脊梁,這連我——那時還是個小孩子——都覺著她太灑脫了。這又是我現在才想起的形容字——灑脫。她確是灑脫:自天子以至庶人好像沒有和她說不來的。我知道門外賣香油的,賣菜的,永遠給她比給旁人多些。她在我的孩子眼中是非常的美。她的牙頂美,到如今我還記得她的笑容,她一笑便會露出世界上最白的一點牙來。只是那么一點,可是這一點白色能在人的腦中延展開無窮的幻想,這些幻想是以她的笑為中心,以她的白牙為顏色。拿著落花生,或鐵蠶豆,或大酸棗,在她的小屋里去吃,是我兒時生命里一個最美的事。剝了花生豆往小邱嫂嘴里送,那個報酬是永生的欣悅——能看看她的牙。把一口袋花生都送給她吃了也甘心,雖然在事實上沒這么辦過。
小邱嫂沒生過小孩。有時候我聽見她對小邱半笑半惱的說,憑你個軟貨也配有小孩?!小邱的脖子便縮得更厲害了,似乎十分傷心的樣子;他能半天也不發一語,呆呆的用手擦臉,直等到她說:“買洋火!”他才又笑一笑,腳不擦地飛了出去。
記得是一年冬天,我剛下學,在胡同口上遇見小邱。他的氣色非常的難看,我以為他是生了病。他的眼睛往遠處看,可是手摸著我的絨帽的紅繩結子,問:“你沒看見邱嫂嗎?”
“沒有哇,”我說。
“你沒有?”他問得極難聽,就好像為兒子害病而占卦的婦人,又愿意聽實話,又不愿意相信實話,要相信又愿反抗。
他只問了這么一句,就向街上跑了去。
那天晚上我又到邱嫂的小屋里去,門,鎖著呢。我雖然已經到了上學的年紀,我不能不哭了。每天照例給邱嫂送去的落花生,那天晚上居然連一個也沒剝開。
第二天早晨,一清早我便去看邱嫂,還是沒有;小邱一個人在炕沿上坐著呢,手托著腦門。我叫了他兩聲,他沒答理我。
差不多有半年的工夫,我上學總在街上尋望,希望能遇見邱嫂,可是一回也沒遇見。
她的小屋,雖然小邱還是天天晚上回來,我不再去了。還是那么干凈,還是那么暖和,只是邱嫂把那點特別的味兒帶走了。我常在墻上,空中看見她的白牙,可是只有那么一點白牙,別的已不存在:那點牙也不會輕輕嚼我的花生米。
小邱更毛騰廝火了,可是不大愛說話。有時候他回來的很早,不作飯,只呆呆的愣著。每遇到這種情形,我們總把他讓過來,和我們一同吃飯。他和我們吃飯的時候,還是有說有笑,手腳不識閑。可是他的眼時時往門外或窗外那么一下。我們誰也不提邱嫂;有時候我忘了,說了句:“邱嫂上哪兒了呢?”他便立刻搭訕著回到小屋里去,連燈也不點,在炕沿上坐著。有半年多,這么著。
忽然有一天晚上,不是五月節前,便是五月節后,我下學后同著學伴去玩,回來晚了。正走在胡同口,遇見了小邱。他手里拿著個碟子。
“干什么去?”我截住了他。
他似乎一時忘了怎樣說話了,可是由他的眼神我看得出,他是很喜歡,喜歡得說不出話來。呆了半天,他似乎趴在我的耳邊說的:
“邱嫂回來啦,我給她買幾個熱包子去!”他把個“熱”字說得分外的真切。
我飛了家去。果然她回來了。還是那么好看,牙還是那么白,只是瘦了些。
我直到今日,還不知道她上哪兒去了那么半年。我和小邱,在那時候,一樣的只盼望她回來,不問別的。到現在想起來,古時候的愛情出軌似乎也是神圣的,因為沒有報紙和雜志們把邱嫂的相片登出來,也沒使小邱的快樂得而復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