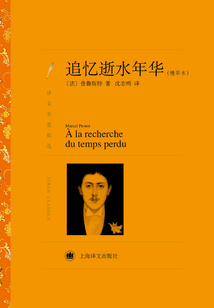
追憶逝水年華(精華本)(譯文名著精選)
最新章節
- 第87章 失而復得的時間(Ⅱ)(6)
- 第86章 失而復得的時間(Ⅱ)(5)
- 第85章 失而復得的時間(Ⅱ)(4)
- 第84章 失而復得的時間(Ⅱ)(3)
- 第83章 失而復得的時間(Ⅱ)(2)
- 第82章 失而復得的時間(Ⅱ)(1)
第1章 譯本序(1)
普魯斯特漫長的文字生涯似乎總體上完成了一部散文式長河小說,主要以無意識回憶為發端,引起種種聯想,產生想象的印象,不斷拓展,延伸重疊,枝枝蔓蔓,無窮無盡,總題為《追憶逝水年華》。他也寫過不少文論,但大多為散文式的、感想式的評論,集中收入《駁圣伯夫》,雖獨立成冊,卻多半內容近似《追憶逝水年華》。本文主要通過《追憶逝水年華》論述普魯斯特的創作思想和小說藝術。
鴻篇巨制《追憶逝水年華》不是通常意義上的長河小說,因為它沒有傳統長河小說的種種特征。從思想內容上講,它著力于表現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無所事事的貴族遺老遺少和飽食終日的資產者、委瑣渺小的凡夫俗子以及他們個人的命運,描繪他們對人類狀況的憂慮,對生存意義的懷疑,由于個人事業和愛情幻滅后內心產生的矛盾和苦悶,通過對近四十年失去的歲月的追憶,再現了昔日榮華的階級如何衰退,如何沒落。這恐怕是對這部長篇小說的思想內容較客觀的概括。
但是,自《追憶逝水年華》第一部問世以來,四分之三的世紀過去了,世人對這部巨著的思想內容,仍然臧否不一。不管分歧有多大,他們對《追憶逝水年華》的創作方法和藝術技巧的評價似乎趨向一致。在經過較長時間的爭論之后,法國文學界幾乎一致認為普魯斯特是現代小說的先驅之一,為他身后的幾代作家開辟了新的創作途徑,有人甚至稱他為“現代小說之父”。顯而易見,《追憶逝水年華》沒有傳統長河小說的構架,即除有一個正主題外,還有若干副主題,故事情節曲折、復雜,圍繞著主線又有一條或幾條副線。相反,它的情節已經淡化,擺脫了強烈的外部沖突,著重刻畫人物的心理狀態,把主題、形象、情節熔為一爐。更值得一提的是,《追憶逝水年華》中的情節酷似斷線后散鋪的念珠,很難按順序、年代加以編排,不僅念珠的排列沒有秩序,而且各粒念珠又像一滴滴油漬,不斷地滋蔓、擴散。總體看來,仿佛是一幅印象派的油畫,近看模糊一片,遠看光彩奪目。不連貫的情節有如斷金碎玉,晶瑩耀目,富有詩意,卻又沒有油漬黯淡無光、索然無味的缺陷。當代法國著名作家、批評家瑞利安·格拉克指出,閱讀普魯斯特的《追憶逝水年華》趣味無窮,有如品嘗當代時興的甜夾咸的食物。他運用心理分析的手法,把現實世界剖析得淋漓盡致,而又仿佛把我們帶入古老的童話世界。我們就像阿里巴巴闖入藏滿珍寶的洞穴那么興奮。這部巨作把巴爾扎克的《幻滅》和《一千零一夜》天衣無縫地融合在一起。[1]
一 大器晚成
馬塞爾·普魯斯特出生于富裕的家庭,幼時即從母親、外祖母習詩作文,研讀經典著作,博覽群書,彈琴學畫,中學文哲成績優異,為后來的文學創作打下堅實的功底。不幸,體格纖弱的馬塞爾九歲上得了哮喘病,倍加受到家庭的溺愛;更不幸的,這位天賦聰穎、極度敏感的藝術型少年處在和他的藝術前途格格不入的社會環境中,盡管周圍有不少文化素養極高的人樂于和他相與。由于自幼出入上流社會,生活又局限于社交應酬,難免染上社交界的輕佻習氣。他沒有盡早地發揮自己創作的天賦,卻一味炫耀廣博的知識和精湛的技巧,為的是博得名流雅士的賞識。《歡樂與歲月》便是他這個時期的產物,書中高談音樂、美術、純文學;并請法蘭西學院院士、著名作家阿納托爾·法朗士作序。誰都看得出,這本印刷精美、裝潢漂亮的書受法朗士的影響十分明顯,但作者卻意氣揚揚,甚為自得,不理會友朋的議論。人們普遍認為這位風流倜儻、聰穎多智的紳士因百無聊賴而涉獵文學創作,毫無前途可言,以致他自己也信心不足了。到了而立之年的普魯斯特還在黑暗中摸索,還在仔細觀察周圍的一切,還在砥礪批評精神,還在積累各方面的素材,從這個意義上講,這時期頻繁的社交活動對他后來的創作倒并非無益。直到普魯斯特研讀羅斯金之后才確立信心,并等到雙親謝世之后才中斷社交活動,深居簡出,雖然重病纏身,卻發瘋似的閉門著書,終于潛心于真正的創作。
為了說明舞文弄墨的普魯斯特怎樣被奉為經典作家,我們將用一些篇幅,敘述《追憶逝水年華》這部風格卓異的杰作得到舉世公認經過了何等艱難的歷程。
經過多年的艱苦創作,1911年普魯斯特認為他的力作即將誕生,準備找個出版者。他把《追憶逝水年華》第一部題獻給《費加羅報》的負責人之一卡爾梅特,希望通過他的周旋,在其好友法斯凱爾主持的出版社出版。但卡爾梅特不大起勁,法斯凱爾的態度也十分冷淡。著名作家讓·科克多倒頗識才具,他替普魯斯特求助于當時負有盛名的戲劇家埃德蒙·羅斯當,因為羅斯當的書在法斯凱爾出版社出版,銷路甚好。科克多為人慷慨大度,答應出面跟法斯凱爾交涉。法斯凱爾勉強同意出書,但要求刪改。不愿意屈從出版商意志的普魯斯特怯生生地試探久已認識的出版家加斯通·加利馬,派人送去幾本手稿。加利馬把稿子拿到《新法蘭西評論》編委會上征求意見,愛挑剔的編委會成員看到題獻給卡爾梅特的字樣心中大為不快,說什么熱衷于上流社會生活的紈绔子弟普魯斯特的手稿充滿“公爵夫人的氣息”。大作家安德烈·紀德隨意翻閱,注意到一句話,那是敘述者對其姑媽萊奧妮的描繪:“我沒跟姑媽待上五分鐘,她就把我打發走,生怕我累著她。她把蒼白而黯淡的前額伸向我的嘴唇,在這清晨時分,她尚未梳理假發,額頭顯得陰郁,椎骨隆起,好似一環冠狀骨刺或一串念珠……”[2]什么“額上的椎骨”!紀德不屑一顧,作品就這樣被輕蔑地否決了。
嘗試失敗,普魯斯特不得不違心地回過頭去接受法斯凱爾提出的刪改要求,但未想到法斯凱爾居然退稿,推說無力出版,深表歉意。其實卡爾梅特并沒有得到過法斯凱爾的任何許諾。普魯斯特仍不死心,他買了一件珍貴的禮品去費加羅報社求見卡爾梅特。這位大人物對普魯斯特的禮物心不在焉地瞥了一眼,根本沒有打開看,連一聲謝也沒說,只字未提法斯凱爾,光講了幾句有關總統選舉的話,普魯斯特只得起身告辭。走投無路的普魯斯特萬般無奈,開始認真考慮自費出版。
好心的朋友路易·德·羅貝爾擔心普魯斯特自費出版在公眾眼里等于把自己降為業余作家,建議他把手稿寄給奧朗道夫出版社,并且親自寫信給經理恩勃洛,推薦普魯斯特,稱他是一位大作家。半個月后,羅貝爾收到經理先生的回答:“親愛的朋友,我也許少見多怪,但我不明白這位先生哪能用三十頁的篇幅來描寫他入睡前如何在床上輾轉反側,叫人百思不得其解……。”[3]
氣惱和失望之余,普魯斯特毅然決定自費出版,交給初出茅廬的青年出版者貝爾納·格拉塞承辦。他對一位朋友說:“這部著作我寫了很長時間,實錄了我的思想精華。它要求在我進入墳墓之前,給它建座墳墓,以了其事。”[4]普魯斯特早為他的巨著寫下總書名:《追憶逝水年華》,第一部名為:《在斯萬家那邊》。
自1913年12月起,普魯斯特拼命動員報界的朋友鼓吹他這部重要的作品。朋友們盡了力,甚至把“天才”的字樣都用上了。但讀者的反應冷淡,他們心目中的普魯斯特仍舊是《歡樂與歲月》的作者,在他們看來,報界的評論不過是幾個上流人士吹捧另一個上流人士而已。法朗士收到贈書和作者的親筆題獻:“贈給我的啟蒙導師,贈給最偉大、最敬愛的人。”可法朗士打開書卻念不下去,后來對《最后一課》的作者阿爾豐斯·都德的遺孀說:“我為他的處女作寫過序。聽說他得了嚴重的神經衰弱癥,身不離床,護窗板成天關著,電燈總亮著。我根本看不懂他的作品。他討人喜歡,絕頂聰明,有敏銳的觀察力。但我早就不跟他來往了。”[5]收到贈書的朋友們出于禮貌,紛紛向他道喜,說些贊揚的話。普魯斯特聽后很不受用,因為他看出不少人根本沒有翻閱他的書。他失望了,一種失敗感侵襲著他。盡管如此,他的出版者格拉塞在路易·德·羅貝爾的支持下為爭取《在斯萬家那邊》獲龔古爾獎而奔波,因為龔古爾獎評委會委員萊翁·多代是個知音。普魯斯特立即抓住這個機會,四處活動,八方寫信,發瘋似的希望擁有更多的讀者,以便保護這株脆弱的幼苗。但在初審時,他就被刷了下來,1913年的龔古爾獎根本輪不到他。
不過,慧眼識真金的人還是有的。書出版后,加利馬和《新法蘭西評論》的主編、詩人雅克·里維埃爾責成蓋翁寫一篇書評。蓋翁讀了小說后欣喜若狂,贊嘆不已。里維埃爾立即向紀德報告,紀德答應閱讀全書。不久,紀德給普魯斯特寄去一封情透紙背的信,其中寫道:“幾天來我一直未離開您的書。我讀得津津有味,完全沉浸在尊著里,可謂大飽眼福。唉!我面對這本愛不釋手的書為何感到如此痛苦呢?……拒絕出版這本書是《新法蘭西評論》最嚴重的失誤,也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遺憾和內疚,因為我有很大的責任。為此我感到羞愧……”[6]普魯斯特大喜過望,立即回信說:“我經常想,某些歡樂是以起先被剝奪較小的歡樂為條件的,如果沒有遭到拒絕,沒有遭到《新法蘭西評論》的一再拒絕,我不可能收到您的信,收到您的信比《新法蘭西評論》要出版我的書,更使我高興。”[7]從此,《新法蘭西評論》向他敞開大門,熱切地準備出版《追憶逝水年華》后面幾卷。加利馬本人一再表示愿意出版普魯斯特所有的書;法斯凱爾深表遺憾,迫不及待地要求彌補過失。這樣一位到處吃閉門羹的作家,一日之間成為所有的出版商爭搶的對象。
不幸,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追憶逝水年華》的出版暫告中斷。勢力弱小的格拉塞出版社暫時關閉,不得不忍痛割愛,把出版權轉給加利馬。幾年后,在幾位朋友的游說和斡旋下,龔古爾評獎委員會經過激烈的爭論,終以六票贊成、四票反對,通過《在如花少女們倩影旁》(《追憶逝水年華》第二部)獲龔古爾獎(1919年11月10日)。然而,輿論卻頗為冷淡,甚至有人譏諷這部“難讀的作品”不過是花花公子的淺薄之作:如花少女的倩影壓倒了有血有肉的主人公形象;不少人對這位躑躅于社會籬墻之外,幾乎與世界隔絕的作家仍抱著懷疑的眼光,認為他寫的是“夢囈”。
對已出版的《追憶逝水年華》第一、二部的思想內容,在較長的歷史時期內的評論界一直褒貶不一。現把褒貶雙方的意見歸納如下:
貶責者認為,在他的作品里只看到貴族或大資產階級沙龍中上流人士聚會的場景。作者不厭其詳地描繪有閑階級的情感:病態的愛情、嫉妒、冒充的高雅等等,反映不出社會的風貌。游手好閑之徒屬于行將消亡的階層,他們的激情無非是矯揉造作的無病呻吟。工人、農民、商人、士兵、學者、革命者、保守派才是構成當代社會的主體,巴爾扎克已經預見到的,普魯斯特卻一無所知或視而不見。巴爾扎克描繪一個世界,普魯斯特只描繪上流社會。當代著名的左翼學者、評論家、巴爾扎克研究專家皮埃爾·阿布拉阿姆指責普魯斯特如同圣西門那樣只注意表現一個狹小的天地,甚至不如圣西門。圣西門的回憶錄雖然只局限于宮廷,但書中的人物畢竟是有職業的,干大事的,為取得政權而奮斗,其中不少人物后來成為軍政要員。而活躍在普魯斯特筆下的全是上流社會中虛度光陰的人物,盡管偶爾出現一個醫生、一個律師、一個外交官,但看不到與他們的職業有關的活動,有的只是無謂的情節和無聊的情調。
欣賞者反對這種說法,認為小說家只能有效地描寫他所熟悉的階層和人物,任何作家的作品都不可能包羅萬象,巴爾扎克也遠沒有寫盡他那個時代的整個社會。例如,工人和農民就很少在《人間喜劇》中出現,即使出現,也僅作陪襯;政治生活很少涉及,軍事生活也表現得不充分。像巴爾扎克這樣的天才,也不可能把整個社會都囊括到他的小說里,而且也沒有必要。不錯,普魯斯特筆下的人物,大多是貴族、大資產者、上流紳士、女士,以及為他們服務的傭人,但在像法國這樣的社會里,這些階層的人士在人數上畢竟占著不少的比例,并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問題是怎樣寫他們,是針砭、批判乃至鞭笞他們的沒落,還是揄揚他們的雍容,潤飾他們的鴻業?普魯斯特的作品顯然屬于前者。再說,他塑造的人物特征其實在各個階層、各個國家都普遍存在,只不過在上流社會更突出罷了。況且,他的作品中時有出現如同弗朗索瓦絲這樣善良、淳樸的農民形象以及其他為數不多的勞動階層的人物,對他們從不鄙視。因此可以說思想內容是具有批判意義的,因而是積極的、有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