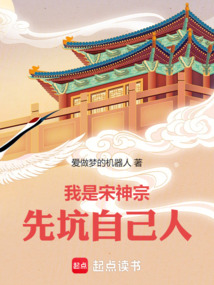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 1評論第1章 大宋御前財政會議
“你們說說,朕的錢呢!”
“朕的錢呢!”
北宋熙寧元年(1068年),四月二十七日,汴京皇宮,垂拱殿。
御座巍峨,雕龍蟠繞,珠翠輝映。
趙頊端坐其上,凝視眾人,這是他即位以來第一次朝著眾臣發怒。
朕,大宋第六任皇帝,趙頊。
兩年前才穿越過來,一年前登基稱帝。
目前人在大宋,九五至尊!
……
年輕的天子動怒,群臣或垂首斂息,或側目而視。
前面幾個老臣面面相覷,官家為何今日一反常態,火氣這么大。
而且財政緊張,也不是一日兩日的事情了,你難道是不知道?
“陛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曾公亮顫顫巍巍地站了出來,抬首之際,嘴唇囁嚅幾下,“國庫虧緊,亦非一日之事,自仁宗皇帝時,就已是難解之題。”
見到曾公亮這老頭站出來,趙頊緩緩收起了怒氣。
這家伙今年都快七十了,當朝次相,三朝元老。
大宋朝宰相有三,首相,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殿大學士,是站在曾公亮左側的富弼。
次相,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正是眼前的曾公亮。
末相,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是在曾公亮左側的陳升之。
“那卿以為,此之問題,該如何解之?”
曾公亮抬頭目光與趙頊相接,又垂下眼簾,“官家,此事當緩緩決之,上可開源,下可節流,雙管齊下,事必功成。”
“何以開源,何以節流?”
趙頊話畢,殿內群臣動作戛然而止,甚至還多了幾分不安。
“去年,銀以兩計收五萬六千,而其出之多者六萬。”
“錢以千計收四千七百四十萬,而其出之多者一百五十二萬。”
“綢絹以匹計收一百四十一萬,而其出之多者十二萬。”
趙頊拿起三司使韓維的大宋財政奏札,將其中赤字的幾條,又重新念了一遍。
“韓相,三司能否告訴朕,這都是怎么虧欠的?”趙頊轉頭看向三司使韓維。
三司使又稱“計相”,掌管大宋主要財政。
韓維看著一反常態,如此認真的趙頊,眼中滿是訝異,只覺一股陌生之感撲面而來。
自己還是官家的老師,官家為何要為難自己?
此時幾位宰相也算是徹底緩過神來,年輕的官家看來是想借著這等難題來掌控朝廷了。
也罷!
這天終會來的。
“去年先皇駕崩,官家登基,國計靡費甚多,另有荊湖水災,耗費錢緡百萬,京東匪禍……”但是朝堂之上,他們只是君臣,韓維站了出來,頓了一下,便是串出了一段話。
其中說得最重要的,就是錢都花在你趙頊登基上去了。
“可有詳陳?”趙頊眉頭微微緊了些許,繼續道。
他這是真的想看看底下人怎么花錢的。
“三司有大致的條陳。”
“今日可能呈遞上來?”
“恐需一段時日整理。”
“多久?”
“十日左右。”韓維也不是專業的理財能手,只能說個大概。
“那今年銀錢綢絹的收支,可能盈余?”
問到此處,韓維心里也沒底,既然去年不行,今年大概是不能盈余的。
“臣不知。”韓維冷著臉搖了搖頭,“不過今年糧谷應該還是能盈余。”
去年大宋朝的糧谷盈余六十萬石,另外黃金也盈余兩千多兩。
“朕知道,若是糧谷也是虧欠,那諸卿恐怕就要寢食難安。”
趙頊也沒有繼續難為韓維,而是將目光投向了站在群臣后面的判司農寺事。
“司農寺,去年收支幾何?”
正在后排站著的判司農寺事聽見官家呼喊自己,頓感不妙,自己這小小司農寺,今日居然被點了名。
這國家收支,大頭都在三司,怎么把我司農寺給拎出來了。
北宋的財政一共分為三個系統。
三司為主,掌田賦、商稅、酒稅、常貢、征榷之利,掌國家財稅十之七八。
司農寺掌坊場、坑冶、河渡、山澤、地利、榷貨、戶絕沒納之財。
另有內藏庫,這是皇帝小金庫。
后兩者加起來也不過十之二三。
“回稟官家,去年司農寺收支均衡,錢緡盈余二十余萬貫。”判司農寺事雖然在朝中是個小透明,但他對自己分內之事,基本也還算清楚。
“糧谷呢?”
“糧谷……稍有虧欠。”
趙頊沒再多問,看來司農寺的情況也并不是很好。
“十日之內,將諸項條陳送到宮中,朕要細細審看。”
“遵旨!”判司農寺事小心擦了擦額頭的細汗,然后退了回去。
“適才呂相說的開源節流,諸卿可有辦法?”
趙頊的問題,又將朝堂打得冷寂。
這有法子就不會拖到現在!
官家是太幼稚,還是在攪弄風雨啊?
趙頊掃視了眾臣一圈。
就在此時,群臣中站出了一人,鏗鏘有力道,“回稟官家,若要開源節流,當行變法之事!”
站出來的人,正是翰林學士兼侍講王安石!
咯噔!
王安石一言,朝堂之中激起三重驚浪。
趙頊的目光也投了過去,果然,王安石還是變法的天命之人。
“王翰林,變法之事不是三言兩語,牽一發而動全身,不可妄言!”參知政事趙抃連忙提醒著這個“莽撞”的后輩。
接著,又有兩位朝臣站了出來反駁王安石的變法之說。
“變法之事,事體龐雜,千頭萬緒,絕非片言只語所能道盡,若是行之不當,動搖國本。”最后,曾經參與慶歷新政的首相富弼也開口道。
眾臣或是反對,或是一言不發。
朝中最開明的次相曾公亮也閉口不言。
王安石最后也只得無奈地退了回去。
變法的事情大宋也不是沒有搞過,慶歷新政就是一地雞毛。
而且很多人看來,變法變法,這變法往往都會變到他們頭上,現在穩穩當當的不是挺好。
現在大宋朝的財政雖有虧欠,但亦有盈余,不是挺好?
至于以后會不會洪水滔天,那是后人的事情了!
群臣不愿,趙頊也沒有再說變法之事。
“昨日韓琦來奏,請旨錄唐魏征、狄仁杰之后,朕已經拒絕了。”趙頊向群臣說起了另外一事。
韓琦,就是“東華門外唱名者方為好男兒”的那位。
趙頊的話,可讓朝中群臣有些不解和著急,恩蔭制度乃是大宋國本,可不能動搖!
他們的子孫,諸多都指望著恩蔭補官。
要沒了這個,過不了兩代,他們家族也會被科舉場上的那些泥腿子踩下去了。
“朝廷恩蔭,是給大宋諸位忠臣的,這前朝朝臣,又與本朝何關?”
趙頊的話,讓群臣的心又放了下來。
的確,這前朝的魏征、狄仁杰,你就是再楷模典范,也不能恩蔭本朝的子孫。
“今日,諸卿也不必再這般請奏!朕也不愿費本朝的錢緡養前朝的臣孫!”
趙頊說到底,說的還是錢的事情。
至少這一項他得砍掉。
“臣等遵旨!”群臣應道。
“啟奏官家,昨日登州來奏,春日饑荒,鄉野多有饑民,欲募饑民補廂軍。”趙抃見趙頊今日很在乎錢緡,于是便將昨日收到的一份奏事向趙頊稟告。
本來按照大宋朝的規則,這般小事,只需要宰相或者副相簽押,即可生效。
副相也就是參知政事。
但既然官家在意錢緡,趙抃自得說說。
“趙卿以為如何?”趙頊聽到此事,心頭微皺。
募饑民補廂軍,這可真是大宋朝的特色,也正是如此,才讓大宋朝內部比歷朝歷代都穩當很多。
這也成了大宋的一項國策。
可代價……就是耗費了非常多的錢緡。
而這些廂軍卻還無一點戰斗力。
大宋朝這屬實是花錢養廢物。
“登州之地,北臨渤海,相望遼東,饑民泛濫,恐危河北邊防,當應允招募。”
“大概所費多少?”趙頊問道。
“還需根據登州饑民之數,才可計算。”趙抃應道。
“根據登州饑民之數?若是一千饑民,所費幾何?”
“不少于萬緡!”
“萬緡,為何這么多?”趙頊震驚。
“官家,這只是初期安頓饑民所需,后續恐怕還需更多錢糧。”
聽到這里,趙頊沉默。
你們糊弄朕啊,那朕就得放狗咬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