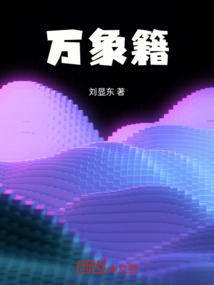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金瓶劫:說不出的愛
短篇小說
一、打虎歸鄉,清河縣的第一縷風
北宋政和年間,殘冬尚在,陽谷縣的風卻已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躁動。當武松踩著未消的薄雪,肩扛斑斕猛虎的頭顱踏入縣城時,鑼鼓聲與吶喊聲如驚蟄的春雷,劈開了蒙在小鎮上空的死寂。他身著染血的獵戶短打,鬢角尚掛著冰碴,那雙曾在景陽岡上瞪裂虎膽的眼睛,此刻卻透著長途跋涉后的疲憊,以及一種與周遭喧囂格格不入的沉郁。
武大郎的炊餅攤就擺在縣衙附近的十字街口。潘金蓮系著青布圍裙,正低頭將剛出爐的炊餅碼入竹筐。她的手指纖長,指甲修剪得圓潤,在白色的面粉上留下淡淡的紅痕。聽見震天的歡呼,她下意識地直起身,目光越過攢動的人頭,瞬間便被那個被衙役簇擁著的身影攫住。
那是怎樣的一個男子?身形如松,肩背寬闊,虎目朗星,鼻梁如削。尤其當他偶爾側過臉,下頜線在蒼白的天光下劃出冷硬的弧度,嘴角似有若無的堅毅,讓潘金蓮握著炊餅的手微微一顫。炊餅“啪”地一聲掉在筐里,驚飛了檐下一只縮頸的麻雀。
“大郎,”她的聲音有些發飄,扯了扯身旁武大郎的衣袖,“你看那……莫不是打虎的英雄?”
武大郎踮著腳,小眼睛笑得瞇成一條縫:“可不是嘛!俺那二弟武松!都說他在景陽岡赤手空拳打死了白額大蟲,俺還不信,這下可真是俺武家的光彩!”他說著,便要擠上前去,卻被潘金蓮輕輕拉住。
她的目光未曾從武松身上移開。那英俊的眉峰間似乎凝結著霜雪,即使在萬眾矚目之下,也透著一股生人勿近的孤冷。這孤冷像磁石,竟比他打虎的壯舉更讓她心頭發緊。她看見他被知縣老爺迎入縣衙,青色的身影消失在朱漆大門后,才緩緩收回目光,指尖仍殘留著剛才觸到武大郎粗布衣衫的粗糙感,與心中那一閃而過的、對某種堅硬而熾熱之物的向往,形成了尖銳的對比。
當晚,武大郎喜滋滋地將武松領回家中。那是間狹小的院落,正房低矮,土墻剝落。潘金蓮早已備下酒菜,青瓷酒壺里溫著自家釀的米酒。當武松低頭跨過門檻,身影籠罩在昏黃的油燈下時,潘金蓮正將一碟醬牛肉擺上桌子。四目相對的剎那,時間仿佛被拉長了。
武松看到的,是一位容貌殊絕的婦人。她身著半舊的月白襦裙,鬢邊只斜插一支銀簪,卻難掩肌膚勝雪,眉如遠黛。尤其那雙眼睛,水光瀲滟,似含著千言萬語,在觸及他目光時,迅速垂落,長長的睫毛在眼瞼下投下一小片陰影,像受驚的蝶翼。
“二郎,這是你嫂嫂潘金蓮。”武大郎搓著手,滿臉堆笑。
“嫂嫂。”武松拱手,聲音低沉,帶著習武之人特有的沙啞。他注意到她袖口磨出的毛邊,以及桌案上那碗特意為他留的、還冒著熱氣的炊餅。
潘金蓮抬起頭,唇邊勾起一抹淺淡的笑:“叔叔一路辛苦,快請坐。大郎念叨了你無數回,今日可算把你盼回來了。”她的聲音軟糯,像江南的吳語,卻又帶著北方女子的爽利,在這簡陋的屋子里,竟如珠玉落盤。
武松坐下,目光掃過屋內簡陋的陳設,又落在武大郎滿足的笑臉上,心中泛起一絲酸楚。他舉杯飲酒,眼角的余光卻瞥見潘金蓮正用絹帕輕輕擦拭他面前的碗沿,動作細致而自然,仿佛早已做過千百遍。那絹帕上繡著幾朵半開的梅花,在燈光下若隱若現。
二、寒梅映雪,叔嫂間的隱秘暗流
武松在哥哥家住了下來,就在正房旁邊的耳房。每日清晨,他天不亮便起身習武,拳腳聲在寂靜的院落里格外清晰。潘金蓮總是比武大郎起得早,當她推開房門,總能看見武松在院中騰挪閃轉,身影在熹微的晨光中如游龍,汗水浸濕了他的短打,在冷空氣中蒸騰出白色的霧氣。
她會默默回到廚房,生火燒水,淘米煮粥。偶爾,她會隔著窗紙,看他收勢而立,胸膛劇烈起伏,額前的碎發被汗水黏在皮膚上。那一刻,她會想起自己年輕時被賣入張大戶家的屈辱,想起被迫嫁給武大郎時的絕望,而眼前這個英武的男子,像一道光,劈開了她死水般的生活。
一日,天降大雪。鵝毛般的雪花簌簌落下,很快便覆蓋了院子。武松練完武,推門進來,肩頭落滿了雪花。潘金蓮連忙遞過熱水:“叔叔快暖暖手,這天兒可真冷。”
武松接過水盆,指尖無意間觸到她的手指,那觸感細膩溫熱,像春日初融的溪水。他心中一震,連忙低頭:“有勞嫂嫂。”
潘金蓮看著他通紅的耳朵,忍不住笑道:“叔叔還怕羞不成?”她取來干布,想替他擦拭肩頭的雪花,手伸到一半,卻又頓住,訕訕地收回,“瞧我,忘了男女有別。”
武松抬眼,見她臉頰微紅,眼神閃爍,心中那股莫名的悸動更加強烈。他想起景陽岡上老虎的血盆大口,想起自己揮拳時的狠厲,此刻面對眼前這個柔弱的婦人,卻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慌亂。“嫂嫂言重了。”他低聲道,轉身走向耳房,腳步竟有些踉蹌。
雪越下越大,武大郎去隔壁王婆家借篩子篩雪,一時半會兒回不來。屋內只剩下武松和潘金蓮。油燈昏黃,映著窗外的白雪,竟生出一種詭異的靜謐。潘金蓮坐在桌邊,假裝縫補衣服,針線卻遲遲穿不進針眼。
“叔叔,”她忽然開口,“聽說你在滄州牢城營里吃了不少苦?”
武松坐在床沿,望著窗外:“男子漢大丈夫,吃些苦算什么。”
“可……”潘金蓮放下針線,聲音輕得像雪落,“再苦,也該有個體己人疼。”
武松猛地回頭,撞進她盛滿水光的眼眸。那眼神里有憐憫,有探究,還有一絲他不敢深究的灼熱。他喉頭滾動,想說些什么,卻只化作一聲沉重的嘆息:“嫂嫂,我武松孑然一身,早已習慣了。”
“習慣了?”潘金蓮苦笑,“我看叔叔并非習慣,只是把心事都藏在心里。就像這雪,看著潔白,底下卻不知埋了多少寒冰凍土。”
她的話像一把鑰匙,猝不及防地撬開了武松緊鎖的心門。他想起父母早亡,兄長懦弱,自己漂泊江湖的孤苦,此刻在這溫暖的屋內,被一個女子如此洞悉,心中竟涌起一股渴望傾訴的沖動。但他很快警醒,這是嫂嫂,是兄長的妻子,他絕不能有任何非分之想。
“嫂嫂說笑了。”他別過頭,語氣恢復了冷硬,“時候不早了,嫂嫂早些歇息吧。”
潘金蓮看著他決絕的背影,眼中的光芒一點點黯淡下去。她拿起針線,卻不小心刺破了手指,一滴鮮紅的血珠滲出來,落在青布上,像一朵驟然綻放的梅花。她望著那滴血,忽然低聲道:“叔叔可知,這世上最苦的,不是無人疼,而是……疼錯了人。”
武松的身體猛地一僵,窗外的風雪似乎更大了,卷著寒意,從門縫里鉆進來,吹得油燈的火苗左右搖曳,將兩人的影子拉得又長又瘦,在墻上無聲地糾纏。
三、欲火焚心,道德與情欲的拉鋸
隨著武松在家中住得越久,叔嫂間那層微妙的窗戶紙越來越薄。潘金蓮不再掩飾自己的心意,她會特意為武松做他愛吃的鹵味,會在他練武后遞上擰干的熱巾,會在他讀書時,安靜地坐在一旁做女紅,目光卻時不時地飄向他英挺的側臉。
武松并非草木,潘金蓮的美貌與溫柔像毒藥,一點點滲入他的骨髓。他開始在夜里輾轉反側,眼前總會浮現她低頭淺笑的模樣,耳邊總會回響她軟糯的聲音。道德的枷鎖與內心的欲望在他胸中激烈搏斗,讓他痛苦不堪。
一日,武大郎去鄰縣賣炊餅,要次日才回。傍晚時分,潘金蓮特意燙了酒,做了幾樣精致的小菜,擺在桌上。武松走進來,見桌上只有兩副碗筷,不由得一怔。
“大郎今日不回來,”潘金蓮站起身,替他卸下腰間的佩刀,“叔叔莫嫌棄,陪嫂嫂吃杯淡酒吧。”
武松想拒絕,卻見她眼中滿是期待,話到嘴邊又咽了回去。兩人相對而坐,默默地飲酒。潘金蓮頻頻為他斟酒,自己也喝了幾杯,臉頰泛起紅暈,眼神更加迷離。
“叔叔,”她忽然放下酒杯,“你看我……是個什么樣的人?”
武松一怔,不知如何回答。在他眼里,她是兄長的妻子,是溫柔賢惠的嫂嫂,但內心深處,卻又渴望著她作為一個女人的鮮活與熱烈。
潘金蓮見他不語,自嘲地笑了笑:“我知道,在別人眼里,我潘金蓮或許是個不安分的女人。可誰又知道,我嫁與大郎,并非所愿。”她的聲音帶著一絲哽咽,“我爹娘早亡,被賣入張大戶家,后來又被他做主,嫁給了大郎……叔叔,你說,這是不是我的命?”
武松握著酒杯的手緊了緊,指節泛白。他知道嫂嫂的身世可憐,卻從未聽她如此直白地傾訴。
“我并非嫌棄大郎老實,”潘金蓮抬起頭,淚水在眼眶里打轉,“只是……只是我這顆心,它會疼,會寂寞,它想要的,或許只是一個能懂它的人。”她的目光緊緊鎖住武松,“叔叔,你懂嗎?”
武松猛地站起身,酒灑了一地:“嫂嫂!休要再說了!”他感到一股熱氣直沖頭頂,理智在情欲面前搖搖欲墜。“你是我兄長的妻子,我武松頂天立地,絕不能做那禽獸不如的事!”
“禽獸不如?”潘金蓮也站了起來,淚水終于滑落,“叔叔,你以為我想這樣嗎?我只是……只是看到你,就忍不住……”她上前一步,幾乎要碰到他的胸膛,“叔叔,你敢說,你對我就沒有半分心動?你敢說,你夜里沒有想起過我?”
武松后退一步,撞在桌角,發出“哐當”一聲響。他看著潘金蓮淚流滿面的臉,看著她眼中燃燒的火焰,心中的堤壩轟然倒塌。他伸出手,似乎想替她拭去淚水,卻在觸碰到她臉頰的前一刻,猛地攥緊了拳頭,指甲深深嵌入掌心。
“嫂嫂,”他的聲音嘶啞,帶著極大的痛苦,“請自重。”說完,他猛地轉身,沖出了房門,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潘金蓮呆呆地站在原地,看著空蕩蕩的門口,仿佛全身的力氣都被抽空。窗外的月光透過窗欞灑進來,照亮了桌上未動的酒菜,也照亮了她臉上冰冷的淚痕。她緩緩坐下,端起武松喝過的酒杯,將剩下的冷酒一飲而盡。酒液辛辣,卻暖不了她冰涼的心。她知道,她和他之間,那道無形的墻,終究是無法逾越了。
四、西門窺玉,寂寞深閨的沉淪
武松的拒絕像一盆冷水,澆滅了潘金蓮心中最后一點希望。她變得更加沉默,每日只是機械地操持家務,眼神空洞地望著窗外。武大郎雖憨厚,卻也察覺到妻子的變化,只當她是思念家鄉,并未深究。
就在這時,西門慶出現了。
西門慶是陽谷縣的富戶,生得風流倜儻,慣會討女人歡心。他早就聽聞武大郎娶了個美貌妻子,一直心癢難耐。那日,他路過武大郎家門前,恰好看見潘金蓮在樓上憑窗遠眺,風吹起她的發絲,容顏在陽光下美得驚心動魄。西門慶頓時魂飛魄散,當即就去找了隔壁的王婆,定下了勾搭潘金蓮的計策。
王婆是個慣會拉皮條的老婆子,花言巧語,最會揣摩人心。她先是借故接近潘金蓮,假意關心,一來二去,便成了無話不談的“好鄰居”。
“他大娘子,”一日,王婆故作神秘地說,“你看你這手針線活,真是巧奪天工。我有個相好的,想做件壽衣,不知你可愿幫這個忙?”
潘金蓮本就寂寞,有人搭話,自然樂意:“王干娘說哪里話,只管拿來便是。”
就這樣,潘金蓮開始在王婆家做針線。西門慶則按照王婆的安排,“恰巧”前來拜訪。第一次見面,西門慶便對著潘金蓮大獻殷勤,又是夸她美貌,又是贊她手巧,言語間盡是挑逗。
潘金蓮起初還有些羞怯,但西門慶的花言巧語、風流姿態,與武松的克制冷漠、武大郎的木訥平庸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尤其是當西門慶拿出綾羅綢緞、金銀首飾送給她時,她那顆被現實磋磨得疲憊不堪的心,終于開始動搖。
“娘子如此美貌,卻屈居在這陋室之中,真是明珠暗投啊。”西門慶端起茶杯,目光在她身上流轉,“不像我那拙荊,黃臉婆一個,哪里懂得憐香惜玉。”
潘金蓮低頭不語,手指無意識地絞著衣角。她想起武松那晚決絕的背影,想起自己日復一日的孤寂,心中涌起一股破罐破摔的沖動。
王婆在一旁敲邊鼓:“可不是嘛!他大娘子,你看西門大官人,一表人才,家大業大,又懂得心疼人,哪點不比……”她話沒說完,卻已點明了意思。
潘金蓮的心跳得飛快,臉上一陣紅一陣白。西門慶見狀,便大膽地伸出手,輕輕握住了她放在桌上的手。那手溫暖而有力,帶著陌生的觸感,讓她渾身一顫,卻沒有掙脫。
窗外的陽光正好,照在王婆家院子里的那株桃樹上,幾朵早開的桃花正肆意地綻放著,像一團燃燒的火焰。潘金蓮望著那桃花,眼中閃過一絲迷離。她知道自己正在墜落,墜入一個萬劫不復的深淵,但此刻,她太累了,太寂寞了,只想抓住這根看似能帶來溫暖的浮木,哪怕它最終會將她拖入海底。
從那以后,潘金蓮便常常以做針線為名,與西門慶在王婆家私會。起初她還有些愧疚,但當西門慶帶她去綢緞莊買新衣,帶她去酒樓吃佳肴,用金錢和甜言蜜語將她包圍時,那點愧疚很快便被虛榮心和被寵愛的快感所取代。她開始精心打扮自己,眉宇間重新有了光彩,只是那光彩之下,卻藏著一絲不安和空虛。
五、血濺鴛鴦,兄長之死的驚雷
紙終究包不住火。潘金蓮與西門慶的私情,很快就在街坊鄰里間傳開了。武大郎起初不信,直到有一天,他親眼看見潘金蓮從王婆家里出來,西門慶緊隨其后,兩人舉止親昵。
武大郎如遭雷擊,氣得渾身發抖。他沖回家,質問潘金蓮。潘金蓮起初還想狡辯,見瞞不過去,便撒起潑來:“我就是跟西門大官人好了!你能怎樣?你看看你自己,矮小丑陋,哪點配得上我?”
武大郎又氣又急,卻拿她沒有辦法。他想起了武松,便想等弟弟回來做主。誰知這話傳到了西門慶和潘金蓮耳朵里。西門慶心狠手辣,怕武松回來報復,便與潘金蓮、王婆商議,決定一不做二不休,除掉武大郎。
那一日,武大郎因氣急攻心,臥病在床。潘金蓮端來一碗湯藥,臉上帶著虛偽的關切:“大郎,快把藥喝了吧,喝了病就好了。”
武大郎看著她,眼神里充滿了失望和痛苦:“你……你真要如此狠心?”
潘金蓮避開他的目光,聲音冰冷:“是你逼我的。”她強行將藥灌進武大郎嘴里。
武大郎掙扎了幾下,便七竅流血,斷了氣。
潘金蓮看著丈夫的尸體,臉上沒有任何表情,仿佛只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西門慶趕來,兩人商議后,便對外宣稱武大郎是暴病而亡。
此時的武松,正在外地公干。當他風塵仆仆地趕回陽谷縣,看到的卻是兄長冰冷的靈柩。他跪在靈前,悲痛欲絕。看著嫂嫂潘金蓮雖然披麻戴孝,卻不見多少哀戚,反而眼神閃爍,他心中疑竇頓生。
在鄰居鄆哥的告知下,武松終于得知了真相。那一刻,他只覺得天旋地轉,心中的悲痛化為滔天的怒火。他想起兄長的憨厚,想起嫂嫂曾經的溫柔,想起自己對她那份不敢言說的情愫,如今都變成了尖銳的諷刺。
“潘金蓮!”他猛地站起身,雙眼赤紅,像一頭被激怒的猛虎,“你這毒婦!還我兄長命來!”
潘金蓮嚇得臉色慘白,躲在西門慶身后。西門慶強作鎮定:“武松,你休要血口噴人!你兄長是暴病而亡,與我等何干?”
武松哪里肯信,他沖上前去,卻被西門慶的家丁攔住。他知道西門慶有錢有勢,告官未必能討回公道。于是,他暗中定下計策,先在家中設下靈堂,逼迫潘金蓮和王婆招供,寫下了供狀。
隨后,在一個陰雨綿綿的清晨,武松提著樸刀,先找到了正在酒樓尋歡作樂的西門慶。兩人在獅子樓展開了一場惡斗。武松懷著殺兄之仇,招招狠厲,西門慶哪里是對手,很快便被武松一刀劈死,頭顱被割下,提在手中。
接著,武松回到家中,將潘金蓮和王婆綁在武大郎的靈前。他看著潘金蓮,眼中沒有了往日的掙扎,只剩下冰冷的恨意。
“嫂嫂,”他的聲音像淬了冰,“你可知錯?”
潘金蓮抬起頭,臉上沒有了往日的嬌媚,只剩下死灰般的平靜。她看著武松手中滴著血的刀,又看了看靈柩上兄長的牌位,忽然笑了,笑得凄涼而絕望。
“錯?”她喃喃道,“我潘金蓮這一生,從被賣入張大戶家,到嫁給武大郎,再到遇見西門慶……我何時有過錯的選擇?”她的目光轉向武松,眼中閃過一絲復雜的光芒,“二郎,你以為我真的愛西門慶嗎?我只是……只是想抓住點什么,哪怕是飛蛾撲火。”
“住口!”武松怒吼,“你毒殺親夫,傷風敗俗,死有余辜!”
“死有余辜?”潘金蓮的眼淚終于流了下來,“二郎,你告訴我,當初在那個雪夜,你若肯帶我走,今日又怎會是這般結局?你口口聲聲說要守禮教,要顧兄長,可你捫心自問,你對我,難道就沒有半分真心?”
武松的身體劇烈顫抖,手中的刀差點掉落。潘金蓮的話像一把尖刀,刺穿了他最后的偽裝,直抵內心最隱秘的角落。他想起那個雪夜,想起她含淚的雙眼,想起自己強壓下的情感,心中痛如刀絞。
“多說無益!”他猛地閉上眼睛,舉起了手中的刀,“你既已不仁,就休怪我不義!”
刀光閃過,鮮血濺在武大郎的靈位上,也濺在潘金蓮那張帶著淚痕卻依舊美麗的臉上。她看著武松,嘴唇翕動,似乎想說什么,最終卻只是輕輕嘆了口氣,緩緩閉上了眼睛。
窗外的雨越下越大,敲打著窗欞,像是在為這場悲劇哭泣。武松站在一片血泊中,手中的刀“哐當”一聲掉在地上。他看著潘金蓮漸漸冰冷的身體,看著兄長的靈位,只覺得天地間一片蒼茫,所有的愛恨情仇,最終都化作了這無法挽回的血色結局。
六、六合殘夢,青燈古佛下的余音
武松殺了西門慶和潘金蓮,投案自首。知縣念他是為兄報仇,又有打虎的威名,最終判他刺配孟州。此后,武松經歷了醉打蔣門神、血濺鴛鴦樓等一系列變故,看透了世事炎涼,最終在杭州六合寺出家,法號“清忠祖師”。
歲月流轉,轉眼已是數十載。武松已是古稀之年,須發皆白,面容清癯,唯有那雙眼睛,依舊透著一股深邃的光芒。他每日在寺中掃地、誦經,青燈古佛,晨鐘暮鼓,看似心如止水,內心深處,卻總有一個角落,藏著那段刻骨銘心的往事。
又是一個雪夜,與當年陽谷縣的那個雪夜如此相似。雪花無聲地飄落,覆蓋了六合寺的庭院,一片潔白。武松拄著拐杖,走到寺外的梅樹下。那株梅樹虬枝盤曲,幾朵紅梅在風雪中傲然綻放,像極了潘金蓮當年絹帕上的梅花,也像極了她臨死前嘴角那抹凄美的笑。
他伸出布滿皺紋的手,輕輕觸碰那冰冷的花瓣,仿佛又回到了那個狹小的院落,回到了那個油燈昏黃的夜晚。他看見潘金蓮為他溫酒,看見她含淚的雙眼,聽見她問:“叔叔,你敢說,你對我就沒有半分心動?”
“阿彌陀佛……”武松低聲念誦佛號,試圖驅散心中的波瀾,可那記憶卻如潮水般涌來,無法抑制。他想起自己當年的克制,想起那份被禮教壓抑的情感,想起潘金蓮那句“疼錯了人”的嘆息,心中依舊會泛起隱隱的痛。
他真的錯了嗎?在那個禮教森嚴的時代,他作為小叔子,愛上嫂嫂,本就是大逆不道。可那份情感,卻又是如此真實,如此熾熱,曾讓他在無數個夜晚輾轉反側。如果當年他沒有那么克制,如果他能拋開世俗的眼光,結局會不會不一樣?
可是沒有如果。兄長的慘死,潘金蓮的凋零,西門慶的伏法,自己的出家……一切都已塵埃落定,只留下一段被世人唾罵的“淫婦”與“義士”的故事,卻很少有人知道,在那故事的深處,曾有過怎樣一場刻骨銘心的愛,怎樣一場被命運捉弄的悲劇。
雪越下越大,紅梅在風雪中顯得更加艷烈。武松站在梅樹下,久久不語。他知道,有些傷口,即使過了幾十年,也依然會在某個特定的時刻,隱隱作痛。有些記憶,即使遁入空門,也永遠無法真正抹去。
他轉身,慢慢走回寺中。身后,梅枝在風雪中搖曳,發出沙沙的聲響,像是誰在低聲傾訴,又像是歷史在輕輕嘆息。那段發生在陽谷縣的往事,如同這片飄落的雪花,終將消融在時間的長河里,只留下一抹淡淡的痕跡,和一曲關于愛、欲望、道德與宿命的,蕩氣回腸的悲劇挽歌。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