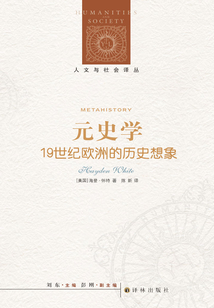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中譯本前言(1)
海登·懷特
《元史學》是西方人文科學中那個“結構主義”時代的著作,要是在今天,我就不會這么寫了。盡管如此,我還是認為本書對于更具綜合性的歷史著述理論有所貢獻,因為它認認真真地考慮了歷史編纂作為一種書面話語的地位,以及作為一門學科的狀況。隨著19世紀歷史學的科學化,歷史編纂中大多數常用的方法假定,史學研究已經消解了它們與修辭性和文學性作品之間千余年來的聯系。但是,就歷史寫作繼續以基于日常經驗的言說和寫作為首選媒介來傳達人們發現的過去而論,它仍然保留了修辭和文學的色彩。只要史學家繼續使用基于日常經驗的言說和寫作,他們對于過去現象的表現以及對這些現象所做的思考就仍然會是“文學性的”,即“詩性的”和“修辭性的”,其方式完全不同于任何公認的明顯是“科學的”話語。
我相信,對于歷史作品的研究,最有利的切入方式必須更加認真地看待其文學方面,這種認真程度超過了那含糊不清且理論化不足的“風格”觀念。那種被稱為比喻學的語言學、文學和符號學的理論分支被人們看成是修辭理論和話語的情節化,在其中,我們有一種手段能將過去事件的外延和內涵的含義這兩種維度聯系起來,藉此,歷史學家不僅賦予過去的事件以實在性,也賦予它們意義。話語的比喻理論源自維柯,后繼者有現代話語分析家,如肯尼斯·伯克、諾斯羅普·弗萊、巴爾特、佩雷爾曼、福柯、格雷馬斯以及其他人,它仍舊是我的史學思想的核心,是我對于史學與文學和科學話語的聯系,以及史學與神話、意識形態和科學的聯系這種思想的核心。我致力于把比喻當作一種工具來分析歷史話語的不同層面,諸如本體論和認識論層面、倫理和意識形態層面、美學和形式層面,正是這一點,使得我在如何區分事實和虛構、描述和敘事化、文本和情境、意識形態和科學等等方面與其他史學理論家不同。
比喻對想象性話語的理論性理解,涉及各種修辭(如隱喻、轉喻、提喻和反諷)生成想象以及生成種種想象之間相互聯系的所有方式。修辭生成的想象充當了實在的象征,它們只能被臆想,而不能直接感知。話語中(有關人物、事件和過程的)修辭之間的話語性聯系并非邏輯關系或與他者的演繹性繼承關系,而通常意義上是隱喻性的關系,即以凝練、換位、象征和修正這樣的詩學技巧為基礎。正因為如此,任何忽視了比喻性維度而對特定歷史話語所做的評價都必定無法理解:盡管該話語可能包含了錯誤信息并存在可能有損其論證的邏輯矛盾,它還能令過去“產生意義”。
特定歷史過程的特定歷史表現必須采用某種敘事化形式,這一傳統觀念表明,歷史編纂包含了一種不可回避的詩學——修辭學的成分。既然沒有哪個被理解為一組或一系列離散事件的集合實際上能夠描述成具有故事的結構,我便采納了這樣一種方式,由此,一組事件的敘事化將更具比喻性而非邏輯性。一組事件轉換成一個系列,系列又轉換成序列,序列轉換成編年史,編年史轉換成敘事作品,我認為,這些行為理解成比喻性的而非邏輯—演繹性的會更有益。此外,我把事件構成的故事和可能用來解釋這些事件的任何形式論證之間的關系,當作是由邏輯—演繹和比喻—修辭的要素構成的組合。這樣,一方面是歷史話語和科學話語之間的差異,另一方面是歷史作品與文學作品之間的類同,對于歷史話語研究而言,如果它們不再強求,比喻的方法看上去尤其是正當的。
我一直感興趣的問題是,修辭性語言如何能夠用來為不再能感知到的對象創造出意象,賦予它們某種“實在”的氛圍,并以這種方式使它們易于受特定史學家為分析它們而選擇的解釋和闡釋技巧的影響。這樣,馬克思在1848年巴黎起義期間對法國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描述為工人們運用辯證唯物主義進行分析做了準備,他正是用這種分析解釋他們在隨后事件中的行為。這種在最初的描述和馬克思的話語中緊隨而來的解釋之間獲得的一致性是形式上的,而不是邏輯上的。它并不是給“真實的不一致性”戴上了“虛假的一致性”的面具,而是諸種事件的敘事化,這種敘事化展示了時間進程中事件群的變化和它們彼此之間關系的轉變。人們不可能將一種實在的事件序列描述得表現出“喜劇”意義,除非把相關的行為者和事件過程描繪成那些能夠看作是“喜劇”類型的現象。不同表現層次彼此類比相連而獲得的話語的一致性完全不同于邏輯上的一致性,在后者中,一個層次被認為是能夠從另一個層次演繹而來的。近來人們想要提出一種有關歷史因果的融貫學說的努力失敗了,這說明科學化的“法則式演繹”范式作為一種歷史解釋工具是不完備的。
我認為,史學家尤其想通過將一系列歷史事件表現得具有敘事過程的形式和實質,以此對它們進行解釋。他們或許會用一種形式論證來彌補這種表現,該論證認為邏輯一致性可以充當其合理性的表征和標示。但是,正如存在諸多不同的表現模式一樣,合理性也有諸多不同的種類。福樓拜在《情感教育》中對1848年事件的描述很少有“非理性的”,即便其中有許多“假想的”和大量“虛構的”東西。福樓拜以嘗試形成一種無法區分對(真實的或想象的)事件的“解釋”與“描述”的表現風格而聞名。我認為,從希羅多德和修昔底德,歷經李維和塔西佗,下至蘭克、米什萊、托克維爾和布克哈特,偉大的敘事史學家往往的確是如此。在此,我們必須像米歇爾·福柯所說的那樣來理解“風格”:它是某種穩定的語言使用方式,人們用它表現世界,也用它賦予世界意義。
意義的真實與真實的意義并不是同一回事。用尼采的話說,人們可以想象對一系列過往事件完全真實的記述,而其中依然不包含一絲一毫對于這些事件的特定的歷史性理解。歷史編纂為有關過去的純粹的事實性記述增添了一些東西。所增添的或許是一種有關事件為何如此發生的偽科學化解釋,但西方史學公認的經典作品往往還增添了別的東西,我認為那就是“文學性”,對此,近代小說大師比有關社會的偽科學家提供了更好的典范。
我在《元史學》中想說明的是,鑒于語言提供了多種多樣建構對象并將對象定型成某種想象或概念的方式,史學家便可以在諸種比喻形態中進行選擇,用它們將一系列事件情節化以顯示其不同的意義。這里面并沒有任何決定論的因素。修辭模式和解釋模式或許是有限的,但它們在特定話語中的組合卻是無限的。這是因為語言自身沒有提供任何標準,以區別“恰當的”(或者字面的)和“不恰當的”(或修辭的)語言用法。任何語言的詞匯、語法和句法都并未遵循清晰的規則來區分某種特定言說的外延和內涵層面。詩人們了解這一點,他們通過運用這種模糊性使作品獲得了特殊的啟示性效果。歷史實在的敘事大師們也是如此。傳統的史學大師們同樣知道這一點,但到19世紀時,歷史學越來越被一種追求明晰性、字面意義和純粹邏輯上的一致性的不可實現的理想所束縛,情況就不一樣了。在我們自身的時代中,專業史學家沒能使歷史研究成為一門科學,這表明那種理想是不可能實現的。近來的“回歸敘事”表明,史學家們承認需要一種更多是“文學性”而非“科學性”的寫作來對歷史現象進行具體的歷史學處理。
這意味著回歸到隱喻、修辭和情節化,以之取代字面上的、概念化的和論證的規則,而充當一種恰當的史學話語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