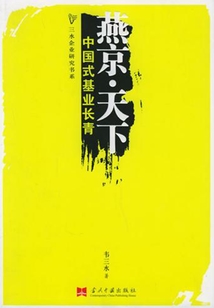最新章節
- 第40章 記
- 第39章 燕京啤酒成長挑戰的面相(7)
- 第38章 燕京啤酒成長挑戰的面相(6)
- 第37章 燕京啤酒成長挑戰的面相(5)
- 第36章 燕京啤酒成長挑戰的面相(4)
- 第35章 燕京啤酒成長挑戰的面相(3)
第1章 推薦序 手把啤酒問青天:誰是當今英雄?(1)
陳玉明《商海觀戰》一書著者,現為《第一財經日報》北京分社社長。
后上班的第一天,接到報社的指示,派我到即將創刊的《第一財經日報》北京分社主管采編工作。韋三水是我在《第一財經日報》認識的除總編輯秦朔之外的第一個人。作為《第一財經日報》北京記者站的站長,報紙創刊之初,暫棲在《北京青年報》十樓一間大辦公室的“一財”北京記者站的五六十位記者,大都是經三水面試招聘進來的。至今,他們對北青報良好的午餐,仍然十分懷戀。
跟三水的初次見面是短暫的,因為下面還有四位部門主任,我也要分別認識一下。時間不長的會面,三水留給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話是:傳媒是個江湖,記者就是劍客,劍客要在江湖上立足,首先得有一手好劍法,就是要有一支過硬的筆。當時聽了三水的話,我立刻想起了小時候閑看過的《神童集》里“別人懷寶劍,我有筆如刀”的句子。三水給我的第一印象,就是這樣:簡單、爽快、不復雜,可愛而又可怕。這都緣于他把傳媒當作江湖。因為十幾年做下來,我知道,在中國,傳媒,可不是江湖?
夜深人靜,熒光拂面,看著三水的書稿,我仿佛又回到了這些年來所經歷過的與燕京以及國內其他啤酒企業的一幕一幕。這種回憶,對我來說,是美好的,當然其中也有一些遺憾。在中國啤酒業,有三個人——李福成、陳世增、彭作義,是我所認識的三位具有某種英雄氣概的人物。英雄氣概與個人魅力是密不可分的。而這種英雄氣概和個人魅力,不光對于屬下,對于外面寫文章的人來說,也是太寶貴了,至少對我是這樣。
我跟李福成認識是在1994年7月。那是我做了三年半記者的時候,因為燕京啤酒的一次價格調整,我專門去京郊順義的燕京啤酒廠采訪,由此開始了我跟李福成及燕京人長達十余年的交情。作為一名既無理論基礎也無實戰經驗的經濟記者,李福成,后來被我尊為學習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三位老師之一。按照時間順序,我的第一位老師是秦全躍,第二位是李福成,第三位是張瑞敏。
跟陳世增認識是在1995年7月,是在我的《天上的豪門地上的燕京》一文見報后,應陳世增之約,專程去了趟位于河北省玉田縣的豪門啤酒廠。此前,我在北京曾經采訪過豪門集團一位姓王的副總。玉田之行后不久,豪門啤酒便跟法國人合了資,我與“下課”了的陳世增也失去了聯系。直到2000年下半年的一天,我突然收到陳世增的秘書、也是當初接我到豪門去的人,發到《北京青年報》來的一頁傳真,說陳總正在河北做一個叫做“國人”的啤酒,希望有時間的話,老朋友見面聊一聊。因我當時剛剛接手主編報社的家電周刊,正忙于實現我兩年之內采訪100個家電老總的計劃,對陳總之約,竟言諾而行未果。到2003年初,報社改革,搞編采分離,我到了特稿部,時間上寬裕下來,前事不忘,就給陳總的秘書打了個電話,說有時間再約陳總聊聊。但也是延宕至今。
10年不見,不知“陳老爺子”安否?
跟彭作義認識是在1998年5月,由《經濟日報》在青島組織召開的《青島啤酒大名牌發展戰略研討會》上。正是那次會議,正式拉開了青島啤酒走下金字塔頂端,在山東乃至全國大肆兼并擴張的帷幕。會議期間,我認識了兩年前臨危受命的彭作義,但并無深談,因此我懷疑老彭是不是記住了我。同年7月,我又去了趟青島,希望約彭總專訪一次,不料為“小鬼兒”婉言擋駕了。從青島啤酒拿了些材料,又掃了一圈外圍,采訪了包括青島啤酒的前領導人等,并參觀了據說當時在國內設備最為先進的青島啤酒二廠之后,便打道回了京。人雖未見著,但我后來寫的《叫好的青島叫座的燕京》一文,老彭一定是看過了的,因為到2000年8月青啤進京從亞投手里收購了五星和三環,發布會后,聽記者同行說,簽約儀式上老彭有“以后誰也不能再說青島啤酒叫好不叫座了”的話。
這三個人物——李福成、陳世增、彭作義,我以為,都可堪稱當世中國之“經濟英雄”,如果我們不以成敗來論英雄的話。英雄的特征之一是心懷天下。陳世增當年不甘于做五星啤酒的聯營廠,因而力創自己的豪門品牌,并在中央電視臺廣告天下,是英雄也;彭作義在青島啤酒因固守高端導致市場不斷萎縮的危險時刻,毅然走下金字塔,并以并購做大市場,亦英雄也;而李福成,在20世紀90年代前期國內啤酒業合資風潮洶涌而來之際,面對來自各方面的壓力,最終保住了燕京啤酒的自主經營權,并在與各路來犯者一次次的較量中紅旗不倒,更是英雄也!1996年6月,本人《燕京啤酒為什么內不聯營外不合資》一文見報后,剛到北京市任常務副市長的金人慶讀后慨嘆:“現在還有這么有骨氣的漢子,我得會會他。”不久,便到燕京視察,并結識了李福成。——此為后來金對李在飯桌上所言,后來李又在飯桌上轉述于我。1997年5月,金人慶效法“上實”組織“北控”紅籌股赴港上市,燕京啤酒名列其首。
這三個人物,雖都堪稱英雄,但命運卻很不相同。彭作義在把青啤的并購戰車高速運轉起來、國內圈地四十余處之后,自己于2001年7月在青島海邊游泳時不幸意外身亡,年僅56歲,“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陳世增遺恨豪門之后,心有不甘,便率部另起爐灶,但始終未能東山再起,算來如今已是年屆七旬之身了,“自古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矣!只有燕京的李福成,今年剛剛51歲,且血壓血脂全不高,“弄潮兒向濤頭立,手把紅旗旗不濕”,成為今天中國啤酒業的某種象征性人物。
“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惜乎市場經濟,全以成敗論英雄!因而使很多本可以成為英雄的人物,因“寧為瓦全不為玉碎”而失去了名垂千古的機會。現代人,太重現世,而把青史看得越來越淡了。我們的市場越來越成熟,我們的商品越來越豐富,但我們的時代有點英雄氣概乃至能夠稱得上英雄的人物,卻越來越少了。新的時代,呼喚新的英雄。經濟時代,呼喚經濟英雄。一個只有明星沒有英雄的時代,是可悲的。一個物質富足但缺乏英雄氣概的民族,是沒有真正的競爭力的。“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全球化,也沒關系,但我們千萬不能在全球化中失去了自我,我們不能上“資本帝國主義”及其買辦走狗們的當。但我們不是堂吉訶德。其實,堂先生的錯誤只是手里拿錯了武器。如果他手里握的不是長矛,而是AK47,就對了。
我的兒子2005年9月1號開學上初二。暑假期間,他去英國參加一個英語夏令營,呆了兩個禮拜。回來后,兒子跟我說,他所在的那個活動小組,有一個日本男孩,也是中學生。結果,他們幾個中國學生,誰也不理那個日本男孩,交談時也不用英語,說中國話。可憐那個日本男孩,堅持了半個小時之后,拎起書包,走了,找老師去了。兒子跟我講到這段的時候,是很得意的。我說:你們這算什么本事,如果哪一天,這個日本男孩長大了,端著刺刀過來了,你們敢不敢也端著刺刀迎上去?顯然,這個問題太突然,也太殘酷了,我兒一時竟無以言對……2005年是抗戰勝利60周年,我寫此文的今晚是9月18日,既是中秋節,也是“9·18”。下午,家人和朋友去歌廳唱歌,三個小時的情呀愛呀之后,最后全體合唱“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回到家里,我兒做的第一件事,是打開電腦,從網上搜出這首歌,下載到他的歌庫里……
國事、家事、天下事,我也算事事關心了。
彭作義不幸遇難后,李福成發去了唁電,乃惺惺相惜也。當初老彭的大肆并購擴張,曾經給燕京帶來了挑戰和危機感,也給李福成帶來了思考和啟發。彭作義之后的青啤,回歸了理性,但也湮沒了彭作義時代的英雄氣概。記得2000年底,青啤進京宣戰,我等還到燕京給李總獻計獻策。今年年初,青啤又有人進京叫板,領軍八百,號稱三千,但我已經沒有過問的興趣了。沒有了“彭大將軍”的戰事,寫出文章來都不精彩。但老彭撒手青啤,對于青島啤酒自身的發展來說,其實未必是件壞事,它使這輛已經快跑散架了的戰車減速下來,得以必要的休整和加固。但這種撒手的方式,也是太過突然、太過殘酷了。老彭剛去世的時候,電視臺要做一期啤酒的節目,有人找我,讓我也去說說,我謝絕了,因為面對剛剛故去的人,我不能表達我內心真實的想法。
老彭去世的第二年即2002年,旗下擁有百威啤酒的美國AB公司持有青島啤酒H股的股份,由10年前最初的4.5%,簽約將逐步增加到27%,僅次于青島市國有股的30.6%,成為青島啤酒的第二大股東。只有傻×才會相信,講究“贏家通吃”的美國人會信守承諾就此罷手。實際上,AB公司1993年利用青島啤酒在港上市之機謀取青島啤酒4.5%的股份之前,就與青啤有過控股合資的談判,但因種種原因未能如愿。此后至今,AB公司之于青島啤酒的所有動作,仨字以蔽之,“徐圖之”而已。所以,“SINCE 1903”的青島啤酒,江山易主,恐怕是早晚的事。英雄已歸彭作義,我們只等著看青島啤酒最后的“狗熊”是誰了;豈止是“狗熊”,業內人士都知道,應該說是“罪人”才對。
20世紀90年代初,國家輕工總會一位主要領導曾題詞曰:“中國民族啤酒業,北有青島,南有珠江,首都有燕京。”僅僅十來年的工夫,這樣的題詞已經掛不出來了。在中國啤酒業的新版三國演義中,來自香港的華潤啤酒,有點像是一只披著“洋”皮的狼,也是屬于拿錢說話的那一類。但錢在中國,不是說了全算。進入啤酒業十余年,至今沒有一個全國性的核心品牌,使華潤啤酒(公司)即使大,也不會強。豈不聞,張瑞敏有言:資本是船,名牌是帆;“有船無帆,行之不遠。”——后邊這兩句,是我根據老師的意思演繹出來的。
作為中國民族啤酒業的旗艦,燕京,可謂任重而道遠。自1980年創業以來,燕京啤酒戰京城、征全國,驅狼趕虎,所向披靡,特別是令洋啤們打不垮又吞不下,真是恨得牙根發癢。但對燕京啤酒真正的考驗,我以為,當在美國AB公司掌控了青島啤酒的經營權之后,也許十年,也許二十年。美國的歷史沒我們長,但美國人比我們有耐心。百威在美國,跟燕京在中國一樣,也是屬于大眾品牌,只是到了中國,身價高了許多,有點像是“北京的白菜到了浙江”的意思。作為大眾品牌的百威,跟那些德國或是歐洲某個小國的啤酒品牌不同的是,它有大市場的運作經驗,將來如果再有青島啤酒“為虎作倀”,給中國啤酒業來個“里應外合”,中國民族啤酒業的生死存亡,那時候就到了決戰的時刻。所以,燕京啤酒現在得居安思危,加緊排兵布陣,在品牌和地盤、無形和有形兩個方面,盡快做強、做大。燕京紅旗不倒,我等“以筆為刀”的朋友,才能笑傲江湖,當然也包括我的同事加兄弟——韋三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