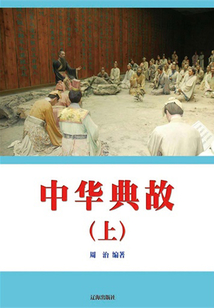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 2評論第1章 安邦治國故事(1)
安居樂業
“安居樂業”用來比喻居有定所、樂于工作的社會安樂藍圖。
此典出自《老子》第八十章:“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又見《漢書·貨殖傳》:“各安其居而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
老子生活在由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的大動蕩、大戰亂的時代。當時,階級斗爭非常激烈,人民不滿意自己的“食”、“服”、“居”、“俗”,不“重死”,敢于犯上作亂,暴動起義,因而就產生了頻繁的戰爭。
針對這種狀況,老子提出了他的理想:
建立一個國小人少的社會。這個社會不要提高物質生活,不要發展文化生活,人民無欲無知,滿足于樸素、簡單的生活條件和環境,讓人民感覺到他們的飲食香甜,衣服美好,住宅安適,生活滿足。
老子的這種理想是復古倒退的,但他的意圖是反對奴隸制,反對一個階級剝削壓迫另一個階級。這一點,有其積極意義的一面。
撥亂反正
“撥亂反正”用以比喻治平亂世,回復正常,將國家政事導入正軌。
此典出自《漢書·禮樂志》:“漢興,撥亂反正,日不暇給。猶命叔孫通制禮儀,以正君臣之位。”
在我國的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中,奴隸主和封建統治階級及其文人,為了鞏固其等級制度和宗法關系而制定了一些禮法條規和道德標準,稱作禮或禮教。統治階級對于禮是非常重視的。儒家從孔子開始就提倡禮治,要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等各級統治者都安分守己,遵守禮制,不得僭越,以便于鞏固統治階級內部而更有效地統治人民。《論語·憲問》中有“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同時也要求對人民“齊之以禮”,《荀子·修身》中有“故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之說。
秦末漢初,由于大規模的農民戰爭,有些禮教受到了很大的沖擊。漢朝建立以后,統治階級為了鞏固其統治,就派人重修禮儀,以正君臣之位,《漢書》將其作為撥亂反正的措施之一。
百廢俱興
這個典故用以比喻在遭受某種破壞之后,建設事業重新振興蓬勃發展的景象。
此典出自宋代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岳陽樓記》:“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俱興。”
《岳陽樓記》是北宋時的政治家和文學家范仲淹為岳陽樓的重修寫的一篇文章。
岳陽樓,在湖南省岳陽縣城西面,面臨著洞庭湖,是唐朝初年修建的。宋仁宗(趙禎)慶歷四年(公元1044年),范仲淹的朋友滕子京被貶到岳州(今湖南岳陽)做知州。到了第二年,政務做得非常突出,上下和諧,一切荒廢的事情都興辦了起來。于是重修岳陽樓,擴大了原來的規模,同時把唐朝名人和當時的名人的詩賦刻在上面。為此,范仲淹應滕子京的邀請,寫了這篇《岳陽樓記》。
半部《論語》治天下
這個典故形容以學識輔佐君王。“半部《論語》治天下”,也可省作“半部《論語》”。
此典出自宋代羅大經《鶴林玉露》乙編卷一:“太宗嘗以此語句問普,普略不隱,對曰:‘臣平生所知,誠不出此。普以其半輔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輔陛下致太平。’”
春秋時代的孔子有許多關于治國的論調。孔子的學生把他的言行整理記錄下來,成為儒家的經典著作,人們稱之為《論語》。
宋代趙普任宰相時,有人說他只讀過《論語》一部書。宋太宗(趙光義)把這些話告訴了趙普,并問他是不是這樣?趙普一點也不隱諱,坦誠地回答道:“我平生所學,確實沒有超出《論語》。從前,我以半部《論語》輔佐宋太祖(趙匡胤)打下天下,今天,我要以另半部《論語》輔佐陛下建立太平盛世。”
扁鵲見秦武王
這則寓言說明要“與知者謀之”,不要“與不知者敗之”,要按照科學規律辦事,依靠真知灼見,莫聽嘖聲煩言。除病與知政,都是同一個道理。
此典出自《戰國策·秦策》:“醫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
這段話意思是說:名醫扁鵲朝見秦武王,武王聲稱自己有些什么病,扁鵲看后表示要給武王醫治。
左右近臣們說:“君王的病是在耳朵的前面,眼睛的下面,要醫治它不一定能徹底治愈,反之會把耳朵搞聾,眼睛搞瞎。”
武王把這些話告訴了扁鵲。
扁鵲一聽大怒,立刻扔掉了手中的石針道:“君王和知道病理的人商量治病的事,卻又和不懂醫道的人一同敗壞它。
如果像這樣去管理秦國的政治的話,那么秦國很快就要亡國了!”
澶淵之盟
澶淵,又名澶州,即今河南濮陽。公元1004年,北宋與遼國在澶淵簽訂和約,史稱“澶淵之盟”。后以“澶淵之盟”比喻簽訂和約。
北宋大臣寇準(公元961~1023年),字仲平,在宋太宗時期任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宋真宗即位后,也非常信任他。
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遼國蕭太后與圣宗親自率領大軍南下,攻打宋朝疆域,直逼京都。參知政事欽若主張遷都南逃,蜀人陳堯叟建議真宗逃往成都。真宗征求寇準的意見,寇準說:“誰為陛下出這等主意,罪不容誅。如今陛下正當英勇之年,將相團結,如果陛下御駕親征,敵人一定聞風而逃。”于是,真宗親臨澶州(今河南濮陽)督戰。真宗把軍事委托給寇準處理,寇準指揮果斷,號令嚴明,士卒喜悅。遼國在戰事上沒有占到便宜,就派遣使者前來,要求訂立盟約,寇準不答應。
有人造謠說,寇準不想講和,是為了擁兵自重,謀取政治資本。在這種情況下,寇準迫于無奈,只好答應了。
由于宋真宗對戰爭早已厭倦了,急于講和。
他派大臣曹利用到遼軍談講和條件,答應每年朝貢給遼國銀兩,宋真宗向曹利用交底兒說:“每年朝貢給遼國的銀兩只要在百萬以下,都可以答應。”寇準把曹利用召到軍帳里向他交代說:“雖然皇帝作了交代,但是你談判時,答應每年輸送的銀兩不許超過三十萬。如果超過三十萬,我就殺了你。”曹利用來到遼國軍營,按寇準的條件和遼國談判,最終果然以三十萬銀兩的條件簽訂了盟約。
朝令暮改
“朝令暮改”的意思是說,早上發布的政令,晚上又改變了。人們用它比喻政令多變,反復無常。
此典出自《漢書·食貨志上》:“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吊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
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賦,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具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于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嘗責者矣。”
西漢時期,有個人叫晁錯(公元前200年~前154年),潁川人。他聰明好學,學識淵博,被稱為“智囊”。文帝非常信任他,任他為太子家令。
文帝后期,官僚、地主、商人加重了對農民的剝削,廣大農民被迫逃亡,生活非常困苦。為了維護漢王朝的統治,晁錯上書漢文帝,主張打擊商人投機倒把的行為,限制官僚、地主對農民的剝削,提出注重糧食、發展農業生產的建議。這就是著名的《論貴粟疏》。
晁錯在《論貴粟疏》中寫道:“農夫一家平均五口人,其中應服徭役的壯男至少有兩人,一年里有幾個月不能在自己的田地上勞動。一家人齊心協力種田也超不過一百畝,收獲也超不過一百石。春耕、夏耘、秋獲、冬藏、采伐薪柴、給官府服徭役等等,一年到頭忙個不停。春天,不能躲避風塵;夏天,不能躲避炎熱;秋天,不能躲避陰雨;冬天,不能躲避嚴寒,一年四季,哪有喘息的機會呢?另外,還有其他的耗費,如送往迎來、吊死喪、問疾病、養育孤兒幼童也包括在內。他們不但勤苦至極,而且還要承受水災和急征賦稅的剝削。如此沉重的賦稅,不分時間地征收,而且變化無常,早上的規定,到了晚上又改變了。在這種情況下,農民有糧食的只好半價出賣,沒有糧食的只好借那種取一還二的高利貸。到頭來他們無可奈何,不得不賣掉田宅、子孫來還債。”
楚王好細腰
“楚王好細腰”這個故事勸誡人們,只依靠個人的好惡去提倡、宣揚某種事物,往往會造成意想不到的惡果。從下面的人來說,不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而是逢迎上面的好惡,一味盲從,也不會有好結果。
此典出自《墨子·兼愛中》:“昔者,楚靈王好士細腰。故靈王之臣,皆以一飯為節,脅息然后帶,扶墻然后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
這段話意思是說:
從前,楚靈王喜歡纖細的腰身。因此,朝中大臣,都害怕腰肥體胖,失去寵信,所以就不敢多吃飯,把“一日三餐”減為“只吃一餐”。每天起床穿衣服的時候,先要屏住呼吸,然后把腰帶束緊。就這樣時間長了,一個個餓得頭昏眼花,扶住墻壁才能站立起來。
一年之后,滿朝文武都成了面黃肌瘦的廢物了。
定于一尊
“定于一尊”指思想、學術、道德等以一個有最高權威的人做唯一的標準。
此典出自《史記·秦始皇本紀》:“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統一全國,稱為始皇帝。秦始皇統一全國以后,廢除了分封制,實行郡縣制,把全國分為三十六郡,郡下又設了縣。他還統一了法律、度量衡、貨幣和文字,修建馳道,實現車同軌、書同文。這些舉措,對鞏固秦王朝中央集權,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在歷史上是一大進步,但也遭到了一些守舊的讀書人的反對。
公元前213年,秦王朝又增加了四個郡。為了祝賀,在咸陽宮里開了個慶祝會。
大臣們都爭相向秦始皇敬酒,表示祝賀。大臣稱贊秦統一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是自古以來所有君王都沒干過的偉大事業。
這時,有位叫淳于越的儒生對秦始皇說:周王實行分封制,周朝享受了八百多年的天下。如今皇帝統一天下,但是自己的子弟和功臣連一塊土地都沒有,這是不行的。不論干什么,不把古人當老師最終都會失敗的。秦始皇見發生了爭吵,就征求其他大臣的意見。丞相李斯說:五帝的事業各不相同,三代的制度也不一樣,不能照搬照抄。以前列國散亂,諸侯混戰,一些讀書人假造圣賢,托古說教,以古否今。
如今天下統一,制度統一,舉國上下定于一尊,只要注意法令,勸導農民只要專心干活就行了。如果拿古書來對照新法,造謠生事,毀謗朝廷,國家還成何體統。為此,李斯建議,除了秦國的歷史和那些有用的書如醫藥、占卜、種樹、法令等外,其余的詩、書、百家言論,都要全部燒毀。
秦始皇聽從了李斯的建議,因此發生了歷史上著名的焚書坑儒事件。
多難興邦
“多難興邦”指國家歷經困難,反可促使上下團結奮斗,使國勢興盛起來。
此典出自《左傳·昭公四年》:“或多難以固其國,啟(開)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
春秋時,晉、楚兩國曾相互朝見。公元前538年,楚靈王派大臣椒舉到晉國去,希望借晉國的勢力讓其他諸侯擁護楚國。
晉平公想自己稱霸,害怕其他國家強大,所以他不想答應楚國的請求。晉國大臣司馬侯對晉平公說:晉、楚兩國的霸業只有靠上天的幫助,而不是可以彼此爭奪就能得到的,君王還是答應楚國的請求才好。晉平公說:晉國有三條可以免于危險,還有誰能和我們匹敵呢?
我們國家地勢險阻又多產馬匹,齊國、楚國又多禍難,有這三條,我們怎么會不成功呢?
司馬侯回答說:依仗著地勢險要和馬匹多而對鄰國幸災樂禍,這是三條危險。四岳、三涂、陽城、太室、荊山、中南,都是九州中的險要地帶,它們并不屬于一姓所有。冀州的北部,是出產馬的地方,并沒有新興的國家。憑借著地勢險要和馬匹多,是不能鞏固自己的,自古以來就是這樣。而往往是多有禍難而鞏固了國家,開辟了疆土;因為沒有禍難而喪失了國家,丟掉了疆土。
晉平公認為司馬侯的分析十分有道理,便答應了楚國的請求。
飛龍失乘
這則典故表明:慎到的政治思想是反對賢治,提倡法治,而主張勢治。
此典出自《慎子·內篇》:“飛龍乘云,騰蛇游霧,云罷霧霽,而龍蛇與、同矣——則失其所乘也。”
這段話意思是說:
飛龍駕云,騰蛇穿霧。等到云氣沒有了,霧也消失了,那些龍和蛇就和蚯蚓、螞蟻一樣不足道了——這是因為它們失掉了所賴以生存的條件。
分崩離析
“分崩離析”用來形容國家或團體四分五裂,不可收拾。
此典出自《論語·季氏》:“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春秋時期,孔子的學生冉求、季路在魯國大夫季孫氏手下任家臣。季孫氏為了擴大自己的統治權力,準備去攻打魯國的屬國顓臾。于是冉求、季路為此去請教孔子。
孔子說:“冉求,你知道顓臾是我們魯國生死存亡的藩屬,為什么要去攻打它呢?”冉求辯論道:“顓臾城池牢固,而且離季孫的封地費地非常近,如果現在不把它攻打下來,將來一定會給子孫后代留下禍害。”孔子很不高興地說:“我最討厭的是不說自己貪得無厭的人,卻一定要找借口去侵犯別人。我聽說過,無論是諸侯、大夫,‘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如果財富平均,便無所謂貧窮;境內和平團結,便不會覺得人少;境內平安,便不會傾危。”孔子又告誡冉求道:“像你們這樣做,其結果必然是:‘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于邦內。吾恐季氏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冉求、季路聽了孔子的這番話,紛紛點頭稱是。
各自為政
“各自為政”用來表示各人按自己的主張辦事,不顧全大局,也不與別人配合協作。
此典出自《左傳·宣公二年》:“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
公元前607年,鄭國侵犯宋國,宋文公任命大夫華元為主帥率領宋軍進行應戰。開戰前,華元為了鼓勵將士,殺羊進行慰勞,并親自分賞。沒想到卻忘記了賞給為他駕車的車夫羊斟。為此,羊斟懷恨在心。
等到戰斗開始,羊斟對華元說:“前日賞羊的時候是由你做主,想分給誰就分給誰;今天駕車就由我做主,想把車駕往何處就去何處。”說完,羊斟駕著馬車長驅直入鄭軍的陣地。于是鄭軍就把他們團團圍住,華元寡不敵眾,只好乖乖地當了俘虜。
宋文公得知華元被俘,非常惋惜,就用100百輛兵車、400匹馬作為禮物,向鄭軍贖回華元。可是禮物送去一半,華元已經逃回了宋國。結果送去的禮物白白地浪費了。
華元回到宋國后,見到了羊斟。華元問道:“是不是那匹駕車的馬使我當了俘虜?”
羊斟回答說:“不是馬,是趕馬的人。”
由于華元在宋國深受宋文公的寵愛,羊斟怕遭到陷害,就逃亡到魯國去了。
更令明號
“更令明號”用來說明賢明君主應重新申明號令,以取信于民。
此典出自《韓非子·外儲說左上》:“更令明號而信之。”
楚厲王為了在有緊急事情時以便動員百姓行動,便設警鼓。只要國家有了緊急情況需要百姓行動時,便以擊鼓為號。一次,楚厲王喝醉了酒便擊起鼓來,頓時全城百姓大驚。左右的人急忙告訴楚王說:“千萬不能亂擊警鼓,否則就會造成混亂,失信于民。”可是楚王毫不在乎地說:“我喝醉了酒,擊擊鼓,不過是和大家開個玩笑罷了,這有何妨呢?”百姓知道事情的真相后,就各自回家去了。
幾個月后,真的有警報了,楚厲王大擊其鼓,可是百姓楚厲王在開玩笑,一個也沒有來。楚厲王所設的警鼓已失信于民,不能號令百姓行動,因此只得“更令明號而信之”。
廣開言路
“廣開言路”這句成語常用來指盡量創造使人們發表意見的機會。
此典出自《后漢書·來歷傳》:“朝廷廣開言事之路,故且一切假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