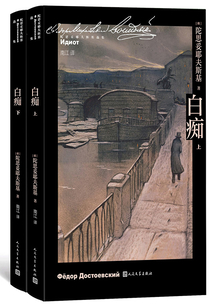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譯本序
屠格涅夫在談到一個真正藝術家的特點時,有一段相當精辟的論述:“在文學天才身上……而且,我還認為,在一切天才身上,重要的是我敢于稱之為自己的聲音的東西。是的,重要的是自己的聲音,重要的是生動的、獨特的、自己個人的音調,這些音調在其他任何人的喉嚨里是發不出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就是這樣一個文學天才,他以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窮人》為開端,唱出了“自己的聲音”,發出了“生動的、獨特的、自己個人的音調”,在俄國文學史上贏得了特殊的地位。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作中,卓越的才能和巨大的藝術表現力,廣泛而重大的社會問題和倫理問題,忠實于生活的執著態度,保守落后的觀點,這一切都錯綜復雜地交織成一個整體,構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特殊復雜性和矛盾性。
果戈理的“自然派”孕育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繼普希金的《驛站長》之后,從《外套》到《窮人》等,在思想上一脈相承,這些作品剖析了社會弊端,表現了“小人物”的悲慘生活,保護了被欺凌與被侮辱者。在俄國現實主義發展的道路上,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其鮮明的創作個性豐富了俄國文學。這種鮮明的創作個性,不僅表現在作家對資本主義金錢勢力的抗議、對大城市的貧民窟和黑暗角落里陰暗生活的揭露、對人物的心理狀態的細膩刻畫等方面,而且也表現在他對現實主義的理解不同于其他俄國作家(如岡察洛夫、屠格涅夫、列夫·托爾斯泰等)。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終強調自己創作的現實主義性質,他不同意當時批評界對他的意見:“人們稱我為心理學家,不對,我只是最高意義上的現實主義者,即刻畫人心深處的全部奧秘。”作家在一八六八年十二月給俄國詩人阿·尼·邁科夫的信中,更進一步指出了他對于現實主義的獨特見解:“我對現實和現實主義的理解與我們的現實主義作家和批評家完全不同。我的理想主義比他們的現實主義更為現實。天哪!講清楚我們大家,我們俄國人,在近十年來我國思想發展過程中的體驗,這難道不會引起現實主義作家的大喊大叫,說這是虛幻嗎!可是這卻是本來的真正的現實主義!”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這些論述,不應當望文生義地簡單理解為他企圖超越時空,擺脫現實主義,否定創作的真實性原則。縱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創作,他的“最高意義上的現實主義”,“比現實主義更為現實”的理想主義,實際上就是強調他在不斷探索形象地概括現實的途徑時,極力要使作品遵循自己的創作思想原則,表達自己的審美要求,滲入自己的世界觀。在這方面,《白癡》堪稱范本,這部作品特別有力地將對客觀現實的真實描繪同強烈的主觀意識融匯在一起,它是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獲得世界聲譽的最優秀的作品之一。
《白癡》寫成于一八六八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成熟期的作品。青年時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經受到果戈理和別林斯基的積極影響,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空想社會主義的傳播,又在他的思想發展過程中留下過痕跡,他憎恨專制農奴制度,不過這種憎恨并沒有上升到先進的革命思想的水平。一八四九年開始的連續九年的流放、苦役生活結束以后,作家又回到社會生活和文學生活中來。苦役和流放雖然擴大了他的社會視野,使他接觸了社會底層生活,了解到人民的疾苦,深化了對人生哲理的思考,但是,俄國反動勢力的猖獗,西歐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失敗,以及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思想的破產,激化了他的精神悲劇。反映在繼《窮人》之后的早期作品中的矛盾,這時變得更為尖銳,更為深刻了,思想上的矛盾使他表現為既是一個政治上的保守主義者,同時又憎恨組成反動陣營的統治階級。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作品中,《白癡》就其創作思想的矛盾而言是極為突出的。作家企圖在作品中真實地反映廢除農奴制前后俄國“近十年來……思想發展過程中的體驗”、社會生活中的問題、人們的心理狀態、精神面貌和道德表現。構成作品特點的,一方面是小說中眾多的鮮明形象、曲折離奇的情節、入木三分的深刻心理分析;而另一方面則是作家世界觀中的矛盾所產生的人道主義的意圖同敵視革命思想的虛偽的反動觀點的沖突。作家認為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是一個過渡的、動蕩不安的時代,金錢勢力日益增長,具有毀滅一切的性質;它支配著人與人間的關系,決定他們的道德觀念和命運;它取代一切人性,造成社會的分裂。作家認為這些現象具有極大的普遍性。長篇小說中所有的主要人物都不滿意自己周圍的畸形生活,都表現得心緒不寧,有的人還呈現出某種歇斯底里癥狀,惶惶然不可終日。因此,在這部小說中,以俄國社會問題為基礎的道德問題和心理問題,比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其他作品(如《被欺凌與被侮辱的》《罪與罰》等)中,更有力地吸引了作家的注意。同時,按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理解,農奴制廢除以后,俄國進入了歷史性危機時期,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而來的是資產階級的小市民理想的勝利——道德感的衰落和淪喪,個性的墮落和退化,美被褻瀆和毀滅,便是這種小市民理想獲得勝利的標志。作家廣泛真實地反映了這一切,然而他不是從支配人們行為的社會動機來考慮人們的一切沖突、斗爭和悲劇性的命運,反而無視社會的制約,將這一切歸結為所謂美德與自私、善與惡在人物內心的斗爭。
《白癡》的男主人公梅什金公爵,是寄寓作家理想的一個基督式的人物。作家在創作筆記里曾寫道,梅什金公爵是基督。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稱之為“比現實主義更為現實”的理想主義的一個典型。小說的情節就是圍繞梅什金和羅戈任同納斯塔霞·菲利波夫娜的關系展開的,雖然推動情節發展的不是梅什金,但是各種情節線索都匯合到他身上,使他居于幾乎介入一切生活沖突的重要地位。作家塑造這個再世基督的“圣潔”形象,本意是要端出一個“在道德上與精神上達到完全均衡的人物典型”(薩爾蒂科夫—謝德林語),這個人物典型既能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對現實的真實描繪、對生活的看法、對理想的概念結合在一起,又能以此為榜樣把世界從矛盾和災難中拯救出來,指引人們去追求美好的未來。這當然是一個十分困難的任務,作家本人也充分意識到了這一點:“長篇小說(指《白癡》)的主要思想,是描繪一個絕對美好的人物,世界上再也沒有比這件事更難的了,特別是現在。所有的作家,不僅是俄國的,甚至是全歐洲的作家,如果誰想描繪絕對的美,總是感到無能為力。因為這是一個無比困難的任務。美是理想,而理想,無論是我們,還是文明的歐洲,都還遠未形成。”
《白癡》塑造正面的美好人物的創作實踐,對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來說,確實是失敗了。但就整個俄國文學的發展進程而言,陀思妥耶夫斯基則是作了一個言過其實的偏頗的論斷。一八六一年的農奴制改革以后,社會在呼喚新人,孕育新人,而十九世紀的許多優秀俄國作家,也一直在孜孜以求地解決現實生活提出的正面人物問題,俄國先進文學界在六十年代初期更把創造正面人物形象作為一項迫切的重要任務。車爾尼雪夫斯基用畢生的革命活動和創作實踐,對此作出了肯定的回答,《怎么辦?》中的新人,尤其是“特殊的人”拉赫梅托夫,就是六十年代平民革命家的美好理想的體現者。
梅什金公爵體現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關于“絕對美好的人物”的理想,但是,這個形象在小說中的發展,卻證明了作家“對于生活和生活中的各種現象有著某種過于天真的、表面的理解”(薩爾蒂科夫—謝德林語)。當然,這也只是一種溫和的批評意見而已。梅什金形象的客觀意義同作家的構思未能一致,主要還是由于作家的創作思想同他所揭示的現實現象的性質、特點相背離。小說一開頭,梅什金像一個遠離人寰的天外來客出現在讀者面前,接著便引來了各種事件,出現了各種人物。公爵自幼父母雙亡,而且身患重癥,被送往瑞士治療。他是在遠離俄國的異鄉成長起來的,是一個在肉體上和精神上都有缺陷的人。他不諳世事,也沒有受過高深的教育,在社交場合不善應酬,遠遠脫離自己出身的貴族階級,完全不了解這個社會的階級的本質,“在發育、心靈、性格,也許甚至在智慧方面”,“完全是一個孩子”。他雖然給人以“白癡”的印象,卻有一顆仁愛之心,純凈無瑕,樂于助人。他曾生活在孤苦伶仃之中,根據自己的痛苦體驗,深知受人唾棄與欺凌的苦澀,因此對于人們(不論他們的貧富)的不幸一律表示同情。這是一個具有堂吉訶德色彩、對于生活的理解帶有某種抽象性的形象。他總是想用感化的手段來改變罪惡的生活,挽救那些墮入邪惡和非正義深淵中的人們,結果連自己在精神上也被吞噬了。面對俄國舊制度的崩潰和資本主義的發展,梅什金公爵要同卑鄙丑惡的現實生活抗爭,是完全無能為力的,他只能宣傳順從、寬恕、不用暴力抵抗邪惡等理論,既不能使人信服,也不能改變任何社會現象。
愛情能考驗一個人的精神價值,梅什金公爵并沒有經受住這種考驗。在納斯塔霞·菲利波夫娜眼里,公爵是道德純潔的象征,同他結合只會玷污他,不會給他帶來幸福,因此她極力促成公爵同阿格拉婭的婚姻。納斯塔霞·菲利波夫娜這種痛苦、復雜、矛盾的感情,梅什金是不能理解的。他只是以基督教的憐恤式的同情、兄弟友愛關系和禁欲原則來回答納斯塔霞·菲利波夫娜和阿格拉婭的塵世的愛慕之情。的確,梅什金善良,溫柔,坦白,可是僅此而已。他并不是生活的旁觀者,總是介入生活中的各種沖突;但結果不僅沒有改善人們的處境,反而使本來已經十分復雜的沖突更加尖銳了。他力圖在尖銳的沖突中找到一條和解的道路,現實的答復卻嚴酷地違拗他的初衷:他曾主動向羅戈任解釋自己同納斯塔霞·菲利波夫娜的關系,以消除羅戈任的敵意,但等待他的卻是后者手中匕首的寒光;羅戈任殺死了納斯塔霞·菲利波夫娜,梅什金陷入恐怖之中,但主宰著他的仍是忍耐和順從。在同羅戈任的較量中,梅什金是徹底的失敗者,他的道德理想在羅戈任的私有觀念沖擊下完全崩潰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通過梅什金公爵與道德淪喪、人欲橫流的資本主義世界的鮮明對比,創造了一個充滿矛盾的形象。這個精神分裂、不懂社會斗爭和社會利益的“基督”,只不過是一個無濟于事的濟世標本而已。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塑造他的美好理想的體現者梅什金公爵形象方面雖然失敗了,但在表現生活真實、不違背生活發展的邏輯方面,他卻是誠實的,而且表現出對生活的敏銳的洞察力。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構思《白癡》的時候,曾談到作品的整個構思“體現在主人公身上……除了男主人公,還有一個女主人公,因而是兩個主人公!!”這個女主人公就是納斯塔霞·菲利波夫娜,這是作家著力塑造的一個最動人的中心人物形象。
納斯塔霞·菲利波夫娜的悲劇是《白癡》的真正的核心和情節的基礎,作品中各種事件的開展,對各種不同的人物及其心理狀態的剖析,對各色人等的復雜關系的揭露,尖銳、緊張和深刻的戲劇性場面的出現,都是圍繞著她進行的。這是一個貌似天仙、嫵媚動人的女性,是美的象征,具有高尚的稟賦和獨立精神。可是在貪婪的財欲必然孳生無恥的情欲的社會里,美被踐踏和褻瀆了。美貌出眾的納斯塔霞·菲利波夫娜在十六歲時便成了貴族地主托茨基丑惡情欲的犧牲品,從此揭開了她悲劇性命運的序幕,隨后她又成了“傾倒者們”進行無恥交易的工具。在爾虞我詐、勾心斗角等等丑惡現象比比皆是的社會里,她充分意識到自己在許多方面都比周圍的人優越,相信自己的靈魂是純潔的。然而,被欺凌與被侮辱的身世又造成了她的畸形心理狀態和永遠不能擺脫的自卑感。她生活在各種陰謀的中心,既表現出自暴自棄、玩世不恭的態度,又對貴族資產階級社會的上層分子以及支配這個社會的法則提出了抗議,她態度傲慢,視錢財如糞土,竭力維護人的尊嚴。這是一個有血有肉的豐滿形象。她以傲慢作為抵御無賴和鄙俗的自衛手段,卻孤立無援;她靈魂深處對生活、對人、對自己的種種合乎人情的要求,是注定得不到滿足的。精神上的創傷一直壓抑著她的心靈,像夢魘一樣使她窒息,同時她又憧憬著一種新的生活,渴望復仇。她把十萬盧布付之一炬,這是她在可能的范圍內對金元王國的大膽挑戰和盡情報復。她取得了精神上的勝利,但并未獲得心靈深處的寧靜;舊仇宿怨在那被世人奉為至寶的十萬盧布燃起的熊熊烈焰中得到了發泄,但內心的創傷卻并未因此平復。不過,這一近似瘋狂的行動還是無情地懲罰了加尼亞——在他身上,貪財的欲念取代了愛情;同時也尖刻地揶揄了羅戈任的銅臭熏天的丑惡靈魂——對女人的占有欲取代了他對金錢的占有欲。在納斯塔霞·菲利波夫娜所處的罪惡環境中,梅什金公爵是惟一珍惜她的美、懂得她的美的價值的人,因此她認為公爵是“一個真正忠實的人”。在納斯塔霞·菲利波夫娜舉行的招待晚會上,羅戈任以重金收買她的美色,女主人公眼看要被推入危險的深淵。公爵真摯地同情她的不幸遭遇,為了幫助她擺脫厄運,便以救世主的姿態向她求婚。納斯塔霞·菲利波夫娜雖然自認為完全配得上他,但傲慢和自卑卻使她欲愛不能。盡管托茨基當年毀掉了她,在她的心靈上留下了永遠不能愈合的創傷,但她現在卻不愿意昧著良心毀掉像孩子般純潔的梅什金;可是另一方面,她又認為梅什金對她的感情并不是真正的愛情,而只是為了撫慰她的靈魂而表現出來的一種憐恤和施舍,這就更加深了她的屈辱感。如果委身羅戈任,也就是屈從于金錢的淫威,則意味著道德淪喪和人格毀滅。她的這一番苦心既折磨著自己,也折磨著并不理解這番苦心的梅什金。她已是走投無路,進退維谷了,但她沒有屈服,她不惜以毀掉自己作為代價,對這個社會的虛偽與權勢投以最后的蔑視,她面對托茨基、葉潘欽等卑鄙而偽善的一群,挑戰似的宣布:“羅戈任,開步走!再見,公爵,我還是第一次看到一個真正的人!……”
納斯塔霞·菲利波夫娜所象征的美,在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度下毀滅了,但她的抗議精神卻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毀了她的是偽君子托茨基和手執屠刀的羅戈任,但是心地善良的梅什金也不能辭其咎。他悲天憫人,為敵對雙方的和解而奔走呼號,但他實際上并沒有幫助納斯塔霞·菲利波夫娜擺脫內心的屈辱和自卑,使她逐漸樹立自信心,在精神上獲得新生,在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徹底改變自己的命運。納斯塔霞·菲利波夫娜的抗爭,對當時俄國現實的丑惡作了淋漓盡致的揭露,這是有積極意義的,但她以一種近乎病態的憤世嫉俗作為抗爭的手段,畢竟不能動搖金錢勢力的根基,到頭來只能以失敗告終。
《白癡》描寫的是十九世紀中期的彼得堡,作品再現了俄國農奴制度廢除以后彼得堡的廣闊圖景,但作家不像他在以前的作品中那樣著重描寫下層社會及其各種人物;在《白癡》中登場的眾多角色,主要是貴族和官僚上層社會的代表,還有活躍在資本主義城市里的不同社會階層和從事不同職業的人物。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所有這些人物的全部活動和相互關系中,批判地描寫了統治階級,揭穿了資產階級私有制的種種罪惡;他抓住金錢勢力的本質,對資產階級表現出來的卑鄙、猥瑣、爾虞我詐、弱肉強食等各種特征,進行了無情的鞭撻。集中體現了這些特征的,就是農奴制廢除后支撐著貴族地主和官僚社會的托茨基們、羅戈任們、葉潘欽將軍一家和伊沃爾金一家等。
貴族地主托茨基是納斯塔霞·菲利波夫娜的保護人,在鑒賞女性美方面他是一個“精確無誤的行家”,并且善于適時地“享用”女性。女主人公生日晚會上的“沙龍游戲”,令人作嘔地暴露了這個衣冠楚楚的偽君子卑鄙丑惡的靈魂。雖然一個受了他的欺凌與侮辱的女性給了他報復性的一擊,曾把他置于十分狼狽的境地,然而托茨基深知,納斯塔霞·菲利波夫娜“在法律上”是抓不住他的把柄的,因而有恃無恐,“甚至認為可以重新利用這個女人”,繼續凌辱她。
羅戈任則是私有制黑暗勢力的化身。金元王國的全部毒菌已侵入了他的骨髓,主宰著他的靈魂。他語言粗俗,行為放肆。在他的心目中,金錢萬能,一切都會屈從于它的權勢。他想用十萬盧布的高價,像買一宗貨物一樣買下他垂涎已久的納斯塔霞·菲利波夫娜。可是羅戈任怎么也不能理解,美可以毀滅,可以玉碎,卻是重金莫贖的——納斯塔霞·菲利波夫娜就在他的身邊,但并不真正為他所有,他在嫉妒、惱怒和絕望中親手殺死了她。
在俄國貴族資產階級社會中,葉潘欽將軍一家很有典型性。這是一個“人丁興旺”的家庭,然而,徒有其表的美滿幸福并不能掩蓋它的空虛無聊和家庭成員之間的互相欺騙。將軍不是名門之后,但因善于鉆營,投靠權貴,所以出現在讀者面前時已是一個體面殷實的富翁了。他同妻子伊麗莎白·普羅科菲耶夫娜“一輩子都過得很和睦”,對她“言聽計從和百依百順”,但就是這樣一個丈夫,為了博得納斯塔霞·菲利波夫娜的垂青,竟在她的生日那天,“以自己的名義饋贈一串價值昂貴的絕妙的珍珠”,妄圖使她在嫁給加尼亞之后充當自己的情婦。在這個家庭中,與眾不同的是將軍的小女兒阿格拉婭。她“剛滿二十歲,完全是個美人,在社交界已相當引人注目”。阿格拉婭的性格似乎不乏真誠,但寄生性的閑逸生活造成了她的嬌生慣養和任性,她蔑視周圍的環境,曾對加尼亞懷有好感,也曾對公爵鐘情;但她沒有明確的生活目標,只能虛度年華。
與葉潘欽家庭不同,退役將軍伊沃爾金一家是個小市民家庭。伊沃爾金嗜酒如命,女兒瓦里婭是高利貸者的妻子,兒子加尼亞更加庸俗和卑鄙。這個家族日趨解體,傷風敗俗,勾心斗角,相互仇恨,同時又虛情假意地維護表面的尊嚴。
在這個由托茨基們、羅戈任們、葉潘欽們和伊沃爾金們組成的魑魅魍魎的世界里,出身貧苦的伊波利特只能注定夭折,他在絕望中說:“人們生來就是為了互相折磨。”苦悶、悲觀以至于仇恨,伴隨著他對于生活、幸福、正義的憧憬。這也是一個被欺凌與被侮辱者,他的內心同樣充滿對不合理的生活的抗議。小官吏列別杰夫在這個社會里扮演著小丑的角色,他逢迎權貴,同時又憎恨他們,詛咒資本主義這個充滿“罪惡和鐵路的時代”,在這個時代里,“財富是多了,但是力量卻少了;團結人類的思想沒有了;一切都變軟了,一切東西都是軟綿綿的,所有的人也都委靡不振!”他感受到了新的生活法則的獸性的本質,但并不理解正在俄國形成的資本主義秩序的相對進步性。在列別杰夫的這一指責里,可以聽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聲音。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寫完《白癡》后不久給俄國政論家尼·尼·斯特拉霍夫的信中說:“長篇小說中許多地方寫得匆忙,許多地方拖泥帶水,不很成功……”其原因何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同一封信中接著寫道,“我維護的不是長篇小說,而是我的思想”,原因就在這里。“我的思想”——這就是作家多次談到的創作意圖,即“描繪一個十全十美的人”。作家的社會理想的深度和內涵對于作品是具有決定意義的,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和創作道路又是一個極為深刻的悲劇。作家表現了被欺凌與被侮辱者的深重苦難和無限隱痛,同時又激烈地反對他們通過任何實際的斗爭擺脫這種處境以求得解放;他主張以宗教的方式解決社會問題,希冀用宗教的微弱燭光來照亮令人窒息的重重黑暗。陀思妥耶夫斯基關于“描繪一個十全十美的人”的創作思想,實際上是力圖通過梅什金公爵這個在與世隔絕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孤獨病態的靈魂,對重大的社會問題表明自己的見解。因此,作家不惜在《白癡》中的許多地方脫離了作品思想與藝術的自然發展,生硬地插入和補充了許多同作品的情節與主題無關的內容,添加了許多贅物,如反對革命民主主義者的社會觀,對所謂虛無主義者、社會主義者的評論,等等。這一切都使作品的藝術結構失之松散,使作品“拖泥帶水”,同時也損害了作品的形象體系:作品中曾經受到譴責的人物,后來被隨心所欲地美化為正人君子;原來曾激起人們憤怒的角色,爾后又毫無緣由地被戴上了高貴的花環。
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俄國的階級斗爭激化和各種思潮激烈交鋒的形勢下,梅什金公爵的形象帶有明顯的論戰性質,他的許多特征帶有很大的反動性,鋒芒指向革命民主主義者。革命民主主義者認為,美好的正面人物應是統一的、完整的,在生理和精神兩個方面都該得到和諧的發展,有崇高的社會理想,對生活滿懷信心,有克服困難的勇氣。在被稱為“生活教科書”的《怎么辦?》里,新人洛普霍夫、基爾薩諾夫、韋拉和“特殊的人”拉赫梅托夫等就是這樣的人。他們有明確的生活目的,志趣高尚,道德純潔,樂于助人,在需要放棄個人利益的時候,他們義無反顧,但并不認為這是自我犧牲。他們以唯物主義的觀點來論證善惡的根源,車爾尼雪夫斯基借助小市民俗物瑪麗亞·阿列克塞夫娜·羅查利斯卡雅的形象指出,世上沒有天生的壞人,人之所以變成他們那個樣子,完全取決于他們不得不生活在其中的社會環境。
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正面人物梅什金,卻是一個生理上和精神上都有嚴重缺陷的人,他似乎超然于塵世之上,不食人間煙火,不論在社會生活方面還是個人生活方面,都同樣地軟弱無能。逆來順受和忍辱含垢是梅什金公爵的生活信條;在他看來,受苦受難也是一種善行,他說:“譬如說拷打吧;它會使人受苦、受傷,也就是肉體上受到折磨,但這一切反而能分散你精神上的痛苦,你只須忍受那些創傷給你帶來的痛苦,直到死去。”
梅什金公爵在葉潘欽家客廳里的一席長談,對于說明作家后期的理想、他的哲學觀和社會觀,具有詮釋意義。梅什金以反對天主教、捍衛基督教“純潔性”的衛道士面目出現,執意把天主教和無神論、社會主義放在一起,肆意進行抨擊:“無神論!……起初是由于愚昧和聽信謊言,如今則是由于狂熱,由于憎恨教會和基督教!……社會主義也是天主教和天主教本質的產物!社會主義跟它的兄弟無神論一樣,是從絕望中產生的……不是憑基督、而是憑暴力來拯救人類!這也是一種憑借暴力獲得的自由,這也是一種憑借劍與血取得的統一!”梅什金把壓迫者奴役被壓迫者的暴力行為同被壓迫者擺脫奴役的暴力斗爭混為一談,斷言通向幸福的途徑不是革命,不是社會主義,而是傳播俄國斯拉夫派的理想——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通過梅什金公爵向革命民主主義者的挑戰,是他對車爾尼雪夫斯基《怎么辦?》的反駁。梅什金還運用作家反動的“根基論”,特別指出自己不會為那些“失去了根基的特殊階層”,即平民知識分子、革命民主主義者擔心,不會為他們辯護;他面對客廳里的顯貴們,向整個貴族階級痛心疾首地呼吁:“我們為什么要自行消亡,讓位給別人呢?只要我們成為先進者,我們也就會成為領導者。”藝術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這里完全以說教者的面目出現,他硬塞給梅什金的一些思想,顯然是主人公的智力所難以企及的。
《白癡》確實存在一些無可諱言的缺陷,但它依然是使陀思妥耶夫斯基蜚聲世界文壇的優秀作品之一,因為它不但廣泛地描繪了俄國當時的社會生活,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資本主義的罪惡,而且塑造了許多極為鮮明、具有豐富而深刻的心理活動的人物。因而,這部小說至今仍為各國讀者所欣賞,依然具有永不衰竭的藝術魅力。
童樹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