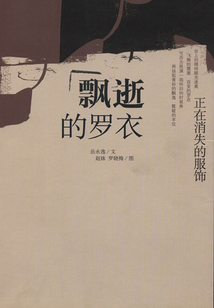最新章節(jié)
書友吧 2評論第1章 序言
一
盡管文學作品,宗教經(jīng)典仍在演繹傳遞著上帝造人的故事,但事實上從達爾文、斯賓塞等人之后,“人是猴子進化來的”幾乎成了人類基本的常識。其實,“人是猴子進化來的”這個被簡化了的經(jīng)典論斷既對又不對。原因很簡單,人確實是猴子進化而來的,因為至少在目前的生物種類中還有至少外觀上看來跟人類非常接近的猴子,說它不正確,問題也同樣在這里,已經(jīng)有不少人有點錯位地責問:既然人是由猴子進化而來的,為什么現(xiàn)在的尖嘴猴腮的那些東西們又還沒有進化成人?
現(xiàn)在的問題是,不管人是由上帝造的,還是由特定時期的猿進化來的,自從人這種東西產(chǎn)生了之后,不論是出于避寒的目的還是出于遮羞的目的,人類在不太長的時期內(nèi)就脫離了赤身裸體的本來面目,比較隨機地摘取自然界的萬事萬物裝點自己身體的每一部分,如花、草、樹皮樹葉、獸皮獸骨、石頭、貝殼等等。就象有毒癮的人一天也離不開鴉片和海洛因一樣,自從人身上有了遮蔽肉體的這些東西之后,除了洗澡和做愛,人類就再也沒有能夠脫離這些附屬物。隨著服飾的日趨多樣與繁復,人類的肉體本身對自然界的適應(yīng)也就越來越弱,所以現(xiàn)在要是聽見某人跑一百米只需要八、九秒,人們就會毫不遲疑地把奧運會的金牌之類的玩意兒掛在他脖子上。同樣,儒雅的現(xiàn)代人要是偶爾目睹有誰能赤身露體地輕松地穿梭于荊棘叢生、野獸密布的森林之中,或者能在喜瑪拉雅的冰山、在北極、南極的冰川自然地生活,都會艷羨不已。但孰不知,這些都是人類肉體曾經(jīng)有的本能。現(xiàn)代這些經(jīng)過狩獵經(jīng)濟、產(chǎn)食經(jīng)濟、商品經(jīng)濟文明化的人類,如果不借助于槍炮等代表文明的工具,在曾經(jīng)是人類與之交融在一起的自然界中,他們就會束手無策、坐以待斃。直到今天,魯賓遜仍然是被大多數(shù)人們推崇的,因為多數(shù)人已經(jīng)完全被文明異化,成為所謂文明的怪胎,與最初意義上的人越走越遠。
實際上,就是有了宗教、音樂、美術(shù)、銀制餐具、華美的衣履、蒸汽機、電、望遠鏡、指南針、小舟等促進人類前行,遠離大自然、殘害大自然的工具,但就像前不久依然挺立、讓世人矚目的紐約世貿(mào)大樓一樣,曾經(jīng)被世人傾心的泰坦尼克還是在它的處女航中,就在無聲地漂浮的冰川面前香隕玉碎、煙消地滅。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服飾作為一種客觀的存在和人類眾多創(chuàng)造物中的一類,它改變了人類的命運。同時,服飾作為人類歷史的一部分不但以其異彩裝點著人類的歷史,它也書寫著、記載著人類的歷史。道理很簡單,只要想想,如果沒有人類為自己加在身上的服飾,那些對于曲線胴體和健壯人體的寫真、素描等傳世之作,那些今天昂首挺立在大街小巷的照相館、美容院等等還有什么存在的依據(jù)和意義?
二
剛剛逝去的這一百多年,中國社會經(jīng)歷著巨大的轉(zhuǎn)型——真正的由農(nóng)業(yè)文明向工業(yè)文明的轉(zhuǎn)型,這是中國許多仁人志士差不多奮斗了一個半世紀的夢想。隨之帶來的是,那些與農(nóng)業(yè)文明風雨同舟,與刀耕火種相伴的,原始的、素樸的、結(jié)實的、笨拙的、粗糙的、手工的、費時的,也傳遞著深情厚誼的服飾地消亡與流失。是要順其自然地讓這些服飾成為農(nóng)業(yè)文明的殉葬品、工業(yè)文明的犧牲品、未來世界的嘲笑品,還是讓它們在后人心目中有一些“真切”的活的記憶?
農(nóng)業(yè)文明與工業(yè)文明雖然存在一種線性的進化關(guān)系,但作為人類社會的兩種文明形態(tài)并不存在現(xiàn)在人們經(jīng)常使用的“先進”、“落后”等“大詞”那種規(guī)約的屬性。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它們是兩種互補和并存的文明形態(tài)。否則,人類歷史就完全是一部“落后”、“野蠻”、“愚昧”的記錄,這樣也就會使“歷史”兩個字本身存在的合理性存在質(zhì)疑,并自然地顛覆。可是事實上,人類并不像那個經(jīng)典的比喻所說的那樣,在倒洗澡水時,也一同將嬰兒倒掉,而是常常很明智地把嬰兒留了下來。文明的類型不同,作為文明的衍生物,服飾就有相應(yīng)的表現(xiàn)。農(nóng)業(yè)文明的以手工為主的服飾雖然在形制上沒有工業(yè)文明服飾的多姿多彩、花里胡哨,但它所蘊集的“千層底”般的人與人之間的真情、親情、愛情、友情,對今天看來惡劣生存環(huán)境的正視、思考、適應(yīng),對浩博的大自然、不可知命運、飄渺的神靈的敬畏,對新生生命的百般呵護,對長者的祝福與祈禱,對美好、祥和生活的期盼等等,都是現(xiàn)代金碧輝煌的商城中玻璃櫥窗里,那些面無血色的、冷冰冰的,主要以價格的高低來衡量其好壞的華美服裝所沒有的。在這既被金錢凝聚,同時又被金錢不斷隔離的社會,尤其有必要為人們?nèi)諠u喪失的“情”譜寫一篇象樣的祭文。但這并不意味著對不得不日漸消失的服飾——在某種程度上代表、體現(xiàn)農(nóng)業(yè)文明的服飾——猶如隔江猶唱后庭花式的夜郎自大、孤芳自賞,也不意味著要像黛玉葬花那樣的顧影自憐、自卑自嘆與自戀。寫這些東西僅僅是想記憶下歷史一些細小的真實,因為這些服飾確實在人類生存的過程中曾經(jīng)出現(xiàn)過,也發(fā)揮了不同程度的作用,凝聚體現(xiàn)著曾經(jīng)享用它們的人們對具體日常生活的認真思考、正視、執(zhí)著與堅韌。
工業(yè)文明是一種革新的、迅速淘汰舊事物的文明。在工業(yè)社會出現(xiàn)的每一種事物,其生命與農(nóng)業(yè)社會中事物比起來都要短暫些。所以,在中國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后,服飾就像同時期的人一樣,特別浮躁,少有典雅、自信、閑適和一分舒坦。許多服飾就像流行音樂等文化快餐,人們?nèi)后w性的一哄而上吃了之后,再豪放地、毫不顧惜地也是痛痛快快地將它從嘴巴或者是從肛門吐掉、拉掉。這些你方唱罷我就登場的服飾,就像日本的首相——換得飛快。對它們的消失,就象春天的一分塵土與兩分流水,只能倍增人的傷感。
為此,盡我自己的所能,在自己的記憶中,在他人的記憶中去搜尋這些已經(jīng)消失或者正在消亡的服飾,從而給過去這一百年的歷史做一個小小的注腳,給后人一點感性的圖像和印跡,使歷史不再顯得那樣的空洞、蒼白、象天上的神一樣那樣遠離普通人的世俗生活。讓他們不要再像我們這樣,一旦說起歷史就是一些八輩子也打不著邊的帝王將相、土匪草寇流氓地痞的“私”生活史,歷史應(yīng)該是發(fā)生在他們前人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每一個細節(jié),是民眾活生生的有血有淚的常態(tài)生活。因此,給歷史的細枝末節(jié)做一個記號是我寫作本書的初衷,而每天人們都得裹覆自己裸體的衣物無疑是一個很好的載體。
三
坐在北京知春路懸在半空的蝸居中,注視著朗朗夜空下的冒著堅挺煙霧的煙囪和猶如山村墓地三三兩兩的陰森森的鬼火般的,也有人說是耀眼的、斑斕的、迷離的燈火,我的思緒離高樓大廈林立的北京、離霓虹燈此起彼伏的北京,離這些年像個暴富的急速膨脹的“土財主”的北京非常的遙遠。我總是情不自禁地思念著那在千里之外的地處南國的故鄉(xiāng),和依舊在那小山莊不停勞作的白發(fā)蒼蒼、身影佝僂的老母親。兒時,同樣是這樣的深夜,當我朦朧地睜開雙眼起來撒尿時,年齡還并不是太老的母親已經(jīng)花白的頭發(fā),總是在昏暗的桐油燈下與暗淡的依稀的桐油燈光一起閃爍。幾乎一年四季的每個夜晚,母親都是在一家人都睡了之后,還在用她手中的針和線給爺爺、奶奶、父親和我們兄弟姐妹做鞋、做衣裳。其實,母親的母親,父親的母親,以及二三十年前天下大多數(shù)母親她們基本上都是像母親這樣過過來的,有的甚至比母親還要辛苦。我并不想夸大“母親”的作用,但我覺得中國的歷史就是在這些平凡的女性手中一針針、一線線縫出來的。沒有她們辛勤、任勞任怨地縫補、編織,中國的歷史肯定更加破敗、蕭條、蒼白與憂傷。
祖母是看著我長到十七歲時才去世的,那時她已經(jīng)八十二歲的高齡。祖母的腳是典型的三寸金蓮,因為不懂事的我在小時候經(jīng)常的傻笑她的小腳和走路時的碎步與顫悠,祖母幾乎沒有當著我的面洗過腳。這雙小腳,使在農(nóng)村必須勞動的她行動十分地不便。在她的晚年,為了減輕母親的勞累程度,直到她死的那一天,祖母的衣物基本都是她自己縫補和盥洗的。由于老眼昏花,在縫補衣物時,只要是放學后我在家,她就會讓我給她把細線穿在針眼的小孔里。作為一個那時還很小的男人——幾歲的孩子,我是在祖母的影響下,學會簡單地縫補衣服的——這項技能在今天已經(jīng)被很多人輕蔑地嘲笑過。當我在無數(shù)個夜晚寫這本小書時,是眼前晃動的走路顫顫巍巍的祖母和母親的白發(fā)伴隨我、激勵我堅持下來的。為此,我要將這本小書獻給我仍在勞作的母親和已經(jīng)在地下長眠十多年的祖母!
岳永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