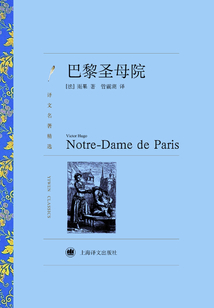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 4評論第1章 譯本序(1)
【一】
'ANáГKH!
那痛苦的靈魂——克洛德·弗羅洛,“站起身來,拿起一把圓規,默然不語,在墻壁上刻下大寫字母的這個希臘文:'ANáГKH!”
他并不是瘋了。
維克多·雨果一八八二年八月十五日[1]在札記中寫道:
“這個X有四只臂膀,擁抱著全世界,
矗立著,衰亡或失望的眼睛都看得見它,
它是地上的十字架,名字就叫耶穌。”
雨果,這個從不望彌撒,明確拒絕身后葬禮上有任何教會演說,甚至不要任何教士參加的人,這個首創其始、遺體以俗人儀式進入先賢祠的巴黎“第十八區的無神論者”,他在這里所說的“耶穌”,也同他在《世紀之歌》等等問世作品中所說的“上帝”、“神”、“人子”、“耶穌”一樣,只能是被天主教當局視為異端的某種東西。
在一首短詩《致某位稱我為無神論者的主教》中,雨果斷然答復:“耶穌,在我們看來,并不是上帝;他還超過上帝:他就是人!”
這個人本身,在浪漫主義大師雨果筆下,就是一座火山:在形色各異的外殼掩蓋之下,里奧深處有永恒的熔漿沸騰轟響。被社會唾棄的圣者若望·華若望,被社會壓在底層的海上勞工吉利亞,被社會放逐的強盜埃納尼是這樣,受天譴的副主教克洛德·弗羅洛以及自感人神共棄的非人生物卡席莫多也是這樣。按照天上的教義和世上的法理來判斷,這樣背負著十字架的“耶穌”,只能是魔鬼,是別西卜,是撒旦。
師承古希臘悲劇大師,雨果敘述'ANáГKH這個字,也就是以激情的筆觸刻畫人的悲劇。首先是人的內心沖突、分裂、破碎以至毀滅的悲劇。在《巴黎圣母院》中突出表現為靈與肉之間矛盾不可調和,終以矛盾所寓的主體的覆滅、以致他人無辜受害而告終。堂克洛德和卡席莫多這一主一仆,各從一個極端,向我們呈現的正是這種痛苦掙扎、毀滅一切的驚心動魄的圖景。
首要的意圖是剖析他筆下的主人公(不僅有副主教和敲鐘人,還有若望·華若望、甘樸蘭,以至羅伯斯庇爾等等)的不由社會身份、時代環境等等規定其實在內涵的人性。人道主義者雨果不止一次讓我們看見:即使邪惡,克洛德·弗羅洛也是以鮮血淋淋的痛楚為代價的。尤其是在作者多方烘托小約翰天真淘氣的可愛性格之后,讓他的哥哥克洛德為他的慘死,發出“我不殺約翰,約翰實由我死”似的悲鳴,我們在惋惜偉大作家如此敗筆之余,不禁要呼喚復仇女神來為我們祛除任何不必要的由弟及兄的同情!
維克多·雨果仍然是偉大的人道主義者。二十九歲,他就已經開始超出他原來的哲學,尋求人性以外更多的東西,或者說,人性里面更深的東西。果然,無論是克洛德,還是卡席莫多,他們歸根到底是社會的人,他們內心的分裂、沖突,反映的是他們那個時代神權與人權、愚昧與求知[2](即使在卡席莫多那樣混沌的心靈中,理性的光芒仍然不時外露,他那聲“圣殿避難”的吶喊絕不說明他是一個白癡!)之間,龐大沉重的黑暗制度與掙扎著的脆弱個人之間的分裂、沖突。而這種反映,是通過曲折復雜的方式,交織著眾多糾葛,歷經反復跌宕的。——唯其如此,雨果這位巨匠才把這場悲劇刻畫得深刻感人,按照某些傳統評論家的說法,甚至“恐怖氣氛渲染得極為出色”。間斷三十年(1831年至1861年)[3]之后,雨果在《悲慘世界》中更為成熟,若望·華若望悲慘的一生,遠遠不是人性內里沖突達至不幸的解決所能解釋的;他最后那樣悲天憫人地圣化,看來有違作者的初衷,是早已超越過什么主教的感化、內心中善戰勝惡的結果,而是這個苦命人痛苦地感受和觀察社會生活,因而明辨善惡、善善惡惡的有意識的行為。
筆下的人物如此作為,正是作者本人明辨善惡、善善惡惡使然。說雨果是偉大的人道主義者,尤其是因為他不僅揭示出人性沖突中實在的社會內涵,而且自己就在生活中斷然作出抉擇,強烈地愛所應愛、憎所應憎[4],并在作品中以引人入勝的筆法誘導讀者愛其所愛、憎其所憎。如果說這恰似雨果自己津津樂道的“良心覺醒”,這個覺醒在《巴黎圣母院》中即已開始。青年的雨果是以這種“內心的聲音”,而不是以其他什么聲音,迎接了他的“而立”之年。
道貌岸然的堂克洛德就是惡魔的化身。這還不僅僅在于他淫穢、不純潔、不信上帝、叛教、致無辜者于死命,還不單單在于他個人作惡多端、行妖作祟,而在于他代表著野蠻的宗教裁判,橫掃一切的捉鬼(la chasse aux sorcières或witch-hunting)鬧劇,蔚為時尚的禮儀周旋進退,以及今日看來不值一笑的偽科學、假智慧,借以欺世盜名的荒謬真理……一句話,他代表著中世紀:整個中世紀的黑暗勢力既以他為仆人、工具,又聽命于他,為他作倀。堂克洛德絕不是浮士德博士,他是公山羊,即,撒旦在人世間寄寓的肉身。
他又是國王路易十一在教會的一個代理人。不,他就是作者著墨最多的又一路易十一,穿上教士服的專愛罵別人“淫棍”的這個暴君。
華洛瓦的查理和安茹的瑪麗夫婦的兒子路易·華洛瓦[5](1423—1483),在位二十二年(1461年登基),是一個不得人心,既為朝臣、又為黎民痛恨的君王。即使隨侍左右的親信:修行者特里斯唐這只警犬,既是理發師、又是劊子手的奧利維埃·公鹿,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冒險家,也莫不痛感此人刻薄寡恩、殘暴多疑、貪鄙而又吝嗇。他對上帝、圣母以至宗教信仰和教會,也采取實用主義態度,正如他對這些他需用一時的佞臣的態度。他像一切暴君一樣,性喜絕對專制獨裁,卻偏愛裝出開明、寬厚、慈祥的模樣。他不讀書,卻附庸風雅,自稱尊重學問。他迷信而自私到這種程度:只允許四種人接近龍顏,即醫生、劊子手、星象家和行奇跡者(尤其是煉金術士)。即使他自己的那副尊容:矮小肥胖(老了以后,由于多病而瘦小枯干),大而禿的腦袋,深目鷹鼻(這大概會被中國的阿諛奉承者美稱為“隆準”的吧?),也令人憎惡。所有這些,在《巴黎圣母院》中都有與情節發展密切結合的生動而真實的描寫。
另一方面,雖然絕對談不上英姿天縱,路易·華洛瓦仍是一位奮發有為、勵精圖治的君主。他繼承父志,終其一生為建立統一的強盛的中央集權的王國而奮斗不懈,傳之于子,歷經查理七世、路易十一自己、查理八世三代統治下法國人的努力,為以后的“太陽王”路易十四、為絕對專制統一的法國,開辟了道路。路易十一就位時的法蘭西,是百年戰爭的創傷尚未治愈,百業凋敝、民不聊生的國家,是外部強敵英國人仍然占領著大片國土、內部大小封建領主割據的四分五裂的國家。在當時的法國,正如路易十一自己所說,“法國人看得見的絞刑架有多少,就有多少國王!”這些自稱主人的領主中最強大的,是割據東部富庶地區的布爾戈尼公爵[6]、霸占沿海地帶的布列塔尼公爵和盤據心腹要地的安茹公爵。路易十一經過長時間的努力,與嘗試振興手工業和農業(農業仍然失敗),并采取增丁添口的措施的同時,通過戰爭、外交、聯姻……一切正當的和不正當的手段,終于剪除了構成最嚴重威脅的布爾戈尼公爵,只留下布列塔尼問題給兒子去解決。英國人被逼迫龜縮在加來城周圍的一隅之地。路易十一甚至不惜下毒,毒死了他的勁敵——英王愛德華四世。在全國境內,路易著手建立和推行統一的稅收、統一的治安、統一的軍隊、統一的司法、不對羅馬教廷俯首帖耳的統一的教會。雨果通過路易十一的口預言:“終有一日,在法國只有一個國王、一個領主、一個法官、一個斬首的地方,正如天堂只有一個上帝!”以后終于實現。
但是,雨果寫的是小說,并不是歷史。作者以罕見的淵博,依據史實,又以藝術夸張的手法,拿出來示眾的是一個全然可憎的陰暗角色。這個家伙對處決活潑、純潔、美麗的姑娘愛斯美臘達負有直接的主要責任,他也是把受盡踐踏的賤民們,即所謂的黑話分子,斬盡殺絕的元兇大憝。黑暗之力——按照中世紀的看法,即魔鬼——通過人間的法律而逞其淫威、大啖人肉的時候,是以神權和王權兩副面孔出現的,一副叫做克洛德·弗羅洛,一副叫做路易·華洛瓦,二者同樣地猙獰可怖,而由于后者躲在背后,深藏在巴士底堅固城堡中,而更加陰狠毒辣,力量也增強了十倍。
卡席莫多不幸是個聾子,幫了倒忙,把六千多義民阻遏于圣母院門前,方便了路易十一的屠殺,致使全部好漢血染前庭廣場。他們堪稱壯烈犧牲!愛斯美臘達是他們的妹子,不錯;但是,一方面,她就是一切慘遭中世紀愚昧黑暗勢力摧殘的無辜百姓中間的一個,也是他們的楚楚動人的形象;另一方面,這些賤民憤然起義,要攻擊的不是司法宮典吏,而是國王,是王權。路易十一渾身哆嗦,臉色煞白,喊道:“我還以為是反對典吏!不,是反對我的!”他調兵遣將,狂呼:“斬盡殺絕……斬盡殺絕!”
遭到路易十一血腥鎮壓而全部玉碎的民眾,就是《巴黎圣母院》的真正主角。他們是用血寫的這部壯麗史詩的主角,哪里像某些遵從傳統的法國評論家、文學史家所說,是巴黎圣母院這座建筑物本身?不。甚至也不是那個俗稱鐘樓怪人的卡席莫多。
由于不幸的造化捉弄,這個棄兒生來畸形,這個內心善良、純真的人承受的苦難也就更比其他畸形兒增加一倍而猶有過之。著意刻畫某些畸形的人的痛苦,不能見容于社會,甚至為全人類所唾棄,使讀者拋灑同情的眼淚,這原是雨果的得意之筆。像甘樸蘭那樣的笑面人,或者從某些生理特征上說也非同常人的若望·華若望,所作所為應該使許許多多上流社會人士感到羞愧,他們被看成異類,恒常陷于走投無路的境地,就是勢所必然的了。這種悲劇的致因,當然并不是生理性質的,而是社會性質的。然而,在卡席莫多,幾乎是他的“又駝、又瞎、又跛”,特別是“又聾”,成為導致他短暫一生的悲劇的不可抗誘因,而在一個關鍵時刻,甚至累及他曾愛過的一切以及他漠然對待的一切,釀成像古典悲劇那樣的統統死光的慘烈結局。善良的人而偏偏形體可憎,邪惡的人而偏偏道貌岸然,雨果善于使用這種鮮明對比的反襯手法,這確實十分扣人心弦。但是,如果說后一事實使讀者覺得不乏其例,甚至比比皆是;那么,前一點也許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只是某些高超的作者有意的、也是專斷的巧妙安排(例如,法國文學中還可以舉出西拉諾[7])。
我們可以從研究古希臘悲劇中,把雨果的前輩古人所說的命運,剖析其動因或契機,大別為三類:一是偶然的不幸,二是人的自我矛盾的不幸的解決,三是人與環境(社會的、自然的)的沖突不可調和。如果單純著眼于卡席莫多的畸形,《巴黎圣母院》這整個的悲劇,那就只是偶然因素起主導作用的一種不幸命運在一個例外情況下造成的結果。
安德烈·莫羅瓦認為,雨果用以構筑他的命運大廈的是三部作品,我們也可以稱作雨果的“命運三部曲”:《巴黎圣母院》(他說是“教條的命運”),《悲慘世界》(“法律的命運”),《海上勞工》(“事物的命運”)。不,并不盡然。固然,《巴黎圣母院》所敘述的命運,一個十分重要的側面是一個教士與他的教條分裂;《悲慘世界》從若望·華若望與雅維爾的沖突的角度,指出了人間法律給人們的只是厄運;《海上勞工》著重刻畫了人向自然斗爭的嚇人場面;但是,偉大作家雨果并不局限于某一個方面。我們在《巴黎圣母院》中看見命運的行動,給予幾乎所有或多或少重要的角色以毀滅性打擊,憑持的既是偶然因素,又是幾個主要人物自身矛盾的紐結及其不幸解決,更重要的是把這出戲劇放在特定的舞臺上,即中世紀的法國,愚昧迷信、野蠻統治長久猖獗的那個社會之中。這三者的巧妙結合而發揮威力,就是雨果筆下致人死命的'ANáГKH。
“生活,就是承受重擔;生活,就是昂首前瞻!”
(《我的豎琴》)
人在命運的重壓下,高瞻遠矚,昂首舉步,走向未來。
“你很清楚:我要走向哪里,
正義,我走向你!”(《出征歌》)
是的,應該像雨果那樣——
“我睜開眼睛,看見了燦爛的晨星……”
(同上)
人呀,你要永遠樂觀:
“相信白晝,相信光明,相信歡樂!”
(《我的豎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