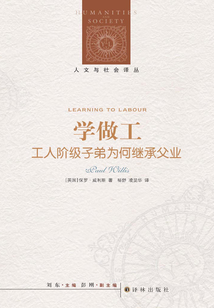
學做工:工人階級子弟為何繼承父業(人文與社會譯叢)
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中文版前言(1)
非常感謝譯林出版社及秘舒、凌旻華兩位譯者把這本書帶到中國讀者面前。中國正經歷著具有世界影響力的歷史性跨紀元變化,文藝科學界正摩拳擦掌準備迎接全新的挑戰,以試圖理解“中國的重大轉型”,我的書能在這個時機被譯介到中國,真是我的榮幸。非常感謝!
我從未到過中國。與其直接討論令我神迷但我又知之甚少的中國現狀,還不如借這個前言來概述一下《學做工》的一些主題和重點,這可能對你們——我親愛的中國讀者——研究和理解自身正在經歷的時刻最為有用。我沒有從某一特定學科,如教育學、社會學、文化研究、人類學的角度出發來進行概述,而是秉著一種多學科或者后學科時代的精神。在我看來,這種精神對我所選擇的方法論的活力和未來至關重要;《學做工》正是使用這種方法的例證,它是批判性民族志的實踐。我和馬茨·特朗德曼共同創辦、編輯的《民族志》(Ethnography)學術雜志[1]也致力于打破并跨越學科的邊界,尤其是社會學和人類學的邊界。在我內心,我希望鼓勵中國的研究者,特別是博士研究生,跨越學科界限,并擔當起重塑民族志這一艱巨而美好的任務,將大多數人接受國家公共學校教育時的經歷和文化描繪出來,而這些經歷和文化通常是隱形的。
文化與民族志的敏感性
我希望中國的民族志學者能重新審視“文化”這一備受爭議的術語和概念的重要性。文化指的是人類在特定環境中創造意義的各種實踐,而不能被簡化為對其他事物的反映,如個體心理、話語或經濟。它自成一體。對文化實踐和過程,尤其是社會底層空間的文化實踐和過程的重視,引發了一系列簡單但具有革命性的問題:“什么是我們正在研究的人群的文化,他們自己的文化?”“他們如何理解自身的文化?”“這個世界在他們看來是怎么樣的?”“他們如何看待自身的處境、掌權者對他們所做與所說的?”“他們是如何引導我們對他們的看法的?”嘗試回答這些問題最終將引向民族志的敏感性和方法論。若要復原底層被統治群體及他們的人性,學者必須和他們一起,在共處和互動的過程中以開放、人性的態度去理解他們。
這里我想強調的是,文化的特性在于社會能動者“意義創造”的積極過程,尤其是在理解自身生存處境,包括經濟地位、社會關系以及為維護尊嚴、尋求發展和成為真正的人而構建的認同和策略的過程中。
意義創造的文化實踐并非在抽象中運作,也不是無中生有地變出意義來。它們不是在個體大腦中或大腦間流動的電流。“意義創造”源于象征性的物質、過程和行為。就像勞動過程中的物質生產一樣,文化層面也有生產過程,即文化生產,在這個過程中人們從事感官上的實踐,用象征性的原始資料生產出新的或者更新的事物,以滿足有用的人類目的。在這種情況下,“產品”是意義和表達,它們不僅自身具有價值,同時對人類理解自身所處的生存環境也多少有用。
我認為,文化生產的文化實踐,其功能在于洞察或“看透”他們的生存狀態,從而從他們的角度決斷出最有利的身份和行動,以及可提供的制約和條件。洞察這一概念試圖在分析的某一時刻捕捉到文化生產的推動力,從而揭示文化所依賴的,及定位文化的結構元素。這些“洞見”嵌在他們的“民間”知識、實際“常識”和“將就”使用的意義之中。在這個意義上,現行的文化形式對于后學科批判性民族志學者來說格外重要,這并非因為它們保留了一套奇怪的習俗,或者實體化的自我具有值得行為學和歷史學記錄下來的價值,而是因為它們包含了對自身生存狀態而言至關重要的、身體力行的洞見。它們是解決問題的實際、生動、就地的方法。如果對一個現存文化形式的民族志記錄感興趣,那么就必須在認識論上取得某種突破。如果你相信某種馬克思主義或者后結構主義,那么你就不必煩心去做田野調查。如果你相信關于孩子們所作所為的制度性或意識形態上的解釋,那你也不必操心去做田野調查。進行田野調查的目的就是為了努力理解特定研究對象是如何理解自身及自身處境的,而這些方式無法被預知,甚至還可能“令你驚訝”。這種文化是如何為自身處境建構意義的?你又如何理解那種意義建構?在這種情形下,我們是如何認識到有可能出現一種由行動者根據自身處境創造出的中斷、差異、地方性知識的,這些對于外界而言,無論是在官方的或意識形態的層面上,還是在商業的層面上,都是不可理解的。例如,通過反學校文化的調解,《學做工》一書中研究的“家伙們”洞察了學校的個人主義和精英主義,他們的群體邏輯認為證書和考試永遠不可能提高整個工人階級的地位,相反只會造成資格泛濫,使中產階級特權合理化。他們并不幻想“事業”發展,而是在使人疲倦的環境中付出自己的勞動力,判斷出必需的最低限度,以免受到來自于被支配地位的雙重侮辱:一種是真實的,一種是意識形態上的。他們釋放出的文化和心理能力在其他地方派上了用場:樂趣、娛樂、“找樂子”。
文化生產過程的“原材料”以及隨之而來的洞察以各種形式出現:可塑的、口頭的、文本的、音樂的;它們的來源亦紛繁復雜:歷史的和當代的、本土的和舶來的、商品化的和非商品化的。我們不應低估歷史文本中的“珍寶”、口述史的資源,以及老一代傳下來的建議。意識形態的敘述和文本也發揮了一定作用。雖然很多文化生產中使用的象征性資源仍未被社會科學分類命名,但它們卻是對記錄真實生活的民族志的補充。在性、性別、種族、民族、年齡等常見類別中,經由社會傳承而形成的特定傳統和延續至關重要。它們在把其他各種象征材料組織起來的同時,也提供了自身特有的象征意義。[2]由于它們服從于文化生產的作用,因此所有這些資源都可被塑造成新的形態,被放入產生新型混合形式的接合中。資源如何被組合,通過何種實踐、出于何種目的被組合,對于這些問題的追問極具民族志意味。
關于文化層面更為關鍵的一點是,“理解”結構位置的過程不僅“揭示”了過程的方方面面,而且也促成了過程的再生產,提供維護和再生產它們(依據權力組織起來的位置和關系)的日常生活中物化的形式。例如,在“家伙們”的案例中,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們洞察的形式恰恰也為他們進入下層經濟結構做好了準備。如果他們的洞察直截了當、真實無誤,那么他們就不必承受那諷刺性的社會再生產的狹隘恥辱了。他們可能已被直接引向社會解放。
除了與對抗、洞察學校要求高度相關外,反學校文化中的反智態度也成為了“家伙們”的第二天性,并在從學校過渡到工作以及之后的很長時期內,對他們的形體風格、態度和價值觀起導向作用。這個模式驅使他們終其一生朝向某種經文化調解、經驗感受形式的意義創造發展。危險的是,這種反智態度使得整個世界被分為兩派:腦力的和體力的。對各個階層的處境和政治做抽象的想象可能看起來無謂而遙遠,這種想象不能用體力來觸及、解決或理解。更為實際的是,所有需要動用腦力的工作,不論是在現在還是將來,看似都只是無聊的文書工作——“誰想整天被紙張文件所包圍?”這使得“再次”回到校園接受高等教育的希望變得更加困難和不可能。“家伙們”的反智主義使他們以及和他們相似的群體向體力工作妥協,一輩子在沒有前途的工作之間換來換去——英國現在有很多長期失業甚至永久性失業的案例。
我們從民族志的視角來理解社會結構,正是由于舊事物的更新和變革具有連續性、波動的穩定性和辯證性。因此,民族志的關鍵問題不僅僅關乎文化實踐到底在“理解”結構位置中有多大的作用,而且也關乎同樣是這些實踐活動,在多大程度上具有諷刺性地維護了那些既有的權力關系和利益。這些問題也引發了一系列具有廣泛意義的政治問題:在未來這些相互關聯的關系循環中,這一平衡如何轉變成被統治者的優勢,在何種條件下對文化生產的洞察可能轉化為政治意識和實踐,并被動員起來中斷社會再生產,而不是反過來強化它。
理論上的不確定性
民族志需要具有生成力的而不是簡化還原的理論:徹底的不確定性對民族志觀點很有必要,以了解允許產生主體創造力和選擇的不確定主觀因素。對于宏觀理論家來說,這些可能僅僅是以一些范例來“解釋”的幻覺,而這些范例只是證明了他們認為本該存在的事情,毫無“驚訝”可談。一些簡單、開放、具有生成力的機制(創造性、洞察、再生產)在結局各不相同的群體中反復出現,如果我們對此予以理論關注,那么就足以涵蓋各種可察覺的結果——這些結果會激怒那些坐在搖椅上的理論家,使他們生產出更復雜的理論,也會讓民族志學者心懷訝異地走進田野。
我主張對某些馬克思主義者關于意識形態的概念進行嚴格限定,這些馬克思主義者認為意義來自于外界,是外界“添加”到他們的主觀性之中的。我的看法基本和上述馬克思主義觀點截然相反。如果你愿意,意識形態也能反方向流動,被壓制的主體和受壓制的地位也能通過他們的文化形式享用認知上的資源,從而在意識形態上尋求異議,或者根據受壓迫者的利益或視角、用某種不同的方式進行重新闡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