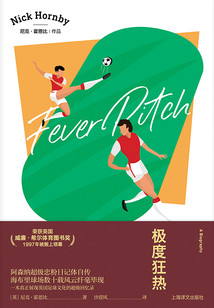
極度狂熱
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發燒的足球場——代譯本序
我只看過兩次英超比賽的現場,兩次都有阿森納隊。一次是在2002年,一家賭博公司邀請,去伯明翰看萊德杯高爾夫球賽,中間有一天,從伯明翰開車去利茲,看利茲對阿森納的比賽。下午的陽光從云層中透過來,三五成群的球迷慢慢向埃蘭路球場聚攏。賭博公司的經理,向我們介紹在球場門口如何投注,花兩鎊買一張彩票預測一下比分,他當時雄心勃勃,以為不久就能在北京工體門口也開這樣一個足球投注點。第二次是去老特拉福德,曼聯的贊助商宇舶表邀請,除了記者,還有幾位花大價錢買了手表的VIP客戶,在包廂里吃飯,有簽名球衣相送,有曼聯名宿作陪,那場比賽,溫格先生被罰上了觀眾席,他在觀眾席上向裁判攤開雙手的形象廣為傳播,身后的曼聯球迷發出陣陣噓聲,后來那張照片被人P了一次,溫格身后曼聯球迷的人頭都被狗頭替代,也就是所謂“曼狗”。我當時就在教授身后,覺得他的樣子好帥。
回想這兩場比賽,我好像更喜歡在埃蘭路看的那場球。因為球迷氛圍更好,中場休息的時候,看臺走道上的球迷都手捧一杯啤酒,廁所里也彌漫著啤酒味兒,小便池是金屬制造,直接鑲嵌在墻里,似乎是怕憤怒的球迷將小便池拆下來。利茲大比分失利,主場球迷對裁判和客隊表現出更大的憤怒。也就是說,那場球有一種略為粗野的危險氣息,相比之下,曼聯的那一場有點兒溫文爾雅。
尼克·霍恩比在《極度狂熱》一書中說,一場好的比賽,要讓你沉醉、難忘,應該具備七種特征。一是進球越多越好;二是裁判糟糕的判罰,你支持的球隊是受害者,但還不至于因此而丟掉比賽,義憤填膺是看球的重要情感體驗;三是喧鬧的觀眾;四是下雨濕滑的場地;五是對方罰丟了點球;六是對方隊員吃了紅牌,下半場膠著之時對方吃到紅牌是最好的;七是某種“不道德事件”,足球機構和記者總會呼吁球隊將注意力放在比賽上,但球迷沒必要聽從道德訓誡,場上不出現點兒幺蛾子,一場球就顯得過于平淡。
霍恩比這個說法,值得再琢磨一下。第一條,進球,可以算是對足球技戰術的要求。第二條,要有罵裁判的機會,比賽中要有“錯誤”判罰,球迷們要感受到不公,要因此發泄。第三條,觀眾要足夠鬧騰,死忠球迷的chant始終在上空回蕩,球員在場上的動作能得到觀眾的回應,這才是好的舞臺效果。第四條,特殊天氣會帶來獨特的視覺體驗,英國的雨雪天氣多,要求隊員更拼命,這也算是一種比賽態度。第五條,對方罰丟點球,在球場中除了勝利的喜悅,還需有幸災樂禍來助興,幸災樂禍是一種有益健康的情緒。第六條,對方球員在下半場膠著時被罰下,這是一種“天助我也”的感受;第七條,場上球員吵架、打架,觀眾在外圍大聲叫罵,這就是赤裸裸的攻擊性。七條中,有四條完全是情緒化——痛斥裁判不公、幸災樂禍、天助我也的自信、仇視與攻擊性。有兩條也偏重情緒——觀眾要看得投入,要鬧騰,雨雪天氣讓球賽在審美上更具吸引力。
霍恩比對好比賽七要素的總結,是他在記述阿森納和諾維奇的一場比賽中寫到的。那場比賽1989年11月4日在海布里進行,阿森納以4:3獲勝。《極度狂熱》這本書就是霍恩比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看球筆記。那是“英超”之前的事情。霍恩比當時住在倫敦郊外,他的主隊是阿森納。不過他很快就接受到了“球迷歸屬地”的教育。霍恩比住的地方叫梅登赫德,雷丁隊是離他最近的俱樂部,球隊主場榆樹公園離他家八英里,海布里離他家有三十英里。1972年足總杯第四輪,雷丁主場對阿森納,霍恩比想,去雷丁買一張票比跑到北倫敦容易,他買了票,在開賽前九十分鐘就進場,結果碰到雷丁球迷一家人,他們戴著藍白橫條的圍巾,和霍恩比聊了起來。雷丁球迷說話有口音,也不愿意像倫敦人那樣說話,霍恩比跟他們說話,也裝出工人階級腔調。雷丁球迷問他,你住哪里啊?霍恩比回答,住在梅登赫德。雷丁球迷說,你住的地方離雷丁只有四英里啊,你不應該支持阿森納,你應該支持你當地的球隊。霍恩比說,我住的地方離雷丁有十英里。他要用距離來解釋自己為什么不是雷丁球迷,但這個解釋說不通。他說,這是我青少年時代最丟臉的時刻,我希望阿森納為我復仇,擊敗這支三流球隊,把這些自命不凡、愚蠢乏味的球迷打成一堆爛醬。
英格蘭足球文化——文化這個詞用在這里非常別扭——姑且這么用著吧,其根基就是互相仇視。利物浦球迷從小就會被教育仇視曼聯和埃弗頓,桑德蘭球迷要恨紐卡斯爾,熱刺要恨阿森納,這里面有歷史原因,比如曼徹斯特和利物浦的一百多年前的利益之爭。但我總覺得,相互仇視并不需要什么理由,球迷需要無理由的、作為文化傳統的相互仇視。霍恩比在書中寫到,有一次阿森納迎戰曼聯,背后有個球迷總是對著因斯學猴子叫,霍恩比回頭看,發現那是個盲人球迷。一個盲人球迷為什么是一個種族主義者?對種族主義說不,這是個持續幾十年的話題了。然而,對種族歧視的反擊也可以演變成另一種仇視,2012年2月,曼聯主場對陣利物浦的那場比賽,解禁之后的蘇亞雷斯拒絕跟埃弗拉握手,曼聯獲勝之后,埃弗拉全場飛奔慶祝,跑到蘇亞雷斯面前又蹦又跳。一年后,曼聯獲得二十冠,埃弗拉慶祝之時拿起一支手臂模型,嘲笑蘇亞雷斯的“咬人”,仇視——報復性的慶祝——嘲笑式的慶祝,這個梁子持續兩年,也就變成了“雙紅會”中的典故。
英超的全球轉播,會讓全世界的球迷看到每一輪比賽的每一場球。2020年6月,英超“重啟”之后的第一場球,謝菲聯客場對阿斯頓維拉,鷹眼系統居然漏掉了一個進球,門線附近的七個攝像頭都被球員給擋住了,球迷們可以從gif圖看到,可以從幾十秒的短視頻中看到。在這樣的傳播環境下,再看霍恩比的這本書,免不了會有點兒不滿足,他說的那些球賽都是幾十年前的事了,對那些比賽,我們并沒有共同記憶。然而,這本書的可貴之處,也在于霍恩比寫的是他的個人記憶,離婚的父親帶著他去海布里,小孩子在球場上找到歸屬感,上大學的霍恩比成為劍橋聯隊的球迷,他不得不學會降低自己對球隊的要求,不再求勝,希望能有一個進球,而后又要接受殘酷的連續失敗——接連有三十場比賽不能獲勝。足球與女友的關系——為什么同年齡的女孩就比男孩顯得要豐富一些呢?不是球迷的人,總覺得要從足球中獲得某種提升——比如足球促進了親子關系,比如從足球中悟出了什么人生道理,可球迷都知道,足球就是足球,看球就是情緒化的、粗野的、帶著莫名其妙的優越感、帶著攻擊性,球迷去看球,可不是為了去凈化,甚至也不是為了去宣泄,那就是度過星期六下午的一種方式,或者陽光明媚,或者陰雨綿綿,大家聚在一起,感受到我們的生活本身就充滿了仇視、粗糲、天不遂人愿、不公,還有狂喜。
足球讀物向來是英國書店中一個專門區域,其中最常見的就是球星自傳,球迷渴望談論比賽,也愿意看到球星的故事。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結束的時候,亨特·戴維斯給英格蘭隊寫了本書,那時候的球星還沒經紀人,隨便寫一個授權書,同意接受采訪并由戴維斯寫書,戴維斯采訪了十九個人,稿費自己拿一半,另一半分給那十九人,每個隊員最終到手一百鎊。當時,球員平均周薪是二百英鎊。到2006年的某一天,戴維斯接到電話,出版商問他是否有興趣給魯尼寫本傳記,魯尼剛滿二十歲,就簽約出版五卷本的傳記,從中拿到五百萬英鎊收入,莫扎特和達·芬奇在二十歲的時候也沒做到這一點。霍恩比在書中寫到了1970年世界杯上的巴西隊,也寫到了1968年曼聯首次獲得歐洲冠軍杯。1968年,有一位叫阿瑟·霍普克拉夫特的記者寫了本書叫《足球人》,而后他進入電視行當,一直做編劇,他把《鍋匠裁縫士兵間諜》改編成電視劇。2011年,英格蘭足球名記西蒙·庫珀出了本書,也叫《足球人》,他說他十六歲開始寫足球,給地方報紙寫了篇古力特的特寫,后來再也沒興趣寫球星專訪了。他說,我得忍受那些經紀人推三阻四,好不容易約上一個球星,他坐在你面前也說不出什么來。有關足球,溫格或許能說出一些讓你受益的東西,但一個球星說不出什么來。但是,也只有西蒙·庫珀這樣的記者,能把一場新聞發布會寫出花樣來,比如魯尼曾經和埃弗頓隊的主教練莫耶斯一起參加賽前新聞發布會,他打開桌上的一瓶礦泉水喝,莫耶斯提醒他,“用杯子喝”,魯尼看了他一眼,接著用瓶子喝水,據說這就是魯尼離開埃弗頓的前兆。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霍恩比的這本《極度狂熱》,看到一個作家講述他的足球故事。當他說到海布里的時候,那就是提到一個圣殿。我們在電視上看到過海布里的謝幕,看到過酋長球場的啟用,看到過阿森納的不敗紀錄,也看到過這個不敗紀錄如何被曼聯終結。這都是英超時代的事,霍恩比所講述的是英超前史,但也由此讓我們看到足球的傳承,作為一種生活,足球在英格蘭得到了最深入人心、最豐富,同時也是最商業的展現。
苗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