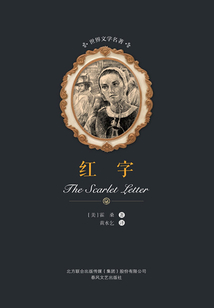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譯序——霍桑與《紅字》的文學技巧
納撒尼爾·霍桑于1804年的美國獨立紀念日誕生于馬薩諸塞州的塞勒姆鎮。他的父親和祖父都是船長。霍桑的祖先到塞勒姆已有兩百年了。他們于1603年跟隨溫思羅普總督來到美洲。霍桑兩位美國著名的祖先(如“海關”一章中所描述的)是威廉和威廉的兒子約翰。威廉是教友派教徒的嚴苛的迫害者,而約翰則是1692年塞勒姆女巫案的三大判官之一。霍桑四歲時,父親在一次漫長的航程中不幸遇難,于荷屬圭亞那去世。窮困潦倒的母親便將這個小家庭(包括她本人、納撒尼爾及兩個妹妹伊麗莎白和瑪麗亞·路易莎)遷往塞勒姆的親戚家。大約九歲那一年,他腳部受傷,不得不長期待在家里,于是他有時間博覽群書,尤其是沃爾特·司各特、約翰·班揚和莎士比亞的著作。隨著時光的流逝,霍桑成了緬因州雷蒙德市一位叔父家的常客。他在這兒盡情地享受戶外生活。大約十四歲時,他舉家遷居雷蒙德市。
這時,納撒尼爾在塞勒姆的一位家庭教師的指導下準備赴考,并于1821年就讀于緬因州布倫斯威克市的波多音學院,于1825年畢業。霍桑在這所學院的學業很一般,只是中等水平。有的評論家認為他在班上的這個成績是具有象征意義的,說明他對“平常與正常”的挑戰與嘲諷,也說明他有一種病態的心理謙讓,以及越來越嚴重的自餒和自我埋沒的心理傾向。霍桑是個英俊的小伙子,但他卻拒絕參加班上的剪影活動。畢業前夕,他在給妹妹路易莎的信中這樣寫道:“我對這個問題思考了很久,最終的結論是我永遠不會成為世界名人,我所希望或向往的一切就是與民眾一道前進。”表面上這封信流露出他的反常心理和對個人的譏諷,實際上卻反映了他內心對人生之夢的熾熱追求。難怪他的一位朋友,民主黨的忠實信徒西雷說:“我喜歡霍桑、欽佩霍桑,但我不了解霍桑。他生活在一個充滿思想和想象而從不讓我介入的神秘的世界里。”
畢業后,他返回塞勒姆老家,幾乎將全部的時間都花在提高創作技巧上。1828年,他出版了小說《范肖》。這是一部描寫他在波多音學院所見所聞的大學生活的小說。他認定自己在文學上最好的表達形式是故事(即我們所說的經典短篇小說)。在此期間,他寫了許多短篇小說,其中有不少發表在雜志上或“紀念冊”上(如圣誕節的贈閱本)。他花了十二年時間在塞勒姆的母親家中寫作。從1825年至1836年的這些歲月被一些評論家稱為“孤獨的十二年”,因為他大部分時間深居簡出,交游甚少,孤獨感一直是他內心的主流。
1836年,霍桑在《大西洋實用趣味知識雜志》任職,但因服務報酬極低或幾乎無報酬,他很快便放棄了這項工作。第二年,他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說集《重講一遍的故事》。雖然此書獲得好評,但他并沒有獲得他期望得到的稿酬。這時,他結識了索菲婭·皮博迪小姐——一位美國的伊麗莎白·巴雷特·白朗寧[1]式的人物。他們于1838年訂婚。為了補充家庭收入,霍桑從1839年至1840年在波士頓海關當煤鹽計量員。1841年,他在布魯克農場住了半年。這是由超驗主義俱樂部發起的一項集體工程,農場的成員計劃一邊共同參加體力勞動以求生存,一邊進行藝術創作活動。霍桑后來根據這些素材創作了《福谷傳奇》。1842年他與索菲婭·皮博迪結婚。婚后小兩口遷往康科德的“古屋”居住。就在這一年,《重講一遍的故事》第二卷出版,受到埃德加·愛倫坡[2]的高度贊揚。有三年半的時間,霍桑和他的妻子在康科德過著非常幸福的生活。盡管不富裕,但他們讀書、寫作、閑聊,享受人們羨慕的“美滿生活”。他們喜歡他們的康科德鄰居,尤其是拉爾夫·埃默森和亨利·索羅。1846年,霍桑生活中發生了三件大事:兒子朱利安誕生;出版了他在康科德創作的另一部短篇小說集《古屋青苔》;因發現生活拮據而接受待遇優厚的塞勒姆海關檢查員的職位。1849年,美國輝格黨上臺,扎卡里·泰勒當選總統。根據“政黨分贓制”[3]的原則,霍桑失去了這一職位,因為他是位忠誠的民主黨員。他對此非常氣憤,求助有影響力的朋友幫助他恢復這一職務。但他的一切努力都歸于失敗,于是他便定下心來完成《紅字》的創作。此書他早在1847年就動筆了,但那時他不怎么上心。《紅字》于1850年出版,被眾多的評論家們公認為最偉大的美國小說之一。同年,霍桑遷居馬薩諸塞州的倫諾克斯鎮,住在一幢“小紅屋”里。他在這兒又寫了另一部小說《七個山形墻的房子》。這是一部以塞勒姆為背景的關于邪惡的遺傳后果的研究的書,出版于1851年。在倫諾克斯期間,他與赫爾曼·梅爾維爾過往甚密。梅爾維爾將自己的名作《白鯨》(1851年出版)題獻給霍桑。1851年晚些時候,霍桑及家人(那時他已有三個孩子,即尤納、朱利安和羅斯)到馬薩諸塞州東部旅行,并待在西牛頓過冬。他在這兒寫了四部長篇小說中最不成功的一部——《福谷傳奇》。《福谷傳奇》是對他1841年在布魯克農場試行的社會主義社會的研究。
1852年,霍桑在康科德購買了一幢名為“路邊”的房子。他在這里為大學朋友富蘭克林·皮爾斯撰寫競選總統傳記。后來,民主黨在競選中獲勝,皮爾斯當選為總統。為了對霍桑表示感謝,皮爾斯委任他為美國駐英格蘭利物浦領事。自1853年至1857年,霍桑一家居住在英國。霍桑出色地履行了領事職責。他抽空游遍了不列顛諸島的各個地區,以日記的形式記載了自己的所見所聞。這些日記后來以《英國筆記》為名發表。1858年至1859年,霍桑一家旅居意大利,尤其是羅馬和佛羅倫薩。他在這兒廣泛地搜集素材。這些材料后來有些以《意大利筆記》為名發表,有些則成了他最后一部完整的小說——《云石牧神》的背景材料。此書出版于1860年,是對善與惡,及對歐洲的美國人的詳盡的研究。同年,霍桑返回美國,在康科德安家。他的健康狀況開始衰退,創作能力開始衰竭,盡管他尚能將一些英國日記融合于書名為《我們的老家》的一部關于英國的雜文集中(霍桑的創作主要來源于三個方面:一是日記,二是閱讀,三是自己虛構)。霍桑在晚年身體狀況迅速惡化。1864年5月19日,他在與他的朋友富蘭克林·皮爾斯(前總統)前往新罕布什爾的白山的旅途中猝然去世,被安葬在馬薩諸塞州康科德的睡谷公墓。
霍桑在世界文學史上一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為他至少有兩方面是現代西方文學的先驅:一是象征手法在小說創作中的應用,二是對人在精神上和道德上失常心理的分析。他在《紅字》中非常嫻熟地運用象征主義、浪漫主義、哥特式文體、心理沖突、間接法、舞臺技巧等文學手法來表現主題。在這方面他是無與倫比的。
首先,霍桑在《紅字》中運用了豐富的象征主義手法(通常以雙關語的形式出現)。書名《紅字》本身為此書定下基調。女主人公赫絲特胸前戴紅字A,公開地表明她犯了清教的“第七戒”通奸罪,是奸婦、淫婦。然而,讀者最終會發現,A不僅僅代表“Adulter?ess”(奸婦),而且也代表“Abl e”(能干)、“Angel”(天使),在赫絲特女兒珀爾眼中,A則代表著她家中缺少的那部分——她的父親“Arthur”(亞瑟)。第一章末尾的玫瑰花是一種象征,它象征著自然對人是仁慈的,盡管人待人并不仁慈。絞刑臺是清教的司法或執法的象征。衣著考究的貝林厄姆總督是整個殖民地的領導和權力的象征。“l eech”這個古語意為“醫生”,但是霍桑巧妙地選擇它,因為它是個雙關語,通常的詞意是“吸血鬼”,用它來描述奇林沃思與丁梅斯代爾之間的關系真是恰如其分。打扮得花枝招展的珀爾,是赫絲特罪行的活的象征。珀爾這名字也是雙關語,意為以極大的代價購買來的珠寶。丁梅斯代爾胸前那“紅色小標志”(A字形未愈的傷口)象征著這位不幸的牧師的悔恨與良知。對他來說,天空中“A”字形的紅色流星象征著通奸的行為。對全體教徒來說,丁梅斯代爾則代表人間的一切美德。另一方面,希賓斯老夫人卻是與森林里可怕的魔鬼有關的一切陌生魔法的象征。
《紅字》中運用的浪漫主義文學手法是霍桑獨特的一種藝術手法。當然,霍桑融合代表浪漫主義的某些通常的辦法,如冒險的行動、英雄人物或獨特的背景等。他甚至涉及某些日常生活中被認為非常遙遠的神秘的事件、場面和思想。在《紅字》中,他降低了所謂浪漫的、獨特的襯托場景的重要性,卻尋求創作能揭示“人的內心世界”的嚴肅主題,而不僅僅創作那在時間、地點或思想方面非常遙遠的小說而已。然后,他選擇稍微遠離公路的地方作為故事的背景。這樣,他想象中的人物在這兒可以自由自在地扮演各自的角色而不必過多地與真人真事相比較。霍桑不愿小說中的人物和行動與具體的真人真事相混淆。然后,他選擇實際存在的人物,并將這些人物摻入想象中的虛構人物。選擇好背景和人物之后,他緊接著就描寫他們,使他們成為真實與虛構的奇怪混合物,于是,這成了他的文學手法最顯著的特征。《紅字》是一部傳奇小說,赫絲特以愛情和情欲為基礎的私通可以被認為是浪漫的,而虛偽和報復則是嚴肅的主題。人的內心世界得到探索,良知和悔恨是值得思考的嚴肅問題。《紅字》的背景——17世紀的波士頓和絞刑臺,是讀者所陌生的。人物是一種混合體,既來自現實生活中的真人(如貝林厄姆總督和約翰·威爾遜牧師),又來自作者的想象(如小說中的四個主要人物:赫絲特·普林、亞瑟·丁梅斯代爾、羅杰·奇林沃思和小珀爾)。作者所運用的“氣氛手法”(即“明暗對照法”)是非常有效的。第一個絞刑臺場景發生在中午燦爛的陽光下(赫絲特被大家看得一清二楚)。第二個絞刑臺場景發生在夜里(黑暗中人們見不到丁梅斯代爾握住赫絲特和珀爾的手)。第三個絞刑臺場景發生在白天,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牧師站在絞刑臺上(丁梅斯代爾牧師在光天化日之下懺悔,承認一切)。讀者由此可以注意到明與暗的道德含意——明揭示邪惡,暗掩蓋罪惡和膽怯。明暗對照法的另一個方面是利用陽光。珀爾很開心,因為劇中她的周圍常常充滿陽光。可是,象征背離德行的赫絲特一到場,陽光就立即消失了。流星炫目的光照亮了和顯現出夜里絞刑臺上這對情人及他們的孩子的那幕景觀。無數的鏡子(如那套盔甲的反射的護胸甲及珀爾往里照的一攤攤水),都給《紅字》浪漫的人物、行動和場景增添了豐富的和多層的意義。
霍桑在《紅字》中繼承了恐怖的哥特式創作手法。他對哥特式小說文體所運用的許多藝術手法非常感興趣。這些手法細分起來,大致可歸納為如下幾種:①手稿。作者試圖讓讀者相信故事來源于某一文獻,令人覺得神秘兮兮的,如“海關”一章所描述的檢查員皮尤那用一塊破紅布扎成A形的“一小卷失去光澤的文件”。②有著會鬧鬼的樓梯的陰森凄涼的城堡(暗示赫絲特的黑牢房和貝林厄姆總督精心裝飾的官邸)。③罪行(如赫絲特的通奸,這是清教徒的法律可判處死刑的罪行)。④宗教(其代表人物是清教徒牧師:亞瑟·丁梅斯代爾牧師、約翰·威爾遜牧師及埃利奧特使徒)。⑤意大利人(其在哥特式小說中被描述為面目微黑的無法無天的人)。他們在《紅字》中的代表人物是那一群相貌粗野、身穿奇裝異服、精力充沛的來自拉丁美洲大陸的水手。⑥缺陷(如羅杰·奇林沃思的肩膀一邊高一邊低)。⑦鬼魂(如亞瑟·丁梅斯代爾徹夜不眠時在鏡子里看到的“惡魔似的幽靈”)。⑧魔法(由希賓斯夫人暗示出來——當她談及森林的魔鬼時,希賓斯夫人后來被作為巫婆處死)。⑨自然(利用自然現象,如天空中的紅字,丁梅斯代爾看見表示“通奸”的A字)。⑩穿盔戴甲的騎士和警察(如貝林厄姆總督官邸里那套盔甲的護胸甲和盔構成的“鏡子”,以及“新英格蘭假日”期間那群穿戴整齊、伴著音樂行進的士兵隊伍)。藝術品(例如丁梅斯代爾公寓有關大衛、巴思謝巴和預言家內森的象征性的《圣經》掛毯)。血(如丁梅斯代爾胸部未治愈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紅色標志”)。
描寫人物的心理沖突是霍桑在《紅字》中運用的又一文學技巧。霍桑不像許多小說家那樣,光描述表層的細節,而是深入一步地分析人物內心的緊張心理。偽君子丁梅斯代爾在腦海中不斷地回憶自己的罪行時,其內心就充滿著悔恨,敏感的良知迫使他半夜起來,徹夜不眠。當奇林沃思開始對丁梅斯代爾實行心理報復時,自己便變成了“魔鬼”。而赫絲特表面上屈從于清教徒的壓力,內心卻在繼續思考著世界上婦女的地位問題。
間接法是霍桑在《紅字》中運用的另一藝術手法。他常常不把問題的正確答案告訴讀者,只是提供多種解決辦法——提供多項選擇,讓讀者自己去尋找正確答案。例如在《紅字》最后一章(第二十四章),他對丁梅斯代爾胸部的“紅色標志”做出多種解釋。三種理論暗示為什么那兒會出現“紅色標志”——其中一種理論解釋牧師的胸部根本就沒有什么紅色標志。
霍桑借用英國偉大的傳奇作家司各特的專門技巧主要有三方面,一是“陌生的”人物出現于故事中,并促使情節復雜化。這種方法有助于制造懸念,使故事神秘化,盡管最后“陌生人”的面紗還是被揭開了。《紅字》中的“陌生人”就是奇林沃思。讀者在小說中很早就知道他是赫絲特的丈夫普林大夫,然而丁梅斯代爾根本不知道。二是霍桑偶爾采用的小人物漫畫式的手法。希賓斯夫人以她考究的服飾并不時地提及森林的魔鬼,就是一幅刻畫得很好的漫畫。三是利用大規模精心策劃的場景,如第一個絞刑臺場景、“新英格蘭假日”活動和第三個絞刑臺場景。
最后,霍桑在《紅字》中還善于運用舞臺技巧。人們常常見到動作仿佛被置于戲劇舞臺的中央,觀眾(讀者)的目光老是盯著這一點發生的動作,耳朵聚精會神地傾聽這兒的所有對白。譬如苦行贖罪中的赫絲特站在絞刑臺上,成了觀眾注目的焦點。人群中抨擊她的女人們不友好地注視著她;“陌生人”好奇地望著她;貝林厄姆總督、威爾遜牧師、丁梅斯代爾牧師等全都盯著她。赫絲特是個靜止的人物,圍繞著她發生了一系列的行動。此外,戲劇性的登場在舞臺上是很重要的。雖然第一章很簡短,但它為赫絲特在第二章的登場制造輿論。第三章接近尾聲時,在丁梅斯代爾要求赫絲特說出情人的姓名之后,他做了“旁白”。赫絲特拒絕供出珀爾的父親的名字,于是松了一口氣的牧師(丁梅斯代爾)低聲地說道:“她不肯講!一顆女人的心的神奇的力量與慷慨!她不肯講!”而觀眾——讀者卻收到了透露秘密的戲劇陳述的全部效果,可是其他“演員”——陽臺上的官員和它下面的人群卻沒有聽見。
正是由于霍桑繼承、借鑒和發展了前輩的文學理論,熟練地運用上述種種文學創作技巧(還不是《紅字》運用的全部技巧),同時,作者在長期的創作實踐中逐漸地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審美觀和創作風格,這使《紅字》贏得了很高的聲譽,盡管經濟收入微不足道。《紅字》自1850年問世以來,一直受到權威評論家們的一致好評,他們盛贊它是霍桑的“代表作”,是“美國文學史上最偉大的小說之一”,更有人稱它為“清教徒的《浮士德》[4]”。同時,它還贏得了美國讀書界的熱烈反響。《紅字》是公認的第一部從美國本身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產生的,并帶有這種條件下形成的特殊思想文化烙印,散發著濃郁的美國鄉土氣息的小說杰作,也是第一部跨出國界,贏得世界聲譽的美國文學名著。一百多年來,《紅字》始終受到世界各國文學愛好者的廣泛喜愛,已成為深受廣大讀者歡迎的世界文學名著。
黃水乞
1994年11月2日于廈門大學
注釋:
[1] 白朗寧(1806—1861):英國女詩人。
[2] 愛倫坡(1809—1849):美國詩人、小說家及評論家。
[3] “政黨分贓制”指美國將政黨大選獲勝后有權委派的官職視為戰利品,以便分配給該黨的有功之臣。
[4] 《浮士德》是德國作家歌德以詩歌形式寫的一個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