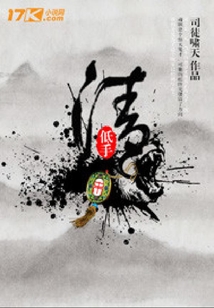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論時局鄭珍暗垂淚
烈日炎炎,漫天黃沙, 一行清軍手持刀槍正朝武昌進發。
屋檐下的兩個文士連連嘆息,其中一個身著緞面長袍,面膚白嫩,油光錚亮的腦門顯得格外神奕,說道:“這大隊清兵入城,想來要與那金田義軍一決武昌,這江下的民農又不免受殃了。”
另一個文士雖說是讀書人,卻生了一副凌人的煞面,瘦且剛健的軀體上著了一件破麻衫,手中偏偏把玩了一絹布折扇,渾與這一身滿不相配,幸災樂禍地說道:“廣西的這群老農氣勢也忒兇!兩月間連占四十座城,眼下武昌保不準就丟了,湖北這地界真個沒法待下去了——我那五年前的案子想必該結了,我便回直隸老家避避難也好,免得顛沛流離!”此人叫董明魁,直隸文安縣人氏,早年在家鄉安穩務農,怎地常被人嘲笑個頭矮挫且受欺侮,故一怒之下遠赴安徽九華山拜師習武,往后不得離山寸步,朝夕十載,終得成就。回到文安縣開設神州武館來授人武學之道,略賺財資,以供糊口。
忽一日,洪門弟子登門踢館,董明魁怕惹是非,故意躲避,爾等便將武館陳設之物盡數銷毀,憤憤而去。時隔整整半個月,幾人又來尋釁,正與董明魁碰個正臉,話休煩絮,便大打出手。最終董明魁失手殺了一人,從此遭了官司。怎地習武之人性格頑劣,哪里愿受那牢獄之災?便連夜收拾細軟之物,挈眷逃離南下。
說來也巧,只因那時北方捻軍正興,府衙便將此案擱置,近年安穩了些,一天董明魁安心游走于集市間,看到了城中布告,是直隸總督署發下的文書,說是抓捕此人以明正典刑。自己本想此案早已遠逝,誰料直隸那邊換了當值官員,誓要立項查處此案,以亮考績。無奈又將家中老小盡遷到太平天國統治地,以防清廷四海追捕。
先前那個文士嘆了口氣,道:“難哪……”董明魁問:“我有何難處?”文士道:“我是說太平軍。如今協理江南軍務的那個人可是個‘硬手腕’,武昌這么重要的地方,少說也埋了數萬清兵,太平軍北伐首戰便是此處,怎能不受重創?”董明魁笑道:“不怕。起義軍里有英王,清廷的人哪個敢和他較勁?”文士道:“明魁兄,你我進店家少座,有些話萬不可在此相談。”
二人進了屋中對立而坐,店家端了清湯面,一盤牛肉伴酒水,以作二人閑聊之資。董明魁早已饑渴,胡亂地吃了幾口酒之后再為那人斟滿了杯,但聽那文士道:“明魁兄剛剛所說的那位英王,還有洪秀全的親兄弟洪仁發,兩個人離奇的失蹤,如今生死還未卜呢。”
董明魁頗有些上心,忙問:“什么原因,是不是被清廷毀尸滅跡了?我看不至于吧……前些月還鬧得嚷嚷,又是擎天柱、又是紫金梁,說的不就是他么?”文士道:“依我看不會,毀尸滅跡對清廷沒有好處,如果是被悄然擄走……那朝廷為何還不布告天下、以定人心——不過據清軍將領分說,最后一次見到二人是在一艘江船上。為了逃脫清兵追擊,那船搖得極快,卻像是在救二人一般。又打聽了太平軍的民農,有的說英王戰死、有的說畏罪潛逃、更有甚者說已投奔了清廷,官拜一品賜花翎,只暫時不便公開,以防輿論升騰爾爾。他們口各不一,實則是無法分辨的。”
董明魁道:“無怪我聽沿街臨坊們說太平軍丟了一個大官,誰丟了卻都不知道,原來丟的是英王,怪可惜這好料子了。”
文士斟滿雙杯酒,遞一支與他,說道:“明魁兄可曾記得宣宗二十二年那道《江寧條約》?”
董明魁聽了最后四個字,心中便炸了鍋似得,恨色乍現于面目,將酒杯往桌上“啪”地一置,說道:“滿清狗和小洋鬼兒立的條約,全國哪個不知,哪個不曉!虧得當年林總督虎門銷煙,到頭來還不順從了鬼子?現今清廷震懾太平軍整日哭爹喊娘地說沒錢,真不如就像肅順說的那般,提取海關鴉片稅!”
那文士連忙提起折扇,展將開來遮住自己的嘴,示意他說話勿要無遮攔,便道:“肅順的這個提議令滿朝文武大臣所鄙夷,此人樹敵甚多,你我出門在外談論時政,莫要教第五只耳聽得,以為你我皆為肅順黨,那便有口也說不清了。”
董明魁哼道:“那待如何?我便瞧那肅六個條漢子!他的提議,依我看哪,都是明政之舉,其余多數官吏墨守成規,只護著自己的利益,忽視了國家根本,這還有得好?就如愚兄適才所說的《江寧條約》,若不是耆英老賊明哲保身,乖哄洋人,又怎會教朝廷如此重負不堪?”
文士道:“勿要怒躁。就算龍駕親赴英國艦船,條約也自是如此,是不可挽回的——條約中的五口通商,兄臺可曾聞說?”
董明魁道:“自然聽過。那便是五口通商,自由貿易,清廷不許多加干涉。哼,這番下來,洋人便可在我土任意橫行了!”
文士道:“五口之中現今只有一處尚未依條例敞開,英國駐我國領事巴夏禮與兩任總督交涉無果,近月他英國海軍艦船于我東海圖謀不軌,蠢蠢欲動,依子尹之見,再僵擱下去……北方必要生出事端來的!明魁兄現今欲北上安家,于我之見并不是上策,還是隨我赴湖北走一遭罷。”原來這文士姓鄭,名珍,字子尹。道光十七年中了舉子,卻一直未入仕途,近年來游走于貴州大小各縣為學子訓導教諭。今只因故友病喪,前來南下吊唁。
董明魁想他讀萬卷書,明晰時局動態尚有幾分見地,自己雖也苦學了多年,卻無能如他那般洞悉朝政,深入人心,便說:“天下之大,我孤獨一人能夠有什么作為呢,北方如若兵動,我便充軍則個。九華山十年鉆修,到頭來卻要將所學之功付之東流,大丈夫有本領又何不為國效力?清廷日益腐朽,我等只可自強自立,才可撥開云霧,方能見月明。”
鄭珍道:“兄長欲要參軍?好教子尹欽佩!你我年歲相當,可子尹只會舞文弄墨,夸夸其談,這些對救國毫無效益,倒不如明魁兄修得一身好本領,投效朝廷,方可實干。”
董明魁略有些慚愧,因為自己曾經與人切磋過武藝,暗地里被人打中了一槍,至此再也不敢小覷洋人的物件。
鄭珍也看出了他的愁容,舉酒借以澆愁,道:“清廷如不換洗改革,滅頂之災便不久矣!”自己說這句話時,‘滅頂之災’四個字壓的極低,董明魁離他寸許都未能聽得到,但話的意思也大概明了,便道:“如果不教清廷好好吃些苦頭,便永自覺為天朝上國,殊不知‘身處深山里,不知何為峰’。”
二人聊得話語甚是投機,怎知這時店中閃進幾位做公的人物,將刀槍倚了,包袱放定,便叫酒肉來吃。聽幾個人的口音象是打京城來的,輕聲細語地談論武昌戰役。有的說:“上頭下了旨意,說是叫請洋人來助,一旦長江以西不保,朝廷與各國的貿易往來便成了一紙空談,你們說洋鬼子能不作急么?”又有人說:“四眼狗敢和洋人叫板?哼,且由他作死!”
董鄭二者見這幾人如信使,并不敢將時政再高談下去,也只顧吃酒。
董明魁道:“你我二人甚是有緣,趕此混亂歲月難中相逢,但此一別不知何時再見,弟弟若此去遙遙無期,定教兄長時常掛念,那時便好不痛苦,倒不如兄弟將日后的去處與我,以便他年相尋。”
鄭珍也早有此意,心想此人日后必成正果,則款款說道:“湖北黃州府,東邊二十里有個羅田縣,我此去也要住上個把月的。羅門莊園的羅公乃吾之舊友,近些年月滿洲人強占土地,計有百畝,羅公本是當地佃戶東家,多怪有個不肖子敗壞門庭,故人亡家破……”
董明魁道:“羅公的父親可是早年羅田縣縣尊大人?世代書香,怎地到了這代如此蕭條?”鄭珍長嘆一聲,說道:“羅門這幾十年來如中詛咒,至縣尊下來的子嗣只有獨枝。其余順產便也夭折。”董明魁一愣,“怎有如此怪事?莫不是縣尊大人生時結了什么孽緣?”
鄭珍突然回顧往事卻不想多說下去,一臉悵然,只一口飲盡觥中酒,待見那幾個做公的離去,遂豁然道:“還不是為了女人!縣尊原本有一妻室,相貌平平卻極為賢惠,陪伴縣尊臘梅寒窗,悠悠十載,寸步不離。”
“日后縣尊中了舉,竟買通了部上,銓選當中做了手腳,最后放了個怪缺——回籍頂官。至此回到老家,人便輕浮了起來。”
“記得嘉慶爺那陣子白蓮教正興,他竟然看中了教派中一女子,身為一縣的大老爺、老父臺,不僅包庇邪教,且與爾等暗中勾結,疏通官道脈絡,匿藏反賊。忽一夜,縣尊與妻同室,借口說:‘朝廷已查明自己的罪行,即將自己縛押進京交與刑部審訊,途中定會被無恥小卒殘害而死,妻如不想茍活于世,你我現下做一對兒苦命鴛鴦于黃泉也好,不知妻意如何?’。妻曰:‘可!’便斟滿毒酒雙杯,縣尊說:‘我兒如今已弱冠,家財之物我已交由他承管,夫人安心便去。’則自己先飲了毒酒,妻見他死得安然,含淚隨之,過不多時便口吐鮮血已斃。待她死絕,縣尊猛地醒神過來,口中念道:‘我羅門一世清廉,既有一妻又怎可納妾?唯今之計,只有你死,我便可明媒正娶,不留外人口舌。朝廷亦可撥發撫恤金與你厚葬,你本農桑出身,可享官屬之禮葬,死也哀榮。’”
董明魁口口聲聲,畢恭畢敬地稱呼縣尊,沒想到從鄭珍口中訴出的竟然是如此狠詐小人,怒得右手如鉗夾般狠狠地將木桌的一角掰開,捏藏在拳里,只一松手,全成了粉末,罵道:“我本以為此人是正值官吏,沒想到能干得出喪盡天良之事,無怪他子嗣個個夭折,如此惡人,斷子絕孫也是該當!”
鄭珍道:“這也是嘉慶年間的事了,來龍巨細我雖不盡全,卻也大概如此。”董明魁直恨得牙癢,忙問:“那廝之后仕途如何?可有被清廷查處?”鄭珍道:“卻也未快活幾年。那時也趕白蓮教沒落,被清廷一鼓作氣地掃盡,他便與那女子一雙殉情跳江了。”董明魁冷笑道:“這廝也是個多情種!他兒子便是你已故的舊友羅公?”
鄭珍道:“正是。羅公知曉父親的昏庸無道,所以在婚姻之上謹記教誨,堅守一妻,日復一日地生活卻也平淡,亦留了枝獨苗,喚啟天,這孩子……”當下黯然地搖了搖頭,眉頭緊皺,續道:“和他先祖一般模樣,寧可為情死,不可為義亡啊!”董明魁聽得一時興起,連吩咐店家再供給酒水伴冰鎮甜瓜來吃,隨即便問:“哦?如何見地?”
鄭珍道:“當年我拜訪羅公之時那孩子剛六歲半,全家上下皆不喜好于他,只因他上,風花雪月,無事不做,且損人話語極其惡劣,可唯羅公偏愛。那時我曾問與他志向,你且猜他如何作答?”董明魁笑道:“莫不是要與皇帝老子那般佳麗千千萬?”
鄭珍一拍大腿,興道:“這話如何之說的!娶得數個內室不止,偏要找個洋小姐來!你說……你說這是否毫無章法、敗壞常倫?從古至今還未見得有人如此冥想——我問他為何要尋金發女郎,他卻說:‘漢子女保守,穿衣不露;洋妞連衣短裙、黑絲長襪,摸著便舒坦!’明魁兄,你瞧瞧,這豈是垂髫之言?活像一登徒子!”
董明魁道:“此乃荒天下之大謬,異國異族豈可結締?將來生出的娃到底是黑頭發,還是黃頭發?”
鄭珍道:“現如今這孩兒也已十六好幾,亦也頑皮。前些年,朝廷明禁八旗年俸,令這些皇家子弟叫苦不堪,各個埋怨。老實本分的多有餓殍,剩下那些輕浮子弟便以各旗投充為名,強占富戶土地,為奴役使,他們連蒙帶騙且動武力。羅公是個對性命極為看重之人,怎可為這些財產棄命?故給了他們,換來平安。八旗等人見他爽快,故給羅家父子抬了旗籍。”
清時旗人各項福利豐厚,可襲官爵,且刑罰不以明正典刑,董明魁頗替那父子欣喜,說道:“這旗籍光照后世,是多少土地也換不來的,倒教他二人撿了實在!”
“唉……”鄭珍道:“這若擱到乾隆老頭子那時候卻是千金難買,不過如此世道,正趕上了太平軍連攻數省,氣勢宏偉,從南京入了安徽,所到之處無不將滿洲人的私產盡收其囊,因為他們恨滿洲人:終日白拿餉祿,無所事事,只知欺侮漢人,好在羅公產下那百畝田地盡散了出去,待太平軍收刮旗人財產時羅公只剩下了莊園一座,怎奈太平軍下令要充公變賣以作軍資,羅公理直氣壯地問是甚緣由不留人安家之所?那邊回曰:‘誰教你是旗人!’,羅公道:‘我祖本乃漢室血統存正,有家譜為證,只也被迫入了滿洲籍貫。’,太平軍道:‘唬誰?天下漢人想入旗的求之不得,你如何被迫?’。”羅公將事態起因講明,太平軍哪里肯信?只道:‘好好的漢人你不做,偏要入旗剝削窮苦人血俸,其心必誅,我等充你莊園,剛好抵了你的罪折!’,羅公從此一蹶不振,收拾一應細軟之物,遣散家仆,搬至鄉下田園,患疾不治,這才亡故。”
董明魁問道:“那孩子如何不肖?”
鄭珍道:“那孩兒痛憤太平軍,在當地縣中創辦了一處團練組織,將家中存留的大小實物一應變賣,招兵買馬,四處灑錢,但也沒能打過一回仗,盡與那些狐朋之黨玩樂是也。一個雜牌軍伴一個無知孩童能打個什么仗來?最后連羅公吃藥錢也花盡,唉……作孽啊!”
董明魁道:“能不能打仗,或勝或敗,且先不論,那孩子尚小卻懂得嫉惡如仇,想來自有一番心術。但過度耗銀,連與父親治病救命的錢也搭盡,卻是不對的。”鄭珍道:“這羅門香火即斷,后世怎地如何,也得指望這孩子了……”
不知何時,外頭也下起了雨,淅淅瀝瀝,正所謂“掃世間之塵土,清身中之濁心”。鄭珍心想這雨又要下個不停歇,吩咐店家切了二斤牛肉包好,清酒一葫。事畢,舉杯敬道:“如此世態,險惡至極,你我塵緣相逢短暫便要相別,飲下此酒,盡作離別詞章。如有他日,你我再見,子尹定要與明魁兄游度后生!”
董明魁心頭一沉,想到離別居然如此之快,心中不免感傷。將杯中酒盡傾在了地上,鄭珍茫然相問:“兄長這是為何?”董明魁道:“這杯酒愚兄萬不能飲,恐有日后生變,你我陰陽相隔。不如暫將情誼寄在酒里,待得再見之時,開封重溫余香!”
鄭珍興道:“妙也!便教這杯酒藏于地下,望開封之時醇香無比!”亦將酒酹了。將包好的酒肉塞了,提起包袱,結了酒錢,方才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