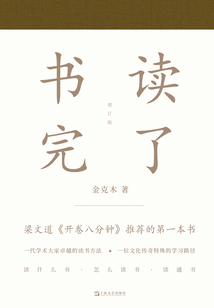
書讀完了
最新章節(jié)
書友吧 4評論第1章 有這樣一個老頭
一
讀書的時候,一個學(xué)哲學(xué)的朋友經(jīng)常到我的宿舍聊天。像任何喜歡書的年輕人一樣,我們的話題最后總是到達(dá)自己心目中的學(xué)術(shù)大家。有一次,他信誓旦旦地對我講,在當(dāng)代中國,只陳寅恪和錢鍾書堪稱大家,其余不足論。他講完后,我小心翼翼地問,這兩人后面,可不可以再加上一個呢?他毫不猶豫地說,不可能,中國再也沒有這個級別的人物了。然后,我給了他一個老頭的小冊子,并且告訴他,我認(rèn)為這個老頭也堪稱大家。
第二天,這位朋友又到我的宿舍來了。他略顯得有些疲憊,但眼睛里卻充滿了光芒。他興沖沖地告訴我,他有點認(rèn)同我的看法了,這個老頭或許可以列到他的當(dāng)代大家名單中。臨走,他又從我的書架上抽去了這個老頭的幾本小冊子。等我書架上這老頭的書差不多被借完的時候,他也開始了辛苦地從各個渠道收集這老頭的書的過程,跟我此前一樣。
不用說,這個老頭就是這本書的作者金克木。為了看到更多如那位朋友樣充滿光芒的眼睛,我起意編這樣一本書。
二
金克木,祖籍安徽壽縣。1912年生于江西,1930年北平求學(xué),1935年在北京大學(xué)圖書館任館員,1938年至香港任《立報》國際新聞編輯,1939年到湖南省立桃源女子中學(xué)和湖南大學(xué)任教。1941年,經(jīng)友人介紹,金克木到印度加爾各答的中文報紙《印度日報》任編輯,1943年至印度佛教圣地鹿野苑鉆研佛學(xué)。1946年,金克木回國任武漢大學(xué)哲學(xué)系教授,1948年起任北京大學(xué)東方語言文學(xué)系教授。1949年之后,金克木的經(jīng)歷跟中國大多數(shù)知識分子沒有什么兩樣。上世紀(jì)七十年代以還,金克木陸續(xù)重印和出版的著作有《印度文化論集》《比較文化論集》《舊學(xué)新知集》《末班車》《探古新痕》《孔乙己外傳》《風(fēng)燭灰》等,譯作有《通俗天文學(xué)》《三自性論》《伐致呵利三百詠》《印度古詩選》《摩訶婆羅多·初篇》等。金克木的一生值得好好寫本傳記,肯定好玩和復(fù)雜得要命。現(xiàn)在,我們來看看這個奇特老頭的幾個人生片斷。
1936年,金克木和一位女性朋友到南京莫愁湖游玩。因女孩淘氣,他們被困在一條單槳的小船上。兩人誰也不會劃船,船被撥得團(tuán)團(tuán)轉(zhuǎn)。那女孩子“嘴角帶著笑意,一幅狡黠神氣,仿佛說,‘看你怎么辦?’”年輕氣盛的金克木便專心研究起了劃船。經(jīng)過短時間摸索,他發(fā)現(xiàn),因為小船沒有舵,槳是兼舵的,“槳撥水的方向和用力的大小指揮著船尾和船頭。明是劃水,實是撥船”。在女孩的注視下,金克木應(yīng)對了人生中一次小小的考驗。
1939年,金克木在湖南大學(xué)教法文,暑假去昆明拜訪羅常培先生。羅常培介紹他去見當(dāng)時居于昆明鄉(xiāng)間,時任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的傅斯年。見到傅斯年,“霸道”的傅所長送他一本有英文注解的拉丁文《高盧戰(zhàn)記》,勸他學(xué)習(xí)。金克木匆匆學(xué)了書后所附的拉丁語法概要,就從頭讀起來。“一讀就放不下了。一句一句啃下去,越來興趣越大。真是奇妙的語言,奇特的書。”就這樣,金克木學(xué)會了拉丁文。
上世紀(jì)四十年代,金克木在印度結(jié)識“漢學(xué)”博士戈克雷。其時,戈克雷正在校勘梵本《集論》,就邀請金克木跟他合作。因為原寫本殘卷的照片字太小、太不清楚,他們就嘗試從漢譯本和藏譯本先還原成梵文。結(jié)果,讓他們吃驚的“不是漢譯和藏譯的逐字‘死譯’的僵化,而是‘死譯’中還有各種本身語言習(xí)慣的特點。三種語言一對照,這部詞典式的書的拗口句子竟然也明白如話了,不過需要熟悉他們各自的術(shù)語和說法的‘密碼’罷了”。找到了這把鑰匙,兩人的校勘工作越來越順利。
上面三個故事,看起來沒有多大的相關(guān)性,但如果不拘泥于表面的聯(lián)系,而把探詢的目光深入金克木思考和處理問題的方法,這些不相關(guān)的文字或許就會變得異常親密。簡單說,這種方法是“眼前無異路”式的,集全部心力于一處,心無旁騖,解決目前遇到的問題。上世紀(jì)七十年代末,金克木把自己解決問題的特殊方法和豐富人生經(jīng)歷結(jié)合起來,寫出了一篇篇珠玉之文。我們選編這本書的目的,就是把這些珠玉相關(guān)聯(lián)的一些收集起來,看能否穿成一條美麗的項鏈。在編選過程中,我小心翼翼地克制自己,盡量把選文控制在談讀書的范圍內(nèi)——否則,這個選本將是全集的規(guī)模。
三
在一個知識越來越復(fù)雜,書出版得越來越多的時代,我們首先關(guān)心的當(dāng)然是讀什么書。如果不加揀擇,見書就讀,那每天以幾何數(shù)量增長的圖書,恐怕會炸掉我們的腦子,還免不了莊子的有涯隨無涯之譏。那么,該選擇哪些書來讀,又如何讀懂呢?
“有人記下一條軼事,說,歷史學(xué)家陳寅恪曾對人說過,他幼年時去見歷史學(xué)家夏曾佑,那位老人對他說:‘你能讀外國書,很好;我只能讀中國書,都讀完了,沒得讀了。’他當(dāng)時很驚訝,以為那位學(xué)者老糊涂了。等到自己也老了時,他才覺得那話有點道理:中國古書不過是那幾十種,是讀得完的。說這故事的人也是個老人,他賣了一個關(guān)子,說忘了問究竟是哪幾十種。現(xiàn)在這些人都下世了,無從問起了。”可是,光“中國古書”就“浩如煙海”,“怎么能讀得完呢?誰敢夸這海口?”夸這海口的,正是嗜好猜謎的金克木——“只就書籍而言,總有些書是絕大部分的書的基礎(chǔ),離了這些書,其他書就無所依附,因為書籍和文化一樣總是累積起來的。因此,我想,有些不依附其他而為其他所依附的書應(yīng)當(dāng)是少不了的必讀書或則說必備的知識基礎(chǔ)。”“若為了尋求基礎(chǔ)文化知識,有創(chuàng)見能獨立的舊書就不多了。”就中國古書而言,不過是《易》《詩》《書》《左傳》《禮記》《論語》《孟子》《荀子》《老子》《莊子》等數(shù)種;就外國書而言,也不過《圣經(jīng)》《古蘭經(jīng)》和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笛卡爾、狄德羅、培根、貝克萊、康德、黑格爾、荷馬、但丁、塞萬提斯、莎士比亞、歌德、巴爾扎克、托爾斯泰等人的著作。
略微深入接觸過上列之書的人都不免生疑,這些“‘太空食品’一樣的書,怎么消化?”選在第一輯里的文章,前一部分是金克木勾畫的“太空食品”譜系,有了這個譜系,我們可以按圖索驥,不必在枝枝杈杈的書上枉費精神。后一部分,則是對這些書的消化之道,體現(xiàn)了金克木自己主張的“生動活潑,篇幅不長”風(fēng)格,能讓人“看懂并發(fā)生興趣”。認(rèn)真看完這些文章,直接接觸原作(即便是抽讀或跳讀),再配合簡略的歷史、哲學(xué)史、文學(xué)史之類,“花費比‘三冬’多一點的時間,也可以就一般人說是‘文史足用’了”。照此方法讀下去,不知道我們是不是有幸某天會驚喜地發(fā)現(xiàn)——“書讀完了”。
可是,古代的書跟我們的時代差距那么大,西方的書跟我們的思維習(xí)慣那樣不同,印度的書有著各種不可思議的想象,如何拆除這些壁壘,明白作者的弦外之音,從容地進(jìn)入書的世界,跟那些偉大的寫作者共同探討人心和人生的奧義呢?金克木提供的方法是“福爾摩斯式讀書法”與“讀書得間”——這是本書第二輯的內(nèi)容。
四
在金克木看來,要真正讀懂一本書,不能用“兢兢業(yè)業(yè)唯恐作者打手心讀法,是把他當(dāng)作朋友共同談?wù)摰淖x法,所以也不是以我為主的讀法,更不是以對方為資料或為敵人的讀法。這種談?wù)撌降淖x法,和書對話……是很有趣味的”。“一旦‘進(jìn)入角色’,和作者、譯者同步走,盡管路途坎坷,仍會發(fā)現(xiàn)其中隱隱有福爾摩斯在偵探什么。要求剖解什么疑難案件,猜謎,辯論,宣判。”這里面有兩層意思,一層是要有尚友古人的胸襟和氣魄,敢于并且從容地跟作者交朋友(卻并不自認(rèn)能比作者更好地理解他本人);一層是跟著作者的思路前進(jìn),看他對問題的描述或論證能否說服我們。這樣做也有兩重收獲,一是讀書時始終興致昂然,二是讀會的書就成了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有字的部分有了方法,怎么讀那些書間的空白呢?——這或許是一個更大的問題。
“古人有個說法叫‘讀書得間’,大概是說讀出字里行間的微言大義,于無字處看出字來。其實行間的空白還是由字句來的;若沒有字,行間空白也沒有了。”“古書和今書,空白處總可以找出問題來的。不一定是書錯,也許是在書之外,總之,讀者要發(fā)現(xiàn)問題,要問個為什么,卻不是專挑錯。”這就是金克木的“得間讀書法”。用這個方法讀書,可以明白寫書者的苦心孤詣和弦外之音,進(jìn)而言之,說不定還會發(fā)現(xiàn)古人著述的秘密。
金克木曾提到佛教文獻(xiàn)的一個特點:“大別為二類,一是對外宣傳品,一是內(nèi)部讀物。”照此分類,金克木認(rèn)為,佛教文獻(xiàn)里的“經(jīng)”,大多是為宣傳和推廣用的,是“對外讀物”。“內(nèi)部讀物”首先是“律”,其次是算在“論”里的一些理論專著,另外就是經(jīng)咒。如此一來,佛教典籍,除了“經(jīng)”,竟大部分是“對內(nèi)”的(“經(jīng)”里還包含很多對內(nèi)部分)。對內(nèi)的原因,或是記載了“不足為外人道”的內(nèi)容,外人最好不要知道;或是滿紙術(shù)語、公式,討論的問題外人摸不到頭腦,看了也不懂。更深層的原因是,“佛教理論同其他宗教的理論一樣,不是尚空談的,是講修行的,很多理論與修行實踐有關(guān)。當(dāng)然這都是內(nèi)部學(xué)習(xí),不是對外宣傳的”。
“不但佛書,其他古書往往也有內(nèi)外之別。講給別人聽的,自己人內(nèi)部用的,大有不同。這也許是我的謬論,也許是讀古書之一訣竅。古人知而不言,因為大家知道。”在金克木看來,恍兮惚兮的《老子》和思維細(xì)密的《公孫龍子》,里面本有非常實在的內(nèi)容,“不過可能是口傳,而記下來的就有骨無肉了”。現(xiàn)在覺得淺顯,仿佛什么人都能高談一番的《論語》,也因為“是傳授門人弟子的內(nèi)部讀物,不像是對外宣傳品,許多口頭講授的話都省略了;因此,書中意義常不明白”。連公認(rèn)為歷史作品、仿佛人人了解的《史記》,金克木也看出是太史公的“發(fā)憤之作”,所謂“傳之其人”,就是指不得外傳。正因如此,書中的很多問題,“‘預(yù)流’的內(nèi)行心里明白,‘未入流’的外行莫名其妙”。知道了這些古人的行間甚至字間空白,或許書才會緩緩地敞開大門,迎我們到更深遠(yuǎn)的地方去。
當(dāng)然,讀過了書,如果不能讓書活在當(dāng)下,“日日新,又日新”,那也不過是“兩腳書櫥”。如何避免這個問題,怎樣才能在書和現(xiàn)實的世界里出入無間?這正是本書第三輯的內(nèi)容——“讀書·讀人·讀物”。
五
金克木寫過一篇題為《說通》的小文章,里面說:“中國有兩種文化,一個可叫‘長城文化’,一個可叫‘運河文化’。‘長城文化’即隔絕、阻塞的文化。運河通連南北,是‘通’的文化。”對社會,對讀書,金先生都反對隔絕、阻塞的長城文化,倡導(dǎo)“通”的運河文化。
金克木出版的單行本中,如《舊學(xué)新知集》《探古新痕》《蝸角古今談》等,書名都蘊(yùn)含著“古”“今”“新”“舊”的問題。如他自己所說,他的文章,“看來說的都是過去……可是論到文化思想都與現(xiàn)在不無關(guān)聯(lián)”。“所讀之書雖出于古而實存于今……所以這里說的古同時是今。”金克木關(guān)注的,始終是古代與現(xiàn)在的相通性,且眼光始終朝向未來。對他來說,“所有對‘過去’的解說都出于‘現(xiàn)在’,而且都引向‘未來’”。脫離了對“現(xiàn)在”的反應(yīng)和對未來的關(guān)注,古書不過是輪扁所謂“古人之糟粕”,棄之不足惜的。
只是,在金克木看來,單單讀通了書還不行,“物是書,符號也是書,人也是書,有字的和無字的也都是書”,因此需要“讀書·讀人·讀物”。“我讀過的書遠(yuǎn)沒有聽過的話多,因此我以為我的一點知識還是從聽人說話來的多。其實讀書也可以說是聽古人、外國人、見不到面或見面而聽不到他講課的人的話。反過來,聽話也可以說是一種讀書。也許這可以叫作‘讀人’。”“讀人”很難,但“不知言,無以知人也”,“知言”正是“知人”和“知書”的重要一步。最難的是讀物,“物比人、比書都難讀,它不會說話;不過它很可靠,假古董也是真東西”。“到處有物如書,只是各人讀法不同。”讀書就是讀人,讀人就是讀物,反過來,讀物也是讀人,讀人也是讀書。這種破掉壁壘的讀書知世方法,大有古人“萬物皆備于我”的氣概,較之“生死書叢里”的讀書人,境界要雄闊得多。
錢鍾書力倡“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xué)北學(xué),道術(shù)未裂”,意在溝通東西,打通南北,要人能“通”。金克木“讀書·讀人·讀物”的“通”,與錢鍾書的東西南北之“通”,是一是二,孰輕孰重,頗值得我們好好思量。毫無疑問的是,有了這個“讀書·讀人·讀物”的通,金克木那些看起來不相聯(lián)屬的人生片斷和東鱗西爪的大小文章,就有了一個相通的根蒂。
當(dāng)然,書是否真的能夠讀完,書、人和物是不是真的能通,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的事,要親身體味領(lǐng)受才好。能確定的只是,金克木提示了一個進(jìn)入書的世界的方便法門。
六
臨了,要說明一下書中數(shù)字、標(biāo)點的用法和文章的寫作年份問題。為尊重原作,我們不對金克木先生與現(xiàn)行規(guī)定不一致的數(shù)字和標(biāo)點符號用法強(qiáng)做統(tǒng)一,而是按其習(xí)慣照排。文章末尾原有年份的,一仍其舊。部分未標(biāo)明年份的,編者根據(jù)各種資料推定寫上,為與原標(biāo)年份區(qū)別,加括號——如(一九八四年)——標(biāo)明。另有少數(shù)年份尚難確定的,闕疑。部分文章在發(fā)表之后,結(jié)集時金先生另加了“評曰”,或指點文章讀法,或又出新意,本書一起收入,以觀其妙。
最后,感謝金木嬰女士授權(quán)此書出版,并應(yīng)編者之邀寫了后記。
黃德海
2005年12月寫
2016年10月改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