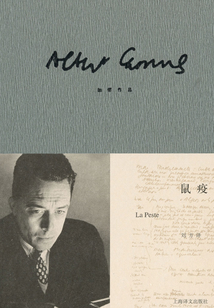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 16評論第1章
用別樣的監禁生活再現某種監禁生活,與用不存在的事表現真事同等合理。
——丹尼爾·笛福
一
構成此編年史主題的奇特事件于194年發生在阿赫蘭。普遍的意見認為,事件不合常規,有點離譜。乍一看,阿赫蘭的確是一座平常的城市,是阿爾及利亞濱海的法屬省省會,如此而已。
應當承認,這座城市本身很丑陋。看上去平平靜靜,需要費些時間才能察覺,是什么東西使它有別于各種氣候條件下的那么多商埠。怎能讓人想像出一座,比如,既沒有鴿子,也沒有樹木,也沒有花園的城市?在那里你既看不見鳥兒撲打翅膀,也聽不見樹葉沙沙作響,總之,那是個毫無色彩的地方。季節的變化只能在天上顯現出來。只有清新的空氣或小商販從郊區帶回的一籃籃鮮花可以宣告春天來臨;那是市場上出售的春天。整個夏天,太陽像火一般燒灼著干燥之極的房屋,給墻壁蓋上一層灰色的塵土;于是,人們只能在關得嚴嚴實實的護窗板的保護下過日子。相反,秋天一到,這里是大雨滂沱,泥濘遍地。晴朗的日子只在冬季姍姍來臨。
要了解一個城市,較簡便的方式是探索那里的人們如何工作、如何戀愛、如何死亡。在我們這個小城里,也許是氣候的作用,那一切都是同時進行的,神氣都一樣,既狂熱,又心不在焉。也就是說,人們在城里感到厭倦,但又努力讓自己養成習慣。我們的同胞工作十分辛苦,但永遠是為了發財。他們對商貿的興趣尤其濃厚,用他們的話說,最重要的營生是做買賣。當然,他們也享受凡人的生活樂趣,他們愛女人、愛看電影、愛洗海水浴。然而,他們非常理智地把享樂的時間留給禮拜六晚上和禮拜天,一星期里別的日子,他們要盡心盡力去賺錢。黃昏時分,他們離開辦公室,定時去咖啡店聚會,去同一條林蔭大道上散步,或去自己的陽臺。年輕人的欲求強烈而短暫,年齡大些的人有壞習慣也無非是參加球迷協會的活動、聯誼會的宴席,去俱樂部靠摸紙牌的手氣狂賭一番。
有人一定會說,那一切都不是我們這個城市特有的,總之,當代人全都如此。在今天,看見人們從早到晚工作,然后決定去玩牌、喝咖啡、聊天,以打發生活中剩下的時間,恐怕再沒有比這更正常的事了。然而卻有一些城市,一些地區,那里的人們會時不時臆想點別的事。一般說,這并不會改變他們的生活。但畢竟有過臆想,而有了這一點就永遠比別的強。阿赫蘭卻相反,它似乎是個毫無臆想的城市,即是說,它是個純粹的現代城市。因此,沒有必要確切介紹我們這兒的人們如何相愛。男人和女人,要么在所謂的做愛中飛快地互相滿足,要么雙雙安于長期的夫妻生活。在這兩個極端之間,幾乎沒有折中。這也并不獨特,在阿赫蘭跟在其他地方一樣,由于缺乏時間,也缺少思考,人們不得不相愛而又不知道在相愛。
在我們這個城市,更獨特的是死亡時可能遇到的困難。不過,困難二字用得并不恰當,說不舒服也許更確切些。生病從來就是不愉快的事,但在一些城市、一些地區,你生病時會有人幫助你;在那些地方,人在生病時幾乎可以聽之任之。病人需要溫馨,他喜歡有所依靠,這是非常自然的。然而在阿赫蘭,極端惡劣的氣候、大量的生意往來、毫無可取之處的環境、黃昏降臨之迅速以及取樂的質量,一切都要求健康的體魄。在那里,連生病的人都倍感孤獨,垂死的人就可想而知了,他像掉進陷阱一般困在幾百堵熱得噼啪作響的墻壁后邊,而與此同時,全體居民都在電話上或咖啡店里談票據、談提單和貼現!大家即將明白,當死亡猝然來到一個乏味的地方,人在死亡時,甚至在現代生活條件下死亡時,可能會有怎樣難受的感覺。
我指出的這幾點也許可以使人對我們的城市有一個相當清楚的概念了。但任何事情畢竟都不應該夸張。需要強調的是,這個城市的市容和這里的生活面貌都很平庸。不過一旦養成了習慣,大家也不難打發日子。既然這個城市恰好對養成習慣有利,我們就可以說一切都還不錯。從這個角度看,生活無疑算不上極有情趣,但我們這里至少見不到混亂。而且這里的居民坦率、討人喜歡、勤快,總能贏得去那里旅行的人們適當的尊重。這個既不別致,又無樹木,而且缺乏活力的城市,到頭來竟仿佛能使人悠閑自在,總之,人們在那里可以沉沉地睡過去。然而,必須加上這點才是公正的:這個城市鑲嵌在無與倫比的景色之中,它坐落在一個光禿禿的高地中央,高地四周是陽光燦爛的丘陵。城市前面是美不勝收的海灣。可惜此城是背對海灣建造的,因此,除非前去尋找,誰都不可能瞥見大海。
介紹到這里,誰聽了都不難相信,我們的同胞無論如何也不可能預見這年春天會發生那些小事變,而那些小事變我們后來才明白正是筆者打算在此為之撰寫歷史的一系列嚴重事件的先兆。對某些人來說,這里發生的事情似乎十分正常,別的人卻恰恰相反,認為那簡直難以置信。但無論如何,一個寫編年史的作者是不會考慮這些互相矛盾的看法的。他的任務僅僅是說:“此事發生了。”只要他知道此事的確發生了,知道這與整個民族生死攸關,知道因此會有成千上萬的目擊者內心里認為他所講之事真實無誤。
此外,倘若他不曾有機遇去搜集一定數量的陳述詞,倘若當時的形勢未曾將他卷入他意欲詳述的那些事件里,筆者(人們會及時認識他的)就幾乎沒有資格從事這個工作。正是這一點使他有理由做史學家所做的事。當然,史學家,哪怕是業余的,手頭總有些文獻。所以講述這個故事的人也有他自己的資料:首先是他本人的證詞,其次是別人的證詞,因為他扮演的角色使他有可能搜集這段歷史中所有人物的心里話,最后是終于落到他手里的文字材料。他打算在他認為適當的時候查考那些資料,并在樂意的時候加以利用。他還打算……不過,也許到了把評論和謹慎措辭拋在一邊而最終講述故事本身的時候了。對頭幾天的敘述需要作些細節描寫。
4月16日清晨,貝爾納·里厄大夫從他的診所走出來,在樓梯平臺上被一只死老鼠絆了一下。他當時把老鼠踢開,并沒有特別留神,便走下了樓梯。但來到大街上,他突然想到這只老鼠不對頭,便往回走,想提醒門房。老米歇爾先生的反應,使他更清楚地意識到他的發現有非同尋常之處。他原以為存在這只死老鼠顯得有些奇怪,如此而已,但門房卻認為出現死老鼠簡直是奇恥大辱。再說,門房的態度斬釘截鐵:這幢房屋沒有老鼠。大夫向他保證說,二樓平臺上就有一只,而且可能已經死了,說了也白搭,米歇爾先生依然信心十足。這幢樓沒有老鼠,因此,這只老鼠準是誰從外面帶進來的。總而言之,那是惡作劇。
這天晚上,貝爾納·里厄站在大樓的走廊上掏自己的鑰匙準備上樓進家,他看見一只碩大的老鼠突然從黑暗的走廊盡頭爬出來,步態不穩,皮毛濕漉漉的。那小動物停下來,仿佛在尋求平衡,然后往大夫這邊跑,又一次停下,原地轉了個圈,輕輕叫了一聲,終于撲到地上,從半張開的雙唇間吐出血來。大夫沉思著看了它一會兒,上樓回到家里。
他思索的并不是那只老鼠。是老鼠咯出的血又勾起了他的心事。他的妻子已病了一年,明天要啟程去一家山中的療養院。他見妻子按照他的要求正躺在床上。看來她是在為旅行的勞累作準備。
“我感覺挺好。”她微笑著說。
大夫注視著在床頭燈光下朝他轉過來的臉龐。在里厄眼里,盡管她已經三十歲了,而且留著病痛的痕跡,但她的臉仍然跟少女時一樣,也許是因為這微笑消除了其余的一切吧。
“你要能睡就睡吧,”他說,“女看護十一點來,我送你們去乘中午的火車。”
他親了親她微微潮濕的額頭。她微笑著目送他走到門邊。
翌日,即4月17日,八點,門房攔住經過他身邊的大夫,指責一些惡作劇的人又把三只死老鼠放在走廊的中間。那些人準是靠大捕鼠器抓住它們的,因為老鼠們渾身是血。門房已在門口站了一陣,手里提著死老鼠的爪子;他在等待那些罪人說挖苦話時自我暴露。但什么也沒有發生。
“噢,那些家伙!”米歇爾說,“到頭來我準能抓住他們。”
里厄感到蹊蹺,便決定從環城街區開始他的巡回醫療,因為他那些最窮困的病人都在這一帶居住。在這些街區收垃圾晚得多,他的汽車沿著街區一條條筆直的塵土飛揚的街道往前行駛,車身緊挨著留在人行道上的垃圾桶。在他經過的一條街上,他數了數,有十二只死老鼠扔在殘羹剩菜和臟布碎片當中。
他要診治的第一個病人正躺在床上。房間臨街,既是臥室,同時又是飯廳。病人是位西班牙老人,滿臉皺紋,神態嚴峻。他面前的被子上放著兩個盛滿鷹嘴豆的鍋。大夫進屋時,半坐在床上的呼吸急促的哮喘病人往后一仰,想重新緩過氣來。病人的妻子端來一個盆子。
“哎,大夫,”在打針時,病人說,“它們都出洞了,您看見了嗎?”
“沒錯,”女人說,“鄰居撿了三只。”
老頭搓搓手。
“它們出來了,所有的垃圾箱里都能看見。是餓的!”
后來,里厄隨便在哪里都能聽到類似的話,街區里人人都在談論老鼠。診治病人結束后,他回到家里。
“上面有您一份電報。”米歇爾先生說。
大夫問他是否見到過很多老鼠。
“哦,沒有!”門房說,“我在監視呢,您懂我的意思。那些畜生不敢來。”
電報通知里厄,說他母親翌日到達這里。她準備在生病的兒媳婦出門期間來這里照顧兒子的家務。大夫進屋時,女看護早已來到。里厄瞧見他的妻子略施脂粉,正穿著套裙站在那里。他對她微微一笑。
“這很好,”他說,“好極了。”
片刻之后,在火車站,他把她安置在臥車里。她看看車廂。
“對我們來說這太貴了,對吧?”
“需要這樣。”里厄說。
“鬧老鼠是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有些奇怪,但會過去的。”
他隨即快快地對她說,他請她原諒,本應該由他來照顧她,他對她太不關心了。她搖搖頭,好像示意他不要說了,但他補充說:
“你回家時,一切都會好些。我們要從頭開始。”
“是的,”她眼睛發著亮光說,“我們要從頭開始。”
片刻過后,她背轉身,透過窗玻璃看外面。月臺上,人群熙熙攘攘,推來搡去。火車頭的噓噓聲傳到他們這里。他叫她的名字,當她轉過身來時,他看見她淚流滿面。
“別這樣。”他輕輕說。
淚水下重又綻出了微笑,但有點不自然。她深深吸了一口氣:
“走吧,一切都會好起來。”
他把她緊緊抱在懷里。現在,他站在月臺上,在窗玻璃的這面,他只能看見她的微笑。
“請你好好保重啊!”他說。
然而她聽不見他說話。
在車站月臺的出口附近,里厄碰上了預審法官奧東先生,他領著自己的小兒子。大夫問他是否出門旅行。這位高個子黑頭發的法官一半像過去所謂的上流社會人士,一半像殯儀館埋死人的人,他用和藹的口氣簡短地回答說:
“我在等奧東太太,她專程看望我的家屬去了。”
汽笛長鳴。
“老鼠……”法官說。
里厄朝火車的方向看了看,但又回過頭來望望出口處。
“是老鼠,”他說,“這不算什么。”
此刻他記得最清楚的,是一個鐵路搬運工人經過時腋下夾著一個裝滿死老鼠的盒子。
當天下午,里厄剛開始診病便接待了一位年輕人,有人說他是記者,一早就來診療室了。他名叫雷蒙·朗貝爾。他身材矮小,雙肩又厚又寬,面容顯得剛毅,有一雙明亮而聰慧的眼睛;他穿一身運動服式的衣裳,生活似乎很寬裕。他談話直截了當。他為巴黎一家大報調查阿拉伯人的生活情況,想得到有關他們衛生狀況的資料。里厄對他說,他們的衛生情況不妙。但他在進一步詳談之前想知道,這位記者是否能夠說真話。
“那當然。”記者說道。
“我的意思是,您能不能對此情況進行全面譴責?”
“全面,不行,這一點應當說清楚。不過,我料想這樣的譴責并沒有什么根據。”
里厄不慌不忙地說,像這樣的譴責的確可能沒有根據,然而在提這個問題時,他只想知道,朗貝爾的證詞能不能毫無保留。
“我只承認毫無保留的證詞,所以我不能用我的有關資料支持您的證詞。”
“這是圣茹斯特[1]的語言。”記者笑道。
里厄并不提高嗓門,說,是否是圣茹斯特的語言,他不知道,但那是一個對他生活的世界感到厭倦的人的語言,不過這個人和其他的人有同樣的看法,而且決心在他這方面拒絕不公正,拒絕讓步。朗貝爾聳聳肩,注視著大夫。
“我相信我理解您。”他最后說,同時站起身來。
大夫把他送到門邊:
“我感謝您這樣看待事物。”
朗貝爾似乎焦躁起來:
“好,”他說道,“我明白。原諒我打擾了您。”
大夫握住他的手說,眼下城里發現了大量的死老鼠,也許可以就這件事寫一篇不尋常的報道。
“哦!”朗貝爾歡呼道,“我對這個感興趣。”
十七點,大夫正為新一輪出診走出家門時,在樓梯上碰見了一個還算年輕的男人,此人外貌敦厚,肥厚的面孔呈凹形,還有兩道濃眉。大夫時不時在住這幢大樓頂層的西班牙舞蹈演員家里遇見他。這個名叫讓·塔魯的人在階梯上專心地吸著煙,同時觀察著他腳邊的一只正在死去的抽搐著的老鼠。他抬起頭,用灰色的眼睛冷靜地、有點專注地看看大夫,向他問好并補充說,這些老鼠的出現是件怪事。
“是的,”里厄說,“但這事兒到頭來會讓人感到惱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