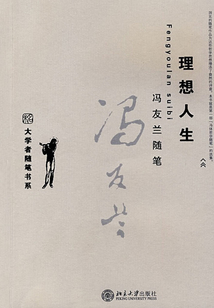
馮友蘭隨筆:理想人生
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一種人生觀(1)
引言
“民國”十二年,中國思想界中的一件大事,自然要算所謂“人生觀之論戰”了。“丁在君先生的發難,唐擘黃先生等的響應,六個月的時間,二十五萬字的皇皇大文”,構成了這“論戰”。而且“這一戰不比那一戰”,這“論戰”里所包含的問題,據唐擘黃先生調查,共有一十三個之多。因為所包含的問題多,所以這個“論戰”格外熱鬧,但是因為太熱鬧了,所以“使讀者‘如墜五里霧中’,不知道論點所在”。胡適之先生說:“這一次為科學作戰的人——除了吳稚暉先生——都有一個共同的錯誤,就是不曾具體地說明科學的人生觀是什么,卻抽象地力爭科學可以解決人生觀的問題。”不但如此,哪一方面人也沒有具體地說明非科學的人生觀是什么,卻也只抽象地力爭科學不可以解決人生觀的問題。張君勱先生說:“同為人生,因彼此觀察點不同,而意見各異。”他隨后舉了二十四種不同的意見,以為說明;但卻沒有具體地說明他“自身良心之所命”的“直覺的”人生觀是與何種相似。所以這次“論戰”雖然波及的問題很多,而實際上沒有解決一個問題。我這篇文章是打算具體地說出“一種人生觀”。至于這“一種人生觀”與這些解決人生問題之方法,是“科學的”,或是“直覺的”,還請讀者批評。
人生之真相
人生之真相是什么?我個人遇見許多人向我問這個問題。這個“像煞有介事”的大問題,我以為是不成問題。凡我們見一事物而問其真相,必因我們是局外人,不知其中的內幕。報館訪員,常打聽政局之真相;一般公眾,也常欲知政局之真相。這是當然的,因為他們非政局之當局者。至于實際上的總統總理,卻不然了。政局之真相,就是他們的舉措設施;他們從來即知之甚悉,更不必打聽,也更無從打聽。這是一個極明顯的比喻。說到人生,亦復如是。人生之當局者,即是我們人。人生即是我們人之舉措設施。“吃飯”是人生,“生小孩”是人生,“招呼朋友”也是人生。藝術家“清風明月的嗜好”是人生,制造家“神工鬼斧的創作”是人生,宗教家“覆天載地的仁愛”也是人生。這幾個名詞,見吳稚暉先生:《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問人生是人生,講人生還是人生,這即是人生之真相。除此之外,更不必找人生之真相,也更無從找人生之真相。若于此具體的人生之外,必要再找一個人生真相,那真是宋儒所說“騎驢覓驢”了。我說:“人生之真相,即是具體的人生。”
人生之目的
不過如一般人一定不滿意于這個答案。他們必說:“姑假定人生之真相,即是具體的人生,但我們還要知道為什么有這個人生。”實際上一般人問“人生之真相,果何如乎”之時,他們心里所欲知者,實是“為什么有這個人生”。他們非是不知人生之真相,他們是要解釋人生之真相。哲學上之大問題,并不是人生之真相之“如何”——是什么,而乃是人生之真相之“為何”——為什么。
不過這個“為”字又有兩種意思:一是“因為”,二是“所為”,前者指原因,后者指目的。若問:“因為什么有這個人生?”對于這個問題,我們也只能說:“人是天然界之一物,人生是天然界之一事。”若要說明其所以,非先把天然界之全體說明不可。現在我們的知識,既然不夠這種程度,我這篇小文,尤其沒有那個篇幅。所以這個問題,只可存而不論。現在一般人所急欲知者,也并不是此問題,而乃是人生之所為——人生之目的。很有許多人以為:我們若找不出人生之目的,人生即沒有價值,就不值得生。我現在的意思以為:人生雖是人之舉措設施——人為所構成的,而人生之全體,卻是天然界之一件事物。猶之演戲,雖其中所演者都是假的,而演戲之全體,卻是真的——真是人生之一件事。人生之全體,既是天然界之一件事物,我們即不能說他有什么目的,猶之乎我們不能說山有什么目的,雨有什么目的一樣。目的和手段,乃是我們人為的世界之用語,不能用之于天然的世界——另一個世界。天然的世界以及其中的事物,我們只能說他是什么,不能說他為——所為——什么。有許多持目的論的哲學家,說天然事物都有目的。亞里士多德說:“天地生草,乃為畜牲預備食物;生畜牲,乃為人預備食物或器具。”(見所著《政治學》)不過我們于此,實在有點懷疑。有人嘲笑目的論的哲學家說:“如果什么事都有目的,人所以生鼻,豈不也可以說是為架眼鏡么?”目的論的說法,我覺得還有待于證明。
況且即令我們采用目的論的說法,我們也不能得他的幫助,即令我們隨著費希特(Fichte)說“自我實現”,隨著柏格森(Bergson)說“創化”,但我們究竟還不知那“大意志”為——所為——什么要實現,要創化。我們要一定再往下問,也只可說:“實現之目的,就是實現;創化之目的,就是創化。”那么,我們何必多繞那個彎呢?我們簡直說人生之目的就是生,不就完了么?唯其人生之目的就是生,所以平常能遂其生的人,都不問為——所為——什么要生。莊子說:“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趻踔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炫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炫謂蛇曰:‘吾以萬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耶?吾安用足哉?’”(《秋水》)“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正是一般人之生活方法。他們不問人生之目的是什么,而自然而然地去生;其所以如此者,正因他們的生之目的已達故耳。若于生之外,另要再找一個人生之目的,那就是莊子所說:“泉涸;魚相與處于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天運》)
不過若有人一定覺得若找不出人生之所為,人生就是空虛,就是無意義,就不值得生,我以為單從理論上不能說他不對。佛教之無生的人生方法,單從理論上,我們也不能證明他是錯誤。若有些對于人生有所失望的人,如情場失意的癡情人之類,遁入空門,借以做個人生之下場地步,或有清高孤潔之士,真以人生為虛妄污穢,而在佛教中另尋安身立命之處;我對于他們,也只有表示同情與敬意。即使將來世界之人,果如梁漱溟先生所逆料,皆要皈依印度文化,我以為我們也不能說他們不對。不過依我現在的意見,這種無生的人生方法,不是多數人之所能行。所以世上盡有許多人終日說人生無意義,而終是照舊去生。有許多學佛的和尚居士,都是“無酒學佛,有酒學仙”。印度文化發源地之印度,仍是人口眾多,至今不絕。所以我以為這種無生的人生方法,未嘗不是人生方法之一種,但一般多數人自是不能行,也就無可如何了。
活動與欲
人生之目的是“生”,“生”之要素是活動。有活動即是生,活動停止即是死。不過此所謂活動,乃依其最廣之義。人身體的活動,如穿衣走路等,心里的活動,如思維想象等,皆包括在內。
活動之原動力是欲。此所謂欲,包括現在心理學中所謂沖動及欲望。凡人皆有一種“不學而能”的原始的活動,或活動之傾向,即是所謂本能或沖動。沖動是無意識的:雖求實現,而不知所實現者是什么;雖系一種要求,而不知所要求者是什么。若沖動而含知識因素,不但要求,而且對于所要求者,有相當之知識,則即是所謂欲望。沖動與欲望雖有不同,而實屬一類。中國之欲字,似可包括二者,比西洋所謂欲望,范圍較大。今此所謂欲,正依其最廣之義。人皆有欲,皆求滿足其欲。種種活動,皆由此起。
近來頗有人說:情感是吾人活動之原動力。如梁任公先生說:“須知理性是一件事,情感又是一件事。理性只能叫人知道某件事該做,某件事該怎樣做法,卻不能叫人去做事;能叫人去做事的,只有情感。我們既承認世界事要人去做,就不能不對于情感這樣東西十分尊重。既已尊重情感么,老實不客氣,情感結晶,便是宗教化。一個人做按部就班的事,或是一件事已經做下去的時候,其間固然容得許多理性作用。若是放心著手做一件頂天立地的大事業,那時候,情感便是威德巍巍的一位皇帝,理性完全立在臣仆的地位。情感燒到白熱度,事業才會做出來。那時候若用邏輯方法,多歸納幾下,多演繹幾下,那么,只好不做罷了。人類所以進化,就是靠這種白熱度情感發生出來的事業。這種白熱度情感,吾無以名之,名之曰宗教。”
關于理性及宗教,下節另有討論。今姑先問:能叫人去做事的,果是而且只有情感么?依現在心理學所說,情感乃是本能發動時所附帶之心理情形。“我們最好視情感為心理活動所附帶之‘調’(tone),而非一心理歷程(mental process)。”“自根本上言之,人之心,與動物之心,終是一復雜之機器,以發動及施行動作——以做事。凡諸活動,皆依此看,方可了解。”情感與活動固有連帶之關系,然情感之強弱,乃活動力之強弱之指數(index),而非其原因。若以指數為原因,則豈不即如以寒暑表之升降為氣候熱冷之原因么?
中和與通
假使人之欲望皆能滿足而不自相沖突,此人之欲與彼人之欲,也皆能滿足而不相沖突,則美滿人生,當下即是,更無所人生問題,可以發生。但實際上欲是互相沖突的。不但此人之欲與彼人之欲,常互相沖突,即一人自己之欲,亦常互相沖突。所以如要個人人格,不致分裂,社會統一,能以維持,則必須于互相沖突的欲之內,求一個“和”。“和”之目的,就是要叫可能的最多數之欲,皆得滿足。所謂道德及政治上社會上所有的種種制度,皆是求“和”之方法。他們這些特殊的方法,雖未必對,而求“和”之方法,總是不可少的。
道德上之所謂“和”,正如知識上所謂“通”。科學上一個道理,若所能釋之現象愈多,則愈真;社會上政治上一種制度,若所能滿足之欲愈多,則愈好。譬如現在我們皆承認地是圓,而否認地是方的。所以者何?正因有許多地圓說所能解釋之現象,地方說不能解釋;而地方說所能解釋之現象,地圓說無不能解釋者。地圓說較真,正因其所得之“通”較大。又譬如現在我們皆以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比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為較優,所以者何?正因有許多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所能滿足之欲,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不能滿足;而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所能滿足之欲,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皆能滿足(或者有少數的例外)。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較好,正因其所得之“和”較大。依此說,我們可得一具體的標準,以判定一學說或一制度之真偽或好壞。他們的好或真之程度,全視他們所得之“和”或“通”之大小而定,亦可說是視他們的普遍性之大小而定。《四書》說“天下之達德”、“天下之達道”、“天下之通義”,特提出“達”、“通”來,可見道德之普遍性之可貴了。
性善與性惡
哲學家常有以“人心”、“道心”,“人欲”、“天理”對言。性善性惡,亦為中國幾千年來學者所聚訟之一大公案。我以上專言欲,讀者必以為我是個“不講理的戴東原”(胡適之先生語),專主“人欲橫流的人生觀”(吳稚暉先生語)了。我現在把我的意思申言之。我以為欲是一個天然的事物,他本來無所謂善惡,他自是那個樣子。他之不可謂為善或惡,正如山水之不可謂為善或惡一樣。后來因為欲之沖突而求和,所求之和,又不能盡包諸欲,于是被包之欲,便幸而被名為善,而被遺落之欲,便不幸而被名為惡了。名為善的,便又被認為天理;名為惡的,又被認為人欲。天理與人欲,又被認為先天根本上相反對的東西,永遠不能相合。我以為除非能到諸欲皆相和合之際,終有遺在和外之欲,因之善惡終不可不分。不過若認天理人欲為根本上相反對,則未必然。現在我們的道德及種種制度,皆日在改良。若有一個較好的制度,就可得到一個較大的和。若所得到之和較大一分,所謂善就添一分,所謂惡就減一分,而人生亦即隨之較豐富,較美滿一分。譬如依從前之教育方法,兒童游戲是惡,在嚴禁之列,而現在則不然。所以者何?正因依現在之教育方法,游戲也可包在其和之內故耳。假使我們能設法得一大和,凡人之欲,皆能包在內,“并育而不相害”,“并行而不相悖”,則即只有善而無惡,即所謂至善;而最豐富最美之人生,亦即得到矣。至于人類將來果能想出此等辦法,得到此等境界與否,那是另一問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