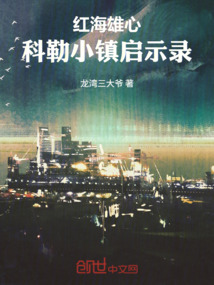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熱病與黃金夢
許爾凱在四十二度的高燒里,看見了自己死去多年的父親。
父親還是穿著那件洗得發白的工裝,背對著他站在南充老家的嘉陵江邊。江面上霧氣朦朧,父親的身影在霧中若隱若現,忽然轉過頭來,臉上沒有五官,只剩下一張巨大的、蠕動的非洲地圖。
“爸!”許爾凱嘶啞地喊了一聲,掙扎著想從那張汗濕的簡易床上坐起來。
一雙有力的黑手按住了他的肩膀。“許老板,不要動,你在發高燒。”
許爾凱艱難地睜開眼,模糊的視線逐漸聚焦。馬馬杜那張寬厚的臉在昏暗的燈光下晃動,額頭上沁著細密的汗珠。遠處傳來施工機械的轟鳴聲,夾雜著工人們用四川話和當地土語的叫喊。
“我睡了多久?”許爾凱的聲音像是從砂紙上磨過。
“一天一夜。醫生剛走,說是惡性瘧疾。他給你打了奎寧,囑咐必須休息。”馬馬杜遞過來一杯渾濁的水,“喝點吧,雖然味道不好,但是燒開過的。”
許爾凱勉強撐起身子,接過杯子抿了一口。水里有股明顯的泥土和漂白粉味道,但他還是一飲而盡。喉嚨里火燒火燎的感覺稍微緩解了一些。
這是2018年4月,許爾凱來到幾內亞的第三年。三年前,他還是四川南充一個小有名氣的建筑商,承接些住宅樓和市政工程。直到有一天,他在一場商會活動上聽說非洲的機會,像是被什么無形的東西擊中了,毅然賣掉了在國內的兩套房產,帶著一支二十人的施工隊遠渡重洋,來到這個西非國家。
最初的設想很美好:中國援非項目多,基建需求大,競爭比國內小,利潤空間大。現實卻給了他當頭一棒。
工棚的簾子被掀開,一個精瘦的四川漢子鉆了進來,帶來一股熱浪和塵土。“老板,你總算醒了!嚇死我們咯!”說話的是項目經理老陳,跟著許爾凱從南充來的老部下。
“工地怎么樣?”許爾凱最關心的是這個。他正在承建的是中國援助幾內亞的一所職業技術學校,工期緊,任務重。
“放心嘍,有我盯到起的。就是混凝土又不夠了,本地供應商說至少要等三天。”
許爾凱皺起眉頭:“三天?我們等不起。聯系沈三那邊沒有?”
“聯系了,福建商會那個沈老板說他的水泥也緊張,如果要提前拿貨,得加30%的緊急費用。”
“狗日的,趁火打劫!”許爾凱忍不住罵了一句,隨即引發一陣劇烈的咳嗽。
馬馬杜輕輕拍著他的背:“許老板,你需要休息,工作的事情晚點再說。”
許爾凱擺擺手,強忍著不適:“老陳,你去把上周的施工進度表拿來我看看。馬馬杜,麻煩你幫我找點吃的,我有點餓了。”
兩人離開后,許爾凱艱難地挪到工棚門口,望向外面的工地。十一月的幾內亞正值旱季,太陽毒辣地炙烤著大地。他的工人們正在腳手架上忙碌著,其中既有從四川帶來的老師傅,也有本地招募的黑人青年。遠處,幾內亞首都科納克里的天際線隱約可見,低矮的房屋中偶爾聳立著幾棟現代化的高樓。
三年前剛到這里時,許爾凱曾被這里的落后震驚。首都科納克里的基礎設施甚至不如中國的一個縣城,電力供應不穩定,自來水不能直接飲用,道路坑洼不平。但漸漸地,他開始看到這里的潛力——到處都是建設工地,中國公司承建的高速公路、政府大樓、體育場館拔地而起。他相信,這片土地將會復制中國過去三十年的發展奇跡。
然而現實遠比想象復雜。文化差異、語言障礙、政策多變、腐敗嚴重......每一個問題都讓他的非洲創業之路步履維艱。最要命的是資金壓力,國內帶來的積蓄已經所剩無幾,而工程款卻總是遲遲不能到位。
“老板,你的粥來了。”馬馬杜端著一碗白粥回來,配上一點榨菜,“醫生說你只能吃清淡的。”
許爾凱接過碗,忽然問:“馬馬杜,你跟我干了兩年了,覺得我們中國人在非洲搞建設,到底為了什么?”
馬馬杜愣了一下,隨即笑了,露出一口白牙:“為了錢,不是嗎?你們中國人來這里都是為了賺錢。”
許爾凱搖搖頭,又點點頭:“是為了賺錢,但不全是。”他望著遠處那些低矮的鐵皮屋頂,“你看那些房子,夏天熱得像蒸籠,雨天漏得如篩子。我想讓更多人住上好房子。”
馬馬杜的笑容淡去,表情變得嚴肅:“許老板,你是我見過的第一個這么說的中國商人。其他人只關心怎么從我們這里賺走更多的錢。”
兩人正聊著,老陳拿著進度表回來了,臉色不太好看:“老板,出問題了。監理說我們用的鋼筋規格不符合標準,要全部更換。”
許爾凱的太陽穴突突直跳:“怎么可能?我們都是按標準采購的!”
“說是新標準,上個月剛發布的。我懷疑是那個監理故意找茬,之前他暗示過要‘表示表示’。”
許爾凱感到一陣眩暈。在這種關鍵時刻出這種問題,無疑是雪上加霜。他強打精神:“約他今晚吃飯,我親自和他談。”
夜幕降臨時,許爾凱的高燒稍微退去一些,但他仍然感到渾身無力。為了工程,他不得不拖著病體,來到科納克里一家高檔中餐館。
監理是一個肥胖的法國人,名叫皮埃爾,在幾內亞已經呆了十五年。酒過三巡,皮埃爾終于切入正題:“許先生,我知道你們中國人很善于變通。標準是死的,人是活的,不是嗎?”
許爾凱心里明白,這是要索賄了。他強壓著怒火:“皮埃爾先生,我們的鋼筋完全符合國際標準,只是幾內亞的新標準有些...特殊要求。”
皮埃爾晃著酒杯,意味深長地笑著:“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特色。在非洲,要學會適應這種特色。”
這頓飯吃了一個小時,許爾凱最終以“再考慮考慮”結束了談話。回工地的路上,他望著窗外的科納克里夜景,心中涌起一陣深深的無力感。
這就是他想要的非洲創業嗎?每天周旋于各色人等的貪欲之間,違背自己的原則去做事?
手機忽然響起,是國內的兒子打來的視頻電話。許爾凱整理了一下表情,接通電話。
“爸,你那邊怎么樣?媽媽說你生病了?”屏幕上是兒子關切的臉。
“沒事,小感冒而已。你學習怎么樣?”
“還行吧。爸,我們同學都說非洲很危險,你為什么非要呆在那里?回國不好嗎?”
許爾凱不知如何回答。他不能告訴兒子,國內的建筑市場已經飽和,三角債問題嚴重,他回去可能連工程款都要不回來。也不能告訴他,自己把所有的希望都押在了非洲這片土地上。
“這里機會多,等你大學畢業了,也可以來非洲看看。”
兒子不以為然:“我才不要去那種地方呢。我們同學都說,非洲又窮又亂,都是傳染病。”
掛了電話,許爾凱久久無言。是啊,在很多人眼里,非洲就是貧窮、戰亂和疾病的代名詞。就連他自己的兒子都不能理解他的選擇。
第二天,許爾凱的高燒退了,但身體仍然虛弱。他堅持要去工地看看。馬馬杜開車送他,穿過科納克里擁擠的街道。路邊是密密麻麻的鐵皮棚屋,婦女們在門口生火做飯,孩子們光著腳踢足球,到處是活力勃勃而又混亂不堪的景象。
在一個十字路口等紅燈時,許爾凱注意到路邊的一塊巨幅廣告牌。上面是法文寫的“ Résidence Belle Vie”,展示著一個現代化住宅小區的效果圖,游泳池、健身房、24小時保安一應俱全。售價每平方米2000美元。
“這是什么項目?”許爾凱問馬馬杜。
“哦,這是一個法國開發商建的高檔公寓,主要賣給外國人和本地富人。聽說賣得很好,雖然價格貴得離譜。”
許爾凱仔細看著廣告牌,內心受到巨大沖擊。2000美元一平米,這在當地是天價。更讓他震驚的是,從效果圖來看,這個項目的建筑質量和設計水平都很一般,遠遠達不到國內的標準。
“這些人真的會買嗎?”
“當然!科納克里的好房子太少了,有錢人都想住安全、舒適的地方。不過...”馬馬杜猶豫了一下。
“不過什么?”
“我聽說這個項目用的材料很差,承諾的配套設施也縮水了。但他們是法國公司,沒人敢說什么。”
許爾凱的心中突然燃起一團火。他想起自己來非洲的初心——讓更多人住上好房子。現在看到的卻是外國開發商用劣質產品賺取暴利,而本地人只能忍受或者支付高價。
“掉頭,我們去這個項目看看。”
在馬馬杜的帶領下,許爾凱來到了“ Résidence Belle Vie”的售樓處。果然氣派非凡,空調冷氣十足,沙盤精致漂亮。售樓小姐是個法國人,態度傲慢,對許爾凱愛答不理。直到許爾凱表示要買十套,她的態度才突然轉變。
許爾凱假裝有意購買,詳細詢問了項目的具體情況。越問越心驚:墻體厚度不足,防水工程簡陋,電路設計存在隱患...這在中國根本不可能通過驗收。
離開售樓處,許爾凱站在炎熱的非洲陽光下,內心卻比空調房里更加清明。一個大膽的想法在他心中萌生:為什么我不能在非洲開發真正的好房子?不比國內的差,但價格比這些法國人的項目更合理?
這個念頭讓他激動不已,連身體的虛弱都忘記了。他立刻讓馬馬杜開車在科納克里轉悠,觀察各個區域的房地產情況。
調查結果令人震驚:科納克里的正規住宅供應嚴重不足,高端市場被法國和黎巴嫩開發商壟斷,價格虛高;中低端市場幾乎空白,普通市民只能住在擁擠、簡陋的鐵皮屋里。隨著幾內亞經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加快,住房需求將會爆發式增長。
回到工地,許爾凱立刻召集核心團隊開會,提出了轉型做房地產開發的想法。
反應出乎意料地冷淡。
“老板,你不是燒糊涂了吧?”老陳第一個反對,“我們做施工的,干嘛去搞開發?風險太大了!”
“就是,”財務小張附和道,“開發需要大量資金,我們現在連工程款都收不回來,哪有錢搞開發?”
其他人也紛紛表示質疑。只有馬馬杜沉默不語。
許爾凱沒有放棄,他詳細分析了自己的觀察和市場情況:“科納克里有200萬人口,每年新增住房需求至少5萬套,而正規開發商提供的住宅不到5000套。這是個巨大的藍海市場!”
“但是資金從哪里來?土地怎么解決?銷售怎么辦?這些都是問題啊!”老陳憂心忡忡。
會議不歡而散。團隊成員們都認為許爾凱是病糊涂了,異想天開。
那天晚上,許爾凱獨自一人坐在工棚里,反復計算著開發一個住宅項目需要的投入和可能的回報。數字很誘人,但啟動資金確實是個大問題。他現有的積蓄已經全部投入到了施工業務中,銀行貸款難度大,民間借貸利率高得嚇人。
就在他一籌莫展時,馬馬杜悄悄走了進來。
“許老板,我思考了你今天的想法。”馬馬杜神情嚴肅,“我認為很有前景。事實上,我有些土地資源,或許可以合作。”
許爾凱眼前一亮:“你有土地?”
“不是我個人的,是我家族的土地。在科納克里郊區,大約50公頃。按照現在的政策,可以轉為住宅用地。”
“為什么你自己不開發?”
馬馬杜苦笑道:“我沒有資金,也沒有技術。在幾內亞,有很多人擁有土地,但沒有開發能力。而你們中國人有技術、有資金,卻很難拿到好地塊。這是一種...資源錯配。”
兩人越聊越投機,從土地政策聊到市場需求,從建筑設計聊到營銷策略。許爾凱發現馬馬杜雖然沒受過正規高等教育,但對本地市場有著驚人的洞察力。
“如果我們合作,你出土地,我出資金和技術,股份各占50%,怎么樣?”許爾凱提議道。
馬馬杜搖搖頭:“不,土地占30%就夠了。我需要你控股,這樣項目才能按照你的理念來做。我不想做另一個唯利是圖的開發商。”
這個回答讓許爾凱對馬馬杜刮目相看。在普遍貧困的幾內亞,很少有人能抵抗住巨大利益的誘惑。
兩人一直聊到深夜,初步確定了合作意向。許爾凱負責資金籌措和建設,馬馬杜負責土地手續和本地關系。項目定位中高端住宅小區,價格比法國項目低30%,但品質要達到中國標準。
興奮過后,資金問題再次擺在面前。許爾凱算了一下,啟動資金至少需要500萬美元,這遠遠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圍。
接下來的幾周,許爾凱一邊忙著學校的工程項目,一邊四處尋找資金。他見了中資銀行的代表,見了在幾內亞的中國商人,甚至見了些本地富豪,但都沒有結果。要么是覺得風險太大,要么是條件過于苛刻。
屋漏偏逢連夜雨。就在這時,他收到國內的消息:最大的債務人破產了,欠他的300萬工程款可能要打水漂。這意味著他在國內的現金流徹底斷裂。
更糟糕的是,幾內亞政府突然發布新政策,要求所有外國建筑企業必須與本地企業組成聯合體才能投標政府項目。許爾凱的小公司頓時失去了投標資格。
內外交困之下,許爾凱病倒了。這次不是瘧疾,而是心力交瘁導致的全面崩潰。在病床上,他不得不面對一個殘酷的現實:他的非洲創業夢可能就要破滅了。
“老板,要不我們回國吧。”老陳看著他消瘦的臉龐,忍不住勸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許爾凱望著工棚頂棚,久久不語。回國嗎?承認失敗,回到那個已經沒有什么機會的市場?他不甘心。
就在他最絕望的時候,馬馬杜帶來一個消息:四川商會在成都舉辦年度大會,許氏宗親會也將同時舉行。馬馬杜建議許爾凱回國參加,或許能遇到轉機。
“我沒臉回去。”許爾凱苦笑,“當初雄心勃勃地出來,現在灰頭土臉地回去求助?”
“在中國文化中,宗親不就是互相幫助的嗎?”馬馬杜不解地問。
許爾凱沉默了。是啊,許氏在南充是大姓,宗親會中不乏成功商人。或許,這真的是最后的機會了。
經過一番思想斗爭,許爾凱最終決定回國。他買了一張回成都的機票,帶著最后一線希望,踏上了歸途。
飛機起飛時,許爾凱透過舷窗看著下面這片讓他愛恨交織的土地,暗暗發誓:我一定會回來,以另一種方式。
他不知道的是,這次回國將會徹底改變他的命運,也讓“科勒文化小鎮”從一個夢想變為現實。
但此刻,他只是一個疲憊而絕望的中年人,在經濟的寒冬里,飛向未知的歸途。
飛機穿越云層,許爾凱閉上眼睛,腦海中浮現出父親的身影。這一次,父親的臉清晰可見,帶著嘉陵江邊漁民特有的滄桑笑容,仿佛在說:“娃兒,莫怕,路都是人走出來的。”
許爾凱的眼角,一滴淚水悄然滑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