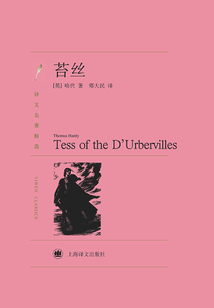最新章節(jié)
書友吧 8評論第1章 譯本序
托馬斯·哈代一八四〇年出生于英國西南部多塞特郡鄰近多爾切斯特的一個小村莊。他的父親是石匠師傅,也是本地教堂圣樂團里的提琴演奏者。從一八五六年起哈代跟一位擅長修葺哥特式教堂的建筑師學藝。學徒期滿后,從一八六二年至一八六七年他在倫敦一家建筑事務所當了幾年助理員,同時開始了他的寫作生涯。哈代起先寫詩,因為得不到出版便轉(zhuǎn)向小說創(chuàng)作。他早期的三部長篇小說是《計出無奈》(1871)、《綠林蔭下》(1872)和《一雙藍眼睛》(1873)。第一部是匿名發(fā)表的,而且哈代沒有得到稿酬反而支付了一些輔助出版費用。第二部的出版使他得到三十英鎊稿酬;情況有了這樣的好轉(zhuǎn)之后,他在應約寫第三部的時候便決定放棄當建筑師的打算,選擇寫作為終身職業(yè)。一八七四年,哈代與吉福特小姐結婚,也是在這一年,他的第一部獲得普遍贊揚的小說《遠離塵囂》在連載后以單行本形式出版,使他在文壇上確立了地位。接著他又寫了幾部重要的小說:《還鄉(xiāng)》(1878)、《卡斯特橋市長》(1886)、《森林中人》(1887)、《苔絲》(1891)和《無名的裘德》(1895);后兩部小說冒犯了維多利亞時代的道德觀念,受到激烈的攻擊,哈代憤而不再寫小說,轉(zhuǎn)而重新寫詩,直至一九二八年逝世。
哈代的寫作生涯以詩開始,中間經(jīng)過二十幾年的小說階段,最后仍以寫詩告終。他比較著名的詩集有《韋塞克斯詩集》(1898)、《時代的笑柄及其他》(1909)、《情勢的諷刺》(1914)和《幻想的時刻》(1917)等,而最重要的是他的關于拿破侖戰(zhàn)爭的史詩劇《統(tǒng)治者》三卷(分別發(fā)表于1903年、1906年和1908年)。他的抒情詩中不乏情節(jié)有戲劇性并語句雋永的作品。有人認為哈代在精神上始終是一位詩人。
哈代的長篇小說絕大多數(shù)以英國西南部那個叫韋塞克斯的地區(qū)作背景,描寫人被命運播弄,在生活和愛情上的不幸遭遇(他的故事極少有幸福美滿的結局)。這大抵因為他是在近代工業(yè)侵入之前的鄉(xiāng)村度過他的童年和青年時期的,鳥語花香、風景宜人的自然環(huán)境給他留下了深刻的美好印象,而隨著年齡的增長,他卻看到美麗的鄉(xiāng)村和城鎮(zhèn)漸漸工業(yè)化以后在經(jīng)濟、政治和社會風俗等方面發(fā)生了使他傷感的悲劇性變化,加上他在研讀《圣經(jīng)》之后反而對基督教失去信仰,不相信有那么一個全能、公正、仁慈的上帝在治理世界和照顧天下的蕓蕓眾生。哈代通過描寫愛情和婚姻,表達了他認為人們對幸福生活的追求均屬徒勞以及陷入悲慘境地的人無論怎樣掙扎都無補于事的觀點。
在哈代的長篇小說中,《苔絲》是最著名的一部。女主人公苔絲出生于一個貧苦小販的家庭,父親約翰·德比有一天被人告知他是古代貴族德伯的后代便得意忘形起來,他和他那短視而愛虛榮的老婆決定讓女兒到一個自稱也是德伯家族后裔的富老太婆家去攀親戚,以期在經(jīng)濟上得到幫助。苔絲去了以后被老太婆的兒子亞歷克誘奸,她懷孕回家,孩子一生下即夭折。過了幾年,苔絲再次離家來到陶勃賽乳牛場干擠奶的活兒,在這里他與牧師的兒子安吉爾·克萊爾戀愛并訂婚。苔絲對文質(zhì)彬彬頗有知識的安吉爾十分崇拜和熱愛,幾次想把自己曾被亞歷克奸污的事告訴他,都因種種緣故而沒有辦到,結婚前數(shù)日她寫了一封長信從房門下邊塞進安吉爾的屋子卻塞到了地毯下面。新婚之夜她把自己昔日的這一不幸事件向丈夫坦白,但是安吉爾沒能原諒她。這以后他們兩人分居,安吉爾去巴西發(fā)展他的事業(yè),苔絲仍在一些農(nóng)場打工糊口,命運卻讓她再次與已經(jīng)披上牧師黑袍四處布道的亞歷克·德伯相遇;亞歷克對苔絲的情欲頓時擊敗了他那沒有根基的宗教信仰,他糾纏苔絲,不得到她決不罷休。這時候苔絲的父親病故,為了母親和弟弟妹妹們的生活,她被迫與亞歷克同居。不久,安吉爾·克萊爾從巴西回國,找到妻子并表示悔恨以往的冷酷無情。苔絲在這種情況下痛苦地覺得,是亞歷克·德伯使她第二次失去了安吉爾,又一次毀掉了她的幸福,她懷著懊惱和憤怒到極點的心情,同時也帶著一種責任感,殺死了亞歷克。在與安吉爾一起度過幸福、滿足的最后五天之后,苔絲被捕并被處以絞刑。“諸神之主(這是埃斯庫勒斯的話)跟苔絲所開的玩笑到此結束了。”(《苔絲》末段首句。)
《苔絲》典型地體現(xiàn)了托馬斯·哈代悲觀的宿命論。如同索福克勒斯筆下的俄狄浦斯改變不了命運的安排,必然殺父娶母最后自己刺瞎雙目流浪而死,熟讀古希臘悲劇大師作品的哈代讓他的讀者看到,苔絲也改變不了命運的安排,最后必然走上絕路。不過,哈代與他的古希臘導師不同,他并不純粹借助于一個個偶然事件來展開他的故事,而是以人物的性格為依據(jù),使故事情節(jié)合乎情理地一環(huán)扣一環(huán)地向前發(fā)展,因此他的故事更有說服力和感染力。
試分析男女主人公的一些主要行為。在第一章第三節(jié),苔絲的父母要她去有錢的德伯太太家攀親戚;她秉性純樸,厭惡趨炎附勢,不愿意去,但是因為她在與弟弟亞伯拉罕一起送蜂蜜進城去的路上出了事故,把家里那匹老馬“王子”弄死了,她覺得自己有責任幫助父母使家庭擺脫困境,所以才答應去,這導致她被亞歷克·德伯奸污。表面上看來,是苔絲父母親想要高攀富親戚的打算給亞歷克·德伯提供了機會,但實際上在這里起決定性作用的是苔絲性格中的責任感。倘若她對父母沒有孝心,倘若她對“王子”死后他們這個家庭陷入困境這件事毫不內(nèi)疚,那么她就不會去德伯家,也就不會遇上亞歷克了。至于在這之前的那天夜里進城送蜂蜜,本來也應該是她父親的事,也是因為父親喝醉了酒,苔絲怕他在半夜里醉醺醺地趕長路會出意外,認為自己應該盡女兒的責任才主動提出由她帶上弟弟代替父親跑一趟的。善良、孝順的苔絲的責任感驅(qū)使她做了這兩件事情,也就使她落入了亞歷克·德伯的魔掌,使她遭受了一個少女所可能受到的最悲慘最可怕的打擊,并且弄得她無法自救,一步步走向最后的毀滅。
苔絲第二次離家外出,在陶勃賽乳牛場認識了安吉爾·克萊爾,經(jīng)過甜蜜的戀愛后兩人決定結婚。本來,他們會過上十分幸福的生活,苔絲可以甩掉不幸的過去了,可是,苔絲偏偏要把自己曾被亞歷克·德伯奸污的事向心上人坦白,結果,出乎她意料之外,她視若神明的安吉爾·克萊爾沒能原諒她,苔絲不得不重又承受生活加在她肉體上和心靈上的新的苦難和折磨。不難看出,在這里,還是苔絲那強烈的責任感造成了惡果——她認為自己有責任把自己的一切都讓所愛的人知道,否則對他就是不公平。與安吉爾分手之后,苔絲在承受生活中新的煎熬時,又不幸地與亞歷克·德伯狹路相逢,最后重新落入他的掌握之中。造成這一局面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亞歷克·德伯這個惡棍本性難改,但是在另一方面,依然是苔絲的責任感在起決定性的作用——在她父親去世、母親和弟弟妹妹生活困難的時候她的責任感迫使她同意與仇人同居在一個屋頂之下!
我們還可以說,最后苔絲壓抑不住心中的怒火把亞歷克·德伯殺死,仍然是受到她那責任感的驅(qū)使;且看她在完成了這件大事后追上安吉爾·克萊爾的這一段:
……克萊爾停住腳步,以詢問的目光望著苔絲。
“安吉爾,”苔絲說,好像她一直等待著他們停步時克萊爾會這樣看著她,“你知道我為什么要追你嗎?我要告訴你我把他殺了!”她這么說著的時候臉上露出令人同情的慘淡微笑。
“什么!”克萊爾說;他覺得苔絲神態(tài)奇怪,以為她是在說胡話。
“我殺了他——也不知道是怎么把他殺死的,”苔絲接著又說。“不過,安吉爾,為了你,也為了我自己,我非這么做不可。……”
顯而易見,苔絲把殺死亞歷克看成是她必須完成的任務,是她應盡的責任——為她自己,為她的丈夫,也為了可能與她遭受同樣不幸的姑娘!因為任務完成了,所以她迫不及待地要告訴她的丈夫,所以她的臉上露出了微笑!
或許有人會說,苔絲強烈的責任感確實是她個性中一個關鍵性的特點,如一條主線貫串于她的每一個重大行為;可是,哈代為什么把男主人公安吉爾·克萊爾描寫得那么不近人情呢?如果說苔絲的行為十分符合她的性格的話,那么安吉爾·克萊爾的行為似乎令人費解。這個人物思想開通,他本人也曾與一個女人有過一段荒唐的交往,但是在苔絲向他坦白了自己過去的遭遇之后,他卻不予同情,冷酷地與她分手。哈代在刻畫克萊爾這個人物時難道就不遵守行為與性格一致的規(guī)則了嗎?
當然不是。克萊爾的行為當然仍是由他的性格決定的。從小說的前半部分我們看得很清楚,他的個性中確實有反抗傳統(tǒng)風俗習慣這一特點;正是因為他思想開通,不受常規(guī)束縛,他才敢于違抗父命不娶默茜·錢特小姐,才會拒絕像兩個哥哥一樣去當牧師而偏偏走上務農(nóng)的道路,才會在乳牛場遇見苔絲這么一個擠奶姑娘后便真心地愛上她。也就是說,安吉爾·克萊爾對苔絲的愛是超越門第和貧富觀念的,是一種真正純潔的愛;他所愛的純粹是他眼中所見如此美麗、心中所想應是十全十美的苔絲。因此,陶醉于甜蜜愛情之中的他當然接受不了苔絲曾被人奸污這一事實,當然承受不了如此沉重的打擊。苔絲向他坦白之后,他簡直無法相信苔絲說的不是瘋話:
“苔絲!”
“呣?最親愛的。”
“我得相信你說的事嗎?看你的樣子我得相信它是真的。哦,你這會兒不可能是精神錯亂的!你應該精神錯亂才對呀!可是你沒有……我的妻子,我的苔絲——你沒有任何東西可以使得我有理由做這樣的假設嗎?”
(第35節(jié))
此時此刻,安吉爾·克萊爾所想到的,不是苔絲那不幸遭遇的性質(zhì),他更沒有想到把苔絲的遭遇和他自己昔日的荒唐事作一個比較。不,他想到的不是這些,他當時不可能如此冷靜地思考這一類問題;他想到的只有一點——多么令人痛心啊,世上再也不存在這么好的苔絲了!他覺得,“苔絲說出了自己過去的事情,使他的生活以及他的整個世界發(fā)生了徹底的、可怕的變化。”他努力“扼殺自己對她的情感。……一顆淚珠正慢慢地淌下克萊爾的面頰——一顆很大的淚珠……”(第35節(jié))十分明顯,安吉爾·克萊爾這時候正在經(jīng)受巨大的失望和痛苦。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就不應該把他在聽過苔絲的坦白之后所作出的反應,看成是一個向來習慣于嚴格要求他人的人在無視其本身的錯處卻以高標準譴責別人的時候所表現(xiàn)出來的態(tài)度(從小說的前半部分,沒有哪個讀者會得到印象,認為安吉爾·克萊爾是一個嚴于律人疏于責己的人);我們不應該指著安吉爾·克萊爾的鼻子責備他說:“你自己這么不檢點,還用這種態(tài)度對待苔絲!”不,我們不應該這樣,而是應該體會哈代所寫:“一個受了愚弄的老實人一旦醒悟過來往往會覺得自己受到了殘酷的對待,克萊爾此刻這種感受正十分強烈。”(第35節(jié))也就是說,熱戀中的安吉爾·克萊爾這時候不但感到失望和痛苦,而且還覺得受到了命運的愚弄,受到了殘酷的對待,因此他克制不住自己,對苔絲采取了嚴厲的態(tài)度,提出兩人分居的主張,把苔絲推向了亞歷克一邊。這以后,他和苔絲天各一方;經(jīng)過相當長時間的反省并飽受相思之苦,他才慢慢改變這種態(tài)度,恢復了對苔絲那種深沉的愛,那就是苔絲被捕之前他們兩人在一起度過的五天里讀者所看見的情形了。
男女主人公的性格使他們在特定環(huán)境里遇到各種事情的時候做出種種必然的反應,這些反應相互作用形成的合力把他們拖入困境,使他們最后遭遇悲劇性的結果;哈代的《苔絲》就是這樣用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和感人的故事表達了作者對生活的看法。這部一百多年前寫下的小說對于今日讀者的意義,當然不在于它的具體故事內(nèi)容和所宣揚的思想,而在于它為我們提供了研究托馬斯·哈代這位跨越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的英國詩人和小說家的生動材料,同時也啟發(fā)我們思考人生的各種問題,盡管,在生活發(fā)展的總趨勢這個問題上,我們不必與哈代持相同觀點。
鄭大民
一九九六年四月
“……可憐的受了傷的名字!我的胸膛是一張床,讓你得以將養(yǎng)。”
——威廉·莎士比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