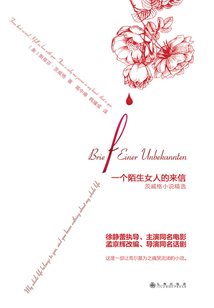
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茨威格小說精選)
最新章節(jié)
書友吧 15評論第1章 前言(1)
靈魂的獵者
高中甫
斯蒂芬·茨威格1881年生于維也納,出生于一個猶太家庭,父親是一個紡織廠主,母親是一個銀行家的女兒。從童年起,他就過著優(yōu)渥的生活,受著良好的教育,對文學(xué)藝術(shù)有著濃厚的興趣。
維也納當(dāng)時是奧匈帝國的首都,這個帝國建立于1867年,到19世紀末國運式微,政治衰敗。可這同時也是奧地利歷史上一個文學(xué)藝術(shù)生機勃發(fā)的時期,正如茨威格所說的,“它是西方一切文化的綜合”——馬赫(1838—1911)的哲學(xué),弗洛伊德(1856—1939)的精神分析學(xué),馬勒(1860—1911)、施特勞斯(1864—1949)、勛伯格(1874—1951)在音樂上贏得的世界性聲譽,建筑和繪畫藝術(shù)上分離派和印象派的成就已飲譽歐洲,而文學(xué)上則是“青年維也納”的崛起。這個文學(xué)流派很快就成為奧地利和維也納文學(xué)生活的中心,它標(biāo)志著一個新的文學(xué)時代的到來,迅即贏得了青年一代的敬仰和追隨。
茨威格就是在這樣一種文學(xué)藝術(shù)氛圍中走上了文學(xué)的道路。
1898年,還是一個17歲中學(xué)生的茨威格在報紙上發(fā)表了第一首詩歌;1901年在維也納大學(xué)學(xué)習(xí)時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詩集《銀弦集》;他的第一個短篇小說發(fā)表于1902年,第一部短篇小說集《艾利卡埃·瓦爾德之戀》出版于1904年;《泰西特斯》是他的第一部劇作,創(chuàng)作于1907年,而作為傳記作家,他寫了第一部人物傳記《艾米爾·瓦爾哈倫》,時為1910年。這表明,近而立之年的茨威格在文壇上的各個領(lǐng)域都進行了嘗試,并贏得了一些名聲。
成功的文學(xué)起步使茨威格選擇了一個職業(yè)作家的生涯,但他清醒地認識到,一如他在自傳《昨日的世界》中自省地寫道:“雖然我很早就(幾乎有點兒不大合適)發(fā)表作品了,但我心中有數(shù),直到二十六歲,我還沒有創(chuàng)作出真正的作品。”標(biāo)志著他形成自己創(chuàng)作風(fēng)格并贏得評論界贊賞的是他1911年發(fā)表的小說集《初次經(jīng)歷》——它有一個副標(biāo)題:“兒童王國里的四篇故事”,內(nèi)收有《朦朧夜的故事》《家庭女教師》《灼人的秘密》和《夏天的故事》,作家和評論家弗里頓·塔爾稱,這個集子的小說才使茨威格成為一個小說家。其中的《灼人的秘密》尤為受到讀者的喜愛。它稍后出了單行本,一次印了二十萬冊。《初次經(jīng)歷》確立了他在德語文壇上的地位,形成了他小說創(chuàng)作上獨具特色的表現(xiàn)風(fēng)格,表現(xiàn)了他藝術(shù)上的追求,探索和描繪為情欲所驅(qū)使的人的精神世界。這成為他此后創(chuàng)作的一個基調(diào)。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把茨威格拋到與過去生活截然不同的生活中去。生性酷愛和平的茨威格在一段短暫的時間里沒有擺脫民族主義的影響,他寫了幾篇頌揚所謂“愛國主義”的文章,并自愿入伍,在戰(zhàn)爭檔案處和戰(zhàn)爭新聞本部工作。但民族之間的血腥殺戮和戰(zhàn)爭的殘酷使他很快覺醒過來。到1916年初,如他在《昨日的世界》中所表明的,他成了一個反戰(zhàn)主義者。同年,他取材《圣經(jīng)·舊約》中的《耶利米書》創(chuàng)作了反戰(zhàn)戲劇《耶利米》。這位猶太民族的先知預(yù)言巨大災(zāi)難的降臨,但在狂熱的年代無人相信他,他被看作傻瓜、叛徒。“用我的肉體去反對戰(zhàn)爭,用我的生命去維護和平”。在這位先知身上,我們看到了茨威格本人的身影。此外,他還寫了一些和平主義的文章,并在此后的年代寫出了反對戰(zhàn)爭、控訴戰(zhàn)爭的小說,如《桎梏》《日內(nèi)瓦湖畔的插曲》《看不見的收藏》等。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以德奧失敗而告終。茨威格在這場戰(zhàn)爭中失去了很多,可他獲得的更多。1926年,他在一篇文章中做了這樣一份總結(jié):“失去了什么?留下了什么?失去的是:從前的悠閑自在、活潑愉快、創(chuàng)作的輕松愜意以及一些身外的東西,如金錢和物質(zhì)上的無憂無慮;留下來的是:一些珍貴的友誼、對世界的更好的認識、那種對知識的熾熱的愛,還有一種新的、堅強的勇氣和充分的責(zé)任感,在逝去多年時光之后,突然成長起來。是的,人們能以此重新開始了。”
茨威格對世界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對生活有了更深層次的理解,熱衷于對人類心靈的探索,增強了作為一位作家的責(zé)任感。他勤奮耕耘,孜孜不倦地寫作。自戰(zhàn)后到1933年這段時間成為他創(chuàng)作上的鼎盛時期。他先后完成了由三本書組成的“世界建筑師”系列:《三大師》、《與魔的搏斗》、《三詩人的生平》。在這些傳記或曰作家散論中,茨威格以多彩生動的文筆,不僅為我們描繪了這些作家的生平,更重要的是展示了這些大師栩栩如生的獨特性格和復(fù)雜而幽暗的精神世界。
除了這些作家的傳記外,他在這段時間還寫了一些歷史人物的傳記:《約瑟夫·富歇》(1929)、《瑪麗·安東內(nèi)特》(1932)及稍后的《鹿特丹的伊拉斯謨:輝煌與悲情》(1934)等。在這些著作里,茨威格一方面遵循自己所確定的原則“精練、濃縮和準確”;另一方面,他關(guān)注的和追求的并非歷史事件的發(fā)展和規(guī)律性的東西,激起他興趣的則是這些歷史人物的藝術(shù)畫像、精神世界。他觀察的不只是人物的外觀,而是他們的內(nèi)心。他對歷史人物的獨特理解以及獨特的心理分析的表現(xiàn)方法,為他在世界傳記文學(xué)中贏得了獨特的地位。
羅曼·羅蘭稱茨威格是一位“靈魂的獵者”。如果說在這些歷史人物傳記中,因受歷史人物本身和歷史事件的左右,茨威格還不能充分發(fā)揮他靈魂獵者的本領(lǐng)的話,那么他在這一時期完成的小說,特別是在他的第二本小說集《熱帶癲狂癥患者》(1922)和第三本小說集《情感的迷惘》(1927)便已淋漓盡致地施展示了他的才能。這兩本小說集連同他1911年發(fā)表的小說集《初次經(jīng)歷》,被茨威格本人稱為“鏈條小說”。《初次經(jīng)歷》寫的是人的兒童期,他通過兒童的視角觀察了為情欲所主宰的成人世界,這個世界充滿了“灼人的秘密”。收有《熱帶癲狂癥患者》《奇妙之夜》《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芳心迷離》的第二本小說集,展示的是由情欲所控制的成年男女的心態(tài),他們在潛意識的驅(qū)使下犯下了所謂的“激情之罪”。小說集《情感的迷惘》除收入冠題那一篇外,還有《一個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時》《一顆心的淪亡》。它們的主人公都是歷經(jīng)滄桑的過來人。作者極為細膩地描繪了這些人物在情欲的驅(qū)逼下遭到意外打擊時心靈的震顫和意識的流動。用茨威格本人的話來說,這些小說是帶有精神分析印記的,是探索個人的,是與“激情的黑暗世界中的幽明相聯(lián)結(jié)的經(jīng)歷”。
人的心靈是一個幽暗的神秘世界,心理學(xué)家一直為揭示這個世界的秘密而不斷地探索和研究。弗洛伊德在世紀交替之際所創(chuàng)建的精神分析學(xué)說在這一領(lǐng)域里做出了劃時代的貢獻,并很快形成了一股強大思潮,影響遍及許多學(xué)術(shù)領(lǐng)域。以文學(xué)而論,弗洛伊德主義已成為現(xiàn)代派文學(xué)的源頭之一。這位偉大的、無所畏懼的心理學(xué)家為許多作家打開了進入這一隱秘的世界之路。茨威格是最早承認和敬重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學(xué)說的德語作家之一。他曾寫道:“在我們總是試圖進入人的心靈迷宮時,我們的路上就亮有他的智慧之燈。”
茨威格這段時期的小說創(chuàng)作,特別是在后兩部的鏈條小說集中,形象地表現(xiàn)了情欲的力量和無意識的驅(qū)動力,可以明顯地看到弗洛伊德的影響。《熱帶癲狂癥患者》中的男主人公僅是由于瞬間的沖動而不惜以生命殉情;《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中的少女對一個登徒子一見傾心,竟像妓女般地委身,最后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一個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時》中一個出身名門、年逾不惑的孀居女人,竟為一個年輕賭徒的一雙手神魂顛倒,最后以身相許,甚至想到與他遠走天涯;《情感的迷惘》中一個享有聲望的莎士比亞學(xué)者,是一個同性戀者,為情欲所逼竟偷偷出沒在下流齷齪的場所,最后導(dǎo)致身敗名裂。茨威格在這些作品中,細膩地表現(xiàn)了激情——情欲的力量,展示出無意識狀態(tài)下人的心態(tài)和意識的流動。
正是由于這些小說中明顯可見的弗洛伊德的影響,當(dāng)時有的批評家譏諷茨威格的作品是對弗洛伊德學(xué)說的庸俗化。這種觀點有失偏頗。茨威格是弗洛伊德的敬仰者,他的精神分析學(xué)說有助于茨威格用一種新的目光、新的思想去探索和窺視人的內(nèi)心世界,去塑造人物的形象,但他不是一個盲目的追隨者,用小說圖解弗洛伊德的學(xué)說。他曾當(dāng)面激烈地反駁了弗洛伊德對他的小說所做的精神分析學(xué)的曲解。茨威格小說本身所具有的藝術(shù)魅力和生動的人物形象也駁斥了對他的這種批評。但不能不承認的是,弗洛伊德學(xué)說同時也給他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帶來了一些弱點:一方面是過多的、不厭其煩的內(nèi)心描寫使作品拖沓、臃腫,另一方面對情欲和無意識的熱衷削弱了作品的時代感;而當(dāng)他把視野轉(zhuǎn)向現(xiàn)實生活時,他創(chuàng)作的一些作品,如《看不見的收藏》《桎梏》《日內(nèi)瓦湖畔的插曲》《舊書商門德爾》,特別是他的最后一部作品《象棋的故事》,就有了尖銳的社會批判力量和強烈的現(xiàn)實主義色彩。
1933年,希特勒攫取了政權(quán),茨威格被拋入另一種生活。隨著1938年奧地利被法西斯德國吞并,他成了一個無家無國的流亡者。作為一個猶太人,他的種族正遭到滅絕性的殺戮;作為一個奧地利人,他已成為一個亡國之人。在流亡期間,他沒有參加反法西斯抵抗運動,但他竭盡自己所能,無私慷慨地幫助那些身受迫害的流亡者。他在從紐約發(fā)出的一封信里這樣表露了他的心跡:“我的一半時間都用來為大洋彼岸辦理宣誓書、許可證和籌措旅費,我怕你想象不出這有多么困難、多么費力。我們這些逃脫了彼岸秘密警察的人把這當(dāng)作首要任務(wù),其他一切相比而言是微不足道的。”
盡管流亡生活顛沛流離,精神上的苦痛折磨著他,茨威格依然勤奮地完成了他的一些重要作品,其中傳記有《瑪利亞·斯圖亞特》《卡斯特里奧對抗加爾文》《麥哲倫航海紀》,他唯一完成的長篇小說《焦躁的心》,他的最后一篇小說《象棋的故事》,以及他的最后一部著作、他的自傳《昨日的世界》。
茨威格本人并沒有看到他的《象棋的故事》和《昨日的世界》的出版。他是一個格外焦躁不安的人,他相信曙光必然到來,卻不堪忍受黎明前的黑暗。這個“歡樂的悲觀主義者,渴望死亡的樂觀主義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最沉重的日子里,于1942年2月22日與妻子一道棄世而去,留下了那封悲愴感人的絕命書,用自己的生命對戰(zhàn)爭進行了最后的抗?fàn)帯?/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