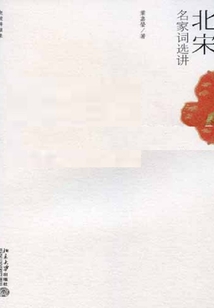
北宋名家詞選講
最新章節(jié)
書友吧 18評論第1章 北宋初期(1)
第一講說晏殊詞
第一節(jié)
以前我們講馮正中的詞“上翼二主,下啟晏歐”,而且也講了北宋初年詞人中可以見到受馮正中明顯影響的就是兩位江西籍詞人晏殊(同叔)與歐陽修,因為馮正中在撫州為官三年,留有極大影響,故后人認為他開創(chuàng)了“西江詞派”,而西江詞派詞人的作品卻是表面相近而實際不同的。以前我們講馮正中詞時就提到過“晏同叔得其俊,歐陽永叔得其深”,我們現(xiàn)在就來把大晏和馮正中作一比較,也和李后主作一比較,看晏同叔何以得正中之“俊”,再看一看晏同叔之為理性詞人與李后主之為純情詞人有何差別。
先談所謂理性,一般人所謂的理性,常是利害人我的得失計較,這樣的人永遠也看不到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我所說的理性不是這樣眼光短淺的人我之間的利害計較,而是另一種可貴的理性,那就是我們在講陶淵明時所講過的,是一種節(jié)制和反省的理性。在以純真向人的方面,陶淵明與李后主有相似的一面,在有反省有節(jié)制的方面,陶淵明和大晏有相似的一面,這便是他們之間關系的不同。作為理性的詞人,大晏的作品中是有反省有節(jié)制的,而且使人能從其所寫的感情之中,體會出思致的意味,同時還具備一種通達的觀照的能力,觀照是說你通過觀察事象之后內(nèi)心中會有一種智慧的照明,尤其是對人生的體會和覺悟,這就是我所謂的可貴的理性。一般人還有一種觀念,認為詩主要是言情的,而詩人中有理性的詩人豈不與此矛盾嗎?
理性的詩人要看他具備的是什么樣的理性,如果是利害人我的得失計較,那一定永遠也寫不出好詩,就算不是利害人我的計較,兩晉間流行過玄言詩,同樣枯燥無味,而像陶淵明、晏同叔這樣的理性詩人的作品就不同于上述兩種情況了,他們所寫的詩,我稱之為理性之詩,他們從生活的經(jīng)歷和體驗之中得到了一種智慧的觀照,他們是用心靈去體驗生活的,他們的心靈是敏銳的,真誠的,他們也同樣把所有敏銳真誠的感受都寫了出來,但比之純情的詩人,則他們卻多了節(jié)制和反省,有一種思致和操持,這是理性的詩人最可貴的一點,陶淵明達到了這一標準,他的詩歌是他的心靈和智慧的結晶,他是這類詩人中最有代表性的作者。大晏沒有他這樣偉大的成就,大晏是“具體而微”的,有那么一點點理性詩人的味道,但是沒有陶淵明那么多那么繁復的思致。一般人還有一種成見,認為“詩窮而后工”,是說詩人生活要窮苦抑郁才寫得出好詩,清朝一位詞人曾說“天以百兇,成就一詞人”,對于某些作者,這話不無道理,李后主后期詞之所以取得那樣高的成就,曹雪芹之所以寫出《紅樓夢》這樣的巨著,都因為他們確實經(jīng)歷了自己一家一國的敗亡。司馬遷早在《史記》中就說“《詩》三百篇大抵圣賢發(fā)憤之所為作也”。這對某些作者來說是果然如此的。
可是,對大晏來說,則是一個例外。大晏是一個仕宦顯達的人,他十四歲時就以神童得到宋真宗的賞識,擢為秘書省正字,當他十四歲那年以神童參加進士考試時,“神色不變”,考試完畢,真宗親自給他出了考試的賦題,他告訴真宗這個題目在溫課時就作過了。從此以后,真宗就對他另眼相看了。真宗立太子,就是后來的仁宗,召見晏殊要他入宮陪伴太子,并說其所以選擇他是因為他生活檢點謹慎,不像其他的大臣出入于聲色之場。晏殊說不然,自己只是因為家里經(jīng)濟拮據(jù),才沒有和他們一樣去聽歌看舞,真宗更信任晏殊的誠實。晏殊直上青云,做過樞密使、參知政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有的人就以此認為像晏殊這樣的人能寫出好詞嗎?或以為他的詞是“富貴顯達之人的無病呻吟”。在晏殊的詞中確實很難找到他人詞中常見的牢騷感慨,抑郁悲憤,他的詞集叫《珠玉詞》,他的詞表現(xiàn)得像玉一樣的溫潤,珠一樣的圓潔,沒有激言烈響,而且無需挫傷憂患的刺激,他所流露和抒寫的乃是他珠圓玉潤的詩人的本質(zhì)。這也是他的詞難講的原因之所在。
現(xiàn)在我們就講他的一首《浣溪沙》:
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閑離別易銷魂,酒筵歌席莫辭頻。
滿目山河空念遠,落花風雨更傷春,不如憐取眼前人。
這是晏殊很有特色的一首詞。“一向年光有限身”,非常尋常的一句詞,卻有極深銳的感受,這里的“一向”是短暫的意思,而什么叫“年光”呢?年光也就是年華,是一年之中的芳華,也就是一年中最美好的時光。陽春三月,春天是短暫的,生命也是短暫的,所以說“一向年光有限身”。這一句中有很深的悲慨,一般人常認為要有極大的挫傷憂患才能寫出好詞,那么像晏同叔這樣仕宦順利,卻也寫出這樣的好詞,這是什么原因呢?我以前說過,李后主寫的“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是透過他本人的沉痛寫出這天地間有生之物同有的悲哀,而大晏他不需要有個人破國亡家的悲慘遭遇,他就以自己敏銳、真純的心靈去體會了那種共有的苦難和悲慨。
花開花落月圓月缺這也是人類共有的無常的悲慨,晏同叔即使是仕宦顯達,他同樣感受到了這種悲慨。李后主寫悲慨時非常主觀,是帶著沉重的哀感寫出來的,晏同叔的妙即在于他雖然也有悲慨而表面上卻好像是在表現(xiàn)一個客觀現(xiàn)實的景象,沒有深悲極恨的口吻,也沒有寫得血肉淋漓,這已足可見出其珠圓玉潤之風格了。可是人生可悲哀的還不只是“一向年光有限身”而已,他的第二句是“等閑離別易銷魂”,何謂“等閑”?等閑就是輕易之意。李后主的詞“別時容易見時難”,“別時容易”就是那么輕易就離別了。天下沒有人沒經(jīng)歷過生離死別,不管是什么樣的離別,只要有聚會就一定有離別,離別是很容易就來臨的,這樣短暫的韶華,這樣短暫的人生,卻充滿了離別的悲哀,所以晏同叔說是“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閑離別易銷魂”,這很容易引起大家的感傷,所謂“銷魂”就是心神之中黯然的悵惘之感。晏同叔所寫的不是和李后主的《相見歡》有許多相似的地方嗎?他說“一向年光有限身”這種無常之感不就等于“林花謝了春紅”嗎?!可是李后主由此寫下去的結尾,乃是“人生長恨水長東”,而晏同叔的結尾卻是“酒筵歌席莫辭頻”,他不沉溺于那種深悲極恨之中,他不僅是有反省有節(jié)制,而且還隱然有著安排處理的辦法。
正是對待苦難處理安排的不同,造成了各個詞人風格的不同。李后主是根本沒有處理安排的辦法的,他只有一味沉溺于悲苦之中;再如蘇東坡是超然的曠達,歐陽修則是有一種遣玩和欣賞的意興;而大晏似乎有一種安排處理的辦法。究竟該怎樣去排解悲哀愁苦?他說是你要有酒的時候就去飲酒,有歌的時候就去聽歌,不要說聽歌飲酒的次數(shù)太多而推辭,因為那銷魂的傷感比那歌筵酒席還更多,所以說是“酒筵歌席莫辭頻”,正像馮正中所說的“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辭鏡里朱顏瘦”,但是馮正中的口吻是執(zhí)著深刻的,而晏同叔卻說得那樣清淡,然而盡管筆墨清淡如許,感覺卻是敏銳的,真誠的。而下半闋的“滿目山河空念遠,落花風雨更傷春”則寫的是念遠傷春之情。理性的詩人不是沒有感情的,不是麻木不仁的。“滿目山河”引起了“念遠”的感情,念遠就是懷念遠行之人,登高望遠,是古今中外一切與親友分別的人的共同感受,從“滿目山河”到“念遠”是他感情的抒發(fā),可是“空”字卻在感情中表現(xiàn)了一份理性的反省,“念遠”有何用呢?要是李后主,他沉溺在“念遠”之情里面,就不會反省到念遠是空的,而晏同叔則有一種理性的“空念遠”的認知。
然后下一句的“落花風雨更傷春”,是詩人對傷春的敏銳的感受。而大晏詞之妙處則在對“空”字和“更”字的應用,起到了雙層加深的作用:“更”字是加倍的意思,是說我已經(jīng)有了念遠的悲哀再加上傷春的悲哀,而一個“空”字也貫串了兩句的情意,念遠是空的,傷春也是空的,“念遠”不一定就能相逢,“傷春”也不一定能將春光留住,不可得的仍然是不可得的,無法挽回的仍然無法挽回,所以“滿目山河空念遠,落花風雨更傷春”二句有詩人的感受,更有理性的認知。那么又該如何去做呢?他說是“不如憐取眼前人”,“憐”也有尊重愛惜之意,大晏是有安排處理的,他懂得只有尊重愛惜了今天,才有真正美好的未來,只是在那里空空的“念遠”、“傷春”,過去的不可挽回,未來的也將不可獲得。可知,大晏詞中是既有詩人的感發(fā),又有理性的反省和節(jié)制,而且還隱然有一種處理安排的辦法。晏殊很喜歡用“不如憐取眼前人”這一句,在他的一首《木蘭花》詞中,他也曾寫道“不如憐取眼前人,免使勞魂兼役夢”,要珍愛今天所有的,不要徒然地勞魂役夢,“勞魂”、“役夢”寫得很好,我們常以為體力才會有“勞”,實際心力也是有“勞”的,“役”者本是行役的往返,他說你是精神夢魂的行役往返。
而晏殊是有一份面對現(xiàn)實的理性的,所以他說“不如憐取眼前人,免使勞魂兼役夢”,他在傷感中還有一種處理安排的辦法。他也不同于李后主“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他曾做到樞密使和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軍事和行政的最高長官,他在處世和論政方面也有才干和眼光。據(jù)史書記載,真宗去世,仁宗即位,真宗的章獻劉皇后任事,當時的樞密使曹利用與宰相丁謂爭權,曾經(jīng)都請求獨見太后奏事。后來晏殊就說請劉太后垂簾與仁宗一起聽政,所有的大臣都不可獨見奏事,于是論議遂定。可以看得出來,在論議政事的時候,晏殊是有主見的。在北宋對西夏用兵時,晏殊也曾提出請罷免內(nèi)臣監(jiān)兵,朝廷不要以陣圖授諸將,而要使將領對指揮戰(zhàn)事有自決權和自主權。可見對軍政事務,晏殊也隱然有一種處理的辦法。所以他是一位富有理性的詞人。晏同叔的詞沒有激言烈響,像李后主的詞“林花謝了春紅”,他第一句的“謝了”二字就表示出這么深的哀悼,是非常強烈的主觀的感情。晏同叔也哀悼人生的短暫,可他的“一向年光有限身”,用的卻是客觀的口吻,沒有直接表示出主觀的感情,這是晏同叔與李后主的最大的不同之處。
現(xiàn)在,我們再講他的另一首《浣溪沙》,來看看他的另一種特色,這首詞是這樣的:
一曲新詞酒一杯,去年天氣舊亭臺,夕陽夕下幾時回。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小園香徑獨徘徊。
欣賞大晏的詞要有耐心,還需要細心,“一曲新詞酒一杯”,這是非常平淡的幾個字,沒有像溫飛卿的“小山重疊金明滅”那樣美麗的詞藻,沒有像李后主“林花謝了春紅”那樣強烈的感情。文學創(chuàng)作中可以選擇各種途徑達到感發(fā)的目的。有的人是以一字一句寫得出色見長的,像王安石的“春風又綠江南岸”,他的“綠”字就是經(jīng)過多次修改才定稿的,他曾經(jīng)用過“滿”、“到”、“過”等字,最后畫龍點睛用了“綠”字,形象鮮明地表現(xiàn)了江南春天的到來。可是大晏的這一句“一曲新詞酒一杯”,卻沒有任何特別精警的字,也沒有強烈的感發(fā)之力,晏同叔銳敏的感受和感發(fā)的力量是要通過他整首詞來傳達的,他說“一曲新詞酒一杯”,后面是“去年天氣舊亭臺”,“一曲新詞”是當歌,“酒一杯”是對酒,當歌對酒的本身,本來就可以給人以感動,曹孟德的“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像曹操這樣一代英豪,當他對酒當歌時也會說出這樣感慨悲涼的話來。
還有歐陽修《采桑子》“十年前是樽前客,月白風清,憂患凋零,老去光陰速可驚”,他說在十年前喝酒之時,這里月光明亮,晚風輕悠,十年間的事一瞬間便過去了,他用“憂患凋零”接在“月白風清”之后,是一種突然的跳接,十年后的今天,回首往事是“老去光陰速可驚”,他后面說“鬢華雖改心無改,試把金觥,舊曲重聽,猶是當年醉里聲”。經(jīng)過了十年的憂患凋零,鬢發(fā)的顏色已有了變化,而心情未改,他“試把金觥”,還要“舊曲重聽”,結果是“猶似當年醉里聲”,仍然像是聽到當年醉里所聽到的歌聲。我們現(xiàn)在說的是兩層意思,第一層是“對酒當歌”的本身就可以引起你內(nèi)心之中的感動,晉朝的桓伊每聽清歌,輒喚奈何,是每聽人唱清歌,就有一種無可奈何的感情;第二層不僅是對酒當歌,而且是重聽當年的歌,重新喚起過去的回憶,所以只是聽歌飲酒的本身,就可以引起你無法安排的感動,像陶淵明所寫的《飲酒》詩二十首,蘇軾曾批評說“陶公方飲酒時,不知緣何記得此許多事”。
從這二十首《飲酒》詩中你可以看到陶淵明飲酒時有多少思量和感想。因此晏殊的詞“一曲新詞酒一杯”一句,乍看雖似乎平淡,而后一句是“去年天氣舊亭臺”,跟去年一樣的天氣,是什么樣的天氣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