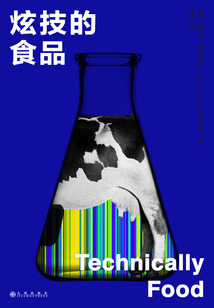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序言
為何是我
從生命中的某個時刻起,食物讓我緊張而焦慮——我12歲時。在那之前,我都輕松地享受著吃的快樂:生日派對中的杯子蛋糕,光明節[1]上的土豆煎餅,周末時祖母拿手的法式哈拉吐司[2]。
有一段記憶我從未與任何人分享:我坐在教室里,突然想要小便,但我知道已經來不及離開椅子,穿過走廊,再走到女洗手間。于是我安靜地坐在那兒,尿在了褲子里。這是一段影響深遠的經歷。
媽媽注意到了正在發生的事,但還沒能引起警惕。她帶我去看醫生,是因為我的一次耳痛。當伯恩鮑姆醫生為我做完耳鏡檢查后,媽媽不經意提到,我總是感到口渴,小便也很多。護士給我做了尿檢,結果顯示:1型糖尿病。我并沒有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隨即被送進了醫院。除了半夜被護士叫醒讓我惱火,我認為醫院的一切還挺整潔有序。爸爸給我帶來了無糖蘇打水,護士在上面標注了我的名字;我看了很多電視節目;哥哥也對我態度溫柔;躺在床上,我能看見101高速公路蜿蜒穿過圣費爾南多山谷。
診斷結果意味著,當我吃東西時,將永遠需要攝入胰島素。這種由胰腺分泌的激素幫助食物(主要是碳水化合物)分解的葡萄糖進入細胞。身體的細胞和器官依賴葡萄糖。想要跑步?胰島素為你提供燃料。沒有了它,你將無法進食。在胰島素被發現之前,糖尿病患者總是瘦得像皮包骨,壽命也很短。我的醫生要求我健康飲食,并堅持運動。這從此成了我的座右銘。一個糖尿病教師(diabetes educator)教會了我如何計算每一餐中碳水化合物的克數——聽上去就很難。計算的結果將決定用餐時需要注射的胰島素劑量——聽上去就很可憐。當我把計算弄錯的時候,身體便會出現汗流浹背或像是在流沙中移動之類的生理反應——很艱難、很可憐、很糟糕。我的病情并沒有妨礙我做任何事,但我卻不擅長監控它。那時,我還僅僅是個少年。
在我的世界中,某種食物的好壞取決于它的主要成分,即碳水化合物、蛋白質、脂肪和纖維。當我吃一個蘋果時,我真正吃進去的是蘋果含有的宏量營養素。我選擇青蘋果,因為它們通常沒有紅蘋果那么甜。我選擇一整個蘋果而不是果汁,因為果汁缺乏纖維,而纖維能夠延緩消化,也不會被完全吸收。果汁中的糖分很容易被身體吸收,這些糖分也會瞬間引發我血糖的飆升——這很難從外部應對。一個健康的身體能夠輕而易舉地應付血液中葡萄糖含量的起伏。然而,如果你有2型糖尿病,就當我什么都沒說。1型糖尿病意味著我似乎在身體中追逐著一個接力跑選手,后者不肯減慢速度把接力棒傳給我。2型糖尿病患者體內仍然在產生胰島素,但他們的身體卻不能正確利用這些激素。2型糖尿病更加普遍,一些病人能夠通過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和飲食控制病情,直到完全康復。
當我對自己的疾病了解得越發深入,我對身體的持續監測也得到了改善。鍛煉跟學會享受黑咖啡、黑巧克力一樣重要——對于我們這樣的人來說,這是關鍵技能。隨著最新的技術發展,我把一個連續血糖監測儀別在了臀部,還吸入速效胰島素。看到我這么做的人通常以為我是在抽電子煙,但我已經不再為患有糖尿病感到羞恥。獲取的知識讓我具備了一個優勢:從分子層面理解食物。我把這當作是自己的超能力,于我而言,這也是活著和死去的區別。我洞察了食物的一切。
就像一個俄羅斯套娃,我的生存由一堆問題套成:這會兒幾點了?吃東西會對我的血糖有多大影響?吃完飯后我要去散會兒步嗎?我要吃的東西有多少是加工食品或包裝食品?我的這個套娃中,中央最小的娃娃是什么樣子的?最重要的問題是什么?我都想知道。
每當我在超市里發現一種新的食品,在把它倒進碗里前,我都會看一眼營養成分表。這個標簽是世界上復制最多的圖表之一,但很少有人像我這樣重視它。一項2018年發表在《營養和飲食學會雜志》(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Nutrition and Dietetics)上的研究稱,在其調查的2000名年輕人中,只有31.4%的人在購物時會“經常”看營養成分表。雖然這個標簽隱藏的信息和它披露的一樣多,但當我們選擇吃什么的時候,它仍然是最有價值的參考資料。
在30多歲時,我意識到這個世界上大部分人都不會像我這樣費心地觀察食品。當開始報道食品技術行業時,我感到這是自己作為記者能做的特殊貢獻。食品的好壞取決于它的成分——以此為基礎框架,我從事高科技領域的背景調查工作十余年,這段經歷也讓我迅速地進入了初創公司的世界。在我看來,目前食品投資領域的熱潮跟互聯網的第一次浪潮驚人地相似。
報道食品技術初創公司也意味著,我身邊(大部分)是年輕的創業者,他們相信自己能夠“讓世界變得更好”。他們募集到的成百上千萬美元認可這份自信——彰顯了他們要么聰明過人,要么將要成就大事。但是我尋找的不是這種“炒作機器”。我渴望了解新聞標題背后的故事。我需要合乎常識的科學,以及理性的認識——什么才能改善我們每個人的食物系統。我也希望探索一組三重價值底線:有益于自己,有益于環境,有益于商業。這本書始于我對自己提出的一個問題:“當我們擁抱一個充斥著實驗室食品的未來時,我們會失去什么?”隨著調查的深入,我試圖將討論延伸到,對像我這樣的1型糖尿病患者而言,新型食品是否也能提高我們的幸福感?
當前這一波食品公司浪潮是由使命驅動的。它們的創始人想要通過未來化的方式來改善我們的世界。他們希望扭轉氣候變化的進程。他們試圖結束工業化農業對動物的虐待及對地球的傷害。但金錢和投資者仍然在這些公司背后推波助瀾。資本主義撬動著杠桿。現在,像泰森、雀巢和通用磨坊等公司(一些我有時稱之為“食品巨頭”的傳奇品牌)已經感受到了利潤下降的壓力——他們過時的產品組合不再受到新生代消費者的青睞——但他們也不會甘為人后。他們過去的行為、金融影響力和控制力——增加糖的用量、利用從眾效應、以兒童為主要營銷對象——都不容忽視。
在這些彼此沖突的勢力之間,緊張關系在加劇。這種狀況影響著像我這樣患有糖尿病的人,影響著我患有乳糜瀉[3]的嫂子,影響著我好友3歲的孩子——他愛吃水果,影響著缺乏食品安全的社區,影響著老年群體以及無家可歸者。食品影響著每一個人。當前世界人口已將近79億,我們的自然資源正顯示出枯竭的跡象,人們希望知道:我們能夠同時做到保持健康、尊重飲食傳統和保護生態環境嗎?這并不是奢望。
為何是現在
拉爾夫·納德(Ralph Nader)是一位長期的消費者權益斗士,他曾憑借推動在汽車上安裝安全帶的維權行動名聲大噪;納德另一廣為人知的事跡,是在20世紀70年代對嬰兒食品的清理。他要挑戰的是廠商在嬰兒配方奶粉中使用添加劑——變性淀粉和味精(谷氨酸鈉)——的行為。廠商這么做不是為了嬰兒的健康,這些添加劑含有高水平的谷氨酸(味精中最主要的氨基酸),會對嬰兒造成潛在的危害。添加這些物質,是為了讓媽媽們更喜歡奶粉的味道,延長保質期,改善溶解性。但納德遇到了麻煩,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FDA)并沒有對廠商的行為主動出擊,而只是被動應對。納德說,發現我們食品供應中的問題這個重擔,被甩給了行業外的研究者。“我們食品行業一以貫之的特點之一,是喜歡先把產品賣出去,再讓別人來檢測。”他說。
那場監管大戰過去已有50多年。最終FDA禁止了嬰兒食品中味精的使用,但為了對沖風險,讓生產商也高興,FDA同時宣稱:“味精對人類而言是安全的,只是嬰兒并不需要。”這個故事的另一個寓意是,這種情況在如今的新型食品公司身上也比比皆是。FDA依然消極作為,食品公司依然沒有主動確認產品的安全性,由此逃避應有的責任。
最近,針對嬰兒配方奶粉銷量的下滑,食品公司推出了一款新型嬰兒牛奶。這種牛奶中含有一長串的成分,其中包括一些令人擔憂的物質,例如玉米糖漿、棕櫚油和聚右旋糖——一種提升口感的纖維。嬰兒食品只不過是加工食品的一小類。有害的物質無處不在,譬如人工合成食用色素、糖精和吡啶[4]等。這些化學物質由于有致癌性,全都被FDA列入了移除清單,但如今它們仍然在使用。你或許想知道為什么。這是因為,FDA給了食品公司足夠長的時間期限,去重新制定配方和去除這些被禁成分。與此同時,產品還未被召回,因此你很容易就能在亞馬遜網店里找到這款嬰兒牛奶。
我們期望自己吃到的食品是有史以來最安全的。在許多方面,它們確實如此。我不否認我們的監管體系基本有效,但全球人口的健康正在衰退,很大程度是因為美式飲食的盛行。是時候審視我們的舊習了,因為我們正在轉向新型食品:不是從奶牛擠出來的奶,不是由雞下的蛋,不是在海里游泳的蝦。未來的食品依賴于訓練有素的科學家,他們中的很多人從醫藥領域跨界過來。細胞和組織生物學家、分析化學家、食品科學家和工程師合作創造出他們聲稱會有益于世界的新型食品。但是要想養活幾十億的人口,我們需要一個規模與之匹配的龐大供應鏈。
要想從幾乎“空無一物”的酵母菌、細菌和其他單細胞生物中制造出食品,我們需要工業化的系統,這個系統依賴于甘蔗和玉米等作物,也需要胰島素、生長激素和氨基酸等物質。如果在當前的工業生產方法下,我們的健康每況愈下,難道我們不應該尋找一種新的方式,來避免相同模式的延續嗎?
在20世紀,隨著食品生產從農場轉移到了工廠,傳統智慧認為人們不愿知道“香腸是怎樣做出來的”。這是說,人類為了滿足口腹之欲而屠殺動物,是一種必要的罪惡,但人們卻不愿意思考這個問題了。2000年初,一場透明化運動開始拉開窗簾,讓光線透進了黑屋。名廚丹·巴伯(Dan Barber)和作家邁克爾·波倫(Michael Pollan)在他們寫作的書籍中告訴我們,食品的品質至關重要,風味是需要我們恢復和保留的自然遺產的標志。千禧一代更希望從有機農場和具有使命感的公司那里購買食品,他們喜歡簡短、能夠識別的成分標簽。我們食物系統中更有力的問責制度、特殊飲食法的增多、健身的興起和營養學研究的新進展,都帶來了可喜的變化。
很難找到一本書像邁克爾·波倫的《雜食者的兩難》(The Omnivore's dilemma)一樣能打動如此多的人(包括我自己),并促使現代食品領域發生深刻的方向性變革。甚至連食品巨頭們也感受到了壓力。科技從業者放棄公司的工作轉而經營農場,消費者開始更關心和在意自己購買的東西。令人興奮的事還包括“從農場到餐桌”運動、“慢食”運動以及回歸生物多樣性。波倫的書從根本上改變了圍繞食品的討論。但他并不是單靠自己就獲得了這樣的成功。事實上,弗朗西斯·摩爾·拉佩(Frances Moore Lappé)的《一座小行星的飲食》(Diet for a Small Planet)一書最早開啟了這場討論。“一小撮人為了少數人的利益,控制著一個最浪費又最低效的食物系統。”她寫道。這個觀點至今都在我耳畔響起。
2015年,當開始報道食品和科技的交叉領域時,我快步跟進食品行業的飛速發展,同時我也在留意,是否會有創業者提及這些作家和他們書里的經驗教訓。但沒有創業者這樣做。跟納德一樣,波倫也十分憂慮我們太過依賴一個自身并不了解的食物系統。他寫道:“增加我們對要吃什么的焦慮,進而再用新的產品來撫平焦慮,這種做法非常符合食品行業的利益。”在書中,他指出當面對超市中滿滿當當的貨架上無窮無盡的新型食品時,我們是多么的混亂和困惑。《雜食者的兩難》早在2006年就出版了,但是到現在,食品行業似乎什么都沒有改變。
由于對自己的飲食無比警覺,我也在尋找方法來舒緩與糖尿病共存產生的精神壓力。我嘗試過各種各樣的飲食法,包括Whole 30飲食[5]、間歇性斷食、植物性生酮飲食[6]。通過這些方法,我覺察到,加工食品吃得越少,自己對血糖的控制就越容易,感覺和睡眠也變得更好。水果、蔬菜、谷物和豆類(僅舉幾例),特別有益于我們的身體健康,但當我們匆匆忙忙地趕時間或面對琳瑯滿目的誘人零食和飯局時,它們很容易就被忽視。未來食品正在突飛猛進,加工植物代替了天然植物,替代蛋白質代替了傳統蛋白質。哪一種更健康?食品技術創新者希望,當這些新型食品變得跟傳統食物同樣美味時,我們便不會在意這個問題了,但我會。它們的實質也同樣可靠嗎?在書中,我將對這些謎一般的食品追根溯源,通過我的報道去揭開它們的神秘面紗。
本書的寫作,是為了幫助那些像我一樣熱愛美食的人多獲得一些科學常識。我所調查的未來食品或許會也或許不會扭轉即將到來的環境災難,它們能否提供一種更全面、更令人愉悅的飲食方式也有待觀察。在疫情仍然持續的當下,我們的飲食正在從動物轉向植物,從簡單化轉向科學化,這是通過持續的努力得來的一條清晰路徑,但愿我們不要丟掉。我希望本書能夠引發更多的討論,讓人們更加關注“香腸是怎樣做出來的”這個問題,即使當香腸已經是由植物和真菌制造的時候。
腳注
[1]又稱哈努卡節、修殿節,是猶太教的傳統節日。——譯者。
[2]哈拉面包(Challah bread)是猶太人的傳統面包,通常編成辮子的形狀烘烤。法式哈拉吐司,是把哈拉面包片在牛奶雞蛋液中浸泡后,再兩面涂抹黃油煎制或烘烤。——譯者。
[3]又稱麩質敏感性腸病,在遺傳易感個體中由環境因素(麩質)觸發的一種慢性自身免疫性腸道疾病。乳糜瀉最初被認為只發生在兒童時期,現在被認為是一種可以發生在任何年齡段的常見疾病。典型的癥狀有:腹瀉、便秘、腹脹、腹部不適、厭食、惡心、嘔吐和體重減輕。——譯者。
[4]吡啶是一種雜環芳香化合物,可從天然煤焦油中獲得,但效率低下,目前吡啶主要通過其他途徑化學合成。吡啶在工業上可用作溶劑、變性劑、助染劑,以及合成一系列產品的起始物,包括藥品、消毒劑、染料、食品調味料、黏合劑和炸藥等。2017年10月27日,世界衛生組織國際癌癥研究機構公布的致癌物清單中,吡啶屬2B類致癌物。——譯者。
[5]這種飲食法注重天然食物,要求在30天內禁止攝入糖、酒精、谷物、乳制品、豆類、味精和亞硝酸鹽等。——譯者。
[6]生酮飲食是一個高脂肪、極低碳水化合物、蛋白質和其他營養素適量的飲食法。——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