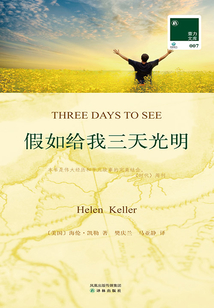最新章節
- 第66章 The Third Day
- 第65章 The Second Day
- 第64章 《Days to See》:The First Day
- 第63章 The Story of My Life(24)
- 第62章 The Story of My Life(23)
- 第61章 The Story of My Life(22)
第1章 《我生活的故事》:跌入黑暗
我是懷著惶恐不安的心情來寫我的人生經歷的。我的童年如同籠罩了一層金色的迷霧,當我嘗試著要把這層神秘的面紗揭開的時候,內心充滿了無限的躊躇。回憶自己的人生道路,并把它訴諸筆端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何況童年離我已經久遠,至于哪些是事實,哪些只是我的想象,我自己都無法分清了。也許女人總是憑想象描繪童年時的圖畫吧,在我生命的最初幾年里,有些事情鮮明而生動,現在回想起來仍然栩栩如生,但是,其余的部分卻模糊不清。何況童年時的許多喜悅和悲哀已經被時間漸漸沖淡了顏色,面目全非。而我早期教育中好些至關重要的事情,也隨著后來若干個激動人心的重大人生經歷而變得虛無縹緲了。因此,為了避免枯燥乏味,我將試圖把那些在我看來最為有趣和最為重要的情節描述出來。
我于1880年6月27日出生在美國南部亞拉巴馬州北部的塔斯甘比亞鎮。
我的祖先卡斯帕·凱勒最初是瑞士人,后來移民到美國,并在馬里蘭州定居。令人驚奇的是,我的祖先當中竟然有一位是蘇黎世最早的聾啞教師,并且他還撰寫了一本關于聾啞人教育的著作,可以稱得上是一位聾啞教育專家。任何一位國王的祖先也并不都是國王,任何一位奴隸的先人也并不都是奴隸,但是我想我那位偉大的祖先在實踐他偉大事業的時候,怎么也不會想到他會有我這樣一位又聾又啞的后人。每當想到這些,我總會對世事的變幻莫測大大感嘆一番。
自從我的祖父,也就是那位偉大的聾啞專家——卡斯帕·凱勒的兒子,在亞拉巴馬州買了土地后,整個家族最終就在那里定居下來。據說,祖父經常要騎馬到費城去購買種植園所需的材料,譬如農具、肥料和種子等。祖父每次在往返費城的途中,總會寫家書報平安,信中對西部沿途的景觀,以及旅途中所遭遇的人、事、物都有清楚且生動的描述。姑母至今還保存著這些書信。今天,我們家族的人仍很喜歡時常翻看祖父留下的信札,因為它們就好像是一本歷險小說,耐人尋味,讓人百讀不厭。
我的祖母可謂出身顯赫。她的父親是拉斐特的救護兵亞歷山大·莫爾,祖父是弗吉尼亞早期的殖民總督亞歷山大·斯波茨伍德,他的表兄是羅伯特·李將軍。我的父親亞瑟·凱勒曾是南北戰爭時南方軍隊的陸軍上尉,我的母親凱蒂·亞當斯是父親的第二任妻子,她要比父親小好多歲。母親的祖父,也就是本杰明·亞當斯,和祖母蘇珊娜·古德休結婚以后在馬薩諸塞州住了許多年。他們的兒子,也就是我的外祖父——查理·亞當斯就出生在馬薩諸塞,隨后他們就遷到了阿肯色州的海倫納。當內戰爆發的時候,查理奮力為南部聯邦的利益而戰,后來成了一名陸軍將軍。他的妻子是露西·海倫·埃弗雷特,她和埃德華·埃弗雷特(即黑爾)是一個家族的,他們都屬于埃弗雷特家族。內戰結束后,這個埃弗雷特家族就遷移到了田納西州的孟菲斯。
在我生病失去視覺和聽覺以前,我一直住在一個小院子里面。這個院子里總共只有一間正方形的大房子和一間供仆人住的小房子。依照南方人的住宅習慣,他們往往會在自己家的旁邊再加蓋一間屋子,以備急需之用。南北戰爭之后,父親也蓋了這樣一所屋子,在他和母親結婚之后,他們就住進了這個小屋。葡萄的枝蔓爬滿了整座小屋,還有薔薇和忍冬,從院子里看去,它就像是一座用樹枝搭成的漂亮涼亭。而小陽臺則藏在黃薔薇和南方所特有的茯苓花的花叢里,儼然成了蜂鳥和蜜蜂的世界。
凱勒家族的老宅離我們的薔薇涼亭只有幾步之遙。因為房子、柵欄以及周圍的樹木都被美麗的英國常春藤所包圍,所以大家都風趣地稱我們的家是“綠色家園”。老宅里面的老式花園是我童年時代的天堂。
在我的家庭老師——莎莉文小姐走進我的生活之前,我經常獨自一個人,沿著方形的黃楊木樹籬,悠然地走在庭園里,憑著自己的嗅覺,循著清新的芳香,去尋找那初開的紫羅蘭和百合花,那時我深深地陶醉在清新的世界里。心情不好的時候,我也會獨自到這里來尋求解脫,那時候,我常常會讓滾燙的臉龐沐浴在清新宜人的樹葉和草叢之中,讓煩躁不安的心情慢慢冷靜下來。置身于這個綠色花園里,真是心曠神怡。我在這個百花園里不停地走著,偶然碰到一株很美麗的葡萄,觸摸上面的花葉,才知道是高高覆蓋在矮小涼亭上的葡萄樹,而我竟不知不覺地走到了園子的另一個角落。這里有滿地蔓延的卷心藤,有低垂的茉莉,還有一種十分罕見的花,叫做蝴蝶百合的。這種花散發出一陣陣甜絲絲的氣味,因為它那容易掉落的花瓣很像蝴蝶的翅膀,由此得名。但最美麗的還是那些薔薇花,在北方的花房里,是很少能夠看到薔薇的。它們到處攀緣,爬動,一長串一長串地倒掛在陽臺上,雖然生長在泥土中,但是卻絲毫沒有塵土之氣,并且還四處散發著芳香。清晨的時候,朝露未干,輕輕地撫摸它們,感覺它們是那么的柔軟,那么的高潔和神圣,會使人完全陶醉于其中。每當這時候,我就不禁會想,它們和上帝花園里的日光蘭比起來一點也不遜色!
我生命的開始就像每個家庭迎接第一個孩子一樣簡單而普通。我的出生也給家庭帶來了喜悅。我出生以后,大家的主要任務就是給我取一個好名字。為了給我取名字,大家都絞盡腦汁,你爭我吵,每個人都認為自己想出來的名字才是最好的、最有意義的。父親希望以“米爾德里德·坎貝兒”作為我的名字,因為這是他最尊敬的一位前輩的名字,為什么最后沒有被采納我就不得而知了;母親則提議用外祖母少女時代的名字,也就是“海倫·埃弗雷特”來給我命名。經過大家的再三討論,最后還是依照母親的意思,用外祖母的名字做了我的名字。
起名事件剛剛告一段落,誰知為了要帶我去教堂受洗禮,大家又手忙腳亂,以至于父親在前往教會途中,竟興奮地把為我新取的名字給忘了。受洗禮時,當牧師問起“這個嬰兒叫什么名字”時,緊張而又興奮的父親竟脫口說出了“海倫·亞當斯”這個名字。從此以后,我也就不再使用外祖母“海倫·埃弗雷特”這個名字,而變成了“海倫·亞當斯”。
家里的人告訴我,當我還在襁褓中的時候就表現出好強、自作主張的個性。對于別人做的一切我都非常的好奇,尤其是對大人的一舉一動,我都想模仿。在我六個月大的時候,我就已經能夠說“你好”了,直到有一天我能夠發“茶!茶!茶!”的聲音,這才引起了全家人對我的注意。甚至在我生病以后我還清楚地記得我早些時候學過的一些字。“水”就是其中的一個。生病以后,我忘記了所有的字怎么讀,但仍記得“水”。
家里人還告訴我,我剛滿周歲就會走路了。記得那天母親把我從浴盆中抱起來,放在膝上,突然,我發現在光滑的地板上閃動著的樹影子,就本能地從母親的膝上溜下來,然后自己一步一步地、搖搖擺擺地去踩踏那些影子。這種沖動的走動,使我摔在了地上,后來母親把我抱了起來。在母親驚訝的眼神中,我學會了走路。
人們常說,美好的時光總是短暫的,對我來說更是如此。春天百鳥啼鳴,歌聲盈耳,夏天到處是果子和薔薇花,待到草黃葉紅已是深秋來臨。三個美好的季節雖然轉瞬即逝,但在一個活蹦亂跳、咿呀學語的孩子的腦海中卻留下了永恒的記憶。在一個百花盛開,知更鳥和百靈鳥歡樂歌唱的春天,在一場高燒的病痛之后,我的幸福就慢慢消失了。在第二年那個可怕的二月里,我突然生病,并且高燒不退。醫生們診斷的結果是急性的胃充血以及腦充血,并且醫生斷言我根本就不可能再活下去了。全家人聽到這個消息,仿佛五雷轟頂一般。但在之后的某一個清晨,我的高燒突然退了,全家人的驚喜可想而知。但是,這一場高燒卻讓我失去了視力和聽力,我又變得像嬰兒一般無知,而我的家人,甚至連醫生,都不知道我已經喪失了聽力和視力,已經不是一個正常人了。
對于那場病,我至今還記憶猶新。特別是母親在我高燒不退、昏昏沉沉、痛苦不堪的時候,溫柔地撫慰我,讓我在恐懼中勇敢地度過。我仍然記得在高燒退后,因為干枯燥熱、疼痛怕光,所以必須避開自己以前喜歡的陽光,我面向著墻壁,或讓自己在墻角蜷伏著。后來,視力每況愈下,對陽光的感覺也漸漸地模糊不清了。有一天,當我睜開眼睛,眼前一片黑暗,使勁睜了睜眼,發現自己竟然什么也看不見時,當時的那種感覺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我悲傷極了,像被噩夢嚇到一樣,全身驚恐,我從來沒有那么絕望過。
失去了視力和聽力后,我逐漸忘記了以前我對生活的熱愛和渴望,只是感到,我的世界充滿了黑暗和冷清。直到她——我的家庭教師莎莉文小姐的到來。是她減輕了我心中的負擔,點燃了我心中已經泯滅的希望,也是她重新給了我認識世界、感受世界的眼睛,讓我在黑暗的世界里也能感受到些許的光明。
我只擁有十九個月的光明和聲音,但我卻仍可以清晰地記得在這有限的時間里所接觸的一切美好的事物——寬廣的綠色家園、蔚藍的天空、青翠的草木、姹紫嫣紅的鮮花……所有這些都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腦海里,永生難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