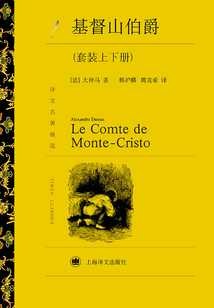
基督山伯爵(套裝上下冊)(譯文名著精選)
最新章節(jié)
書友吧 4評論第1章 譯本序(1)
一
法國文學史上有兩位著名的仲馬:一位是本書和《三個火槍手》的作者大仲馬(1802—1870)。同歐仁·蘇一樣,大仲馬是十九世紀上半期法國浪漫主義文學潮流中另一個類型的杰出作家,他在當時報刊連載通俗小說的高潮中,用浪漫主義的精神和方法,創(chuàng)作了故事生動、情節(jié)曲折、處處引人入勝的長篇小說,把這種文學體裁發(fā)展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水平、新境界。另一位是《茶花女》的作者小仲馬(1824—1895),他是法國戲劇由浪漫主義向現(xiàn)實主義過渡期間的重要作家;他是大仲馬的私生子,當他把小說《茶花女》改編成劇本首演成功時,曾電告其父:“就像當初我看到你的一部作品首演時獲得的成功一樣。”大仲馬回電道:“親愛的孩子,我最好的作品就是你。”
這里且說大仲馬。一八〇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大仲馬誕生于法國北部的維萊科特雷鎮(zhèn)。他的父親曾是拿破侖手下的陸軍少將,母親是科特雷鎮(zhèn)上一家旅館的老板的女兒。大仲馬才四歲,父親就離開了人間,因此他在幼年、少年以至青年時代始終生活在窮困之中。大仲馬的母親希望兒子能學得一技之長,節(jié)衣縮食為他請了小提琴教師,但他學不下去;后來母親又要他去神學院就職,他也安不下心來。然而他是個有天賦的孩子,而且有他自己的抱負。一次偶然的機會,他跟撞球店老板賭輸贏,結(jié)果贏了九十法郎,他把這筆錢用作到巴黎去的旅費,開始了他的新生涯。到巴黎以后,他憑借父親的人事關(guān)系,在奧爾良公爵的私人秘書處尋到了個抄抄寫寫的差事。與此同時,他狂吞亂咽般地大量讀書,廣泛涉獵了文學、歷史、哲學和自然科學等知識領(lǐng)域,為日后的多產(chǎn)創(chuàng)作奠定了基礎(chǔ)。看了倫敦的劇團在巴黎演出的莎士比亞戲劇以后,他激動不已地感到“精神上受到強烈的震動”。他花了五個星期寫出了第一個劇本《克里斯蒂娜》,而且得到了內(nèi)行人的好評。但由于一個演慣了古典主義劇目的名演員的阻撓,劇本未能如期上演。現(xiàn)在我們熟知的《亨利三世及其宮廷》,是大仲馬寫的第二個劇本。這個劇本之所以負有盛名,一則由于作品充分顯示了作者卓越的才華,二則由于它是法國第一部突破古典主義傳統(tǒng)的浪漫主義戲劇。經(jīng)過很有戲劇性的一番周折以后,這個批判封建專制主義的劇本終于在古典主義固守的堡壘——法蘭西劇院上演并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它上演的時間,比雨果的《歐那尼》還早一年,不僅開創(chuàng)了歷史劇這個新的文學領(lǐng)域,而且體現(xiàn)了一些浪漫主義戲劇的創(chuàng)作原則,這正是大仲馬在法國文學發(fā)展史上的一個偉大功績。
一八〇三年七月,大仲馬投入了推翻波旁王朝的戰(zhàn)斗,不僅參加巷戰(zhàn),而且獨自把三千五百公斤炸藥從尚松運到巴黎,奧爾良公爵接見了他。前者不久成了國王,但并未采納他的建議,還嘲笑他道:“把政治這個行當留給國王和部長們吧,你是一個詩人,還是去做你的詩吧!”后來他參加了以共和觀點著稱的炮兵部隊,并在歷史劇《拿破侖·波拿巴》的序言中公開了他與國王的分歧。這下他就闖下了大禍,因此被指控為共和主義者,于是被逼經(jīng)常到瑞士、意大利等地去旅行,看來他不光是到國外去游山玩水,其中也還有著“避風頭”的苦衷。但他畢竟是帶著戲劇家的心和眼睛踏上旅途的,一路上難免會有意識地觀察風俗人情,收集奇聞軼事,甚至深更半夜也會到教堂里去聽故事。凡此都在有意無意之間為日后的小說創(chuàng)作作了充分的準備。
三十年代初,法國報刊大量增加,為了適應(yīng)讀者的需要,往往開辟文學專欄,連載的通俗小說便應(yīng)運而生。大仲馬是喜歡司各特的。他仔細鉆研了司各特的歷史小說及其特色后,便運用自己編織故事的神妙技巧和豐富充沛的想象力,從歷史上取材,寫了不少通俗而引人入勝的長篇小說,在報刊上連載,成為當時法國首屈一指的通俗小說專欄作家。一八四四年,《三個火槍手》的巨大成功,已為他奠定了歷史小說家的聲譽;一八四五年秋開始在《辯論報》上連載的《基督山伯爵》又轟動了整個巴黎。稿費源源而來,他這時真可以說得上是富埒王侯了。一八四八年,他竟然耗資幾十萬法郎建起一座富麗堂皇的府邸,并把它命名為“基督山城堡”。
大仲馬巨大的工作熱情和毅力,超乎常人的充沛精力,也許同他祖?zhèn)鞯膬?yōu)異體質(zhì)不無關(guān)系。他熱愛寫作,而且寫作起來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是文思如涌,一瀉千里。大仲馬成名后,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經(jīng)常有一些合作者,他們有的為大仲馬查找文獻資料,有的向大仲馬提供故事的雛形,有的甚至與大仲馬共同執(zhí)筆,參與初稿的寫作,但是無論在哪種情形下,主骨和靈魂總是大仲馬。在這一點上,一直有人對大仲馬頗多微詞,譏諷他是“寫作工廠”的老板。但大仲馬是很坦然的,他理直氣壯地回答說:“莎士比亞也是借用了別人作品的主題進行創(chuàng)作的,難道他就不是偉大的作家了嗎?瞧我的這只手吧,這就是我的工廠。”
大仲馬生性落拓不羈,愛開玩笑,他的一生也像他的作品一樣充滿著傳奇色彩。譬如說,有一回他在俄國旅行時,有個年輕人要求做他的仆役。大仲馬不僅一口應(yīng)允,而且還寫了一份由他簽署的“護照”給他,并附了張紙條,申明這個年輕人沿途的一應(yīng)花銷都可將賬單徑寄巴黎,由他付賬。結(jié)果,這個年輕人果然一路通行無阻地到了巴黎。
還有一次,大仲馬到西班牙去旅行,一個海關(guān)職員要檢查他的行李。這時,旁邊不知是誰說了句:“你要檢查大仲馬先生的行李?”那個職員一聽,忙不迭地趕快放行,一邊嘴里還喃喃地說:“原來是三劍客先生!”得知大仲馬來訪,西班牙全國上下一片歡騰,人們像迎接凱旋歸來的英雄般地歡迎他。面對這動人的情景,就連一直對父親耿耿于懷的小仲馬也覺得這次隨父親去西班牙是“不虛此行”。
大仲馬雖然天生有強健的體魄,但由于長年超負荷工作,再加上生活放蕩,他的精力消耗太大,所以到一八六七年,他就經(jīng)常頭暈目眩,無力再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一八七〇年十二月,大仲馬臥床不起,五日晚上,他死在女兒的懷里,時年六十八歲。維克多·雨果得知噩耗后,說了下面這段話:“他就像夏天的雷陣雨那樣爽快,是個討人喜歡的人。他是濃云,是雷鳴,是閃電,但他從未傷害過任何人。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像大旱中的甘霖那般溫和,為人寬厚。”
大仲馬作為十九世紀最多產(chǎn)而且最受讀者歡迎的作家之一,在法國文學史上的功績是不可抹殺的。他的文學作品到底有多少呢?很難說出一個確切可靠的數(shù)字。眾多研究大仲馬的專家的統(tǒng)計結(jié)果很不一致。最保守的統(tǒng)計,是戲劇九十部,小說一百五十部(計三百本)。最著名的戲劇除《亨利三世及其宮廷》(1829)以外,還有《安東尼》(1831)和《拿破侖·波拿巴》(1831)。最著名的小說除《基督山伯爵》外還有:描寫路易十三到路易十四時期的達達尼昂三部曲,即《三個火槍手》(1844)、《二十年后》(1845)和《布拉熱洛納子爵》(1848—1850);描寫“三亨利之戰(zhàn)”的三部曲,即《瑪戈王后》(1845)、《蒙梭羅夫人》(1846)和《四十五衛(wèi)士》(1848);以及描寫法國君主政體瓦解的一系列小說,如《約瑟·巴爾薩莫》(1846—1848)、《王后的項鏈》(1849—1850)、《紅房子騎士》(1846)、《昂熱·皮都》(1853)和《夏爾尼伯爵夫人》(1853)。而其中影響最大、最受讀者歡迎的,當然首推《基督山伯爵》和《三個火槍手》。
二
從一八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起,巴黎的《辯論報》上開始連載《基督山伯爵》。小說馬上就引起了轟動,如癡如狂的讀者從四面八方寫信到報館,打聽主人公以后的遭遇;被好奇心撩撥得按捺不住的讀者,甚至趕到印刷廠去“買通”印刷工人,為的是能對次日見報的故事先睹為快。一部當代題材的小說能產(chǎn)生這樣的“轟動效應(yīng)”,而且其生命力竟能如此頑強,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仍受到全世界億萬讀者的喜愛,這種情況在文學史上也是不多見的。
話得從一八四二年說起。歐仁·蘇的社會風俗小說《巴黎的秘密》在報紙上連載后一炮打響,于是出版商約請大仲馬也以巴黎為背景寫一部當代題材的小說。大仲馬接受約請后的第一步工作,就是搜集素材。他在巴黎警署退休的檔案保管員珀歇寫的回憶錄里,發(fā)現(xiàn)了一份案情記錄,它記述了拿破侖專政時代一個年輕鞋匠皮科的報仇故事,說的是巴黎一家咖啡館的老板盧比昂和他的三個鄰居,出于嫉妒跟剛訂了婚的鞋匠皮科開了個惡意的玩笑,誣告他是英國間諜。不料皮科當即被捕入獄,從此音訊杳然。七年后他出了獄;由于同獄的一位意大利神職人員在臨終前把遺產(chǎn)留給了他,他出獄后就變得很富有了。但他得知當年的未婚妻早已嫁給了盧比昂,于是就喬裝化名進入盧比昂的咖啡館幫工,先后殺死那三個鄰居中的兩人,并用了十年的時間,處心積慮地把盧比昂弄得家破人亡。但最后他在手刃盧比昂時,當場被那第三個鄰居結(jié)果了性命。
大仲馬敏銳地覺察到,“在這只其貌不揚的牡蠣里,有一顆有待打磨的珍珠”。他根據(jù)這個素材,構(gòu)思了一個復仇故事的輪廓。然后,他又聽取了在創(chuàng)作上和他多年合作的助手馬凱的一些很有見地的建議,決定花大量的篇幅去寫“主人公同那位美貌姑娘的愛情,那些小人對他的出賣,以及他同那位意大利神職人員一起度過的七年獄中生活”這些引人入勝的情節(jié)。鞋匠皮科在小說中成了水手唐泰斯,故事的背景也改在了風光綺麗的馬賽港。大仲馬不愿意讓小說中的冤獄發(fā)生在拿破侖的第一帝國時代,于是把故事的時間往后挪到了王朝復辟時代,讓唐泰斯成了波旁王朝的冤獄的受害者。皮科的那幾個仇人,則從市井平民變成了七月王朝政界、金融界和司法界的顯要人物。
為了寫作這部小說,大仲馬去了馬賽,重游了加泰羅尼亞漁村和伊夫堡。大仲馬的腦海里,醞釀著一幕幕場景:少年得志的唐泰斯遠航歸來,與美麗的加泰羅尼亞姑娘梅爾塞苔絲舉行訂婚儀式;船上的會計唐格拉爾和姑娘的堂兄費爾南(即后來的德·莫爾塞夫伯爵)串通一氣,寫信向警方告密,誣陷唐泰斯是拿破侖黨人;當時也在場的裁縫卡德魯斯曾想阻止他們這樣做,但終因喝得酩酊大醉而不省人事;在喜慶的訂婚宴席上,憲兵突然闖進來帶走了唐泰斯;代理檢察官維爾福為了嚴守父親的秘密,維護自身的利益,昧著良心給無辜的唐泰斯定了罪,把他關(guān)進伊夫堡陰森的地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