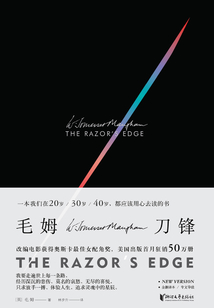
刀鋒
最新章節
書友吧 47評論第1章 導讀:上刀山做自己
鄧鴻樹[1]
《刀鋒》出版于一九四四年,是毛姆晚期最知名的小說。他自一九一五年發表代表作《人性的枷鎖》,當時已活躍于英美文壇三十余年,以許多具有異國風采的短篇故事與膾炙人口的劇作聞名于英語世界。
毛姆寫《刀鋒》時年近七十歲,算功成名就,可依照自己的意思盡情創作。小說初稿完成后,他于信中寫道:“寫這本書帶給我極大的樂趣。我才不管其他人覺得這本書是好是壞。我終于可以一吐為快,對我而言,這才是最重要的。”
作家寫得盡興,讀者反應也超乎預期地熱烈。《刀鋒》描寫“英國人眼中的美國人”,美國讀者特別捧場,出版首月在美國就狂銷五十萬冊,令毛姆很有成就感。他在信中對侄女說:“這把年紀還能寫出一部如此成功的小說,我感到十分滿足。”福斯公司很快就以高價買下電影版權,兩年后推出改編電影,入圍“奧斯卡最佳影片”等多項提名,并勇奪“最佳女配角獎”,更加打響原著小說的知名度。
“活著到底是為了什么,人生究竟有沒有意義,還是只能可悲地任憑命運擺布?”主角拉里在未婚妻面前說出內心的疑惑。這位青年為何忽然解除婚約,放下一切,到海外過著不務正業的放逐生活?這就是《刀鋒》的故事。
本書具備毛姆作品的代表元素:強烈的自傳性、劇中劇的多重敘事手法、游走的地理背景、露骨的情欲、禁忌的題材,以及對社會邊緣人的紀實描寫等,文筆淺顯,展現典型的毛姆風格。
與毛姆其他作品相較,《刀鋒》的地位尤其特殊,因為,這是他唯一一本以自己真名作為敘事者的小說,說故事的作家就叫“毛姆”:“本書集結了我對一位男性友人的回憶。”書中人物雖都“另取其名”,情節為避免枯燥有所增添,可是,內容卻“毫無虛構”,都是源自毛姆與友人的親身經歷。本書既像傳記,也像回憶錄,情節更如小說般精彩。因此,毛姆開宗明義指出:“我之所以稱其為小說,純粹因不曉得還能怎么歸類。”
生命的大哉問
本書題詞揭示,“刀鋒”一詞出自印度教圣典《迦托·奧義書》:悟道之途艱辛困難,如同跨越鋒利的剃刀。若救贖之路必經刀山,找到答案的代價為何?這就是故事主角拉里心中的疑惑。若真有人在刀山上找到答案,那該如何看待山下的俗世呢?這就是毛姆撰寫本書的因由。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拉里服役于空軍,有次出任務遭遇空戰,軍中最要好的同袍犧牲生命救他,改變了他的人生觀。他的未婚妻是芝加哥豪門千金,對婚姻與事業早有安排。無奈,拉里退伍后,完全變了一個人,不上大學,不結婚,也不愿就業,執意獨自到巴黎游覽。
拉里出身卑微,雙親早逝,從小被一位醫生收養,得以躋身上流社會。不過,他不愿追求崇尚名利的美國夢,戰時經歷讓他省思生命的意義:“我想確定究竟有沒有上帝,想弄清楚為什么有邪惡存在,也想知道我的靈魂是不是不死。”
此大哉問與他的飛行經歷有關:他在浩瀚無垠的天空中高飛,想要“遠遠超越世俗的權力和榮譽”。可是,戰友之死讓他驚覺生命之無奈與不可超越:“上帝為什么要創造邪惡呢?”他于是拋下親友,到歐洲游歷,一路自我充實,最后卻對西方宗教哲理感到徹底失望。后來,他遠赴印度,在一位象神大師的靜修院受到啟發,頓悟了生命的真義。
亂世的眾生相
毛姆并未寫出一本說教氣息濃厚的傳道書,而是秉持小說家的敏銳觀點,冷眼旁觀生命的沉重,并以游記的輕松口吻與言情小說的情節,層層包覆令人不勝唏噓的人生真貌,這是《刀鋒》最成功的地方。
故事主軸建立在拉里與未婚妻伊莎貝爾的觀念沖突之上。伊莎貝爾認為追求知識“聽起來不太實用”,投入職場才是男人應盡的責任。她對滯留巴黎的拉里說:“你是美國人,并不屬于這里……歐洲玩完了,我們是全世界最偉大、最強大的民族。”拉里為“解答明知解決不了的問題”,拒絕成家立業,實在不成體統——“男人就該工作,這才是人生的目的,也才是造福社會的方法”。
若伊莎貝爾代表實用主義,她家財萬貫的舅舅艾略特則象征著物質主義。這位美國大亨常年在歐洲揮霍,捐錢助人只為掩飾對生命的無知;在歐洲置產過著浮華生活,也僅為麻痹對死亡的恐懼。毛姆眼中的歐洲,充斥著許多沉淪與腐化的人物,故事的最后,在法國蔚藍海岸發生的那場駭人命案,更加深化了美麗世界的丑陋。
《刀鋒》背景設于一九一九年至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兩次世界大戰期間,這是現代史最動蕩的年代。書中所刻畫的眾生相,顯然都是亂世的產物。這段歷史期間,歐洲許多國家都有戰事發生,斯大林、希特勒等強權崛起,大英帝國衰退,西方社會問題嚴重。書中人物游走于巴黎、倫敦與其他歐洲大城,雖不見戰火余燼,實已悄然卷入另一撥歷史巨變。
相較于歐洲不安的局勢,兩次大戰期間,美國逐漸壯大,成為繁榮國家。不過,一九二九年華爾街股市崩盤,造成長達十年的經濟大蕭條,引發嚴重的政經與社會問題。當歐洲動亂之際,追求功利的美國夢也逐漸顯露丑惡的一面。一九四九年阿瑟·米勒發表《推銷員之死》,推銷員的長子堅持做自己、不做美國夢,實與同時期的《刀鋒》有異曲同工之妙。
沉默的結局
現實生活里,毛姆與拉里一樣,心底都有沉重的秘密。毛姆雖結婚生子,卻多年隱藏同性戀的身份。同性戀在當時的英國是可受公訴的罪行。一八九五年,毛姆二十一歲時,劇作家王爾德因同性戀受審,遭受極大屈辱。此事對毛姆有深遠影響,日后他善于處理不倫、丑聞、肉欲等違背道德的禁忌題材,其創作動機應出自內心深層的吶喊。
毛姆為逃避英國社會與文化的壓抑,長年旅居國外,甚至定居于法國蔚藍海岸的小鎮。他對東方文化很感興趣,可能是因為東方對身體與欲望的看法,有別于講求原罪的西方。
一九三八年,毛姆為親身了解印度教的內涵,特地遠赴印度搜集資料,并前往金奈附近一處靜修院,拜見圣哲拉馬納·馬哈希。等待期間,毛姆突感身體不適,當場昏倒。馬哈希得知這個消息,前去探望,不發一語與毛姆對望半小時。圣哲最后說:“沉默也是一種對話。”毛姆深獲啟發。
拉里“漫長的旅程,起始于對邪惡的叩問”。他在亂世中尋求生命的意義,在遙遠的東方接受靜思的洗禮:“象神大師常說沉默也是種對話。”他懵懂求知期間,經歷男女荒唐事;悟道后,計劃返回美國,“回去過活”,可是,竟“從此無消無息”。拉里是否與作家一樣,內心深處都有掙脫不了的束縛、俗世眼中不可告人的“邪惡”?
有些疑問“可能原本就沒有答案”,這應是毛姆最后無法論斷拉里功過的緣故:“拉里的故事到此為止,固然不盡完美,我也莫可奈何。”對讀者而言,也是如此。《刀鋒》結局沉默的余音中,人性的枷鎖再現,無從解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