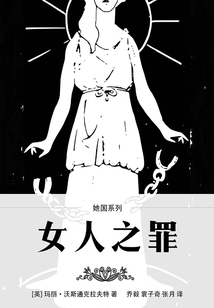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 1評論第1章 譯者序
《女人之罪》寫于十八世紀末,是早期的女權主義哲學家和小說家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一部未竟作品。雖然我對于這個時代的英國的文獻有一些涉獵,但這是我首次嘗試翻譯這么早的文學作品。具體來說,小說原文的句子結構十分復雜,給翻譯帶來了不小的麻煩。原文考究的語言也反應了沃斯通克拉夫特本人在當時的英國有著很高的社會地位。她的丈夫,同時也是《女人之罪》遺稿的編者威廉·戈德溫,是當時有名的政治評論家和小說家。他們的女兒瑪麗·雪萊是著名小說《科學怪人》(又名《弗蘭肯斯坦》)的作者,而女婿則是鼎鼎大名的詩人帕西·雪萊。由此讀者可以大致感受到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社會地位,而《女人之罪》就是出自這樣一位社會上層的文化名流之手。
十八世紀末的英國,工業革命正處于上升的過程中。但是這時社會的精英們已經感覺到了工業化對于社會的負面影響。就像詩人華茲華斯在1802年出版的《抒情歌謠集》的前言中說:“一系列前所未見的原因匯到一起形成一股力量,把人們敏銳的心智變得遲鈍,把所有自發的精神貶為一種原始的麻木。”我們能在本篇小說中看到,文化的高貴傳統沒落了,依靠商業貿易富裕起來的資產階級新貴品味低俗,只會縱欲享樂。在這種社會風氣下,親情的紐帶、同情的力量都沒落了,一切人際關系都變成了赤裸裸的金錢關系。同時,沃斯通克拉夫特為我們呈現了這部近代英國的文化悲劇的另一個面貌:在男性權力的統治之下,女性只有依附于男性,才可能有一個平和的生活,并且還要總是看著男人的臉色行事,而幸福與獨立更是一些不現實的奢望。可以說,沃斯通克拉夫特作為一個社會上流的女性,她有更多的力量以一己之身,努力克服這個時代。而她的作品正是她的武器。
如果想理解沃斯通克拉夫特筆下的人物瑪利亞,理解瑪利亞在身陷囹圄的時候的心靈斗爭,我們首先需要重新反省一下我們所知道的歷史。文藝復興的繪畫、宏偉的教堂,啟蒙運動留下的先賢祠,轟轟烈烈的資產階級革命。再想想我們所知道的中國近代史,五四運動民主、科學的吶喊,北伐戰爭打倒列強、除軍閥的號角,以及后來曠日持久的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以上所說的一切,都是男人的歷史,好像只有男人在推動歷史的前進,而絕大多數的女性只是默不作聲地跟在后面。在《女人之罪》的視角中,女性似乎天生就被認為是有罪的,需要在“人性”的法庭中為自己的清白辯護。在小說中描述的男權之下,女性的性別好像被簡化成了一種財產,當一個女孩成長為一個女人,她就具有了成為一個男性財產的資格,可以娶得,甚至可以強奪。而從沃斯通克拉夫特這里開始的事業,也可以說是一個至今未竟的事業,就是書寫一部女性的抗爭史,一部女性想要張揚自己溫柔而獨特心靈,以求得自身的獨立的歷史。母性,想象力,敏感,同情心,這些都是沃斯通克拉夫特在瑪利亞身上所描繪的女性心靈。
世界的母性不能破碎。人類對于幸福的終極記憶,就是每個人在自己母親的子宮里度過的生命最初的時光。人世間所有溫暖、幸福的事物,無不帶有關于母性的比喻。比如像母親腹中一般溫暖的房間,滋養一個民族的土地與河流,還有保護我們的愛人的懷抱。母親的希望中從來沒有流血犧牲,沒有冠冕堂皇的權力與榮耀,只有在平安之中自由的伸展。世界的母性雖然不時地被貶低、被忽視,但是母性正如我們腳下的大地,永遠無私地承載著我們的腳步。把母親和新生兒粗暴地分開,把一個嬰兒從一個母親的懷抱強行搶走,則是世界上最殘酷的行為。這也是為什么世界上最慘的故事,就是一個孤兒失去母親的流離,或者一個民族失去故土的流離。
所以,在潛意識的認識里男性的歷史是波瀾壯闊的,一場接著一場的道德勝利,建立起看似理性而正義的秩序,若我們認為只有這種歷史才是有價值的,那么我們就無法看到想象力和同情心的可貴。想象力和同情心的力量超越了一個人的血肉皮囊,那我們能夠想象和感受他人的感受,以情感的紐帶把一個家庭,乃至一個民族聚集起來。在閱讀中讀者將看到,小說中也有幾位擁有正面形象的男性,他們的共同點是都曾經遠離過自己的國土和家園,背負著孤獨與苦難,去國懷鄉。等到他們回到家園的時候卻發現,時過境遷,雖然祖國還是那個祖國,但在一個面目全非的冷酷社會中,他們流離失所的心靈已經無處棲息。我想,正是瑪利亞身上的女性光輝和這些溫情猶存的男人們對于歸宿的渴望,才使得小說可以在閃爍的希望之中進行下去。
至此,我希望在不透露太多小說情節的前提下提前與讀者分享我自己的翻譯感受。思想不失片面,讀者在自己閱讀之后會有自己的所思所感,望不吝賜教。
袁子奇
2013年10月15日
于美國俄亥俄州哥倫布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