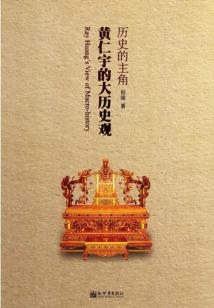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 2評論第1章 前言(1)
黃仁宇先生可謂是近世紀以來史學界的一大異數,他的“大歷史觀”“將宏觀及放寬視野這一觀念導引到中國歷史研究里去”,從而高瞻遠矚地考察中國歷史,在史學界影響深遠。
黃仁宇先生提出的“大歷史觀”,可以歸納為兩種切入歷史的取徑:一種系以宏觀歷史之角度,從歷史的縱橫總體聯系上把握微觀的歷史研究對象,即“把握”是宏觀的,研究仍是微觀的。另一種強調從較長的時段來觀察歷史,注重歷史的結構性變動和長期發展趨勢。黃仁宇的研究顯系后者。
在黃仁宇“大歷史”的范疇內,分析因果關系及其歷史的合理性是主要的,對其他細端末節,不過分重視,甚至每個歷史人物的賢愚得失,都認做次要。對此,他解釋說:“縱使事實之衍化對我們個人不能如意,或者在短時看來為荒謬不合理,可是把這些事情前后連貫,又從超過人身經驗的角度看去,則它們有其意義;最低限度,這些事跡使我們知道我們生命旅途之原委。”尤其對于學習歷史的人來說,重要的并不是歷史應當或不應當如何展開,因為它一經展開就具有客觀性和不可逆轉性,無須人們從主觀上加以想象或構造,人們應當思考的問題是歷史何以如是展開。以“天地不為堯舜而存,也不因桀紂而亡”的客觀態度,放寬歷史的視界,探尋事件的前因后果,正是黃仁宇“大歷史觀”所提倡的學習方法。
那么人們也許會有這樣的疑問:是不是凡有一件重要事件的發生必有后面的背景,只要它能與以前或以后的人與事相互印證,就取得它在長期歷史上的合理性?存在就一定合理嗎?這是否又陷入了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套路?對此,黃仁宇的解答是:“大歷史著重大眾的集體智慧、勇敢和道德,目的是勾畫一個歷史的大綱,著重東西的匯合。”其實“大歷史觀”強調用較長時段來觀察歷史,注重事物之間的因果關系,只是為我們提供了研究歷史的一種方法、一個新的視角,重要的還在于我們如何將其作為一種工具加以掌握和運用。就像在歷史研究中的地理環境決定論和人口決定論一樣,它們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絕不能究其一點而不及其他。
“大歷史觀”筆下的通史也與一般意義上的中國通史不同。在注重歷史發展邏輯之余,各朝代已不再是可以拿來互相比較的單位,而是前后一貫,具有因果關系。
黃仁宇先生以“大歷史觀”為其思想核心的作品,在不失史家謹嚴之基本原則下,走出殿堂,讓大眾愿意去接受,使得了解歷史不再被視為畏途,不再是幾個歷史學家書齋中的“玩物”。以現代史學大家錢穆先生“不知一國之史則不配作一國之國民”的標準來看,黃仁宇先生對于中國“國民歷史性格”的發展是功不可沒的,他是一個真正的“平民學者”。
震撼史學界的《萬歷十五年》是黃仁宇先生的代表作,該書最初是用英文寫成,但最早出版的卻是中文版。1980年其中文版由中華書局在北京出版,其老友廖沫沙特地題箋,印在封面。這部書的英文版是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當時美國名作家厄卜代克特地在《紐約客》雜志撰寫推薦文章。《萬歷十五年》一書先后兩次獲得美國國家書卷獎歷史類好書提名。后來,中國臺灣出版人陶希圣先生很欣賞這本書,就由其主持的食貨出版社出版了臺灣版,并親自為這本書作書評附于書后。從此,黃仁宇在兩岸三地成為知名度頗高的歷史學者,文章時有見報,并集結成多本專著,其作品被各方追捧,真可謂是史學界之異數。探究其原因,這恐怕與黃仁宇先生的文風有很大的關系,他的作品,首先建立一個大的歷史架構,然后以個人的人生經歷(作為國民黨下級軍官在抗戰中對中國社會政治結構的問題的體會,以及在美國生活多年對東西方文明的比較、認知與反思)對照歷史記載,從而發展出一套對中西方歷史文化的獨特解讀。寫作格式不拘成例,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將歷史呈現于讀者眼前,因而吸引了廣大讀者。
盡管黃先生的書受到了讀者的追捧,一時洛陽紙貴,然而在學術界黃先生卻是毀譽參半、褒貶互見,沒能獲得一致的肯定。正統的歷史學者或漢學家常質疑先生半路出家,學術著作不夠嚴謹;將數百年、上千年的大歷史架構合于一瞬,總讓他們覺得過于冒險,把歷史解釋得過于簡單化了。在先生的回憶錄《黃河青山》中,也屢屢提及他撰寫的書在美國是如何如何的難以出版,以及他與費正清、亞瑟?萊特等知名漢學家在對中國史解讀和撰寫方式方面意見是如何如何的相左。實際上,先生半路出家不假,但他對中國歷史,尤其是明代史,確實是下過苦功的。他曾用兩年半的時間,把卷帙浩繁的《明實錄》閱讀完,并做了詳細的筆記,由此可知其用功之勤、功底之扎實。
中國臺灣影響頗大的《中國時報》曾組織了一場《與大歷史對話——黃仁宇研討會》,并分別安排了專題演講與綜合座談會,“業內人士”與“業外人士”各抒己見,互相爭鳴,成為史學研討會的一大奇觀。有學者說,隨著《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的第一章決定歷史走向的重要因素個人能力有限,生命的真意義,要在歷史上獲得,而歷史的規律性,有時在短時間尚不能看清,而需要在長時間內打開眼界,才看得出來。
——黃仁宇《萬歷十五年》
讀黃仁宇先生的作品,聽黃仁宇先生講中國歷史,在腦海中必須有一個清楚的概念,那就是黃仁宇先生的歷史觀是什么。可能在很多人看來,一般哲學意義上的世界觀、歷史觀,都很虛無縹緲,沒有辦法講得清、道得明。其實,這種想法是不對的。大凡真正的歷史學家,必然會有自己對整個歷史的看法,有自己對社會和人生的態度,而這種態度和看法,又會不可避免地浸潤到他的歷史著作中去。黃仁宇先生也是如此,只有真正了解黃仁宇先生的歷史觀,我們才能真正了解他的史學思想。
黃仁宇先生是一個經歷豐富而又坎坷的歷史學家。他出身戎馬,早年四處奔波的軍旅生活,使其能夠深入了解中國的底層情況,對于中國社會有了更理性的認識;其后赴美求學,除了獲得不少書本上的知識外,還實際體驗了西方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這些都極大地拓展了他的視野。黃仁宇先生也自稱,他的歷史觀是與眾不同的。正是由于有了開闊的視野,其文章才能經常察人所未察,言人所未言,慧眼獨具,發人深思。那么,黃仁宇先生的歷史觀是什么呢?這就是他所反復指出的“大歷史觀”。即必須在長時間的范圍內,綜合考察決定歷史走向的各種因素,通過分析和比較,來探究歷史的真實面目,發現其中的規律,從而獲得真正的知識。
黃仁宇先生所關心的,是那些決定中國歷史進程的因素。他欲通過歷史研究而探求的,是中國在過去的幾千年中,所發生的那些歷史事件背后的原因,以及將會決定中華民族未來走向的因素。
在黃仁宇先生看來,雖然決定中國歷史進程的因素有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無疑是下面將要論述的幾個方面。
地理條件促使中國走向統一
中國在公元之前,而且自嬴秦之后,以統一為正軌,實有天候和地理的力量支撐著。
——黃仁宇《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
地理條件對人類的影響,自古以來就是歷代思想家、哲學家所關注和思考的核心問題,因為關注和思考這種影響,實質上就是在關注和思考人類自身文明的起源問題,而這正是歷史研究的永恒命題之一。
眾所周知,人類的文明古代形態可以分為很多種類型,比如中華文明、古希臘文明、羅馬文明、非洲文明、俄羅斯文明、兩河流域文明、瑪雅文明等等。以研究文明形態而享譽全球的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先生,甚至將人類歷史上存在過的、有影響的文明劃分為26種。面對眾多的文明形態,人們不禁要問:為什么各種文明之間會存在如此大的差異?原因當然會有很多,但最重要的是什么?有不少人將其歸結到地理條件上。比如,有的學者分析,由于希臘半島多丘陵、少平原,故而形成了彼此互不統屬的各個部落,難以存在強大的中央集權;同時,由于內部資源嚴重不足,加之靠海,又順其自然地迫使它走上了海外殖民的道路。還有,法國的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曾在他的名著《論法的精神》中說,非洲人之所以個性獨特,乃是由于非洲地處熱帶,不僅當地土著居民的皮膚被曬黑,高溫也改變了他們的血液成分,使得他們疏懶而不愿意工作!這可就帶上了種族偏見的有色眼鏡了。
關于中國文明的起源問題,曾經轟動一時的是前蘇聯學者列·謝·瓦西里耶夫的《中國文明的起源問題》,他認為中國文明是來自西域,即“文化外來說”。針對這種會影響民族自尊心的觀點,中國學者紛紛撰文反駁,認為中國文明完全是本土產生的。后來,隨著發掘資料的大量出土,中國學者的觀點得到了證實。
至于中國為什么會走上強大的中央集權道路,這方面的研究更多。其中影響最大,也能自圓其說的,當屬魏復古(Karl A.Wittfogel)博士的觀點。在研究中國史的領域中,魏復古是個非常值得重視的人物。黃仁宇先生提到,當自己在密歇根大學當研究生時,主修中國研究的人都常常提到他。魏復古的代表作《東方專制主義》(Oriental Despotism),主要是分析埃及、美索不達米亞、波斯、印度和中國的古文明到底出了什么問題。在書中,魏復古說,這些“東方文明”都隸屬于他所設計的“水力社會”范疇,也就是說,農業生產必須依賴大規模的灌溉工程,而為了順利完成大規模任務,對大批的勞動力就必須施以嚴格的命令,因此專制主義在這些地方就會無法避免。也就是說,在魏復古的字典中,“水力社會”和東方社會是同義詞。
黃仁宇先生指出,魏復古創造出的這套東西,無非是為了避免馬克思的“亞細亞生產方式”。但魏復古為了自己理論的需要,將“東方”包括了印加帝國(今日秘魯共和國地區),卻把日本排除在外。在魏復古看來,由于日本的灌溉工程是片斷零碎而非協調一致,所以日本社會是“水利農業”,而非完全的“水力”,由于缺乏集權的需要,因此即使是封建時代的日本都“無法發展戰爭的藝術”。
關于東方專制主義是否已經成為歷史,魏復古說“不”。他認為這些東西即使是在當今社會,也相當活躍。他還認為,蘇聯是俄國“在亞細亞的復活”,以工業基礎充實其新專制主義;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更是“貨真價實”的亞細亞復活。
大而化之的概括盡管很有吸引力,但好比街頭的算命先生,可以用含糊不清的“玄語”唬住有心求得神靈保佑的信客,信之則靈,看你怎么理解。魏復古的理論看似深刻,但由于他的“理論”實在太缺乏歷史事實的支持,因而很難有太大的說服力。事實上,早在20世紀90年代,中國史學界就曾在《史學理論研究》等雜志上,對魏復古的理論進行過集中批判。黃仁宇先生也在《黃河青山》一書中提到,由于魏復古的“東方專制”理論過于花里胡哨,引起本來是好朋友的李約瑟先生的批評,認為魏復古“否定事實”。總體來說,黃仁宇先生對此問題的思考,是在對魏復古理論批判的基礎上展開的。
那么,黃仁宇先生眼中的地理條件對中國社會的影響,究竟如何呢?他說,“到目前為止,中國歷史還帶著早期統一的永久痕跡,而影響統一的主要因素則是大自然的力量。”黃仁宇認為,歷代王朝所面臨的最重要問題,都是回應地理條件的挑戰。
在這些地理挑戰中,最重要的當然是整治黃河。中國文化發源于黃河流域。治水在中國文明發展中的重要地位,已經成為兩千年來政府官員和眾多學者不斷強調的主題。黃河流經黃土地帶,而黃土覆蓋著華北幾省的廣大地區,土質疏松,風沙所沉淀的黃土厚度介于30-100米之間,黃河河水因此夾帶大量的淤泥,常常會塞滿河道,溢出堤防,造成難以計算的生命和財產損失。
只有一個能控制所有資源、公平分配國內資源的中央集權政府,才能解除人們面臨的威脅,提供所需的安全保障。所以黃仁宇先生才會說,人民需要一個能全盤處理水患問題的當局,因而造就中國這個國家的誕生,可見光是治水一事,中國之中央集權,已無法避免。
早在公元前651年,黃河流經的各個諸侯國就召開會議,類似于現在的阿拉伯聯盟會議,除了討論其他事宜,最重要的一條就是保證不興修妨礙其他國家的水利工程(如截斷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