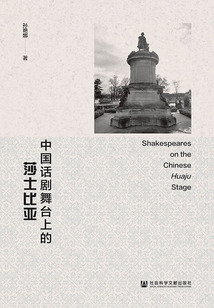
中國(guó)話劇舞臺(tái)上的莎士比亞
最新章節(jié)
- 第25章 參考文獻(xiàn)
- 第24章 結(jié)語(yǔ)
- 第23章 田沁鑫的莎士比亞話劇演出
- 第22章 林兆華與莎士比亞戲劇演出
- 第21章 《莎士比亞與多元化話劇(1990至現(xiàn)今):文化改編》:1994年上海國(guó)際莎士比亞戲劇節(jié)
- 第20章 徐企平與莎士比亞戲劇演出
第1章 值得一讀的莎士比亞中文話劇改編和演出史
程朝翔
這是一本好書,值得一讀。
第一,作者對(duì)歷史有宏觀的把握,能夠根據(jù)歷史分期,說(shuō)明莎士比亞的中文話劇改編和演出在不同時(shí)期的不同特點(diǎn)。作者按照文明戲、初期話劇、戰(zhàn)時(shí)話劇、“十七年”話劇、新時(shí)期話劇、多元化話劇六個(gè)時(shí)期,將改編和演出歸納為文化轉(zhuǎn)譯、文化模仿、文化武器、文化寫實(shí)、文化探索、文化改編六個(gè)不同的特點(diǎn)或者側(cè)重點(diǎn)。這種歷史觀將作者的莎士比亞研究融入中國(guó)的語(yǔ)境,而不是作為舶來(lái)品游離于中國(guó)社會(huì)和文化之外。
第二,作者有鮮明的觀點(diǎn),而很多觀點(diǎn)能點(diǎn)出莎士比亞所代表的跨文化交流的關(guān)鍵。例如,對(duì)于“中學(xué)為體,西學(xué)為用”的批評(píng),雖然是一帶而過(guò),但反映了作者的深層思考,即在“中學(xué)為體,西學(xué)為用”的框架下無(wú)法建立文化關(guān)聯(lián),而沒有文化關(guān)聯(lián)則使外來(lái)文化很難扎根。而“洋為中用”的莎士比亞戲劇改編則建立起了文化關(guān)聯(lián),因此可以持久。作者認(rèn)為“洋為中用”的民族化改造拉近了莎劇與中國(guó)一般觀眾的距離,使莎劇在中國(guó)更能為一般大眾所接受,“偶有傷及原著”也是末不是本。這種觀點(diǎn)頗有見地,涉及文化接受的一個(gè)關(guān)鍵性問題。
在具體個(gè)案的分析中,作者有褒有貶,觀點(diǎn)鮮明。對(duì)于作者認(rèn)為不成功或者有問題的改編,提出了比較尖銳的批評(píng)。對(duì)于他人的研究成果,也有自己的看法。例如,個(gè)別國(guó)外專著,對(duì)中國(guó)的實(shí)際情況了解有限,但進(jìn)行了相當(dāng)主觀的評(píng)價(jià),反映了文化偏見。作者對(duì)此的批評(píng)既尖銳又恰如其分,顯示出良好的學(xué)術(shù)判斷力和鮮明的立場(chǎng)與態(tài)度。
第三,可能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有豐富的一手材料。在每一個(gè)時(shí)期,作者都聚焦重要人物(改編者和導(dǎo)演)和重要作品,進(jìn)行了細(xì)致全面的介紹和分析,使全書有血有肉、扎實(shí)有料。對(duì)于作品和人物(改編者和導(dǎo)演)的分析是全書最精彩的部分。
對(duì)于一本好書來(lái)說(shuō),一手材料最重要。只要有了扎實(shí)的一手材料,即使讀者不同意作者的結(jié)論,也可以受到啟發(fā),產(chǎn)生出一些自己的想法。而沒有材料的著作,即使觀點(diǎn)再多,可能也是空的。
我認(rèn)真拜讀了全書,產(chǎn)生了一些想法,如果不是受到這本書的豐富材料的啟發(fā),是不會(huì)有這些想法的。而這些想法也是忍不住要參加書里精彩的討論。謹(jǐn)此分享。
書中詳細(xì)介紹了徐曉鐘1980年版的《馬克白斯》,提到劇中用紅臺(tái)布來(lái)渲染弒君的血腥和兇手的罪惡。在中國(guó)臺(tái)灣,京劇家吳興國(guó)1986年將《麥克白》改編為京劇《欲望城國(guó)》時(shí),也曾用紅綢布來(lái)象征弒君后的血流成河。徐曉鐘等中國(guó)大陸作家似乎更早使用了京劇的類似寫意手法。
徐曉鐘的《馬克白斯》是一部杰作,但在文化市場(chǎng)上的知名度遠(yuǎn)遠(yuǎn)不如吳興國(guó)的《欲望城國(guó)》。這也許與文化產(chǎn)業(yè)的運(yùn)作方式有關(guān)。在中國(guó)大陸,重要的劇院往往都是國(guó)家的事業(yè)單位,承擔(dān)著國(guó)家的文化任務(wù)。這種劇院的保留劇目本來(lái)就精益求精,外國(guó)劇作入選的概率是低而又低。吳興國(guó)創(chuàng)立的“當(dāng)代傳奇劇場(chǎng)”是市場(chǎng)化運(yùn)作的單位,自然能將受市場(chǎng)歡迎的劇目長(zhǎng)期、不斷地推出,滿世界巡演。而在中國(guó)大陸,與之相當(dāng)?shù)闹挥幸患遥蔷褪峭瑯邮袌?chǎng)化運(yùn)作的林兆華戲劇工作室——至少同樣有名的只有這一家,據(jù)說(shuō)也是舉步維艱。林兆華的藝術(shù)成就使他能夠建立自己的工作室,而自己的工作室又使他更有成就、更有聲譽(yù)。他能把自己的作品全部都制作成DVD,固化為文化檔案,并在文化市場(chǎng)廣泛傳播,這是個(gè)創(chuàng)舉,也是在中國(guó)導(dǎo)演中絕無(wú)僅有的。他的導(dǎo)演理念也以《導(dǎo)演小人書》的形式廣為傳播。
要想戲劇繁榮、文化繁榮,就應(yīng)該既辦好北京人民藝術(shù)劇院這種國(guó)家文化單位,又大力發(fā)展林兆華戲劇工作室這種文化產(chǎn)業(yè)單位,使徐曉鐘這種戲劇大家的重要作品能夠成為保留劇目,固化為檔案,并且產(chǎn)業(yè)化、市場(chǎng)化。或許國(guó)家可以投資國(guó)家文化單位,包括北京人藝、青藝、中戲等,建立半市場(chǎng)化的大師工作室,使大師和杰作不至于湮滅——戲劇是一門很容易湮滅的藝術(shù)。
本書多處涉及改編與原作關(guān)系的問題,這也是一個(gè)關(guān)鍵問題。在今天,“改編忠實(shí)于原作”實(shí)際上已經(jīng)成為一個(gè)偽問題,不值得多加討論。首先,莎士比亞的《李爾王》有對(duì)開本、四開本;《哈姆萊特》有對(duì)開本加好幾個(gè)四開本,據(jù)說(shuō)每一個(gè)不同的版本都是不同的劇作。如果需要“忠實(shí)于原作”,也得選擇忠實(shí)于哪一個(gè)原作。其次,無(wú)數(shù)學(xué)者、作家、導(dǎo)演、演員都在不斷“還原”莎士比亞,但似乎尚未還原出一個(gè)唯一的、最終的莎士比亞。但每一次還原都有可能是正當(dāng)?shù)摹⒑戏ǖ倪€原。因此,每一次還原都是有意義的,但誰(shuí)也不能說(shuō)自己的還原“忠實(shí)于”原作或原作家。每一次還原都是一次不同的解釋而已。再次,假設(shè)有一個(gè)唯一真正的莎士比亞,每一個(gè)改編者都忠實(shí)于這個(gè)唯一真正的莎士比亞,那么所有的改編也就都一樣了,莎士比亞因而也就只有一副面孔了。那么,如此乏味的莎士比亞離死亡也就不遠(yuǎn)了。當(dāng)然,所謂翻譯即背叛(traduttore traditore),改編其實(shí)也必然是背叛;狹義地忠實(shí)于原著也是不可能的。
話雖如此,改編畢竟是改編,好的改編要與原作有血肉關(guān)系,顛覆了原作的改編也與原作是打斷了骨頭連著筋的。書中詳細(xì)介紹了三個(gè)具有代表性的改編者李健吾、林兆華、田沁鑫。
李健吾的《王德明》(1945)由黃佐臨導(dǎo)演,將《麥克白》完全中國(guó)化:“故事發(fā)生在五代初期唐天祐十八年的常山王治下——鎮(zhèn)州、冀州、深州與趙州等地,講的是王德明(原名張文禮)謀害其義父常山王王镕并篡奪王位,最后又被人仇殺的故事。”劇中有諸多中國(guó)文化元素,包括扶乩的巫婆、孔孟之道、元曲《趙氏孤兒》中的“搜孤”與“救孤”橋段等。然而,在中國(guó)化背后,“卻依然有著莎士比亞的靈魂”。這個(gè)靈魂就是同樣的故事結(jié)構(gòu)所表達(dá)的同樣的思想,即“權(quán)力、陰謀、野心之間的糾纏”;改編者“利用原作的某一點(diǎn),或者是結(jié)構(gòu),或者是性格,或者是境界,或者是哲理,然后把自己的血肉填了進(jìn)去,成為一個(gè)有性格而向上的東西”。閱讀了本書,我們了解了李健吾所改編的莎士比亞既是真正的莎士比亞,又是李健吾原創(chuàng)的杰作。
林兆華改編、導(dǎo)演了四部莎士比亞劇作。對(duì)他來(lái)說(shuō),這些劇是林兆華的,而不是莎士比亞的:“我得把各種主義化作我林兆華心靈的東西,用林兆華的心靈去構(gòu)造這個(gè)戲。”不過(guò),他把莎士比亞嚼碎了,吐出來(lái)的卻還是莎士比亞的味道,雖然是林兆華消化過(guò)了的莎士比亞。
他的“人人都是哈姆雷特”好像是在說(shuō)“人人都是莎士比亞”,都在學(xué)莎士比亞,像莎士比亞一樣想和寫與做;他的理查三世也同樣是“對(duì)邪惡的研究”,只不過(guò)是另一種研究而已,將邪惡游戲化、日常化、平庸化——后者或許與阿倫德有關(guān)。
他的大將軍是軍事貴族、社會(huì)精英,高高在上,不可一世,而周圍是一幫由保安和民工扮演的充滿民粹想法的暴民——在震耳欲聾的搖滾樂的麻痹下,而搖滾樂又伴隨著戰(zhàn)場(chǎng)上嗜血的麻痹,雙方大概都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如伊格爾頓所言,“足球是人民的鴉片”;在此,搖滾樂大概也是人民的鴉片,而人民包括軍事貴族和草根民工。
我在國(guó)家大劇院觀看了田沁鑫的《明》(2008),感覺人物是從不遠(yuǎn)處的國(guó)博溜出來(lái)的古董,他們不知道莎士比亞是誰(shuí),但又在調(diào)侃莎士比亞。他們倒是像《資治通鑒》里的人物,調(diào)侃莎士比亞可能是為了本書作者所說(shuō)的“中學(xué)為體,西學(xué)為用”,但與莎士比亞沒有半點(diǎn)文化關(guān)聯(lián)。劇作整得美輪美奐,真是大明皇帝的奢華,不過(guò)也真真反映出那個(gè)朝代腦殘的敗家子式的鋪張。
我沒看過(guò)田沁鑫的《羅密歐與朱麗葉》(2014),但是根據(jù)本書作者詳細(xì)、全面、清晰地描述,覺得這是一部不錯(cuò)的莎士比亞話劇改編。本書作者對(duì)于該作過(guò)分渲染青春叛逆略有微詞,但我根據(jù)本書作者所提供的一手材料,覺得這好像不是問題。
在這部劇作中,“演員身著時(shí)尚服裝,騎著自行車滿場(chǎng)飛,戴著墨鏡耍酷,恣意找茬打群架,還彈著吉他唱著搖滾,打著手機(jī)耍著棒球,洋溢著現(xiàn)代年輕人騷動(dòng)的青春氣息。演員個(gè)個(gè)的京腔片子,不言而喻故事是發(fā)生在北京的,朱家大院和羅家大院,從公開找茬打群架看似應(yīng)指的是20世紀(jì)的七八十年代,但演員口中說(shuō)的漫天霧霾卻又是近年來(lái)中國(guó)出現(xiàn)的惡劣天氣”。而其巧思則“在于從莎士比亞原作的豐富層次里,挑出‘青春’和‘沒有世俗約束的純粹愛情’,作為焦點(diǎn)”。
本書作者說(shuō),田沁鑫“要借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朱麗葉》給觀眾講述一份發(fā)生在中國(guó)少男少女羅密歐與朱麗葉之間的愛情,一份純純粹粹的愛情,一份不受任何世俗觀念約束的愛情,不談門當(dāng)戶對(duì),也不講究彩禮多少,愛情是讓人撕心裂肺的,為了愛情可以去赴湯蹈火”。這也正是莎劇的真諦。
莎士比亞的朱麗葉芳齡13,羅密歐也年齡相當(dāng);這是一個(gè)青春、理想、叛逆的年齡,為了愛情可以在所不惜。家族的血仇、愛人殺害了親人等等都可以忽略不計(jì)。在這個(gè)年齡,如果少年老成,只能說(shuō)社會(huì)已經(jīng)剝奪了孩子們的青春,使孩子們都暮氣沉沉。如果過(guò)了這個(gè)年齡還如此沖動(dòng)和鋌而走險(xiǎn),那只能說(shuō)是傻——成熟的代價(jià)就是要考慮責(zé)任,家庭責(zé)任和社會(huì)責(zé)任。如果為了愛情而冒險(xiǎn),那也只能是理性算計(jì)和調(diào)動(dòng)充分資源之后的冒險(xiǎn),不能把愛人和自己送進(jìn)墳?zāi)埂R虼耍炝_的愛情是人類最純潔、最沒有利益考量、最不管不顧的特殊愛情,而田的版本似乎呼喚出了這種愛情的靈魂。
這是一本好書,因此值得修訂。例如,在林兆華的四部莎劇里,《大將軍》只是提了一下,《仲夏夜之夢(mèng)》也沒有展開論述。我沒在劇場(chǎng)看過(guò)《仲夏夜之夢(mèng)》,因此希望在本書再版時(shí)能領(lǐng)略該劇的風(fēng)貌。
2020年4月6日于石河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