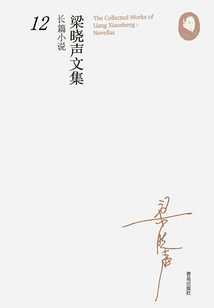最新章節(jié)
書友吧第1章
詩人成為斗士的年代,對任何一個國家都是不堪回首的。當(dāng)歷史的塵埃落定,成為斗士的詩人的死,首先當(dāng)令他的同胞因之心疼。懷著心疼的情感來讀詩人的詩,其詩宛如圣徒蘸自己的血寫成的血經(jīng);懷著心疼的情感來細(xì)看詩人竟成斗士的心路,于是明察那歷史不堪回首的病癥,才是對詩人斗士之死的大敬……
梁曉聲
2011年8月29日于北京
夕陽紅透,余霞許縷。
一聲汽笛,似老翁之悲情一嘆。長江——從武漢至黃石的一段江面,晚霧縹緲,倏濃倏淡……
輪船緩駛江中,銹跡斑斑,仿佛一條患了皮膚病的江豚仰浮于江面——這是1921年底一個陰霾的日子。
甲板上寂靜悄悄,一男子背對層艙,撫欄而立,乃是清華學(xué)子聞一多。
聞一多,原名聞家驊、聞多,出生于湖北蘄水縣(現(xiàn)浠水縣)巴河鎮(zhèn)望天湖畔聞家鋪,堂兄弟中排行十一,大家族中稱其“一哥”或“一弟”,婚后順稱其妻為“一嫂”。因其清華學(xué)友潘光旦一句戲言“聞何謂多?”遂更名“一多”。時年二十二歲,此行乃遵父母媒妁之命趕往家中與表妹高真完婚……
下雨了。雨絲如發(fā),聞一多長衫已濕,似乎渾然不覺,思緒回到從前……
篷船撞霧而現(xiàn),聞父剪臂佇立船頭。
聞父:“家驊,為什么不帶領(lǐng)著背詩?”
席篷內(nèi)探出少年聞一多的頭:“父親,背哪一首呢?”
聞父:“就背杜甫的《贈衛(wèi)八處士》吧!”
少年聞一多:“好……”
江上響起男童們語調(diào)稚嫩的背詩聲: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復(fù)何夕,共此燈燭光。少壯能幾日,鬢發(fā)各已蒼。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
聞父:“停,這后一句怎講?”
少年聞一多:“哪里想到二十年后,又能與君子您衛(wèi)八處士相見于您家的廳堂呢?”
聞父點頭:“繼續(xù)。”
男童們的背詩聲:
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怡然敬父執(zhí),問我來何方……
小船徐遠(yuǎn),其聲亦然。
一只花色的小皮球從一客艙蹦出,滾過濕漉漉的甲板,滾向舷邊……
女人的聲音:“別撿了,危險!”
聞一多轉(zhuǎn)身,看到一個三四歲的小女孩在艙門外,掙著身子要撿球,然而小手被一只女人的手拽住;女人的身子隱在艙內(nèi),聞一多只能看見她的半條裸臂……
女孩:“我的球,我的球……”
聞一多快步走到舷邊,撩長衫,彎下腰,以手擋住滾至的球,撿了起來……
一名船工恰在此時走過他身旁,恭敬地問:“您是……聞少爺吧?”聞一多拿著球,疑惑地望著船工。
船工:“聞少爺,您也回客艙去吧,看您衣服都淋濕了!”
聞一多有些遲疑地:“我們……相識過的嗎?”
船工:“聞少爺,您四伯父,不是在巴河鎮(zhèn)里開著一家商鋪么?我在他鋪子里打過雜。還是他老人家托人介紹我到這艘船上的呢!我家在武漢鄉(xiāng)下,這樣對我來回探家方便多了。我給他老人家打雜的時候見過您幾次。”
聞一多:“那么,是自己人了,何必在船上也叫我少爺?”
船工:“越是自己人,越該分清身份嘛。要不,這大千世界人和人的關(guān)系,豈不就亂套了嘛!”
聞一多搖頭道:“不好,不好,人生在這個世界上,本是不該被什么老爺、少爺或下人的名分區(qū)分開來的。總之,別人若叫我少爺,小時候還聽得,現(xiàn)在長大了,聽著就不知如何是好了。”說罷苦笑。
船工:“那,以后再遇見您,我稱您聞先生就是了。”
聞一多認(rèn)真地:“聞一多。以后直呼我的名字吧。我還是名學(xué)子,哪里當(dāng)?shù)闷饎e人稱我先生。”
船工也認(rèn)真地:“偌大中國,不是僅有一所著名的學(xué)校叫清華么?您家鄉(xiāng)人,誰不知您是清華的才子呢?我一個目不識丁的普通人,豈敢直呼您的名字?”
別處傳來叫聲:“韓福祿,這邊艙里有人暈船吐了,快來收拾一下。”
船工:“聞先生,我得去了。您還是別在甲板上了,快進(jìn)艙里吧!”
船工離去,聞一多又將身體轉(zhuǎn)向了大江……
憑欄的聞一多,雙手無意識地轉(zhuǎn)動著球,輕而長地嘆息一聲,低吟出兩句詩:
暮雨朝云幾日歸
如絲如霧濕人衣……
他的表情隨之惆悵。與表妹的包辦婚姻,委實是他不甚情愿的。
背后女孩怯怯的聲音:“先生……”
聞一多緩緩轉(zhuǎn)身,見女孩站在離他幾步遠(yuǎn)處,正望著他……
聞一多:“小姑娘,有什么事嗎?”
女孩:“還我球……”
聞一多低頭看一眼手中的球,恍然大悟地:“噢,我都忘了,當(dāng)然應(yīng)還給你!”
女孩伸著手正要走向他,聞一多制止地:“別過來,船邊太危險。”
他掏出手絹擦擦球走向女孩,將球還給她,同時抱起了她……
聞一多對小女孩柔聲地:“記住,這個球,你也要當(dāng)它是有性情的東西看待它。它是小球,所以你不能踢它,更不能踏它,你拍它時,要輕輕的。你拍得太重,它就不高興了。一不高興,它就會滾向一邊去,不想跟你玩了……”
女孩似懂非懂地點頭。
聞一多抱著她走到艙門口,將她輕輕放在艙門內(nèi),待直起身時,才見是個小艙,僅兩張鋪位;而一位二十六七歲的女子,一手握卷,斜坐于鋪位,正面帶微笑,神態(tài)端莊矜持地望著他。她身穿旗袍,看去是位生活優(yōu)越的少婦。
聞一多也微笑了一下,退開。又踱回到船舷邊憑欄而望。
少婦注視他的背影……
韓福祿提著手提話筒喊:“各位先生,各位女士,現(xiàn)在餐廳已為諸位備好晚餐,諸位文明艙的先生女士們請用餐了……”
聞一多一扭頭,與少婦的目光相視。
韓福祿匆匆走過來:“聞……您一直沒離開甲板啊!您可真是的!”
聞一多一笑:“我有換的衣服。再說我喜歡在這樣的絲絲細(xì)雨中獨自待會兒。”
韓福祿:“該吃飯了。”
聞一多:“我現(xiàn)在不餓。老韓,你忙去吧。”
韓福祿走開,回頭望他,邊走邊自言自語:“書讀多了,人就是會變得與眾不同啊!”
男女乘客,陸陸續(xù)續(xù)從聞一多背后走過,少婦一手牽著女孩,一手撐傘,也從聞一多背后走過。聞一多全然不覺,一直陷入某種沉思中……
天黑了。
船在夜行,江聲汩汩——聞一多的背影還在原處。少婦的身影出現(xiàn)在他背后,撐著傘,替他遮雨……
聞一多仍不覺。
聞一多低聲自吟:“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
少婦低聲道:“念橋邊紅藥,年年知為誰生?”
聞一多立刻轉(zhuǎn)過身,一時不知所措地:“謝謝,這怎么可以,淋濕了你自己。”
少婦:“聞一多,詩啊詞啊那是當(dāng)不得飯的,心頭愁緒,也并非靠了才子情調(diào)皆可了去。”說著,將傘遞向聞一多,與他扶欄并立。
聞一多接傘在手,不免奇怪地:“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少婦微微一笑:“你剛才與船工交談,我無意間聽到了。”
聞一多:“獨自寂吟,想必也讓你見笑了。”
少婦:“詩人愛詩,猶如女子愛美,誰取笑這一點,誰便是在證明自己的愚蠢。難道我是一副愚蠢的樣子嗎?”
聞一多不好意思地笑了:“我雖還算不上是詩人,但我的確愛詩。愛唐詩,愛宋詞,愛古代和現(xiàn)代的一切好詩,就像男人愛……”
他似乎意識到自己的話多了,忽然緘口。
他將臉轉(zhuǎn)向了江面——泊在江兩岸的小船上,漁火點點……
聞一多:“一年湖上春如夢,二月江南水似天。”
少婦:“這是元代迺賢的《春日懷江南》。”
聞一多刮目相看地側(cè)臉……
少婦:“你的話只說了一半,你愛詩就像男人愛什么呢?”
聞一多婉轉(zhuǎn)地:“在一切的人生中,我覺得,為藝術(shù)的人生是最值得的。我的一生,將是為詩的一生。”
少婦:“已然決定了!”
聞一多鄭重點頭。
雷聲隱隱,遠(yuǎn)處天穹上裂出一道閃電,江風(fēng)驟起。
聞一多:“女士,風(fēng)雨要來了,請回艙吧。”
少婦點頭。
聞一多撐傘,將她送回艙口。待她進(jìn)艙,聞一多請求地:“能否,將這把傘借我?”
少婦詫異地:“怎么,你還要待在甲板上?”
聞一多吞吐地:“我……只不過喜歡獨自待在雨中站會兒罷了……”
少婦:“可是,現(xiàn)在大約快十點了……”
又一道閃電,又一陣?yán)茁暎L(fēng)更大了,站在艙外的聞一多,長衫的下擺不時被風(fēng)掀起……
少婦:“這一場雨來勢洶洶,我的傘是難以擋住它的,你別淋感冒了。”
聞一多笑笑。剛想說什么,一陣大風(fēng)將傘葉吹折……
少婦也笑了,誠懇地:“聞一多,進(jìn)來坐吧。”
聞一多猶豫。
閃電、雷聲、雨點……
少婦在艙內(nèi)一閃身:“請!”
聞一多猶豫地邁入了艙。
一陣風(fēng)將艙門“砰”地關(guān)上,緊接著,瓢潑大雨在艙外下了起來……
女孩已酣睡在一張鋪位上,少婦坐于女孩身旁,指著另一張鋪位說:“詩人,隨便坐吧。”
聞一多局促而坐。
少婦:“我也要謝謝你。”
聞一多困惑不解地望著她。
少婦:“謝謝你替我女兒撿起了球,謝謝你用兒童詩般的語言,對她說的一番話。”
聞一多又不好意思起來,低頭道:“哪里,您過獎了。”
少婦:“聞一多,實不相瞞,沒見到你之前,我已經(jīng)了解你不少了。”
聞一多詫異地抬頭望她。
少婦:“我的弟弟也是清華學(xué)生,不過他偏攻理科。我早就聽他講過,清華有一名叫聞一多的學(xué)生,入學(xué)考試時數(shù)理化成績不好,但文科成績卻名列第二。尤其將一篇題目是《多聞闕疑》的命題作文,寫得思路獨特,邏輯清晰,文采飛揚,深獲文科老師們贊賞……”
聞一多:“一多慚愧。”
少婦:“我還知道,你是清華學(xué)生詩社、劇團(tuán)的主要發(fā)起人,是《清華周刊》的主筆之一,是清華第一名報美術(shù)專業(yè)的學(xué)生,周刊的封面和插圖,往往出自你的筆下……”
聞一多:“那些,都只不過是我喜歡做的事情,所以做來投入而已。”
少婦:“那么,響應(yīng)罷課,參與學(xué)潮,也是你喜歡做的事么?”
聞一多嚴(yán)肅地:“那不同。一多雖然已立志將此生獻(xiàn)給詩和美術(shù),對政治之事,一向并無興趣,但若事關(guān)公理和正義,一多還是不愿袖手旁觀的。竊以為,‘風(fēng)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guān)心’,當(dāng)是今日之清華學(xué)子的社會大立場,當(dāng)是今日之中國青年的社會大立場。”
少婦:“據(jù)說,只有你聞一多等二十九名學(xué)生,堅決不肯向校方低頭認(rèn)錯?”
聞一多微微點頭。
“倘被取消畢業(yè)資格,也決不后悔?”
聞一多點頭。
“倘被剝奪留美之機(jī)會,也在所不惜?”
聞一多點頭。
少婦:“好一個聞一多,能在這艘船上認(rèn)識你,也算不虛我此行了。”
聞一多起身,彬彬有禮地:“我想,我該告退了……”
少婦:“聞一多,你坐下。因為你是我弟弟的清華同學(xué),因為你是聞一多,因為通過我們的一番交談,我自認(rèn)為更了解你了……”
聞一多:“可是,畢竟太晚了……”
少婦:“你因為沒有買到一張臥鋪票,又不愿在底艙擠著,對不?”
聞一多低頭默認(rèn)了……
少婦:“聞一多,你今晚就睡在那張鋪位上吧。”
聞一多訝然地:“這怎么行!”
少婦:“又怎么不行?”
聞一多張張嘴,不知說什么好……
少婦:“我的先生在馬來西亞經(jīng)商。他認(rèn)識湖北航局的一位官員,所以船上特為我們母女預(yù)留了這一小艙,你只管睡下無妨。”
聞一多:“我想,我也許會帶給你諸多不便。”
說著,再次起身,彬彬有禮地微鞠一躬,走至艙門——剛將門推開一道縫,一陣風(fēng)夾著雨撲入艙門,門前地上頓時濕了一片……
聞一多本能地隨即將門推嚴(yán)。
背后少婦平靜的聲音:“清華學(xué)子的頭腦中,想來不該也有什么男女授受不親的思想在作祟吧?”
聞一多的手從門把手上放下了,緩緩轉(zhuǎn)身,望著少婦,莊重地:“那么,一多謝了。”
大雨“嘩嘩”地潑著舷窗,客輪在風(fēng)雨中徐徐前行……
艙內(nèi),少婦摟著女兒熟睡了……
聞一多仰躺著,頭枕雙手,又陷入回憶:
春光明媚的蘄水老家,遍地油菜花黃。胞弟家駟和表妹高真在深黃淺黃中奔來跑去,張網(wǎng)撲蝶。
少年聞一多的身影踏田埂走來,喊:“駟弟!表妹!回家吃飯啦!”
高真循聲望道:“是一哥!”
聞家駟:“你叫得親勁兒的!”學(xué)她聲調(diào),“是一哥!”
高真:“你學(xué)我干什么?我叫錯了不成?”
聞家駟:“你當(dāng)然沒叫錯,他也當(dāng)然是我們的一哥。可是,任你現(xiàn)在叫他一哥叫得再親,長大以后你就叫不成他一哥了,我卻一直還可以叫他一哥!”
高真:“那又為什么?”
聞家駟張張嘴,欲言又止。
高真:“說嘛,說嘛!”
聞家駟:“現(xiàn)在不能告訴你。”
高真:“說嘛,說嘛,現(xiàn)在不告訴我不行!”
聞家駟拗不過她,又說:“我告訴了你原因,你可不許害羞。”
高真:“如果不是羞人的事,我就不害羞。”
少年聞一多的身影走來。
聞家駟:“那,我就給你說個明白——以后,你是要嫁給一哥做媳婦的。這是大人們商議時我偷聽到的事。你成了他的媳婦,連我也要叫你嫂了,你那時還能叫他一哥么?你只能這么叫他了——夫……啊……”最后兩個字,聞家駟學(xué)了一句青衣念白……
高真羞得雙手捂臉,繼而將雙手握成小拳,不停地擂打聞家駟。聞一多走到他們跟前,大人似的:“表妹,怎么打起駟弟來了?”
高真羞視聞一多一眼,嗔道:“他壞嘛,他欺負(fù)我。”
聞一多:“駟弟,你為什么要欺負(fù)表妹呢?”
聞家駟:“我……我……”眼珠一轉(zhuǎn),岔開話頭,將手中的瓶子舉給聞一多看,“一哥,你看我為表妹捕了多少蝴蝶呀!”
聞一多接過瓶子,轉(zhuǎn)動地看著問:“那,你們兩個打算將這些美麗的小生命怎么辦呢?”
聞家駟:“我早就想好了,全都做成標(biāo)本,也代表你的一片心意,送給表妹!”
高真:“我不要……”
聞家駟打斷地:“你不要?那你求我?guī)銇碜剑俊?
高真:“我……我想……我原本是想,一哥愛看書,做成書簽,送給一哥!”
聞家駟:“一哥,一哥,你心里只有一個一哥!還莫如我自己都用線拴了,當(dāng)一只只小風(fēng)箏放著玩兒!”
聞一多:“駟弟,我不許你把它們都做成標(biāo)本,更不許你都用線拴了當(dāng)小風(fēng)箏放著玩兒。表妹,我也不會接受你用它們做成的書簽,將這么美麗的小生命活活弄死了,那是何等殘忍的事啊!”
聞家駟和高真一時怔怔地看他……
聞一多:“還是還它們自由吧!”
他說罷,打開瓶蓋,于是一只只蝴蝶飛出,盤旋在黃燦燦的油菜地的上空,情形煞是好看。
但瓶中還剩下一只蝴蝶不往外飛。
高真:“一哥,給我留下一只!”
聞一多卻將那一只也輕輕抓出一揚手放飛了,并說:“你們多不小心啊,把這一只的翅子都弄破了,看它已無力高飛了,可憐的蝶兒!”
高真狠瞪了聞一多一眼,一扭身跑了。
聞家駟埋怨地:“這可是你惹她生氣的吧?就留一只給她玩又有什么不行呢!”
聞一多望著高真背影一笑:“我惹她生氣的,難道不會再哄她高興起來?”
聞家。
一群孩子們同桌吃飯。高真眼中噙淚,怏怏地不動筷子。孩子們的目光皆望向聞一多……
聞一多:“那些美麗的蝴蝶,使我聯(lián)想到梁山伯和祝英臺,我又怎么忍心不把它們放飛了呢?”又對坐在身旁的高真說,“表妹,別生我氣了,吃完飯我讀梁山伯與祝英臺的戲本給你聽!”
高真抹抹淚,終于拿起了筷子。
雨過天晴,一個清新的早晨。客輪不知何時停靠于黃石碼頭。艙中,少婦被下船人的腳步聲擾醒,坐起身,見對面床上已沒了聞一多,傘撐開放在鋪位前的地上,床上還有一冊刊物。
她起身走過去,首先收起傘,接著款款坐在鋪位邊,拿起刊物,見是《清華周刊》。她翻開刊物,內(nèi)夾一頁紙,上有鉛筆素描,畫的是睡著的她和女兒。
多謝昨夜懇留,為您及女兒草此素描,以博一哂。又,傘已修好。不過,是船上的韓師傅幫我修好的,一多不敢奪人之功,實告。
聞一多
少婦邁出艙,正巧見韓福祿在拖甲板。
少婦:“韓師傅……”
韓福祿抬頭四顧,問:“太太是叫我么?”
少婦:“你的熟人聞一多留言這么稱呼你,所以我也這么稱呼你。”
韓福祿:“不敢當(dāng)不敢當(dāng),我一個船上干粗活的人,哪里也配您太太這么近便地稱呼!請問太太有何吩咐?”
少婦微笑道:“那個聞一多,他哪里去了?”
韓福祿:“聞少爺啊,他已經(jīng)下船了。他家在浠水,得在這兒上岸,再改乘另一段巴河上的木船。”
少婦:“他不愿你叫他聞少爺,你可是又叫了!”
韓福祿:“這不是背后嘛!”
少婦繞到船體另側(cè),雙手撫欄張望岸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分明是在尋覓聞一多的身影,卻又哪里可見!
少婦若有所失地回到艙中,坐下翻看刊物,中有一頁,印著聞一多的詩《二月廬記》:
面對一幅淡山明水的畫屏,
在一塊棋盤似的稻田邊上,
蹲著一座看棋的瓦屋——
緊緊地被捏在小山底拳心里。
……
此時,平靜的巴水河如綢帶般閃著波光。河上,一條載客木船緩緩行駛,船口放著一大一小兩個旅箱。兩岸風(fēng)光旖旎。
船家將櫓搖得“欸乃”聲聲……
艙內(nèi),坐著聞一多和到蘄水接他的老人家韋奇。聞一多默默望著兩岸,心事重重的樣子……
柳蔭下睡著一口方塘,
聰明的燕子——伊唱歌兒
偏找到這里,好聽著水面的
回聲,改正音調(diào)的錯兒。
……
韋奇:“少爺,你有心事?”
聞一多反問代答:“韋奇,我們之間,暗訂一條君子協(xié)議怎樣?”
韋奇一怔,遂道:“韋奇聽少爺?shù)摹!?
聞一多:“以后,你不要再叫我少爺了。我在清華已改了名,先生學(xué)生都叫我聞一多了。以后你就叫我一多吧!”
韋奇:“少爺,我不會那么叫你的。”
聞一多:“為什么?”
韋奇:“你們聞家一向?qū)ξ也槐。乙獮槟銈兟劶业南氯耍鰝€懂規(guī)矩的好榜樣。我若那么叫你,哪兒還有一點兒下人的規(guī)矩了!”
聞一多:“那,就我們兩個人時,行嗎?”
韋奇:“少爺行不行,往后,韋奇試試看吧。”
聞一多不悅地瞪他……
韋奇:“好,我保證在這條船上不叫你‘少爺’了。回家完婚,是大喜的事,你怎么反倒像開心不起來呢?”
聞一多收回目光,望向艙外。
韋奇:“你們聞家是遠(yuǎn)近聞名的耕讀之家,聞老先生又是前清秀才,從祖上就傳下了個個能詩能文的好家風(fēng);他們高家,也是黃岡的大戶,而且嘛,和你們聞家一樣,是盡人皆知的書香門第,高真姑娘我也見過,有模有樣的,何況你倆結(jié)為夫妻,聞高兩家,就親上加親了……”
聞一多:“韋奇,不談這事。”
韋奇:“你如果再不回來完婚,聞老先生八成就要派我去北京把你帶回來了!”
聞一多轉(zhuǎn)移話題:“我父母二老,他們身體都健康吧?”
韋奇:“都好,都好。”
聞一多:“今年雨多,我的‘二月廬’沒有塌墻漏雨吧!”
韋奇:“沒有沒有。我知道你要是一回來,就會從早到晚待在你的‘二月廬’里讀書,替你上心維修著它呢,哪里會讓它塌墻漏雨。”
聞一多的一只手,不禁地攥了韋奇的一只手一下:“我在清華,其實也經(jīng)常思念家鄉(xiāng)、思念父母、思念我的‘二月廬’,還經(jīng)常思念你。回憶我小的時候,你帶我到巴河鎮(zhèn)去,讓我騎在你的脖子上看戲的種種情形……”
韋奇:“如果少爺和高真姑娘將來在北平安家,需要個人看家護(hù)院,我愿去。”
聞一多:“你不是已經(jīng)默認(rèn)了我們的君子協(xié)定了么?”
韋奇低下頭憨憨地笑……
船尾忽然傳來哭泣聲,二人的目光望向船尾,見船家十六七歲的女兒,赤腳蹲著,一邊擇菜,一邊用手背抹淚——衣服褲子,綴滿補(bǔ)丁。
韋奇嘆口氣,悄說:“唉,姑娘怪可憐的,從小死了娘,是跟著爹在這條船上長大的。長大了,也就該嫁了。窮人嫁女,是件愁事。心里喜歡的男人,往往娶不起她;相中了她的,又往往不是她的心上人。‘有情人終成眷屬’這句老話,在窮人家女兒們的身上常是反的啊……”
聞一多再次將目光望向船家女兒,一時表情沉郁。
岸上忽起一個男人的鄉(xiāng)間長調(diào),接著是男人蒼涼的歌唱:
好山好水好風(fēng)光,
不抵妹妹好模樣,
舍得賣掉我雙眼,
只為妹妹你穿上一件好衣裳……
聞一多撩起衫襟,從兜里掏出一卷錢,抓著韋奇的另一只手悄悄塞給他,低聲地:“這點兒錢,是我節(jié)省下的生活費,此番回來沒買到鋪位,又節(jié)省了一筆錢。一會兒我們下船時,你都給船家,囑咐為他女兒買兩身衣服。”
韋奇點頭。聞一多掏出紙筆,問韋奇:“你記得剛才岸上那個人的歌是怎么唱的么?”
韋奇搖頭:“我哪里用心聽來著呢!”
船家的女兒卻說:“我也會唱。”
語調(diào)平靜得出奇。說時,目光凝視遠(yuǎn)處,看也不看聞一多和韋奇……
韋奇:“那么,有勞姑娘替我們唱一遍行么?”
于是船家女兒唱了起來:
好山好水好風(fēng)光,
不抵妹妹好模樣……
其聲凄楚哀怨。
船家在船尾突然高喝:“別唱了!一個待嫁的姑娘家,信口亂唱的什么!也不怕這位文明的先生笑話……”
船家女兒噤聲了,但見一行淚滴在她頰上。
聞一多與韋奇對視,二人的臉分別轉(zhuǎn)向兩岸……
船靠岸了。
岸上早有聞家雇的轎夫守著轎子在等候。聞一多踏上岸,一轎夫迎上前躬身道:“聞少爺,聞老爺指派我們來接您,請上轎吧!”
聞一多:“我就不必你們抬著了,只抬兩件行李箱就是了。”回頭望向船上,見韋奇正向船家交代什么,船家女兒站于一旁……
聞一多在岸上剛走了幾步,船家女兒的歌聲又從背后唱起:
好山好水好風(fēng)光,
不抵妹妹好模樣,
舍得賣掉我雙眼,
只為妹妹你穿上一件好衣裳!
賣掉了雙眼我不在乎,
免得個看妹妹和別人去拜堂……
聞一多駐足回頭,見船已離岸,船家女兒窈窕的背影立在船頭,聞一多趕緊掏出筆,邊聽邊在手帕上記,過往行人好奇地看他。木船漸遠(yuǎn),歌聲漸遠(yuǎn)……
聞一多在巴河鎮(zhèn)街中左顧右盼地走著,韋奇快步趕上。
韋奇:“一多,你怎么不坐轎子?”
聞一多:“你這不是改過口來了么?書是沉重之物,我要再坐上去,那可真真是將轎夫當(dāng)牛馬了,我是人,他們也是人,人不可以根本不替別人想一想。”
韋奇:“那就別逛街了,緊走幾步快回家吧!你父母一定在家等急了!”
聞一多:“我又哪里有閑情逸致逛街。歸程匆匆,連件小東西都沒給我的表妹帶,我想在這街上挑選一件。”
韋奇:“這一次可是你自己提到她的。”
聞一多:“我不是不愿你在我面前提到她,而是不愿和你談我們的婚事。”
韋奇:“還不是一樣的么?”
聞一多:“不一樣。”往前走了幾步,站住,對韋奇又加重了語氣說了一遍,“很不一樣。”
韋奇一時莫名其妙。
聞一多在一家鋪子前挑選女子飾頭的鬢花,比較著一紅一紫兩支鬢花,拿不定主意地問韋奇:“你覺得我的表妹她會更喜歡哪一種顏色呢?”
韋奇:“哎呀,只要是你買了送給她的,哪一種顏色她都會喜歡的。快買下一支走吧!”
聞一多:“那,還是要紫色的吧。紫色會使女子端莊,盡管我自己更喜歡紅色……”
聞一多將手探入兜里,一時愣住:“韋奇,我的錢都給了那船家了。”
韋奇:“快走,快走!掌柜的,你不是認(rèn)得我的么?就記在聞家的賬上吧!”
韋奇扯著聞一多便走……
巴河鎮(zhèn)中古戲臺前,各類小販叫賣聲此起彼伏,好生熱鬧;幾名工匠正在攀梯盤架地布置戲臺,看來不久將有戲演出。聞一多經(jīng)過時不由得駐足觀望……
田間路上,韋奇在前,聞一多在后匆匆地走著……
來到門首掛著“春生梅閣”匾額的大院前,他們剛停下,對掩的大門忽地打開,門內(nèi)擁出的男女傭婢七手八腳、各行其是地搭梯子,掛彩燈,貼剪紙什么的……
聞一多奇怪地:“韋奇,春節(jié)還有半個多月呢,家里干嗎這么早就張羅著裝點門戶?”
韋奇:“裝點門戶?哎呀我的大少爺,就別跟我撇文腔了,這是在為你的婚事做準(zhǔn)備!”
兩位往門上貼剪紙的小女婢竊笑。
而男傭們則打趣:
“聞少爺,就等著沾光喝您的喜酒啦!”
“聞少爺,您再不回來,人家高家可就打算退婚啦!那時節(jié),你們表兄妹親上加親的一段好姻緣可就吹啰!”
聞一多甚難為情。
韋奇:“你又愣的什么神啊!你倒是跟我邁腳進(jìn)門啊!”
韋奇扯著聞一多,繞廊轉(zhuǎn)柱,進(jìn)了一重院子,又進(jìn)了一重院子——各種關(guān)系的親戚們,有的從窗口望見了他,有的在院子里碰見了他,無不與他親切地打招呼;而聞一多幾乎來不及一一回應(yīng),任憑韋奇扯著匆匆往前走……
二人終于走到一處幽靜的廳堂外,韋奇通報:“老先生,老夫人,一少爺回來了!”
屋內(nèi)傳出聞母急切的聲音:“兒啊,還不快進(jìn)來!”
韋奇輕輕推了聞一多一下:“快進(jìn)去啊!唉,我怎么覺得你越有學(xué)問了,倒好像變得有點兒傻了呢?”
聞一多邁入廳堂,聞母已迎在門口。
聞一多:“父母親大人在上,不孝兒給父母親大人請安……”
他說著就要跪下請安。
正襟而坐的聞父語調(diào)緩慢地:“家驊,我們耕讀之家,主張的是追隨時代進(jìn)步潮流,與社會共文明,這些個老規(guī)矩,不刻意而為也罷。”
聞母:“就是,就是!兒啊,娘著實想你啊,多少次夢里夢見了你!快來坐在娘身旁……”
于是,聞一多被母親握著手,領(lǐng)到母親身旁的座位坐下;他看了父親一眼,父親也正嚴(yán)肅地望著他;他不由得垂下了目光,顯然地——他這個已略獲才名的兒子,對父親是敬畏有加的。
聞母的手卻一直握著兒子的手不放,目光也始終不離兒子的臉。
聞母:“兒啊,你臉色蒼白,面容倦怠,想必一路之上很辛苦吧?”
聞一多剛要說什么,不料父親開口道:“雖說路程千余里,但卻畢竟是坐火車,坐輪船,不像古人,只能騎馬甚而步行,若言辛苦,未免嬌氣。我們聞家的男兒,年輕時便當(dāng)養(yǎng)成善于吃苦耐勞的本色。如今之中國,社會的新知識分子如你輩,只讀些經(jīng)史子集是不行的哦。那樣么,將來報效國家的資本是不全面的,依我的眼看來,中國的苦痛還很長久,那苦痛未必就不會涉及你的身上,所以……”
聞夫人:“哎呀,得啦得啦,兒子進(jìn)了家門剛剛坐下,你就開始一套套地訓(xùn)誨起來了,也不怕兒子煩!說點兒正事不行嗎?”
聞父:“我說的,也是正事。”
聞一多:“兒不煩,兒覺得,父親的話極有道理,故不敢妄言‘辛苦’兩字。”
聞父欣慰地點頭。
聞母:“兒子,你如今已經(jīng)二十多歲了,在清華苦讀了整整十年了,知道的事情懂得的道理,明明要比你父親還多啊!何必總順著他的話,奉承他呢?”
聞一多:“媽,我不是在奉承父親,我是發(fā)自內(nèi)心地覺得父親的話有道理。”
聞父的表情更加欣慰,甚至不無得意。
聞母:“不說那些不說那些。兒啊,我和你父親,和你高真表妹的父母,已經(jīng)商量好了,打算把你們的婚事趕在春節(jié)前操辦完了,那樣兩家也可以從從容容地過一個春節(jié)……”
“這……”聞一多心有異議,欲言又止。
聞父:“兒子,你和你高真表妹的婚事,乃是我們聞高兩家家長在你們小時候替你們議定的。你們漸漸長大以后,心里都是清楚的,你也從來沒有說過什么不愿意的話。如今你們都到了該談婚論嫁的年齡了,難道你竟心生反悔嗎?”
聞一多:“父親……”一抬頭見父親一臉嚴(yán)肅,低頭不說下去。
聞父:“有話便說。”
聞一多:“兒對男婚女嫁之立場,在給父母二位大人的信中毫不隱瞞地表白了。”
聞父:“信我早已看過,也讀給你母親聽過了……”
聞一多:“所以我此次回來,只不過是想再次當(dāng)著父母二位大人的面……”
聞父忽然地:“韋奇!”
聞一多和母親都不禁一驚,氣氛一時凝重。
韋奇聞聲而入,低聲地:“先生有何吩咐?”
聞父:“麻煩你給他沏一杯茶。”
聞一多暗舒一口氣。
韋奇沏茶后退出。
聞父不動聲色:“先喝口茶吧。”
聞一多擎杯,淺呷一口。
聞父望著聞母道:“我想單獨和兒子說些話。”
聞母:“怎么,我才見兒子沒一會兒,就趕我走?”
聞父:“父子之間,不唯親情話語。我是理解你的心情的,待會兒讓兒子去你屋里,你們母子盡可以聊個夠。”
聞母想說什么,卻沒說,不得已地站起,俯身悄對兒子說:“兒子,千萬別惹你父親生氣。”
聞一多:“母親放心,兒不敢。”
聞母在婢女的攙扶下,一步三回頭地離去。
聞父大聲地:“韋奇!”
韋奇門外應(yīng)道:“在。”
聞父:“將門掩上,不許別人打擾我和家驊的談話。”
韋奇:“是。”——從外將門掩上。
聞一多反而勇敢地抬起頭,正視著父親,似乎準(zhǔn)備與父親唇槍舌劍。氣氛一時又凝重起來。
不料聞父微微一笑,慈愛地:“兒子,想必方才茶燙,現(xiàn)在肯定涼了,我看出你正渴著,再多喝幾口。”
聞一多擎杯深飲,放下杯低聲說:“父親,兒也常想父母,常想家。”
聞父:“一路有何見聞?”
聞一多:“天災(zāi)人禍,沿途流民多多,時見賣兒女者,令人心生同情。”
聞父:“北平的政局還穩(wěn)定么?”
聞一多:“兒一向遠(yuǎn)避政治,不愿與任何在黨人士結(jié)交。對‘政局’二字,亦感覺遲鈍,恐兒說不出什么來。”
聞父:“那么,怎么又卷入一次學(xué)潮之中了?”
聞一多:“那完全是當(dāng)局逼迫的。還在今年春天,北洋政府就因籌集軍費參加軍閥混戰(zhàn),長期拖欠教育經(jīng)費。北平國立八所學(xué)校教職員工為了中國之教育事業(yè)可以進(jìn)行下去,也為了自己索薪的正當(dāng)權(quán)利,宣布停課,然而北洋政府卻置之不理。6月3日,馬敘倫、李大釗領(lǐng)導(dǎo)的索薪團(tuán)展開罷教斗爭,二十二所學(xué)校六百多名學(xué)生也集于新華門前請愿,北洋軍閥竟出動大批軍警,毆打請愿者,致使二十余人受傷。清華學(xué)校有美國退還的庚子賠款作經(jīng)費基礎(chǔ),沒有拖欠教職薪金,起初自然與此事無關(guān)。然而‘六三’事件之后,我們清華學(xué)子還能置身事外作壁上觀嗎?那樣麻木不仁,無動于衷,同界有難而不聲援的話,清華學(xué)子今后還有何臉面邁出校門以對中國社會?”
聞一多神情激動起來。
聞父卻異常平靜地:“說下去。”
聞一多:“所以,我們清華學(xué)子于6月8日通過罷課案,決定執(zhí)行市學(xué)聯(lián)決議,l8日罷課。而校方卻將大考提前至18日進(jìn)行,并宣布屆時不到考場者等于自動退學(xué)。目的十分清楚,就是要破壞我們的罷課。當(dāng)天晚上,我們再開全校學(xué)生大會,以424票對2票,通過又一項決議——無論校方如何脅迫,清華學(xué)子堅持罷課到底。并要求罷課終止之時,校方給以補(bǔ)考的權(quán)利……”
聞父:“可是報上說,校方也做了讓步,將大考日期推遲至22日,那一天,有三分之二的學(xué)生進(jìn)入了考場,這又怎么解釋呢?”
聞一多:“父親,那是校方后來狡辯而已。若拒不參加考試,尤其對于我們高四級學(xué)子,就意味著八年寒窗付之東流,出國留學(xué)之愿望也成泡影……”
聞父站了起來,踱幾步,猛轉(zhuǎn)身盯著兒子問:“既然明白這個道理,為什么不韜光養(yǎng)晦,審時度勢,而偏偏與二十八名激進(jìn)學(xué)生堅持拒考到底?還自言什么遠(yuǎn)避政治,哼!”
聞一多也不由得站了起來,更加激動地:“父親,人可遠(yuǎn)避政治,但不可遠(yuǎn)避正義,雖涉嫌參與政治,兒亦不畏任何人指斥、任何方面壓力,而要恪守敢當(dāng)敢為的個人立場!我等二十九名清華學(xué)子之動機(jī)堂堂正正,而校方卻在報上污蔑我等乃因?qū)W業(yè)荒疏、成績低劣,借故逃避大考!還逼迫我們寫什么所謂‘自新’的悔過書!父親,事關(guān)孩兒人生的第一次人格尊嚴(yán),孩兒非受什么政治的蠱惑,乃為社會之正義而抗?fàn)帲藶槿烁裰饑?yán)而抗?fàn)帲o理懲罰,乃氣節(jié)所不許也。且從不肯赴考,已經(jīng)光明磊落到今天。父親,我們是中國有個性的新國民,怎甘做高壓手段面前俯首帖耳的奴隸!……”
聞父嚴(yán)厲打斷:“不要再說了。這些話,你在給我的信中都已經(jīng)寫到,我并沒有回信對你大加指責(zé)。你語氣激動,言辭咄咄地干什么?難道我是那對你實施高壓的一方么?!”
聞一多一愣,低聲說:“父親原諒。”
聞父:“還不給我坐下!”
聞一多落座時,袖子拂翻了茶杯,茶杯落地而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