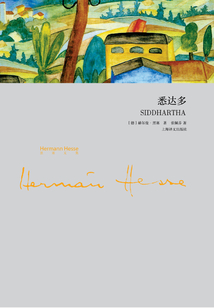
悉達多(黑塞文集)
最新章節
書友吧 1評論第1章 譯本序
赫爾曼·黑塞(1877—1962)是二十世紀重要德語作家,也是一位熱愛中國文化,在東西方間架設“魔術橋梁”的偉大西方人。在中國國內,上世紀80年代前,對他的作品翻譯幾近空白,僅于1936年出版了他的中篇小說《美麗青春》。此后二十多年,情況有了很大變化,他的主要小說、詩歌和散文都陸續有了中譯本。據我所知,迄至2011年謝瑩瑩翻譯的《黑塞之中國》問世,全國已出版黑塞著作不下二十種,較有影響的譯本有:《在輪下》(張佑中譯),《卡門青德》(胡其鼎譯),《納爾齊斯與歌爾德蒙》(楊武能譯),《荒原狼》(有趙登榮、倪誠恩和李世隆、劉澤珪兩種譯本),《黑塞詩選》(錢春綺譯),《黑塞小說散文選》(張佩芬、王克澄等譯),《朝圣者之歌——黑塞詩歌散文選》(謝瑩瑩等譯)以及《堤契諾之歌》(竇維儀譯)。我個人則出了三種:《黑塞小說散文選》(1986年),內收作者著名中篇《悉達多》(當時譯為《席特哈爾塔》)、《黑塞散文選》(1997年)和《玻璃球游戲》(1998年),并撰寫了一本《黑塞研究》(2006年)。
其實黑塞的評論文字也很出色,而且數量巨大,超過了三千篇(德國學者弗克爾·米夏爾斯語),可惜國內介紹甚少。黑塞從童稚少年到八十五歲高齡去世前一日,終生從未中斷閱讀,可謂博覽群書,而且善于把自己的讀書經歷化為文學,幾乎篇篇都很重要,與他同時代的著名作家圖柯爾斯基曾撰文評價他這方面的成就,說:“黑塞的評論性文字在德國目前并無人可與之相比擬。人們從黑塞的每一篇書評里都能夠學到一些東西,甚至獲益良多。”
本文試舉幾例。《世界文學的圖書館》自1929年問世以來始終受到德國創作界和學術界的關注,全文三萬字左右,不僅概括了黑塞遍及古、今、東、西的閱讀經歷,還完整地闡釋了書籍和人類生命意義之間的聯系。翻開第一頁,映入眼簾的就是兩段勸人閱讀世界文學的精辟言論:
真正的教育是不尋求任何目標的教育,如同任何尋求完美的努力,其意義就在努力本身。同樣,我們追求強壯的體魄、熟練的技巧和美麗,并非最終目標,也不是為了讓我們富裕、成名和有權力,其價值在自身之內,它提高了我們的生活情趣和自信心,使我們活得更愉快,更幸福,給予我們內心更安全、更健康的感覺。因此,我們追求‘教育’——換句話就是精神完善——也同樣不是為了達到任何有限目標而必得走的艱難道路,而是為了開闊我們的心胸,提高我們的悟性,豐富我們的生活內容,以及增加獲得幸福的可能性。因此,真正的教育和真正的體育一樣,永遠同時給予我們滿足與激勵,永遠時時處處都朝向目標,在任何地方都不停息;它是一場永無盡頭的旅程,是在宇宙的節律中運行,是一種不受時空局限的生活。教育的目標不是訓練提高單個人的技術和能力,而是幫助我們賦予人類的生命以意義,闡釋過去,無畏地迎向未來。
達到這種真正教育的最重要途徑之一,就是學習、研究世界文學。研讀世界文學會讓我們逐漸熟識、親近許多民族歷史上的詩人和思想家用其著作遺留下來的巨大珍貴財富——思想、經驗、象征、夢幻和理想。這條路永無止境,任何時候、任何人都不可能走到終點,不可能完全認識、精通,即或只是某一個擁有偉大文明的民族的全部文學,更何況是全人類的文學呢。然而,每一深入讀懂、領悟任何一位第一流思想家或者詩人的作品,就是一次令人幸福的經歷——不是記住死知識,而是活生生的心領神會。我們不要人云亦云,以為多多益善,而應當自由挑選適合自己的杰出著作,以便我們在閑暇時刻潛心閱讀,得以想象人類以往所思考、所追求的是何等寬廣和豐富,得以對整個人類的生命總體在生氣勃勃的共振關系中產生共鳴。這種閱讀歸根結蒂屬于了解生命總體的意義,而并非僅僅服務于實用的需要。
《卡夫卡釋》(1956年)是黑塞晚年的著名論文,問世后幾十年間經常被收入世界各國出版的散文或評論選集,其中涉及讀者和作者關系的見解經常被人援引。文章通篇以卡夫卡讀者身份寫成,這里也摘譯兩段:
試圖用批判分析征服作品的欲望,大大損傷了他們全心全意觀察和傾聽作品的基本能力。一個人若是只滿足于從一首詩或者一篇小說中提取出它在思想、政治傾向、教育或者教益上的含量成分,那么他就是只滿足于小部分,而藝術的奧秘、真實以及作者的獨特本質,卻全都失落了。
誰若能夠真正閱讀一個詩人,也就是說,并不期待解決問題,并不企盼在智慧或道德上有所收獲,而是單純地樂意接受這位詩人所給予的,那么這些作品也就會以它們各自的語言給這個讀者提供他所希望的任何回答了。
歌德曾嗤笑死讀書的人說:“學究不體會詩人之本真性,而只研究其師承”(錢鐘書譯文),黑塞也強調了這一點:“對于一個善于讀書的人來說,閱讀一本好書好似去結識一個陌生人的品性和思想方式,試著去了解他,讓他成為自己的朋友。……一個人如果被一本書吸引住,開始去認識作者,去理解他,與書產生一種親密的關系;這時,書才對他產生真正的影響。”
托馬斯·曼被稱為黑塞的“精神兄弟”,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在美國電臺發表過許多堅定追求、探索人生真諦的言論,其中也有關于書籍和文化的話,如:“藝術是什么?文化又是什么?它既非游戲,也非奢侈,誰眷戀于此,誰執著于此,誰就不會有怯懦之品性。它是世界上最嚴肅的事業,因為它得映射出某個時代的具有進步意義的信仰,它實際上是一種超越時代的使人類更加接近理想的努力,這理想便是人的人性化。”而黑塞用另一種語言說了同樣的精神:“對我而言,一本書的價值同它的名聲與受歡迎的程度毫不相干。書本的存在并不像體育新聞或搶劫謀殺案那樣,為了在一段時間內讓每個人讀,成為一個流行話題,然后被遺忘。書本要被靜靜地讀,認真地享受,還要被愛。這樣它們才會展露它們最深處的美麗和力量。”(謝瑩瑩等譯文)與此同時,黑塞也沒忘記向讀者提出忠告,說:“歸根結蒂,優秀書籍與高尚欣賞趣味的敵人不是那些輕視書籍的人,而是那些濫讀書的人,”“許多農婦一生只擁有一部《圣經》,也只讀這一本書,卻從中獲得很多知識、安慰與歡樂,而一個隨意購書的富翁從他那無比豐富的圖書館里卻無法獲得那么多。”
關于讀書方法,黑塞對青年讀者也有過指點:“漫不經心地、消遣式地讀書恰似蒙著眼睛信步走過一處幽美的景色。我們也不應該為了逃避自己和瑣碎的日常生活而讀書,恰恰相反,我們讀書是為了能夠更成熟、更清醒地牢牢把握住自己的生活。我們也不應該像膽怯的小學生走近板著臉的老師那樣走近書本,也不應該像酒鬼走向燒酒瓶,而應該像登山者攀登阿爾卑斯山,或者像戰士沖入武器庫,我們不逃避生活,我們迎向生活。”
黑塞活了八十五歲。他出生時世界上還沒有汽車,夜晚時房間里也只有煤油燈,當他逝世時,第一顆人造衛星早已環繞地球運行,然而他一生始終生活在多災多難時代:德意志第二帝國、第一次世界大戰、魏瑪共和國和世界性經濟危機、希特勒的第三帝國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最后是兩個并存的德國,他去世時兩個德國已并存了十二年有余。他親身體驗的機械主義和物欲之破壞人性促使他大半輩子致力于讓每個人的“私人生活向著從獸類到人類的道路邁進一步”,從本文所援引的少量文字也可“管中窺豹,時見一斑”了。
黑塞身后留下了“近四十部著作:長篇小說,中、短篇小說集,詩集和散文集,以及三千篇左右的評論文字。這些著作在幾十年后并未被遺忘,恰恰相反,它們是以最重要和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方式生氣勃勃地留存世間的,也就是說,它們是受到廣泛閱讀而并非僅供研究的文學流傳后世的。”(德國著名學者弗里頓塔爾語)黑塞一生曾獲多種文學獎,并于1946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
本書所收三部中篇小說:《蓋特露德》(1910年)、《克諾爾普》(1915年)和《悉達多》(1922年)均屬黑塞早期著作,不過前兩篇和第三篇間隔了一場剛剛平息的世界大戰,使作品具有了不同底色。《蓋特露德》寫兩個音樂家的一場三角戀故事,兩個性格對立的人物其實是作者的兩個自我,而女主人公蓋特露德則是“一種象征”。顯然,婚姻在作家眼中并非單純夫婦關系,而是藝術家應對世俗生活和藝術追求矛盾的難題,書中引用尼采的名言:“人類從音樂精神中獲得再生”,暗示了小說的主題。男主人公戀愛失敗,卻促進了他的藝術創造。
《克諾爾普》被黑塞稱為“我最喜愛的小說”,又說“對我而言,克諾爾普和故鄉早已合二為一”。小說主人公是窮苦人家的孩子,人們為他安排的前途是工人或者手藝匠,他卻滿腦子哲理思考,詩句總是脫口而出,成為當地老百姓歡迎的“游吟詩人”,黑塞哀嘆民間的天才往往遭到淹沒。克諾爾普也沒有逃脫這種悲劇命運。這部充滿了感傷之情的小說展示了上世紀初德國南方小城卡爾卡夫的風俗圖景,斯蒂芬·茨威格讀后說:“書里有一個德意志國家,是從來還沒有人認識到的,就連我們德國人自己也不例外。”
《悉達多》始寫于1919年,受戰火震撼的黑塞越來越深信,“詩必須同時是信仰”,于是他總結自己的宗教觀寫成了一篇文章《我的信仰》。黑塞在文章里寫道:“我進行試驗,把我的信仰寫成了一篇小說,這本書就是《悉達多》。”作品敘述一個婆羅門貴族青年尋求人生真諦的一生,他從錦衣玉食到游學為僧,又從驕奢淫逸到擺渡濟世,最終悟道成“佛”。黑塞試圖通過文學尋找出“人類靈魂在沒有時間性世界里的發展可能性”。誠如黑塞所自白的:“我努力探索一切信仰和一切人類虔誠善行的共同之處,究竟有什么東西是超越一切民族差別之上,有什么東西可以為所有種族和每一個個人所信仰和尊敬。”《悉達多》成為作家產生世界性影響的成功“試驗”之一。
黑塞曾說:“我死后五十年,如果在這世界某處仍有人關心我的著作,不管哪一國人從我的作品中,選擇適當的內容視為己有,我也無所謂,但經過五十年后,如果我的作品早已為世人所遺忘,那這些作品就可以不必存在于世了。”如今,黑塞已逝世五十年,而黑塞的作品在世界各地仍深受喜愛,事實證明他的作品屬于經得起時代考驗的經典。
譯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