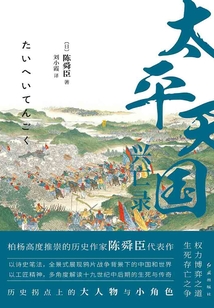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 4評論第1章 長崎夜談
一輪圓月映在水中,水波又把月影揉碎。微波蕩漾,光和水仿佛在嬉鬧。
“就在這兒分手吧。請上船。”一個年輕的小伙子說道。
“實在太感謝了!”連理文說得很慢,他的日語還不熟練。
跟他并肩站著的小伙子提著燈籠,燈光照在岸邊的一艘小船上。“照顧不周,還請包涵。”小伙子微微低頭行了個禮。
“正助,你這么年輕,就有這樣的成就,真了不起!”
“連先生,你的日語進步多了,說起客套話來也進步多了。”
“哈哈哈……是嗎?”
“畢竟你來日本還不到一年呢。”
“那咱們就再見了。”連理文說完上了船。
遠處的海面上,依稀可見唐船[1]的黑影。船夫靜靜地搖著槳,小船在不知不覺中離了岸。站在岸上送行的小伙子把燈籠舉過頭頂,燈光清晰地映照出他長長的臉,上頭還殘留著少年的影子。他叫大久保正助,虛歲剛剛二十。
唐船一靠近,小船上的連理文就摘下包裹著的頭巾,辮子松弛地垂落在他背上。唐船似乎早就知道他要到來,從甲板上垂下一條繩梯。就這樣,連理文在薩摩的坊津海面坐上了開往長崎的唐船。
這是一八四九年的事。日本的年號是嘉永二年。這一年,從清國開往長崎的貿易船有八艘,其中第七號船在天草失事了。連理文在薩摩海面搭乘的是第四號船。在德川幕府閉關鎖國的時代,從清國開往日本的交易船必須持有證明,即所謂的“信牌”。第四號船的信牌上寫著“李亦圣”,船主是鈕心園,但實際上船主是廈門金順總號的老板連維材。七年前鴉片戰爭結束后,清國被迫接受了《南京條約》,五口通商,而在那之前,就像當時的日本只把長崎作為對外窗口一樣,清國只有廣州是貿易港。之后,金順記主要在香港和上海拓展業務,總店形同虛設。連維材的四兒子理文原來在上海,去年他主動要求去琉球。
“哦?想去一年看看?也好。”連維材答應得爽快。
其實,理文想去一個陌生的地方忘掉一切。他結婚才一年多,妻子突然病逝了,他的內心創傷極深。琉球的工作很艱巨,而這正是理文所渴求的。
薩摩的島津藩早就把琉球置于自己統治之下,并通過琉球和清國交易。所謂的“交易”,即琉球作為清國的附屬,接受清國的冊封,并向清國朝貢。當然,這是得到幕府承認的。原則上,和清國及荷蘭的交易只能在長崎進行,而且必須通過幕府的壟斷機構——長崎會所。但在日本各藩中,只島津搞對外貿易,擁有從清國進口的“唐物”。文化七年(1810年),島津迫使幕府準許其在長崎出售唐物。起初,在貨物品種上有限制,但島津硬是擴大了品種。島津之所以如此具有威懾力,是因為手中有一張王牌——“這是為了幫助琉球,如果不這么做,琉球就會脫離日本。”對此,幕府不得不讓步。
總之,島津充分利用參加長崎會所的特權,不,應當說,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了這一特權,起初只是買賣琉球的朝貢貿易品,后來也偷偷從事其他對外貿易。倘若其他藩私藏唐物被發現,幕府立刻就會懷疑其走私,這有可能導致其傾家蕩產。但島津藩只要一說“這是琉球的朝貢貿易品”就萬事大吉了。可以說,這是島津藩最完美的護身符,由此,既保證了貿易品來源之合法,又可以拿到合法市場——長崎會所上出售。
當然,走私貿易不會有正式記載,但琉球搞朝貢以外的貿易,圈里人心知肚明。唐船在琉球停靠,出售唐物,購買被稱為“俵物”的海產品。不過和長崎不同的是,在琉球交易不需要那個麻煩的信牌。后來,唐船擴大范圍,甚至出現在了薩摩的海面上。由于和島津貿易有利可圖,很多持正式信牌的唐船在開往長崎前,都會先在薩摩海面或近海各島處理一部分貨物。有的唐船進入長崎時幾乎是一艘空船。
島津藩的走私對象主要就是金順記。連理文去琉球也是為這事兒。另外,他還擔負同薩摩談判的重任。島津藩琉球館的大久保利世,就是對方的負責人之一。理文和他的兒子正助成了好朋友。
按慣例,四號船會在坊津卸下和島津交易的貨物,然后開往長崎。連理文有事要去長崎,于是決定乘坐這艘船。為他送行的青年正助后來成了大名鼎鼎的大久保利通[2],而當時,正助在島津藩記錄所擔任見習文書。
四號船甲板上鑼鼓喧天。為慶祝安全抵達,舉行這種熱鬧的儀式已成為慣例。唐船先在港外下碇,等候長崎衙門處理。不一會兒,岸邊劃出幾十只小船,給唐船拴上纜繩,將其引如港內。入港后,唐船再次下碇,鑼鼓再次響起。等鑼鼓聲停,長崎衙門的檢查官和通事們便登上唐船。他們把寫著禁令的木牌掛在桅桿上。禁令是以日文寫成的,由通事譯成漢語,念給船上的人聽,主要是關于天主教的事。
念完禁令就是辦入境手續,即檢查信牌、貨物單和花名冊。連理文是在薩摩海面上船的,但花名冊上寫著他是從清國上船的。貨物單是開船之前就做好的,去掉了給薩摩的貨物,這就需要事先和島津當局商談交易數量——這也是連理文的工作之一。
出示證件之后,就是那個有名的“踩圣像”考驗,通過者才可上岸,但上岸后不能在街上隨便走動。荷蘭人在出島,中國人在唐人坊。其實,元祿以前,中國人和日本人在長崎是雜居的,這或許是因為中國人不太信天主教,幕府比較放心。不過,這直接導致了私人間的秘密交易。再加上康熙帝對耶穌會采取寬容政策的消息傳到日本,幕府提高了警惕,開始關注中國人和天主教的關系。
唐人坊建于元祿二年(1689年),位于長崎十善寺御藥園地(幕府的藥草園),面積為九千三百七十三坪[3],比荷蘭人居住的出島(不足四千坪)寬敞多了。荷蘭人把出島稱作“遠東監獄”,因為他們一步也不能離開;中國人若要參拜寺院,在官吏陪同下,還是可以走出唐人坊的。
雖然外國人被圈在一個地方,但他們可以叫妓女進去,以解在異國的寂寞。長崎丸山的妓女分為“掙荷蘭錢的”和“掙唐人錢的”。海上航行艱苦勞累,要說有什么愉快的事,那就是玩弄玩弄妓女了。“踩圣象”一結束,商人和水手都露出了喜悅的神色。經常往來這條航線的人大多有各自相好的女人,有些船主甚至還有“長崎老婆”。
連理文興致勃勃地朝唐人坊走去。他是初次到長崎,自然沒有相好的女人,令他激動的是他知道哥哥哲文比自己早一步到了唐人坊。連哲文比連理文大兩歲,他已脫離家業,專心從事繪畫。半年前,他從寧波乘坐以“鄭朗伯”的名義領取信牌的第一號唐船來到長崎。原則上,商人、船主和水手只能在長崎留居數月,然后乘原船返回。但有的中國人是受長崎地方長官的非正式邀請而來的,他們可以長期居住,比如某些醫生、畫家、文人和僧侶。據說哲文是因為聽了同行畫家的介紹才產生了來日本的念頭。他畢竟是藝術家,喜歡四方云游。他曾一度待在蘇州,但就連近在上海的理文也很難見到他。
“已經三年沒見面啦。”在去往長崎的船上,理文扳指一算感嘆起來。他上就要三十歲了。一想到年齡,腦中就會浮現亡妻的面容。妻子面孔修長,身材苗條,到死都沒失掉孩子氣。對,她長得很像正助。在前往唐人坊的路上,理文終于發現了自己對正助懷有好感的原因。在鹿兒島,他和正助的朋友也有來往,他們類型各不相同,比如一個叫西鄉吉之助(西鄉隆盛)的青年,身材魁梧,性情穩重。理文雖覺得他是個有為青年,但總覺得不如正助親切。跟正助分別時,理文曾把魏源的《海國圖志》送給他。正助翻看了幾頁,低聲道:“我想讓吉之助也看看。”《海國圖志》是鴉片戰爭后不久,魏源根據林則徐提供的資料所寫成的。在書中,魏源敘述了世界形勢,并主張中國必須推進近代化。確實應該讓西鄉吉之助這樣的青年讀讀這本書,不過理文只想到了要送給大久保,而沒想到西鄉。
唐人坊亦稱“唐人館”,中國人也稱其為“華館”,境內稱為“館內”,直到現在日本還留著“館內街”的地名。華館四周圍著七尺[4]多高的磚墻,墻外掘出六尺深、六尺寬的壕溝。華館的大門被稱為“一門”,里面有官吏值班室和交易所,跨進“二門”才是被稱為“唐人本部屋”的居住區。
已有三艘唐船進入長崎,館內居住著有四五百名中國人。二門旁站著二十來名同胞,大概是來接人的。理文以為哥哥會在里面,但看了一眼發現沒有,正準備往前走,忽然聽到有人叫他。
“喂!在這兒!在這兒……理文,你發什么呆呀!”
理文順著聲音再次看向二門旁。“啊,三哥!”他驚詫地睜大了眼睛。
從人群中走出來的正是哲文。理文剛才沒有認出他是有原因的——哲文發型變了。清代的中國人都是剃去前半個腦袋上的頭發,將后半個腦袋上的頭發梳成辮子,像理文這樣在日本待了近一年的人,大多會用頭巾遮住腦袋。而哲文卻蓄了滿頭黑發。理文不覺從側面瞅了瞅,哥哥腦后已沒了辮子。
“你腦袋怎么啦?”
梳辮子是滿族風俗。滿族統治中國后,將自己的風俗強加給漢族。這種強制非常徹底,即所謂的“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理文自然對哥哥感到訝異。
“當和尚不就沒事了!”哲文笑了。
滿族信佛,尊敬僧侶,準許和尚剃發。因此,清初不少大漢民族主義者為抵抗這種奇異的風俗,便出家當了和尚。不過哲文剪掉辮子后又開始蓄發,整個腦袋長著三厘米長短的頭發。他似乎還有點擔心,邊走邊不時摸摸腦袋。
“你真出家了?”理文追問道。
“當然。這不是真和尚頭的聲音嗎!”哲文用拳頭敲了敲腦袋,不辨真假地笑道。
“那……找人起法號了嗎?”
“法號?嗯,有,九曲。”
“哈哈哈!”理文也笑了。
哪里會有這么奇怪的法號!哲文的雅號是九曲山人。福建武夷山中有處九曲名勝,大儒朱熹曾作《九曲歌》。連家兄弟幼時常跟隨父親去武夷山臨溪寺玩,還背過《九曲歌》。
“不說這個了。”哲文把手放在理文肩上,“走吧,你也累了,屋里備了酒菜。”
理文感受到了從哥哥手心里透出的溫暖。
屋子里,一張紅漆圓桌,三把椅子,兄弟倆相對坐下。哲文背后有一張山水大屏風,理文一看就知道是哥哥畫的。他雖不會畫畫,但有著表現美的愿望,縱使不知道如何表現,但一看哥哥的作品,就深深地產生了一種奇妙的共鳴:“這正是我心中所想啊……”
三年沒見,自然有滿腹的話要說,但千頭萬緒,反而不知從何說起了。理文本想問問父母的情況,但一想哲文在來日本之前都沒見過父母,而自己一年前見過父母,要問也應該是哥哥問自己。
“咱倆誰的日本話說得好?”理文還未開口,哲文先說道。
“哎呀,這怎么說呢?”
“要不,現在我們只說日語。我在日本待了半年,你待了一年。”
“長一倍。”
“不過,待得長不一定就說得好,總之比比吧。找個女子給我們當裁判。”
“女的?”
哲文并未回答,回頭用日語道:“袖若,你過來。”
屏風后走出一個年輕女人。
“這是我弟弟理文。怎么樣,很像我吧?”
這個叫袖若的女人坐下來,笑道:“到底是兄弟,一眼就能看出來。”
哲文告訴理文,袖若是引田屋的妓女。理文在日本待的時間長,對日本妓女的情況有所了解。在薩摩時他便聽說了長崎妓女和清國商人殉情的故事。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人們依然津津樂道。還有一個故事,說的是文人船主江藝閣和妓女袖扇生了一個孩子。理文一說這事,哲文佩服道:“了解的不少呀,這事也傳到薩摩了?”
“江藝閣是名人,薩摩和長崎會所又有聯系,自然知道一些。”理文道。
有些人在本國默默無聞,但在日本眾所周知。畫家伊孚九和文人江藝閣便如此。據說賴山陽[5]想見江藝閣,特意來到長崎來,結果唐船未到,二人沒見上面,但也傳為了佳話。當時,賴山陽叫來跟江藝閣相好過的妓女袖笑,還做了幾首戲詩。不過,袖笑和袖扇并非同一人。引田屋的妓女大多以“袖”為名。引田屋又名花月樓,長崎的中國人稱其為“養花山館”。
袖若彈起了三味線。
在日本待了一年的理文已經習慣了這樣的氣氛。薩摩人的習慣是跪在榻榻米上的,這令他苦不堪言,而在唐館坐的是椅子,他覺得舒服多了。他凝視著袖若的手,那拿著撥子的手白到令他頭暈目眩。他只看手,因為看袖若的臉使他感到痛苦。
哲文曾愛過一個叫清琴的女人,但她同詩人龔自珍殉情了。那是八年前的事。袖若的臉乍看沒什么,但越看越像清琴。“莫非……”一想到哥哥的情感遭遇,理文就難過起來。他的妻子也去世了,因而很理解哥哥的心情。
袖若彈著三味線,用清脆的嗓音唱著小曲,這期間,酒菜已經上齊。一個半老漢子跟在仆役后面走進來道:“今天的菜是特別做的,最近我也會做幾樣拿手菜啦!”他是唐館的廚師。唐船上的廚子、雜役,一上岸就變成了唐館里的廚子、雜役。
酒一上來,話匣子就打開了。袖若或許是意識到了自己的工作,一直說個不停。她說到了比自己大二三十歲的袖扇和袖笑的傳聞,也說了從前輩妓女和鴇母那兒聽來的舊事。“從前和現在可不一樣啊!”在長崎,不管談什么,似乎都要以此為開場白。
長崎作為交易窗口,但如今,貿易已經衰落了。一百六十年前,唐人坊建成時,這里常住著五千唐人,最多時甚至過萬,十分熱鬧。現在超過五百人的時候都很少,秋季唐船一走,就只剩幾十人了。這主要是因為貿易發生了變化,這一點連妓女都知道。
在長崎黃金時代,日本主要出口銅。清國鑄銅錢,但國產的銅不夠用,所以從日本大量進口。鑄幣是政府的事,采購原料自然也是國家行為。進口商經政府特別許可,有了“辦銅官商”這樣威嚴的名字。他們一般都和本國官僚有著密切聯系,是所謂的“御用商人”,與周圍小商人之流大不相同。日本出口銅的代表是兼營銅山的泉屋,這是住友家的店號。元祿時代可說是出口銅的高峰時期,當時每年運走的銅有時超過七百萬斤[6],而現在呢?最多也就五六十萬斤。當時清國的銅價猛降,由于購買鴉片,白銀大量外流,因此銀價上漲,銅價下跌。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一兩銀只能換八百文銅錢。
如今,一兩銀能換二千文銅錢,銅對商人的吸引力也就減弱了,于是以干鮑魚、干海參和魚翅為代表的海產品,即“俵物”代替銅成了對清出口的主要商品。但俵物畢竟不能完全替代銅。貿易減少是不可避免的,長崎經濟也就衰退了。酒樓和妓院之類的地方對市面行情最是敏感,妓女懂點經濟知識并不奇怪。
袖若按自己的理解,說了一通長崎的今昔盛衰。
“你知道的事情真不少。”哲文半開玩笑道。
“說得真好。”理文也夸道。
袖若的話單刀直入,簡單明了。“這都是從大人物那兒聽來的。”她說道,“不知好日子什么時候能再來呀。客人們都在發牢騷,說是薩摩搞的鬼,什么事都不好辦了,真的……”
“薩摩?”理文不覺順嘴說了句。
“咦?聽起來令弟的日本話帶點薩摩口音呢。”
“沒有,我朋友中有薩摩人。”理文慌忙回應道。
俄而,袖若起身離開。她是當紅妓女,還要去另一位客人那兒。
管弦旋律一消失,房間突然安靜起來,不過這氛圍倒是很親切。房里只有兄弟二人。哲文大概是考慮到,兄弟倆畢竟闊別三年,重逢時有女人和歌聲,氣氛會更融洽,因而才這樣安排的吧。桌上的菜沒怎么動。
“吃點吧,不吃廚子會不高興的。”哲文拿起筷子。
“是呀,他還特意跑來打招呼。”理文將匙子插進鮑魚湯里。
“薩摩的名聲不佳呀。”
“在長崎似乎確實如此。”
“太霸道了。跟我們家的金順記一樣。”哲文雖不問家業,但對父親的性格和那反映父親性格的金順記的本質一清二楚。
“不是霸不霸道的問題。”理文是金順記里的人,他帶著辯解的口吻道。
“那倒是。光是霸道怎么行!你說,薩摩這樣下去能行嗎?”
“哥哥是畫家,對這種事也有興趣?”
“當然。對女人、對世上的事,我都有興趣。若對什么都沒興趣,就畫不了畫啦。如果不比一般人更有興趣,就畫不出真正的好畫。至少我這么認為。”
“我覺得薩摩可以的,長崎也就發發牢騷,誰也不敢公開反對薩摩。”
薩摩進行走私貿易,這是眾所周知的。他們不僅在琉球和薩摩海面上收購唐物,還在日本各地采購俵物。幕府采取壟斷政策控制對外貿易,拿俵物來說,日本百姓甚至禁止食用所謂的俵物“三品”——海參、干鮑魚和魚翅。諷刺的是,島津藩卻在北海道和北陸一帶偷偷收購俵物,有時甚至裝作外國船只。他們把這些俵物運到琉球,主要賣給金順記的唐船。所以,落到長崎會所的俵物數量少,質量也差。而沒有信牌的船經過琉球時,就先把運送的俵物廉價上市了,要是特意運到長崎就不劃算,因而來長崎的唐船也減少了。
“這么說,日本要變了,可能還很重大,如果薩摩有能人的話。”哲文道。
“有!”理文立即道,“薩摩只缺財力,不過,現在似乎也有了。”
“那恐怕也是靠我們金順記吧。”
“不,沒有金順記,也會有別人和島津做生意的。”
“這就是時代的潮流吧。”
“對。”理文使勁兒點點頭。他想起了大久保正助和西鄉吉之助。
掌燈了,屋子里洋溢著更加親切的氣氛。哲文隨手斟上紹興酒,一口喝干,道:“不僅日本,我們國家也要變啊!”
“十年前的鴉片戰爭起不就變了嗎?過去廣州一口通商,現在五口了。”
“那只是表面,今后連內部……嗯,五臟六腑都要變。”
“是嗎?”
“來日本前,我去了趟廣西。”哲文換了話題。
理文第一次聽說此事。算算時間,應該是半年前,當時他正奔走于琉球與薩摩之間。父親雖常對其指示工作,但并未談及家中情況,而哲文在外漂泊,四處游走是常態,自然也不會有人特意告訴理文他的行蹤。
“桂林嗎?”
桂林作為廣西著名的風景勝地,有著“桂林山水甲天下”之美譽,和廬山、黃山一樣,這也是畫家有生之年必去之地。哲文去桂林,一點兒也不稀奇。
“桂林是順便去的。”
“順便?那你去什么地方了?”
“桂平。”
“桂平,好像聽說過,在桂林附近嗎?”
“離得很遠呢!”
“風景好嗎?”
“有個西山……其實是因為西玲在那兒,我是受父親之托去請安的。”
“原來如此。”理文點了點頭。
西玲這個名字,在連家是要避諱的,在母親面前更是不能提,因為她和父親有著特殊的關系。連維材能夠創建金順記這樣的大店鋪時,得益于白頭夷富羅斯的資金援助。
所謂“白頭夷”,是指巴斯人,他們很多至今仍住在孟買一帶,在印度金融界擁有龐大的勢力。他們本是住在波斯的拜火教徒,因拒絕改奉回教逃到國外。他們是天才的金融家,在十九世紀的世界經濟舞臺上曾非常活躍。廣州也有不少巴斯人。富羅斯同中國女人生了個女兒,就是西玲。他死后,連維材撫養起了恩人的女兒,但不知何時起,他們有了非同尋常的關系。西玲個性強烈,不鬧點事兒出來就不安心。然而鴉片戰爭期間,她失去了摯愛的異父弟弟,又遭到了英國兵的凌辱,就此變了個人似的。
連維材盡量讓西玲和連家保持距離,因此連家兄弟很少見到西玲。盡管西玲和父親有著微妙的關系,連家四兄弟私心里卻都對她抱有好感。在四兄弟少年時期,西玲簡直像夜空中一顆明亮的星星。她比長兄統文只大了四歲,美貌而豪爽,似乎永遠在躍動。連家兄弟沒有姐妹,這樣的西玲正是他們的憧憬對象。
“西玲很精神,快四十了,還是那么漂亮。”不等弟弟發問,哲文就匯報道,他似乎很了解弟弟的心思。
“聽說她當了尼姑,真的嗎?”
“沒有,只是住進了尼姑庵,是帶發的尼姑,聽說是靠庵主的關系去的。”
“還好,只是寄身在尼姑庵。”理文松了口氣。
“桂平這地方,實在偏僻得很。”
“是嗎?”
“不過,這偏僻的地方說不定會成為改變世道的根據地。只要到那兒去看一看,你就會產生這樣的想法。”
“什么根據地?”
“改變世道……也可以說是改變國家吧。說不定會發生驚天動地的大事。”
“那兒究竟發生了什么?”
“有個叫拜上帝會的組織。”
“拜上帝會?”理文覺得在什么地方聽說過。
據說上帝是天上的神,既然稱為“拜上帝會”,想必是個宗教團體。“上帝”這個詞在中國古籍里也常出現。就當時人的感覺來說,這個詞有些道教的味道。可是,據說拜上帝會和道教毫無關系。會里的人公開聲稱,廟宇里供奉的帶胡子的神像不過是木偶,甚至到處都有他們搗毀神像的傳言。有人簡單地說拜上帝會就是天主教,但也有人說擺出一副了解內情的樣子,說他們只是把天主教改頭換面用以賺錢而已。這些是理文在上海聽說的。
鴉片戰爭后,外國傳教士明顯活躍起來。他們傳教熱情很高,可惜信教的人并未快速增長。有些品行不端者為了與外國人做生意才當了基督教徒。當時中國人對洋人十分反感,那些接近傳教士的人,大多都會遭到白眼。理文在上海時常與知識分子討論基督教的問題,他認為基督教要想掌控中國人的心是很難的。不過他也深知基督教勢力強大,金順記同洋人接觸多,關于基督教,他自然比尋常人知道得多些。英國、美國、法國以及荷蘭,都信奉基督教。來日本之前,他稍稍調查了下日本的情況,知道日本也常發生“切支丹殉教”[7]的事。姑且不說這些,總之他對基督教在中國的前途是持否定態度的,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是從事不光彩的鴉片貿易的洋人都是基督徒。
“拜上帝會可不一樣。”一個青年為了和連家做生意,從廣州跑來上海時曾這樣告訴理文。那是理文第一次聽說“拜上帝會”。
理文問有何不同,對方回答:“他們都是中國人,和外國人沒一點關系。”
“果真如此,或許會成為一股力量。”理文曾經這樣認為。不過他雖關注過拜上帝會,但畢竟身在上海,離廣東遠,無法更深入地了解。去琉球前,他順便去了香港和廣州。當時他聽說,有個奇怪的宗教團體頭目被當局逮捕,關進了打牢,據說那個團體信奉的是基督教等外國宗教。“咦?會不會是上次廣州來的那個青年說的那個什么會呀?”他以前不夠上心,早把名稱忘了。
從香港到廣州,理文接觸的人都不曾注意過這個宗教團體,自然也弄不清狀況。有人只說:“反正是在鄉下瞎搞亂搞,誰知道呢!”于是理文覺得這個拜上帝會恐怕成不了氣候。然而此時他卻從哥哥口中聽到了不一樣的評價。哲文是藝術家,不是實業家,但他思維極其敏銳,瞬間判斷事物的能力比誰都強。
“這個拜上帝會,去年不是被當局搜捕了嗎?”
“嗯,有這事。一個叫馮云山的人被抓了,不過很快就被釋放了。”
“哦,果然是同一件事。”
“你聽說過?”
“嗯,在廣州聽說過。是我去琉球之前。五月左右吧。”
“馮云山被釋放,其實還和西玲有關。”
“和西玲有關?”
“怪吧?一個尼姑竟然去幫助基督教的人。不過這才是真正的西玲啊。”
哲文說,創立拜上帝會的中心人物是洪秀全和馮云山,根據地是桂平縣紫荊山一帶,山腳有個村子叫金田村。在當地的保守士紳來看,他們的活動確實是胡作非為。他們否定偶像并付諸實踐,在象州甘王廟當著官吏的面毀了神像,還在廟壁上寫了痛罵廟中神靈的詩。
桂平縣有個鄉紳叫王作新。他在當地組織了團練——類似于日本的“自警團”。他們聲稱由自己來保衛家鄉,但費用要當地的士紳來出,這個組織因此不知不覺具有了士紳私人軍隊的性質。王作新指使手下以“蠱惑鄉民,結盟拜會,踐踏社稷神明”為名逮捕了馮云山。但拜上帝會也是有組織的,成員曾亞孫、盧六很快把馮云山搶了回來。這是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事。
王作新把此事上告到桂平縣,訴狀上說拜上帝會成員已達數千人之多。馮云山也向桂平縣呈遞了狀子,反駁道:“教人敬天,反被人誣控。廣東之禮拜堂懸掛兩廣大憲奏章,并有皇上之御批……”
鴉片戰爭后締結的條約中都有允許基督教傳教自由這一項,皇帝雖不滿意,也不得不予以承認。廣東的禮拜堂兩側都掛著公文,并由兩廣總督向百姓解釋。皇帝批準的公文,誰也不得破壞。這對禮拜堂來說,真是最好的護身符。
桂平知縣王烈感到不好辦。王作新訴狀中提到“拜上帝妖書”,但這是皇上批準的。在這和平寧靜的鄉村小題大作,王烈很不高興,于是打回了王作新的訴狀,批駁道:證據不足,不作切實調查,不得輕率從事。王作新不甘心,再次動員團練抓了馮云山和盧六,送到了巡檢司。兩人被關進大牢,但鄉間衙門也不敢擅做主張。洪秀全為了營救馮云山去了廣州。馮云山被扣上了“意圖謀反”的罪名,事情弄大了,地方衙門是解決不了的,到兩廣總督所在的廣州去,通過上層進行營救或許還有些用。
“是西玲讓洪秀全這么做的,還有到廣州后怎樣接近上層,西玲也都詳細地交待了。”哲文道。
“她這個人還是老樣子,不做點什么總不安心。”
“有段時間好像老實了一點,但最近常傳出她和拜上帝會有關的消息。”
“父親不放心,所以才讓哥哥去的吧?”
“不錯。行了,這事不說了。理文,去外面走走吧?”哲文提議道。
“好。”理文也正想呼吸一下外面的空氣。兄弟倆這一點倒是相通的。
說是“外面”,當然還是在唐人坊之內。夜空中云層密布,街旁的窗子里漏出點點燈光,寂寞而荒涼。最初唐人本部屋有二十棟建筑,可容五千人。人數過萬時,每間屋子都擠得滿滿的。后來,有些因陳舊損壞而不能使用的就拆除了,基本上沒建過新的。現在只有七棟了,而實際使用著的不過五棟。坊內的空地很寬闊,使人不由得產生衰落和荒蕪之感。
“有點寂寞吧?”理文道。
哲文笑道:“今天四號船來了還稍微熱鬧點了。”
微風輕拂。農歷六月已經是盛夏了。云縫中微微透出一點月光。
哲文停下腳步環顧四周,突然道:“一個人也沒有。”
“是呀,上了岸,都在屋子里舒舒服服地躺下了吧。”
“有些話想在沒人的地方跟你說。”
“在哥哥的屋子里不能說嗎?”
“那兒雖寬敞,可同一個屋頂下有幾十個人。難保沒有政府密探,或者為了買賣方便而去告密的家伙。”
“政府?”
“雙方的政府。幕府和清政府都想了解各種情況。他們想了解什么,咱們管不著,但咱們有些事可不能讓他們知道。”
“哥哥是覺得有人在監督你?”
“是啊。糟糕的是剪了辮子。”哲文又用手摸了摸腦袋。盡管對外說是出家,但剪辮子這件事本身就被當局視為危險的信號。哲文似乎有點后悔,但他這個人一旦打定主意就會一條道走到黑。他再次朝四周看了看,然后問道:“你乘四號船直接回上海嗎?”
“我還沒決定,也許直接回去,也許在薩摩下船,經琉球去福州。我還需要仔細考慮一下。”
“怎么樣都行,總之,你一回國就去廣西。這不是我的意思,是父親的意思。”
“去廣西?是跟拜上帝會有關嗎?”
“剛才在房里說了,拜上帝會或許會改變世道,父親對此深信不疑。”
“你這么確信?”
“我確信。”
“這么一個基督教組織,能奪取天下……”理文說到這里,也朝四周看了看。
“能不能奪取天下還不敢說。不過,我確信一定會震撼天下,改變世道。”
“哥哥來日本前見過父親嗎?”
“沒有,是溫章跑來蘇州告訴我父親的意思的,他還叮囑說他是原封不動地口授父親的話。”
溫章是協助連老爺子創建金順記的大掌柜溫翰的兒子,今年不到五十,但已繼承其亡父的地位,擔任金順記的大掌柜。這人絕對可信,他說是口傳父親的話,就一定千真萬確。
“廣西是中國的邊境之地,從這樣的地方開始撼動天下?幾千人在偏僻的鄉村不算少,但從全國來看,就……”理文歪著腦袋,感到懷疑。
“薩摩也遠離日本的中心,是最南端的邊境……看來父親是希望這些邊境力量能改變這兩個國家啊!”
“會有怎樣的變化呢?”
“不管怎樣變化,父親認為總歸要比現在好。”
“是呀!”在理文看來,父親在本質上是個舊事物的破壞者。
“剛才我在屋子里說去桂平西玲那兒是請安問好的,其實不是,我是按照父親的意思,向西玲傳達今后的方針的。”
“今后的方針?”
“對。馮云山已經被釋放,應該暫時冷靜一下。今后情況會更復雜,西玲一個人應付不了。把你派去和拜上帝會保持密切聯系,讓她暫時別和他們接觸。”
“要我和拜上帝會保持密切聯系?”
“沒錯,所以你必須去廣西。雖然不急于一時,但也不能太慢了。”
“薩摩的工作怎么辦?”
“薩摩和琉球的工作我來接管。我剪掉辮子,其實就是這個目的。再休息幾天,就得交接工作了。”
“父親還是和過去一樣!”
不滿和滿足兩種情緒在理文心中交替著。他不滿的是自己就像棋子,被父親隨意驅使,明明自己已經是二十九歲的成人了。但他這次能夠承擔重大任務,他對此倒是很滿意。拜上帝會能不能奪取天下姑且不論,起碼父親預計它會震撼整個中國。父親要他和這樣一個組織保持“密切聯系”,恐怕既指經濟上的資助,也指為這個組織出謀劃策。理文暗想,父親最初可能是想把這工作交給哥哥的,但一想到任務太重就改變了主意擔。雖然薩摩和琉球的工作也很艱巨,但已經由他踏出了一條路,和島津的負責人談判,應該還不至于難住畫家哥哥。
遠處傳來女人嬌滴滴的說話聲,夾著三味線的琴聲。風不知何時停了。理文渾感到渾身都在冒汗,不只是因為風停了,還因為接到新任務情緒激動。
“哥哥也要把廣西的工作交接給我啊。”
“父親如今應該在廈門,你可以到那兒去問他。至于廣西當地的情況,西玲很清楚。對了,來日本前在寧波聽溫章說父親似乎有點擔心。”
“擔心什么?”
“首先是父親的莫逆之交、人稱‘天下大俠’的王舉志先生已經不在了,因此父親和各地幫會組織的聯系比以前弱了。”
“是嗎?父親是要把各個幫會組織和拜上帝會拉到一起吧。”
“其次,洪秀全為營救馮云山去了廣州后,一直沒回紫荊山。馮云山也跟著去了廣州。盡管這兩件事并不相干,但父親擔心兩巨頭都不在會出問題。”
“想來當地的大地主和當權派早就盯上他們了,說不定會趁著兩巨頭不在把他們搞垮。”
“有這方面的擔心,不過留在紫荊山的頭目中也有能干之人。有個叫楊秀清的干得很出色。父親擔心的或許是這些留下的人太出色,以至于一個系統變成兩個系統……總之,廣西那邊的工作是非常艱巨的。”
哲文正低聲說著話,突然被一個尖細的女人的聲音壓住了:“誰?是哲文先生嗎?剛才我回到您那兒去了。”袖若在打著燈籠的侍女陪伴下朝他們走來,燈光照在她腳下,她的腳步有些搖晃。
哲文匆忙在理文耳邊道:“我再跟你說幾句。拜上帝會一開始就不是一般的宗教團體,他們早就決心要造反,起碼上面的頭頭是這樣打算的。換言之,你也要去造反。你要有思想準備。”
“明白了。沒有什么可怕的。”
“好!好!”哲文邊說邊從弟弟身邊走開,迎著袖若道,“你真快呀!”
“到各個屋子里去只是盡盡人情。卻被他們灌了不少酒。”
“再上我屋里坐坐吧,再喝點兒,反正時間還早。”哲文回頭對弟弟說道,“回屋去,咱們痛痛快快地喝幾杯。”
那一點微亮的月光,又被云層遮蓋了。
注釋
[1]當時日本稱中國開往日本的船為唐船。
[2]明治維新的重要人物。
[3]1坪約合3.3平方米(用于臺灣地區)。
[4]中國1尺約為33厘米。日本江戶時代1尺等于18.89厘米,7尺等于1.3223米。日本明治維新時代1尺等于30.3厘米,7尺等于2.121米。
[5]日本江戶后期的歷史學家、儒學家、詩人,著有《日本政記》《日本外史》等。
[6]中國(除臺灣)1斤等于500克,日本1斤等于600克。
[7]切支丹是基督教的日本譯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