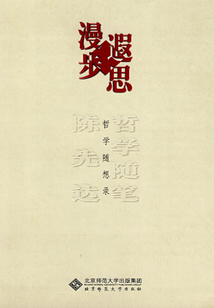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 1評論第1章 上篇(1)
宗教·神話·哲學
神話是人在幻想中對自然力的改造。宗教是人對自然力的崇拜。哲學則是人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揭示。神話不是迷信,因為人們意識到神話的非現實性。宗教是迷信,因為它把自然力人格化,對自然力采取崇拜的態度,認為自然背后有一種超自然的力量。
神話是人話。它是人按照人的模樣創造的另一個世界。人對神的崇拜與人不可分,或與收割有關(對風雨雷電、土地、太陽的神化),或與婚姻有關(愛神),或與生死有關(死神),或與戰爭有關(戰神)。人正是根據神對人自身的價值分為好壞善惡并采取相應的態度。神的生活與人的生活一樣,有男有女,有兒有女,有悲歡離合,有恩怨愛戀,只不過是具有無窮的威力而已。而宗教則不然。一神教的神是至高無上的、唯一的。非一神教的神雖不是唯一的,但也是超凡入圣與人迥然不同的。它具有人的一切優點,但又凌駕于人之上從而成為與人對立的存在物。
神話可以鼓舞人的斗志,提高人與丑惡現象斗爭并戰而勝之的信心。宗教不同,它削弱人的力量,使人服從超自然的力量,從而貶低了人類自己。哲學是一種理性力量,它使人認識自然,認識人與自然的關系,從而真正發揮人自身的力量。由神話轉入宗教是必然的,因為它們都不理解自然力的本質。只要把自然力由幻想的力量變為異化的力量,就完成了由神話向宗教的轉化。哲學是與科學相聯系的,它是在人類改造自然的過程中對自然本性的探求。
哲學離人并不遠,它就存在于人的生活之中。人當然不是按照哲學生活,但生活中有哲學。人的一切活動,人的生活方式、行為方式、思維方式中都存在著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問題。悲觀主義者和樂觀主義者、個人主義者和集體主義者的生活方式、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顯然是不一樣的。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擺脫哲學,問題只是自覺的還是自發的哲學、系統的還是零碎的哲學。我們之所以提倡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就是要把自發變為自覺,零碎變為系統,錯誤變為正確。
使人們對哲學產生錯誤看法的是哲學中的問題。沒有問題當然沒有哲學。哲學中的問題并不是來源于驚奇,而是來源于實踐的探索;哲學中的問題并不是超時代的永恒的問題。哲學之所以是時代精神的精華,正因為它解決的是時代的問題而不是超時代的問題。在哲學史上哲學由本體論到認識論再到方法論的研究重點的轉移,就是因為問題的轉移。而問題轉移的原因在于時代的確有解決這些問題的需要。當然,哲學中有些問題好像是永恒的,例如世界的本質問題、必然性和偶然性問題、人的本性問題、存在和思維的關系問題,等等,其實這些問題之所以不斷重復,是因為它的普遍性和抽象性以及重要性。但是不同時代不同條件下的哲學家根據自己時代所達到的水平給以回答,從而推進對這些問題的理解。形式上是問題的無休止的爭論,實際上是問題的推進。
不要回錯了家
人都有個家。或者是已有家,或者是將有家,至少是有過家。家,不是生命的驛站,對中國人來說,他生于斯死于斯,歡樂與共,禍福相依。在外面旅途疲勞、風餐露宿的人回到溫馨的家,泥爐紅火,熱茶熱飯,兒女相依,是何等高興。
人們只知道肉體的奔波需要休息,可知道靈魂也需要休息?一個人如果羈于名利,終日孜孜以求,用盡心機,不也很累嗎?靈魂也需要個家,需要有個安身立命之所。這個家,這個安身立命之所,就是哲學。
但是,哲學是多種多樣的。也就是說,家是多種多樣的。抽象地說,宗教可以安身立命,唯心主義也可以安身立命,不過這是一種消極的人生哲學,它雖然可以使人得到某種心理平衡,緩解心靈的痛苦,但代價是巨大的。它使人以消極的態度對待生活,在家如出家,入世如出世,無論對國家、對家庭、對個人都未盡到責任,我說這叫回錯了家。
有人公然攻擊馬克思主義是異族文化,破壞了中國人的安身立命之學,在他們看來,只有儒家學說才是安身立命之學,所以大力鼓吹在中國復興儒學。我們并不否認,中國傳統文化其中包括儒家學說的人生哲學以及道家有關養生的理論確有可取之處,應該研究。但在社會主義國家,我們當然要提倡無產階級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我們認為:這種立場、觀點、方法,不僅能使我們正確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而且能正確面對人生。不管順境逆境、得意失意,都能處之泰然。“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這個“放眼量”就是一種人生境界,一種積極的向前的思想境界。誰說馬克思主義不能安身立命?它完全能夠。但它不是從個人主義出發,而是把個人放在群眾之中,放在國家民族之中,以唯物辯證的態度正確對待生與死、樂與苦、幸福與痛苦,這才真正為自己的心靈找到了家。
明白人與明白學
做人要做明白人,不要做糊涂人。
什么是明白人?明白人是能夠清楚地知人處世處事,不被“馬屁精”高帽子弄得糊里糊涂的人。而要做到這一點,首先要有自知之明。《道德經》說,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可只有自知才能知人。
《鄒忌諷齊王納諫》講的就是明白人的故事。齊王的首相鄒忌身高八尺,美風姿,非常漂亮。他早晨起來照鏡子,左顧右盼得意得很。他問妻子:“我與城北徐公孰美?”妻子回答說,你太漂亮了,徐公怎么能和你比呀。他問妾,問他的客人,都是同樣的回答。鄒忌是個明白人,躺在床上想了又想,終于弄明白了這個道理:我的妻子夸我,是出于私情偏愛;我的妾夸我,是怕我疏遠她;客人討好我,是為了從我這里得到好處。
可要做明白人不容易,必須去蔽,即去掉各種使自己受蒙蔽的東西。認識的主體是人,可人在認識事物時會受到各種蒙蔽。名可為蔽,利可為蔽,親可為蔽,疏可為蔽,如此等等。所以,要正確認識必須解蔽。戰國時的大思想家荀子就寫過著名的文章《解蔽》,他說人之所以不明白,是因為蔽太多,即為片面性認識所局限,“欲為蔽,惡為蔽,始為蔽,終為蔽,遠為蔽,近為蔽,博為蔽,淺為蔽,古為蔽,今為蔽”。故荀子特別強調要解蔽。
要解蔽,必須有正確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即反對主觀主義和個人主義。一個剛愎自用、財迷心竅的人,處處是蔽。因此要學哲學。哲學之所以是明白學,正因為它的最大功效是去蔽。唯物主義去主觀武斷之蔽,辯證法去片面之蔽,共產主義人生觀去各種利己主義之蔽。我們要記住毛澤東的這句話: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
哲學與自然科學
哲學不能脫離自然科學,但不同于自然科學。哲學不是關于某一領域某一對象的知識,而是普遍性的判斷。它不僅講規律,而且講意義,即著眼于這個規律性判斷對人的意義。自然科學的內容是共同的,它沒有個性,也不能有個性。而哲學是哲學家的觀點和體系,它不僅包含共同的東西,而且凝結著哲學家個人的特殊的人生體驗。沒有個性,就沒有哲學家。但這決不是說,哲學純系個人意見,只是就體系而言它具有個性,就其內容而言,凡屬真理性的內容決不僅限于個人,而是具有普遍性。所以認為哲學純屬個人意見的說法是片面的。
哲學的水平依存于科學水平,但又有相對獨立性。按科學水平來說,我們當代一個中學生的科學水平,數理化方面的知識,可能比古代的哲學家,例如老子、莊子、柏拉圖、蘇格拉底等,要多得多,可在哲學智慧方面是無法相比的。中學生的自然科學知識是我們時代的常識,而古代哲學家們的思想是人類的智慧,它不僅是他們那個時代的高峰,而且超越自己的時代,對于整個人類都有照耀作用。
哲學和自然科學的區分是不能抹殺的。用自然科學的觀點來衡量哲學是不對的。但不能把哲學和自然科學看成兩個截然不同的領域。新儒家們過分強調哲學的非科學性,強調哲學與科學、知識與非知識的區別,強調哲學的功效不在于增加知識,而在于提高人的境界,認為哲學是一種純形而上的追求,是一種道德的境界。可是哲學一旦脫離自然科學,消解哲學思維中的科學精神,就會陷入唯心主義的困境。所以我們還是應該提倡哲學與自然科學的聯盟、結合,把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使哲學成為有知識的智慧、有智慧的知識。
境界
道,是中國古代哲學的基本范疇。它的一個含義是規律,天道是宇宙規律,人道是社會規律;另一個含義是境界。得道是達到一種境界,是從道中達到的自由。可見,境界并非是人的純主觀體驗,而是對道即規律的把握。
恩格斯說,自由是對必然性的認識。這不僅是指人的行動的自由,而且是指人所達到的自由境界,隨心所欲不逾矩,就是這種境界。人的自由境界不可能是超規律的。違背規律得到的只能是懲罰,是寸步難行。莊子超生死的人生境界,鼓盆而歌的通達,是因為他認識到死的必然性,所以能順其自然。順其自然如果不以規律為依據就是怯懦,就是奴性。
智慧是哲學的生活化、實際化,所以智慧就是被運用于生活中的哲學。一個人不管讀了多少哲學書,要是除了條條而外一無所能,不明智,不通達,不大度,是不能妄稱智者的。
科學的發展是階梯式的,一個臺階一個臺階上,后來者超過前代人。哲學不一樣,它的發展是波浪式的,有高潮有低潮。例如,中國春秋戰國時的諸子百家,魏晉的玄學,宋明的理學,以及明清之際的思想家們,對哲學做出了自己的貢獻,在中國思想史上處于不同的高峰期。
知識與智慧
知識是智慧的基礎,智慧是知識的綜合和升華。荀子在《正名》中說過,知有所合謂之智。沒有知識的智慧是空論,是假大空。不包括智慧的知識是假知識。知識與智慧是相互依存的。
中國的哲學發達,所以中國人的智慧也是超群的,許多西方學者是非常稱贊中國人的。法國哲學家伏爾泰就說過,中國人在所有的人中是最有理性的;萊布尼茨也說過,如果讓哲學擔任裁判的話,一定會把金蘋果獎給中國人;當代西方著名的學者李約瑟在《中國科技與文明》中認為,全世界都認識到他們深受來自中國的恩惠。
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瑪雅的文化都是令人嘆為觀止的,但都發生過中斷,有的已經消失和隕落,唯獨中國文化經過多少次戰亂和朝代更迭而沒有中斷,如長江大河滾滾向前,給全世界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產。我們應該珍惜這份遺產,很好地繼承和發揚它。
我們依靠什么
有的學者認為,迄今為止在西方社會中存在非道德主義以及反道德主義,但也存在著強大的宗教勢力,只要基督教信仰存在一天就會給社會提供一種安定力量,同時也是對抗反道德主義的力量,宗教是西方重要的精神支柱。中國之所以發生某些道德滑坡現象,是因為人們沒有了宗教信仰,脫離了數千年的“信天事天法天”的宗教信仰,從而找不到維系道德、維系人心、維系社會的安定力量。
我們并不否認宗教的某些積極功能,但社會主義國家的精神支柱不可能是宗教。我們當然重視社會主義道德,但是維系道德的力量并非宗教。對鬼神的信仰、對來世的憧憬和對天堂的向往、對輪回和地獄的恐懼,同社會主義道德是不可能結合的。因為社會主義道德的本質不是簡單的個人的善行以及從善行中得到的回報,而是集體主義原則,它是同徹底地消滅剝削、消滅壓迫,同社會進步和全體人民的幸福結合在一起的。不進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不進行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的教育,社會主義道德是不可能確立和鞏固的。
智慧與痛苦
1944年11月,維特根斯坦在給他的學生馬爾康姆的信中說:“假如你不想受苦,你就不能正確思考。”智慧當然有可能給人帶來某種痛苦,例如在封建統治下某些思想家為社會、為統治者所不容,遭受政治迫害,為真理而犧牲。盡管并不是在任何社會中都是如此,可是思考本身作為一種窮根究底的研究,往往是痛苦的,它往往使人犧牲健康、休息、家庭,沉湎于思索,特別是對于社會問題的思考,懷著焦慮和憤怒更是痛苦。
哲學若不想流于空談,必以追求真理為目的。哲學不是文字游戲,不是思辨,不是概念的戰爭,哲學應該求真,這一點連維特根斯坦也承認,他說,研究哲學如果給你的只不過是使你能夠似是而非地談論一些深奧的邏輯之類的問題,如果它不能改善你對日常生活中重要問題的思考,如果它不能使你在使用危險的詞句時比任何一個記者更謹慎,那么,它有什么用?
宗教是痛苦的避難所,它是人處在極端痛苦時的安靈劑。可哲學不是痛苦的避難所,而是通向智慧的大門。哲學與宗教的不同正在于它是積極的探索。宗教是逃避痛苦的痛苦,而哲學是通向智慧的痛苦。
有的哲學家把痛苦說成是存在的必然產物,在他們看來,存在就是痛苦。《道德經》中說: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如果存在就是痛苦,那人類永遠走不出痛苦,因為人本身就是一個感覺實體。這樣來理解痛苦就把痛苦本體化了,完全降低了痛苦在人類探求智慧中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