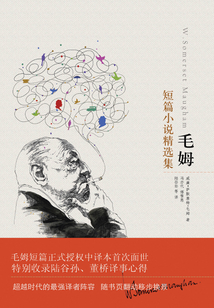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 13評論第1章 雨(1)
馮亦代搖譯
差不多是上床的時候了,到他們明天清晨一覺醒來,眼前就會看到陸地。麥克費爾醫生點燃了煙斗,探身靠在船欄上,在九天之上尋找南十字星座。經過在前線待了兩年,一處早該愈合的傷口,竟久久不能復原,他很樂意能在阿皮亞安安靜靜地至少住上十二個月,而且就在旅途之中,他已經感到好得多了。因為有些旅客第二天要在帕果帕果下船,晚上他們跳了一會舞,至今他的耳鼓里還敲打著自動鋼琴刺耳的鍵音。但是甲板上終于安靜下來了。不遠處,他看見自己妻子正和戴維森兩口子坐在長椅上談天,他就踱步過去。當他在燈光里坐下來,脫掉帽子,你便可以看到他一頭深色的紅發,頭頂有一塊已經光禿禿了,紅潤而滿布瘢痕的皮膚輝映在紅發之間;他年已四十,瘦骨嶙峋,一張干癟的臉,刻板而迂腐;說起話來,滿口蘇格蘭腔,聲調緩慢低沉。
在麥克費爾一家和海外傳教士戴維森一家之間,產生了一種同舟的情誼,這種情誼如果說是由于任何共同的愛好,倒不如說是由于氣質上的近似。他們主要的聯系是看不慣那些白天黑夜都在吸煙室里玩撲克或橋牌和酗酒的人們。麥克費爾夫人一想到他們夫婦倆居然成為戴維森家唯一在船上愿意交往的人,不免有些受寵若驚,甚至醫生本人,雖然有些靦腆卻并不愚蠢,也有一星半點兒意識到這種禮遇。只是由于他稟性好辯,因此夜晚在他們那間艙房里,總讓自己對傳教士兩口子吹毛求疵一番。
“戴維森夫人說,要是沒有我們,她簡直不知道怎樣度過他們的旅程,”麥克費爾夫人說,一面麻利地收拾干凈她的假發,“她說在船上這伙人中間,只有我們才是他們愿意結交的。”
“我并不以為一個海外傳教士該是這樣一位大亨,居然擺出這副臭架子來。”
“這并不是擺臭架子。我完全理解她說話的意思。戴維森兩口子若是混在吸煙室里那批粗坯中間,就太不恰當了。”
“他們所信奉的宗教創始人可并不這樣孤芳自賞。”麥克費爾撲哧一笑。
“我不知道曾經告訴你多少回不要拿宗教開玩笑,”他妻子回答,“我不該喜歡你這種德性的人,亞歷克。你從來不看別人的優點。”
他用那雙灰藍色的眼睛,斜瞥了她一眼,但是沒有作答。經過多年夫妻生活,他學會了得到和睦的最好辦法,就是讓他妻子講完最后一句,不再回嘴。他比她先脫掉衣服,就此爬上上鋪,躺下來看一會兒書入眠。
第二天一早,他走上甲板,船已經近岸了。他用貪婪的眼光注視著這塊陸地。眼前是一條狹長的銀色沙灘,后面緊接著是一抹隆起的草木茂盛的山岡。椰子樹林又密又綠,一直伸展到海濱,樹叢中可以看到點點薩摩亞人的草屋;這里那里點綴著一座白色閃耀的小教堂。戴維森夫人走來站在他的身邊。她一身黑衣服,頸間戴了條金項鏈,下面搖晃著一個小小的十字架。她身材瘦小,褐色而無光澤的頭發梳攏得十分平整,在一副夾鼻眼鏡后面有雙鼓出的藍眼珠。她有張瘦長得像綿羊的臉,但是毫無蠢相,反倒是極度的機警;有種飛鳥似的迅捷動作。她最最令人注意的是她的語調,高亢,刺耳,一點也不婉轉;聽進耳朵里是種僵硬單調的聲音,攪動得神經不安,一如風鉆的無情喧囂。
“這里對你說來一定像是家鄉。”麥克費爾醫生說,帶著淺淺的勉強的笑容。
“我們那兒是群淺水的島嶼,你知道,跟這兒不一樣,是珊瑚島。這兒是火山島。到我們那兒還有十天的航程。”
“在這些地方,簡直像是家居鄰近的街道。”麥克費爾醫生打趣說。
“哎,這樣說法不免有些夸張,但是在南海一帶,人們對于遠近的看法是有些不一樣。至少你說的也對。”
麥克費爾醫生輕嘆一聲。
“我很高興我們幸而不是駐在這兒,”她繼續說下去,“他們說在這塊地方工作很困難。郵船的來來往往使人安不下心來;其次還有設在這兒的海軍站;這對于當地土人很不好。在我們那一區里沒有這兒那種困難可以讓我們埋怨的。也有一兩個生意人,當然啰,但是我們注意使他們行動規矩,如果他們不守規矩,我們就弄得他們受不了,寧愿永遠離去。”
她正一正鼻上的眼鏡,帶著一種冷酷的眼光凝視著這個蔥蘢的島嶼。
“對海外傳教士說來,這兒簡直是白費氣力的工作。我對上帝真是感恩無窮,至少我們不是在這塊地方。”
戴維森的教區包括北薩摩亞在內的一群小島;這些小島分散得很廣,因此他經常要坐小劃子才能到達遠處的島上。在他遠行的日子里,他的妻子就留在大本營主持海外教會的工作。麥克費爾醫生一想到她必然會使用的管理方法的效率,不免感到心里一沉。她說到當地土人的腐化墮落,其語調之激昂恐怖,簡直無法使之平靜。她知羞識恥的敏感有獨到處。早在他們相識初期,她就對醫生說過:
“你知道,我們初到島上時,這些土人的婚俗,使我們大吃一驚,簡直無法向你敘述。我會告訴麥克費爾夫人,她會轉告你的。”
接著,他便看見自己妻子和戴維森夫人的帆布躺椅并在一處,熱切地咕噥了差不多有兩小時之久。當他為了活動活動四肢,而在她們面前來回漫步時,他曾聽到戴維森夫人激動的耳語,一如山間遠處的洪流,他也看到自己妻子張大了嘴,臉色慘白,顯然她為這一驚人的經歷而感到一種享受。到了夜晚,在他們的艙房里,她把所聽到的一切,用壓低的聲調向他復述了一遍。
“哎,我說的怎么樣?”第二天早上戴維森夫人喊著,興高采烈,“你曾經聽見過比這更可怕的事嗎?你不會懷疑為什么我不親口告訴你了吧,你信了吧,雖然你是位醫生。”
戴維森夫人端詳了一下醫生的臉色。她戲劇性地切望看到自己預料中的效果。
“你能猜想到我們初到該地時的心情低沉嗎?你簡直不能相信我對你說在任何一處村莊里也不可能找到一個好姑娘。”
她選用了“好”這個詞的嚴格的專門意義。
“戴維森先生和我討論了一番,我們決心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禁止跳舞。土人對跳舞簡直發了瘋似的。”
“我年輕時自己就不反對跳舞。”麥克費爾醫生說。
“昨晚上你要求麥克費爾夫人同你跳一圈時,我就猜想到了。我認為男人和他自己妻子跳舞并沒有害處,但她不肯陪你跳,倒使我釋然了。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必須嚴于克己自持。”
“在什么情況下?”
戴維森夫人從她的夾鼻眼鏡后面飛了一眼,卻沒有回答他的問話。
“但是在白人中間,事情就截然不同,”她說下去,“雖然我要說自己同意戴維森先生,照他說來做丈夫的怎么能站在一旁眼看自己的妻子抱在別個男人的臂圈里,至于我自己,自從結了婚,我從來沒有跳過一步舞。可是土人的跳舞是另一回事。跳舞不僅本身不道德,而且肯定導致傷風敗俗。無論如何,感謝上帝,我們撲滅了跳舞,我想我沒有說錯,在我們這一區里已經八年沒有跳舞了。”
眼前,他們的船已經到了港口,麥克費爾夫人也來到他們一塊。船轉了一個急彎便鼓輪慢慢地向前行進。這是一處為廣大陸地所圍繞的海港,大得足以容下一隊列海軍艦只,在港口的周圍,聳起一脈懸崖峭壁,碧綠的群山。在港口附近,迎著海上吹來的微風處,是所為花園圍繞的總督府,旗桿頂上沒精打采地懸掛著一面星條旗。他們航過兩三所整齊的帶廊子的平房和一處網球場,接著就到了碼頭和一群倉庫。戴維森夫人指指停泊在離船約有二三百碼遠的縱帆船,這是載他們到阿皮亞去的。岸上有從島上各處來的一群熱切、喧囂和情緒高漲的土人,有些是為了好奇,有些則是在同去悉尼的旅客做生意;他們帶來了鳳梨、大串大串的香蕉、塔巴土布、用貝殼或鯊魚齒做成的項圈、胡椒木碗,和作戰用劃船的模型。美國水兵,整齊利落,臉上刮得干干凈凈,帶著友善的神情,在土人中穿來穿去,另外還有一小群官員。他們行李正在搬上岸時,麥克費爾兩口子和戴維森夫人一起眺望著人群。麥克費爾醫生注意到大部分小孩和少年都患有一種皮膚傳染病,畸形的潰爛像是蟄伏的潰瘍癥,他那雙職業性的眼睛,因在他經驗中第一次看到象皮病,而發出敏銳的閃光,那些男人不是有條粗胖、笨重的手臂,就是拖著一條龐大變形的小腿踽踽而行。男男女女都穿著薩摩亞圍腰。
“這是最猥褻的穿著,”戴維森夫人說,“戴維森先生認為應該用法律來禁止這種服裝。你怎么能盼望人們具有道德,而他們除了在胯間圍上一塊紅布,什么也不穿著呢?”
“這很適應當地的氣候。”醫生說,擦擦額上的汗水。
現在他們已經上了岸,雖然是大清早,那個熱勁兒壓得人透不過氣來。為群山圍繞,沒有一絲兒涼風吹進帕果帕果來。
“在我們那些島嶼上,”戴維森夫人的高亢聲調繼續下去,“我們實際上根除了這些土人穿的東西。少數幾個老人還接著穿,但就是那么幾個人了。婦女們都已穿上了齊胸的筒裙,男人們穿上了長褲和汗衫。我們初去的時候,戴維森先生在他的一份報告里寫道:這些島嶼上的居民永遠不會成為基督徒,除非十歲以上的兒童規定必須穿長褲。”
但是戴維森夫人用她那鳥似的眼光,向港口上空飄動著的成群烏云瞟了兩三次。雨點開始降下來了。
“我們得找處地方躲躲。”她說。
他們夾在人群里擠進一處白鐵瓦楞板蓋頂的大棚下面,這時瓢潑大雨已經傾瀉下來。他們在那里站了一會兒,戴維森也同他們合在一塊了。在旅途中,他對麥克費爾夫婦禮貌周到,但是沒有他夫人那樣的交際手段,老是一個人在那兒看書。他是個沉默而經常悶悶不樂的人,使你感覺到他的和藹可親,完全是基督教給他的一種任務;他稟性冷淡甚至有些乖僻。他那副長相也是絕無僅有的。他的身材又高又瘦,長長的四肢松散地連接在軀體上;兩頰深陷,顴骨出奇地高突;他帶著一種死氣沉沉的氣派,可是只要注意到他那豐滿而性感的雙唇,不免會使你吃驚。他留著很長的頭發。他那雙烏黑的眼珠,深藏在眼窩里,又大又悲愁;手指又大又長,長得很好看,給他一種毅然有力的外相。但是他最最突出的一點是給你一種有一團火在身里被抑壓的感覺,這團火含而不露卻又蠢蠢欲動。他是那種難以親近的人。
他如今帶來了不受歡迎的消息。當地正麻疹流行,在島上卡納卡人中間這是既嚴重而又致命的疾病,縱帆船上的水手中也發現了一宗這樣的病,而這條船正是要載著他們繼續航程的。病人已經上岸進了檢疫站的醫院,但是阿皮亞來電報指示,這條縱帆船除非確定沒有另外的水手傳染上病,否則就不讓進港。
“這意思是說我們不得不在這兒至少停留十天之久。”
“但是阿皮亞迫切需要我。”麥克費爾醫生說。
“這也沒有辦法可想。如果船上不再發現染病的人,縱帆船可以開航,可只能載白人旅客,所有土人的來往要被禁止三個月。”
“這兒有旅館嗎?”麥克費爾夫人說。
戴維森咯咯一笑。
“沒有。”
“那么我們怎么辦?”
“我已經同總督說過了。海邊有個做生意的有幾間屋子出租,我的建議是等雨一停,我們就到那兒去想想辦法。不要指望能舒舒服服。如果我們能有一張床,頭上有個屋頂,這就該謝天謝地了。”
但是雨沒有停下來的樣子,最后,只能張著雨傘穿著雨衣,他們出發了。島上沒有市鎮,只有一區官署建筑群、一兩家商店,在街后椰樹林和大蕉叢中,有幾處土人的居處。
他們要找的那座房子從碼頭走去用不了五分鐘。這是所兩層樓的木板房,每層都有寬敞的陽臺,屋頂是瓦楞鐵皮。屋主是個混血種,名叫霍恩,娶了個土生妻子,前后圍繞著一群孩子,第一層是鋪面,出賣罐頭食物和布匹。他領他們去看的屋子差不多空無一物。在麥克費爾的屋子里除了一張又破又爛的床、一頂千瘡百孔的蚊帳之外,就是一把快要散架的椅子和一個臉盆架。他們沮喪地環視了一周。瓢潑大雨簡直沒完沒了。
“除了拿非用不可的東西,我決不打開行李。”麥克費爾夫人說。
戴維森夫人一面打開手提包一面走進屋來。她顯得輕快敏捷,令人喪氣的環境毫未影響她。
“要是你們聽我的話,你就馬上拿出針線來補綴蚊帳,”她說,“要不你就不要想今晚合得上眼。”
“有那么厲害嗎?”麥克費爾醫生說。
“這是蚊子猖獗的季節。如果阿皮亞政府官邸請你參加晚會,你便能看到太太小姐們都把兩條腿藏在發給她們的枕頭套里。”
“我切望雨能停一會兒,”麥克費爾夫人說,“要是太陽出來,我就會有心思把這塊地方弄得舒坦一些。”
“噢,你要是等那么一天,那就得等好多日子了。帕果帕果是太平洋雨下得最多的地方。你知道,群山,那個海灣,它們招引來了水,無論如何,人們在一年的這個時候都會知道雨要來的。”
她從麥克費爾醫生身上打量到他的妻子,他們束手無策地在室內各人各站一邊,一副失魂落魄的樣子,她把嘴巴一撅。她看到一定得由自己來指揮一切了。像這類不中用的人使她不耐煩,但卻不由自主地雙手發癢要把一切安排得順理成章。
“成,你把針線給我,我給你們來補好這頂帳子,你們就去打開行李拿東西。一點鐘吃午飯。麥克費爾醫生,你最好先到碼頭去,看看你那些大件行李是不是放在干燥的地方。你知道這些土人是怎么個德性,他們很可能把這些行李一徑放在那兒任憑風吹雨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