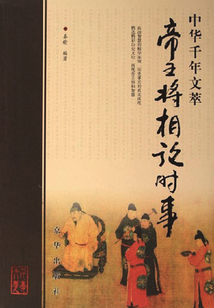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呂尚
呂尚,即西周開國功臣姜子牙。姓姜,亦姓呂,字牙,東海人。初事殷紂王,后隱于北海。在其八十高齡時,輔助周文王,號太公望。滅商后,被周武王尊為師尚父,封于齊國。《六韜》是他的一部政論和軍事論說集,以與文王、武王對話形式編寫,在政治史、軍事史上有極高的價值。以下各篇均出自《六韜》。
國務
文王問太公曰:“愿聞為國之大務,欲使主尊人安,為之奈何?”
太公曰:“愛民而已。”
文王曰:“愛民奈何?”
太公曰:“利而勿害,成而勿敗,生而勿殺,與而勿奪,樂而勿苦,喜而勿怒。”
文王曰:“敢請釋其故。”
太公曰:“民不失務,則利之;農不利時,則成之;省刑罰,則生之;薄賦斂,則與之;儉宮室臺榭,則樂之;吏清不苛擾,則喜之。民失其務,則害之;農失其時,則敗之;無罪而罰,則殺之;重賦斂,則奪之;多營宮室臺榭以疲民力,則苦之;吏濁苛擾,則怒之。故善為國者,馭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見其饑寒,則為之憂;見其勞苦,則為之悲;賞罰如加于身,賦斂如取己物。此愛民之道也。”
六守
文王問太公曰:“君國主民者,其所以失之者何也?”
太公曰:“不慎所與也。人君有六守、三寶。”
文王曰:“六守何也?”
太公曰:“一曰仁,二曰義,三曰忠,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謀,是謂六守。”
文王曰:“慎擇六守者何?”
太公曰:“富之而觀其無犯,貴之而觀其無驕,付之而觀其無轉,使之而觀其無隱,危之而觀其無恐,事之而觀其無窮。富之而不犯者,仁也。貴之而不驕者,義也。付之而不轉者,忠也。使之而不隱者,信也。危之而不恐者,勇也。事之而不窮者,謀也。人君無以三寶借人,借人則君失其威。”
文王曰:“敢問三寶?”
太公曰:“大農、大工、大商謂之三寶。農一其鄉,則谷足;工一其鄉,則器足;商一其鄉,則貨足。三寶各安其處,民乃不慮。無亂其鄉,無亂其族,臣無富于君,都無大于國。六守長,則君昌;三寶完,則國安。”
上賢
文王問太公曰:“王人者,何上,何下,何取,何去,何禁,何止?”
太公曰:“王人者,上賢,下不肖,取誠信,去詐偽,禁暴亂,止奢侈。故王人者,有六賊七害。”
文王曰:“愿聞其道。”
太公曰:“夫六賊者:一曰,臣有大作宮室池榭,游觀倡樂者,傷王之德。二曰,民有不事農桑,任氣游俠,犯歷法禁,不從吏教者,傷王之化。三曰,臣有結朋黨,蔽賢智,障主明者,傷王之權。四曰,士有抗志高節,以為氣勢,外交諸侯,不重其主者,傷王之威。五曰,臣有輕爵位,賊有司,羞為上犯難者,傷功臣之勞。六曰,強宗侵奪,凌侮貧弱者,傷庶人之業。七害者:一曰,無智略權謀,而重賞尊爵之故,強勇輕戰,僥幸于外,王者慎勿使為將。二曰,有名無實,出入異言,掩善揚惡,進退為巧,王者慎勿與謀。三曰,樸其身躬,惡其衣服,語無為以求名,言無欲以求利,此偽人也,王者慎勿近。四曰,奇其冠帶,偉其衣服,博聞辯辭,虛論高議,以為容美,窮居靜處,而誹時俗,此奸人也,王者慎勿寵。
五曰,讒佞茍得,以求官爵,果敢輕死,以貪祿秩,不圖大事,得利而動,以高談虛論,說于人主,王者慎勿使。六曰,為雕文刻鏤,技巧華飾,而傷農事,王者必禁之。七曰,偽方異技,巫蠱左道,不祥之言,幻惑良民,王者必止之。故民不盡力,非吾民也;士不誠信,非吾士也;臣不忠諫,非吾臣也;吏不平潔愛人,非吾吏也;相不能富國強兵,調和陰陽,以安萬乘之主,正群臣,定名實,明賞罰,樂萬民,非吾相也。夫王者之道如龍首,高居而遠望,深視而審聽。示其形,隱其情,若天之高不可極也,若淵之深不可測也。故可怒而不怒,奸臣乃作;可殺而不殺,大賊乃發。兵勢不行,敵國乃強。”
文王曰:“善哉。”
文啟
文王問太公曰:“圣人何守?”
太公曰:“何憂何嗇嗇:音sè,阻塞,萬物皆得;何嗇何憂,萬物皆遒。政之所施,莫知其化;時之所在,莫知其移。圣人守此而萬物化,何窮之有,終而復始。優而游之,展轉求之;求而得之,不可不藏;既以藏之,不可不行;既以行之,勿復明之。
夫天地不自明,救能長生;圣人不自明,故能明彰。古之圣人聚人而為家,聚家而為國,聚國而為天下;分封賢人以為萬國,命之曰大紀。陳其政教,順其民俗;群曲化直,變于形容;萬國不通,各樂其所;人愛其上,命之曰大定。嗚呼!
圣人務靜之,賢人務正之,愚人不能正,故與人爭;上勞則刑繁,刑繁則民憂,民憂則流亡。上下不安其生,累世不休,命之曰大失。天下之人如不充水,障之則止。啟之則行,靜之則清。嗚呼!神哉!圣人見其所始,則知其所終。”
文王曰:“靜之奈何?”
太公曰:“天有常形,民有常生,與天下共其生而天下靜矣。太上因之,其次化之。夫民化而從政,是以天無為而成事,民無與而自富,此圣人之德也。”
文王曰:“公言乃協予懷,夙夜念之不忘,以用為常。”
《左傳》
《左傳》,《春秋左氏傳》的簡稱,我國一部偉大歷史名著,也是一部歷史散文杰作。關于《左傳》的作者和成書年代,歷來有過許多爭論,司馬遷、班固均認為是春秋末年魯國史官左丘明編寫,至唐代則有人懷疑《左傳》非左丘明作,有認為是“史佚、遲任之流”,有認為是吳起,或認為是楚人作,莫衷一是。現在比較一致的看法是,作者可能是戰國初期人,根據春秋時代各國史料編寫成書,后經許多人增益。
《左傳》是先秦時代內容最豐富、規模最宏大的歷史著作。所記載歷史年代大致與《春秋》相當,同起于魯隱公元年(前722年),終年比《春秋》晚28年,即魯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全書共18萬字。按魯國隱公至哀公12個國君順序,比較系統、客觀地記述了春秋時代各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等方面的一些事件,對王室衰微、諸侯爭霸、統治階級腐朽殘暴、宗法制度崩潰,以及各種制度禮儀、社會風俗、道德觀念、天文地理、歷法時令、古代文獻、神話傳說、歌謠諺語等都有大量記敘。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真實地反映了那個時代的歷史面貌,是研究中國古代社會很有價值的歷史文獻。
介子推不言祿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將必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奸,上下相蒙,難以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誰懟:怨恨誰。懟:音duì”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
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國語》
《國語》是我國第一部按國別記事的國別史。它記載上自西周穆王二年(前990年),下至東周定王十六年(前453年),前后共538年的歷史。全書二十一卷,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卷。《國語》以“國”分目,記“語”為主,故名《國語》。其作者問題,宋以前大都認為它和《左傳》同出左丘明之手,故在
漢唐時都把其稱《春秋外傳》。宋以后學者們認定其“必非出一人之手”,可能是戰國初年一位熟悉各國歷史掌故的人,根據春秋時代各國史官的原始記錄,加工整理匯編而成。
《國語》反映了春秋時期各國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各方面的歷史,勾勒出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轉化階段的時代輪廓,表現了許多重要人物的精神面貌。雖然其在史學價值和文學成就上不及《左傳》,但仍有其獨到之處。首先,它開創了國別史的體例;其次,由于作者是以變革發展的史學觀念來看待歷史,盡管大部分是從維護正統,甚至保守的立場記錄的史事,但通過作者采擷的篇章、事件、言論,除客觀保存了大量史料外,也反映出當時處于社會大動蕩時期人們思想意識和一些進步觀點。《國語》作為優秀的歷史散文,在散文發展史上有其獨特的成就,擅長于記載歷史人物的語言和對話,語言古樸簡潔,議論時旁征博引,對話幽默風趣,口吻畢肖,頗能表現出人物的個性與精神面貌。
王孫圉對簡子
王孫圉聘于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于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于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又有藪曰云連徒洲云連徒洲:楚地方言,即云楚澤,也稱云土、云社。在今湖南、湖北境,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龜、珠、齒、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所以共幣帛以賓享于諸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寡君其可以無罪于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圉聞國之寶,六而已:圣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蔭嘉谷,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龜足以憲臧否,則寶之;珠足以御火災,則寶之;金足以御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材用,則寶之。若夫嘩囂之美,楚雖蠻夷,不能寶也。”
管仲
管仲,即管子,名夷吾,字仲或敬仲,生活于公元前725-前645年。穎上(穎水之濱)人。少時家境貧寒,后入政界,事奉齊公子糾,奉齊桓公時得到重用,拜為上卿,尊為“仲父”,輔桓公四十年,使齊成為當時強盛國家。《管子》一書并非他親著,只是托名而已,也非一時一人之作,而是匯集了從春秋到秦漢各家學說的一部政論集。
立政
國之所以治亂者三,殺戮刑罰,不足用也。國之所以安危者四,城郭險阻,不足守也。國之所以富貧者五,輕稅租,薄賦斂,不足恃也。治國有三本,而安國有四固,而富國有五事,五事,五經也。
君之所審者三:一曰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此三本者,治亂之原也。故國有德義未明于朝者,則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見于國者,則不可授以重祿;臨事不信于民者,則不可使任大官。故德厚而位卑者謂之過,德薄而位尊者謂之失。寧過于君子,而毋失于小人。過于君子,其為怨淺;失于小人,其為禍深。是故國有德義未明于朝而處尊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力未見于國而有重祿者,則勞臣不勸;有臨事不信于民而任大官者,則材臣不用。三本者審,則下不敢求。三本者不審,則邪臣上通,而便辟制威。如此則明塞于上,而治壅于下,正道捐棄,而邪事日長。三本者審,則便辟無威于國,道涂無行禽,疏遠無蔽獄,孤寡無隱治。故曰刑省治寡,朝不合眾。
右三本君之所慎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國柄;二曰見賢不能讓,不可與尊位;三曰罰避親貴,不可使主兵;四曰不好本事,不務地利,而輕賦斂,不可與都邑。此四固者,安危之本也。故曰卿相不得眾,國之危也;大臣不和同,國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國之危也;民不懷其產,國之危也。故大德至仁,則操國得眾;見賢以讓,則大臣和同;罰不避親貴,則威行于鄰敵;好本事,務地利,重賦斂,則民懷其產。
右四固君之所務者五:一曰山澤不救于火,草木不殖成,國之貧也;二曰溝瀆不遂于隘,障水不安其藏,國之貧也;三曰桑麻不殖于野,五谷不宜其地,國之貧也;四曰六畜不育于家,瓜瓠葷萊百果不備具,國之貧也;五曰工事競于刻鏤,女事繁于文章,國之貧也;故曰山澤救于火,草木殖成,國之富也;溝瀆遂于隘,障水安其藏,國之富也;桑麻殖于野,五谷宜其地,國之富也;六畜育于家,瓜瓠葷菜百果備具,國之富也;工事無刻鏤,女事無文章,國之富也。
(下略)
五輔
古之圣王,所以取明名廣譽,厚功大業,顯于天下,不忘于后世,非得人者,未之嘗聞。暴王之所以失國家,危社稷,覆宗廟,滅于天下,非失人者,未之嘗聞。今有土之君,皆處欲安,動欲威,戰欲勝,守欲固,大者欲王天下,小者欲霸諸侯,而不務得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亡。故曰:人,不可不務也,此天下之極也。
曰:然則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利之之道,莫如教之以政。故善為政者,田疇疇:音chóu,田畝,已耕作的田地。墾而國邑實,朝廷閑而官府治,公法行而私曲止,倉廩實而囹圄空,賢人進而奸民退。其君子,上中正而下餡諛;其士民,貴勇武而賤得利,其庶人,好耕農而惡飲食,于是財用足而飲食薪萊饒。是故上必寬裕而有解舍,下必聽從而不疾怨,上下和同而有禮義,故處安而動威,戰勝而守固,是以一戰而正諸侯,不能為政者,田疇荒而國邑虛,朝廷兇而官府亂,公法廢而私曲行,倉廩虛而囹圄實,賢人退而奸民進。其君子,上謅諛而下中正;其士民,貴得利而賤武勇;其庶人,好飲食而惡耕農,于是財用匱而飲食薪萊乏。上彌殘苛而無解舍,下愈覆鷙而不聽從,上下交引而不和同,故處不安而動不威,戰不勝而守不固。
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亡。故以此觀之,則政不可不慎也。
德有六興,義有七體,禮有八經,法有五務,權有三度。所謂六興者何?
曰:辟田疇,制壇宅,修樹藝,勸士民,勉稼穡,修墻屋,此謂厚其生。發伏利,輸墆積,修道途,便關市,慎將宿,此謂輸之以財。導水潦,利陂溝,決潘渚,潰泥滯,通郁閉,慎津梁,此謂遺之以利。薄徵斂,輕征賦,弛刑罰,赦罪戾,宥小過,此謂寬其政。養長老,慈幼孤,恤鰥寡,問疾病,吊禍喪,此謂匡其急。衣凍寒,食饑渴,匡貧窶,振罷露,資乏絕,此謂振其窮。凡此六者,德之興也。六者既布,則民之所欲,無不得矣。夫民必得其所欲,然后聽上;聽上,然后政可善為也。故曰:德不可不興也。
曰:民知德矣,而未知義,然后明行以導之義。義有七體。七體者何?曰:
孝悌慈惠,以養親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禮節;整齊撙詘,以辟刑戮;纖嗇纖嗇:一絲一毫。省用,以備饑饉;敦蒙純固,以備禍亂;和協輯睦,以備寇戎。
凡此七者,義之體也。夫民必知義然后中正,中正然后和調,和調乃能處安,處安然后動威,動威乃可以戰勝而守固。故曰:義不可不行也。
曰:民知義矣,而未知禮,然后飾八經以導之禮。所謂八經者何?曰:上、下有義,貴,賤有分,長、幼有等,貧、富有度。凡此八者,禮之經也。故上下無義則亂,貴賤無分則爭,長幼無等則倍,貧富無度則失。上下亂,貴賤爭,長幼倍,貧富失,而國不亂者,未之嘗聞也。是故圣王飭此八禮以導其民。八者各得其義,則為人君者中正而無私,為人臣者忠信而不黨,為人父者慈惠以教,為人子者孝悌以肅,為人兄者寬裕以誨,為人弟者比順以敬,為人夫者敦蒙蒙:“蒙”的異體字。以固,為人妻者勸勉以貞。夫然,則下不倍上,臣不殺君,賤不逾貴,少不凌長,遠不間親,新不間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凡此八者,禮之經也。夫人必知禮然后恭敬,恭敬然后尊讓,尊讓然后小長貴賤不相逾越,少長貴賤不相逾越,故亂不生而患不作。故曰:禮不可不謹也。
曰:民知禮矣,而未知務,然后布法以任力。任力有五務。五務者何?曰:
君擇臣而任官,大夫任官辯事,官長任事守職,士修身功材,庶人耕農樹藝,君擇臣而任官,則事不煩亂;大夫任官辯事,則舉措時;官長任事守職,則動作和;士修身功材,則賢良發;庶人耕農樹藝,則財用足。故曰:凡此五者,力之務也。
夫民必知務,然后心一,心一然后志專,心一而意專,然后功足觀也,故曰:力不可不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