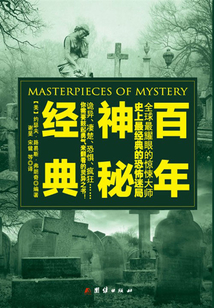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失竊的信函
第1卷
埃德加·愛倫·坡/著
錢峰/譯
過分的聰明和機靈只能是狡猾和陰險,在這個世界上,最令人擔心的事就是濫用自己的聰明才智,這會引起超出我們想象的嚴重后果。
——辛尼加
這是一八××年巴黎的一個秋天。在一個剛剛進入暮色卻大風不停的夜晚,圣·日耳曼區都諾街33號三樓,我與我的朋友舍瓦利埃·奧古斯特·杜賓正在一間非常小的圖書室里享受著我們固有的閱讀時刻。我們常常進行這樣的閱讀:一邊進行冥想,一邊叼著煙斗,或者彼此討論一些都感興趣的話題。可是這一次,我們兩個人卻誰都不說話,已經沉默了將近一個小時了。如果一個不了解其中情況的人看到我們這種狀態,一定會以為我們兩個簡直是無聊透頂,不去想些實際的事,卻只在這里吞云吐霧,弄得滿屋子都是煙味,有什么意思?事實并非如此。那個時候我正在思考之前跟杜賓談到的發生在莫格街的一樁命案和關于瑪麗·羅杰之死的奇案,而正在我總結這兩樁已經是很久之前發生的命案時,我們的房子大門突然被打開了。會是誰這么晚跑到巴黎郊區來拜訪兩個幾乎是隱士的閑漢呢?原來竟然是我們已經非常熟悉的老朋友,巴黎警察局局長C先生。當我想到自己剛才還在想有關刑事命案的問題,這會兒就來警察了,覺得真是有些滑稽,不自覺地失笑了。
我們兩人都非常歡迎突然造訪的局長先生。雖然局長先生確實有一些我們難以認同的缺點,但總的來說,他還是一個非常不錯的朋友,而且我們總是能從他這里得到很多快樂。再說,自從瑪麗·羅杰的案子告破之后,我們也已經有好多年沒有相見了。在我們的房間里并沒有點大燈,整個房間看上去有些暗,杜賓見到局長先生來了本來是想將大燈點亮的,可是在聽完局長先生此行的目的之后,他又干脆地回到了椅子上放棄了把大燈點上的打算。局長先生此行的主要目的還是緣于一件已經讓警方非常傷腦筋的公事,他希望能夠從我們這里得到一點意見,或者聽聽杜賓對其的分析。
“局長先生要是想聽我們的分析的話,”杜賓在聽完了局長先生的來意之后,停下了自己準備點燃燈芯的動作,他說,“那我建議我們還是就在這黑暗中進行我們的談話吧,因為我們在這種環境里進行思考會更加敏銳。”
“你這人毛病還真多啊,還真沒見過像你這么古怪的人。”局長先生說。所有的問題只要是局長先生認為自己無法理解的,或者是和他的思維角度不同的,他都會稱這些為“古怪”。我想,在局長先生的日常工作生活中,一定會有很多非常“古怪”的事。
“您恭維我了,其實我也覺得自己是一個非常古怪的人。”杜賓對于局長先生的評價完全沒有在意,同時又遞給了局長先生一支煙,然后將一把非常舒服的椅子讓給局長,請局長坐下詳細說說讓他感到麻煩的事件的始末。
“您大概是無事不登三寶殿吧?這次又有什么讓您為難的事?”我問局長先生,“不會又碰到了沒有頭緒的無頭命案吧?”
“你倒是很了解我,不過這次和命案沒有關系,”局長先生向我們說道,“其實呢,這本來并不是一件麻煩事,本來應該沒有什么復雜的,我們自己應該是有能力將這件事解決好的。但是,我覺得已經很久沒有聽到你們的消息了,所以突然想聽聽你們這兩位推理大師的意見。杜賓,我是很看重你的,我想你會對這件事很有興趣的,因為這可是一件非常古怪、充滿蹊蹺的事。”
“您的意思是說,這是一件非常簡單卻十分古怪的事?”杜賓總結了一下,向局長先生問道。
“嗯,我想是這樣,可又不完全是這樣,”局長先生邊思考邊回答說,“我想應該這么說,從理論上說,這件事應該是非常簡單,處理起來不會有什么麻煩的,可在實際上,它卻給我們造成了很大的困擾,讓我們為此撓破了頭。”
“那么會不會是因為你們把這件事看得簡單了?”杜賓問。
“那怎么可能!你可不能在我這兒胡說,哈哈……”局長先生說,然后大笑起來。
“我想您有些誤會我的意思,我是說,可能正是因為這件事情就是一件非常簡單的事,你們卻把它想得太復雜了,所以才會有所困擾。”杜賓解釋了一下自己剛才想要表達的意思。
“噢?還有這種說法?”局長先生笑著問杜賓。
“我的表達就這么差嗎?這不是一個很明顯的道理嗎?您覺得這很難懂?”杜賓開始認真起來。
“是!我跟你開玩笑了!哈哈哈……”局長先生看來很滿意杜賓的解釋,因此顯得很開心,“你就喜歡在我面前故弄玄虛,說實在的,這點我可是很有意見的!”
“局長先生,您還是先給我們說說到底發生了什么事吧!”我知道局長先生是一個愛跟人閑扯的人,所以趕緊把他拉回到了正題上。
“別著急,我馬上就會說到的,”局長先生說,然后他不再笑了,讓自己安靜了一下,深呼吸了一口氣,又扭動了一下自己的坐姿,顯然是一種正襟危坐的架勢,然后一本正經地對我們說道,“關于這件事的整個經過,我就簡單扼要地給你們介紹一下,不過在向你們介紹這件事之前,我想讓你們首先明白,我們討論的這件事可是屬于最高機密的,不管發生了什么,你們都不能將今晚我們所說的話泄露出去,不然,我的麻煩就來了。”
“這個您請放心,我們不是那種隨便說話的人!”我向局長保證道。
“您多慮了,如果您覺得我們是那種不可靠的人,您完全可以不跟我們討論這件事。”杜賓的回應則與他一貫的風格一樣,說話基本上不給對方留情面。這一點,局長先生當然非常清楚,因此也不以為意。
“好,這件事情的情況是這樣的,”局長先生開始講述這件事的始末,“這是一個身處高位的人跟我說的。他告訴我,在我國皇宮中被人盜走了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目前的情況是,已經基本上確定了盜走這份文件的人,也基本上知道目前這份文件是在此人的手中。”
“那么你們又是如何知道這份文件仍然掌握在小偷手上的?”杜賓插話問道。
“關于這一點,是沒有什么可以懷疑的,”局長先生說,“如果這份文件已經被這個小偷流傳到外面了,那將會造成嚴重的后果。可是,從總的情況上來看,至少到現在,一切都是正常的,還沒有出現我們預料的情況,也正是因為這樣,我們必須盡快將這份文件拿回來,不然,如果耽誤了時間的話,受到影響的將是我們的皇室。”
“您能不能再把這個情況解釋得更詳細一點。”我向局長先生提出請求。
“不如這么說,”局長似乎還是在繞圈子,“如果外面的人掌握了這份文件,那么他就能夠獲得相當大的權力,而且這項權力足可以掌控現在的政治局勢。”似乎,局長先生依然沒有向我們說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他還是用那些他非常熟練的官方辭令向我們隱瞞實情。
“您所告訴我們的信息還是無法讓我們明白這到底是怎么回事。”杜賓說。
“還沒有懂?好吧,這樣解釋吧,假如此文件被某人拿到了,實在對不起,這個人的名字我沒有權力向你們透露。”局長先生稍微進行了停頓,“很可能出現的情況是另外一個在我國有著十分崇高地位的大人物聲名狼藉。換句話說,這份文件就是一個不可告人的把柄,如果被某人得到這個把柄,那么這位大人物將會有很大的麻煩,不僅是名聲的問題,還關系到他的地位、健康,等等。”
“如果像您說的這樣的話,這份文件最重要的價值就是一個要挾工具,”我插話分析道,“那么偷走這份文件的人也應該得讓失主知道這份文件已經被他偷走了,不然他是無法充分發揮這份文件的要挾功能的。另外,敢這么做的人真是大膽啊,竟然敢偷……”
“敢這么做的人一定就是D大臣,”局長先生將我的話打斷,“因為只有他是一個做事不計后果和手段的人,就算是再難堪、再卑鄙的手段,他也使得出來。而且成功將這份文件偷走,實在讓人沒有想到他竟然還有如此巧妙、大膽的手法。其實,這份文件就是一封信,它的收信人正是我們這位有著崇高地位的大人物,而當時得到這封信時,她正在皇宮中,且周圍根本沒有其他任何人。可是就在她將信讀到一半的時候,另一位大人物闖進了皇宮,趕巧的是,收到這封信的大人物根本不想讓剛剛進來的這位大人物知道這封信的存在。在這種比較尷尬但很緊張的時刻,她已經沒有時間將這封信藏在抽屜中,幸虧她聰明絕頂,她急中生智,干脆就將這封信平攤在了面前的桌子上。而很幸運的,此信只露出一點最上方的地址,所以闖進來的那位大人物并沒有在意這封信。巧合的是,此時D大臣也前后腳地來到了皇宮中,他與剛才闖進來的那位大人物,一個站在信件主人左側,一個站在右側。此時,目光敏銳的D大臣一下子就從僅僅露出地址的一點字跡上認出了寫信人的筆跡,因此他是知道寫這封信的人的。而且,D大臣也發現了,信的主人,也就是我們的那位大人物,此時不論是言行,還是舉止,都是有些慌張的,所以他已經斷定在這封秘密信件中有信主人不想被別人知道的秘密。D大臣就跟往常一樣,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向我們的大人物將公務報告完畢,之后,他拿出一封與大人物試圖隱藏的那封信非常像的一封信,并將這封信打開,假裝閱讀,并在讀完之后將他手中的這封信放到了桌上那封信的旁邊。在緊接著的15分鐘內,D大臣又和兩位大人物談論了一些其他方面的公事,在其最后準備離開時,便虛偽地錯拿了桌上大人物并不想讓人知道存在的那封信。而信的主人雖然非常清楚地看到了這一切,可是她不能聲張,眼看著D大臣就這樣將這封信調了包,因為在她的旁邊還有另外一位她想對其隱瞞這封信的大人物。而D大臣則在那位大人物的注視下,肆無忌憚地盜取了那封信,從容不迫地離開了皇宮。”
“你剛才所說的要挾就是這個了,”杜賓轉過頭對我說,“局長先生剛才的這番講述已經把D大臣是如何讓失主知道是他盜走了這封信進而達到要挾失主的目的的整個過程,講得非常清楚了,現在你也明白了吧?”
“杜賓說得非常對,D大臣已經非常公開地向我們的大人物宣示了他已經掌握了大人物的把柄,”局長先生又補充了杜賓對我說的話,“在剛剛過去的這段時間中,D大臣靠著自己掌握著大人物的把柄而不斷對大人物進行要挾,并在這把保護傘的保護下弄出了很多不法的事。因此,大人物已經下定決心要把這個把柄拿回來,當然,所有這些事都必須秘密進行,不能公開處理。在實在沒辦法的情況下,這個大人物將這件事才交給了我來辦。”
“這是意料之中的事!如果大人物一定要選擇一個委托人,那么第一人選除了您之外,不會有第二人。”杜賓好像非常悠閑地吐了一個完美形狀的煙圈兒,然后接著說,“我想,在國內,除了您之外,恐怕再沒有這樣聰明和睿智的警探了。”
“這話你可說大了!”局長先生雖然表面上推辭,內心卻聽得心花怒放,他繼續說道,“其實我自己也覺得,大人物既然選擇了由我來辦這件事,肯定是很早就注意到了我的聰明才智吧!”
“像您這么說,”我試著分析D大臣在拿到這封信之后的心態,“現在已經能夠確定目前掌握這封信的就是D大臣,而且這封信仍然在D大臣的手上。可是D大臣至今仍然沒有將這封信公布出來,那說明D大臣所認為的公布這封信的最佳時機還沒有來到,他仍然在等待一個最好時機。所以,現在他一定已經將這封信給收好了,因為他現在最怕的就是這封能夠成為把柄的信件會不翼而飛。”
“是這樣的,”局長先生說,“我與你的想法是一樣的。因此,在此之前,我一直在想辦法在最小的影響范圍內將他的住所進行一次徹底搜查,以找到這封信。”
“這不是您最擅長的嗎?”我說,“以您的職位和權力找這樣一個借口應該不是很難吧?”
“當然,這也是我自信的地方,所以我并沒有太多擔心,”局長先生繼續進行解釋,“另外,我還得知D大臣平日的作息規律也是非常利于我搜查他的府邸的。他這個人常常夜不歸宿,而且他的住所中除了很少的幾個仆人之外,也沒有其他什么麻煩的人。那些仆人基本上都是意大利那邊的那不勒斯人,他們除了很會喝酒之外,我看不出他們有什么別的優點。另外,我還偵察到這些仆人休息的睡房離D大臣的住所還有相當長的一段距離。你們很清楚,所有巴黎房間中的密室鑰匙都在我的手上,所以進行一次大搜查并不是什么難事。最近這三個月,我幾乎天天晚上都親自去D大臣的住所進行詳細的搜查,因為我接受的這項任務可不僅僅和我個人的名譽有關,如果能夠辦好這件事,就一定能夠得到大人物的垂青,賞金肯定不會少拿。這也是我為什么沒有放棄搜查的動力所在,可是直到現在,我都一無所獲。我真是覺得D大臣是一個狡猾的家伙,他的住所已經不知道被我翻過多少遍了,可是上上下下、邊邊角角,每一個地方我都仔細搜過,始終沒有發現這封信,我真是認輸了!”
“那么會不會存在這種可能,”我猜測著說,“D大臣根本就沒有把這封信藏在自己的住所,而是早早地藏在了其他的地方?”
“這種可能性并不大,”杜賓接過我的話,“據我所知,現在皇宮中的情勢撲朔迷離。而且我聽說,其中不少陰謀D大臣本人也參與其中了,如果這些并非傳聞而是實有其事,那么他必然要把這封能夠當作把柄的信安置在一個自己可以隨時拿到手的地方,只有這樣它才能隨時被派上用場,扭轉不利的局面。我是說,這封信他一定就放在伸手可得的地方,以便不知什么時候就顯示它的作用,要不然,這封信對他來說根本沒有意義。”
“那么你說的‘隨時被派上用場,扭轉不利的局面’具體是指什么呢?”我問杜賓。
“我想D大臣除了將信公布出來以便使大人物的名譽受損這個選擇之外,完全還可能有另外一個選擇,即在某些緊急時刻,他可以將這封信銷毀而求自保什么的!”杜賓說。
“嗯,你這個說法也很有道理,”我說,“如果是這樣,那么這封信很可能并不在D大臣的住處,而是他一直隨身攜帶著。”
“對啊,”局長先生說,“可是我曾經秘密安排過兩次詳細策劃的行動,對D大臣進行突襲,并讓人假裝對其進行搶劫。在這兩次行動中,我們對其進行了很徹底的搜查,可是搜遍了他的全身上下,仍然沒發現這封信。”
“你們還是少費這勁吧!”杜賓說,“難道D大臣就是一個笨蛋嗎?以他的資歷和智慧難道會想不到你們會安排這種假突襲真搜查的手段?”
“他確實不是笨蛋,”局長先生用非常輕蔑的口氣說,“我想你們可能還不知道,D大臣還算是個詩人,不過,我一向認為,詩人和笨蛋區別不是很大。”
“您說得不錯,在我眼里,詩人和笨蛋也是一線之隔而已,”杜賓深吸了一口自己的煙斗,吐了一個大煙圈,繼續說道,“其實我也常常寫幾句并不是很入流而總是被人譏諷的詩,所以我還算不上什么詩人,不然的話,我也成了一個笨蛋了。”
“局長先生,您能不能向我們介紹一下之前去搜查D大臣住所的詳細情況?”我問局長先生。
“好的,其實在之前的搜查工作上,我們用了大量的時間,非常細致地對他的住所的所有地方進行了檢查。你們應該也有所耳聞,我們巴黎警察十分擅長那種地毯式的搜索工作,在這方面我們經驗十足。在那整整一星期的7個夜晚中,我們對所有的房間都進行了非常仔細的搜查。具體地說,從進入房間開始,首先是房間中的各種家具或者櫥柜,包括每一個抽屜,我們都進行了搜查,我們的警察都是經過非常嚴格的專門訓練的,因此如果在抽屜的夾層中有什么秘密的話,我們一定可以發現。所以,假如這封信件被D大臣藏在了抽屜的秘密夾層中的話,那它是不可能被藏住的,抱著這種想法的人一定不了解我們的能力。至于我們是怎樣識破抽屜夾層中的秘密的,其實說起來也并不復雜。所有的柜子都有自己的體積,這也就意味著它有自己的空間,所以我們準備了十分精確的規尺,通過對柜子的測量來推測柜子是不是存在一個秘密的夾層,就算只是非常微小的數據差值,我們也不會輕易放過,而正是這種細致,所以大部分夾層都能被我們識破。我敢說,至少在巴黎,想通過設計一個抽屜夾層而隱藏什么秘密的辦法是行不通的。在檢查完所有的抽屜之后,我們繼續進行的是對座椅的檢查,特別是厚厚的軟坐墊,我們檢查得尤其仔細。一般來說,我們將選擇一根又細又長的針刺進坐墊,尋找里面是否存在異物。而對桌子的檢查則要麻煩一點,我們會將桌面掀開……”局長先生將他們進行搜查的所有細節都告訴了我們,并對一些特別問題進行了說明。
“可是把桌面掀開是為了什么呢?”我不太理解他們的這一措施,因此有些好奇。
“這個你就不明白了,”局長先生回答著我的問題,“你要知道,有不少狡猾者會將一些重要的東西隱藏在桌子腿里面。他們會先將桌面弄開,然后將實心的桌子腿鑿成空的,用這個辦法來藏匿一些精小而重要的東西,最后再將桌面按照原樣裝回去,這樣藏東西一般是很難被發現的。不僅是桌子可以這么藏東西,包括床架或者床腿也能進行這樣的利用,所以對這些類似的家具,我們都進行了細致的搜索。”
“那么還可能直接從桌腿的某一部分進行這種鑿空藏物呀,再說,鑒別桌腿里面是不是空的可以聽一聽敲打它時發出的聲音即能判斷。”我說。
“那不一樣,只有將桌面移開,我們才能弄清楚里面的一切,”局長先生顯然并不完全認同我的建議,“你要知道,如果是在桌腿內部藏東西,那么是不會只放入所藏的東西的,他一定還會將周圍塞滿諸如棉花之類的東西隔音,同時這些東西也能保護所藏的物品不至于產生異狀。另外,在對于D大臣住所的搜查問題上,我們進行得非常隱秘,所以要盡量避免制造一些不必要的聲音,以防驚動他人!”
“但如果像您所說的這種搜查方法,”我繼續自己的質疑,“那么要想將所有的家具都進行一次這樣的搜查恐怕是不太可能的吧?而且僅僅只是一封信而已,它可以被卷成很細的如一根粗毛衣針一樣,這樣藏起來的話,是非常不好尋找的。而且假如它被藏在椅子腿里面,難道你們還要將整把椅子全部拆開檢查嗎?”
“你說的這種情況我們也有考慮,這種情況下我們自然不會將整把椅子全部拆開檢查,”局長先生仍然充滿自信,“我們選擇的是比這更為精密和有效的檢查方法,特別是對一些家具中的死角處。對這些地方的檢查,我們一般用的是高倍放大鏡進行查看,凡是任何比較新的痕跡,都能通過這種檢查而發現。很多家具在被鏤空的過程中會留下一些可疑的痕跡或者碎屑,用高倍的放大鏡基本上都能將這些痕跡找出來,特別是一些新近人為制造的粘合的痕跡、接合處的裂縫等,根本無法不被我們發現。”
“是這樣啊!那我想你們肯定也對鏡子進行了檢查吧?”我問,“因為鏡面的玻璃與鏡框之間的木板也必然存在著縫隙,按照你們的那種地毯式的搜索自然也會注意到這些地方吧?”
“這個是肯定的,只要是在房間中的所有家具、裝潢和擺設,不管它有多么復雜,也不管它有多么簡單,所有的一切我們都進行了十分仔細的檢查。”局長先生說,“除此之外,房子結構本身我們也進行了搜查。我們先將整個建筑分成幾個部分,然后對其分別編號,目的就是不漏掉任何一處,然后對各個部分進行地毯式搜索,我們甚至將左右兩處緊鄰的建筑物也納入了我們搜查的范圍。”
“連相鄰的建筑物也進行了搜查?”我對此感到驚訝,“那你們所花費的時間肯定不少!”
“正像你說的,這讓我們花了很多精力。”局長先生說,“但是沒辦法啊,我們對這個任務十分重視,就算排除萬難也得把它辦好!”
“那么房子周圍的地面你們是否也進行了搜索?”我問局長。
“當然不會放過,但是相對來說這個部分還是比較簡單的,”局長先生回答著我的問題,“因為那里的地面全是用石磚鋪成的,我們需要做的工作就是看一看在兩塊石磚之間是不是存在著青苔或者其他被破壞的痕跡就好了。”
“是不是也已經搜查過D大臣家中存放的資料文件,或者書房中的藏書之類的?”我問道。
“這是我們重點搜查的部分,所有文件,每一包、每一捆,都由我們專業的人員進行了檢查。”局長先生說,“而且我們沒有像普通的搜查一樣,一到檢查書籍時,就把書拿出來簡單地打開或者抖一抖就行了,我們基本上是每頁都翻過的。一些書的封面,我們也都進行了非常精確的測量和觀察,如果發現其厚度異常或者有新近粘合的痕跡,那就專門挑出來進行進一步的檢查,一些值得懷疑的書頁也是通過這個辦法進行檢測的。”
“地毯下面的地板呢,有沒有進行搜查?”我問。
“這也是不會漏掉的,”局長先生非常仔細地向我們進行著描述,“我們先將地毯移開,然后通過高倍的放大鏡一一查看,尋找其中是不是有什么看上去奇怪的地方。”
“壁紙呢?”我問。
“也搜查過了,不僅是壁紙,墻壁本身我們也進行了檢查。”局長先生說。
“有沒有地下室?那里也沒有檢查出什么線索嗎?”我忽然想到了一個我們常常忽視的地方,因此問道。
“是的,檢查過了。”局長先生說。
“既然房間里的所有地方你們都進行了檢查,卻沒有發現任何線索,”我將自己對這個問題的意見說了出來,“那么我想,可能是你們在推理上出現了錯誤,那封信根本就沒有藏在D大臣的住處。”
“對啊,我覺得你說的可能是對的,”局長先生苦惱地說道,“也就是因為如此,我實在沒有什么辦法了所以才到你們這邊來,想聽聽你們是怎么看待這個問題的,能不能給我提出一些好的建議。”
“如果您讓我提建議,那我就建議你們再次徹底搜查一遍那棟房子。”杜賓一直保持沉默,卻忽然冒出了這么一句非常離譜兒的話。
“你這個建議我覺得很沒有必要,”局長先生并不認同杜賓剛剛說的建議,“經過我七天的搜查,我現在基本上斷定那封信并不在D大臣所居住的房子中。”
“其實我的建議就是這個,除此之外恐怕很難再向您提什么更好的建議,”杜賓繼續自己的話,“另外,我想你肯定是了解這封信的具體形式和內容的吧?”
“你說得不錯,我確實了解有關這封信的各種細節。”局長先生掏出一個小筆記本,然后用非常大的聲音把信里面的內容念給我們聽,并且向我們講述了這封信件與眾不同的地方。當他把這些都告訴完我們之后,就走了。局長離開的時候讓我覺得他當時非常沮喪,這還是我頭一次見到他這個人竟然會沮喪。
將近一個月之后,我們又迎來了局長先生。像你以前看到的一樣,我們仍舊是在到處是煙霧的書房里彼此沉默著、思考著,一個又一個的煙圈中不時有智慧碰撞出的火花。局長入鄉隨俗,也拿出自己的煙斗,很自然地找了一把椅子坐下來,和我們聊了起來。
“找到那封被盜走的信件了嗎?”我對這個問題仍然念念不忘,“照我猜測,以D大臣的機智,你們可能還是沒有找到吧?”
“你說對了,我簡直被這個家伙給弄瘋了,他實在狡猾到家了。”局長先生說,“我從你們這兒回去之后,雖然仍然不抱什么希望,可是還是聽從了杜賓的建議,再一次仔仔細細地將D大臣的房子進行了一次全面搜查,結果,當然又是一無所得。”
“噢,我有一個問題一直想問您,我很想知道大人物給您許諾了多少賞金?”杜賓問道。
“呃,賞金當然是非常豐厚的,不過具體的數字,我實在不方便向你們透露。”局長先生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充滿顧慮,“但是,我可以告訴你們,如果有人幫助我找到這一信件,我可以給他五萬法郎作為回報。從如今的情態發展來看,這封信已經越來越重要了,找到它已經是刻不容緩了,當然,關于這件事的賞金如今也上漲了一倍之多。只是,現在的我很悲觀地認為,就算是賞金比現在還要高一倍,我想我也無法找到這封信件!”
“我想,局長先生,在這件事上……”杜賓將自己的煙斗放在嘴邊,深吸了一口,用一種非常悠長的語調說,“您的思路應該換一個角度。”
“你能具體說說嗎,我到底該從什么地方入手?”局長先生很急切地問道。
“嗯,關于這個……”杜賓吐了一個煙圈,好像已經想好了所有的問題,“如果您覺得我的意見是可取的,那您就先耐心聽我說一件與這封信件的丟失關聯不大的事情。我不知道您是不是清楚有關阿布尼西醫生的事?”
“這個,我倒是真沒有什么了解,阿布尼西醫生是什么人?”局長先生說。
“您不知道也不算什么意外,因為本來這就是一個沒有什么特別之處的故事,”杜賓依然語調悠長地說著,“我聽說,距今很長時間之前,一個腰纏萬貫但十分吝嗇的有錢人,有一次得了一場大病,可是他根本不想為自己的病花費一點金錢,于是他就想出了一個可以滿足他吝嗇的看病辦法。他約了阿布尼西醫生進行聊天,然后在聊天中將自己的病情說成是他的一個朋友的癥狀,希望通過這個辦法而從醫生嘴里套出醫治這種病的方法。這個守財奴跟醫生說:‘如果我的朋友是什么什么癥狀,那么請問醫生,他應該怎樣做呢?’可是守財奴沒有想到阿布尼西醫生的回答更加精妙,醫生對他說:‘如果像您所說的這種情況,那我就建議他,馬上去請一個醫生為他進行診斷。’”
“噢,我明白杜賓的意思了。”局長先生立刻敏感地知道了杜賓想要說的意思,只是似乎有點難為情,他說,“杜賓你也不用這么委婉地說這件事,我個人非常希望接受高人的指點,假如他能夠幫我將這封信拿回來,我肯定會將獎金支付給他。”
“局長先生既然這么說,”杜賓說話的同時,拉開了自己身前的一個抽屜,從中取出了支票本,并說道,“那您可以在支票本上為我們填一張五萬法郎的支票,一旦您將自己的大名簽到上面,我就立刻告訴您這封信到底在哪里。”
我實在沒有想到杜賓竟然還藏著這么一招,心中感到震驚的同時還隱約替他擔心,他真的已經知道信件在什么地方了?當然,我們的老朋友局長先生,此時的表情就如被雷擊了一樣,震驚中還帶著木然,在接著的大約幾分鐘時間里,局長先生都沒有緩過神兒來。他一句話也說不出,坐在那里一動不動,好像不認識杜賓一樣地看著眼前這個令人難以捉摸又如此市儈嗜財的老朋友。當局長的大腦又重新回到現實的時候,他仍然看上去有些不適,可是并沒有怎么猶豫就拿起了一支筆,將五萬法郎的數字填到了支票上,并將自己的名字簽到上面之后遞給滿臉透出詭異的杜賓。杜賓接過支票,對其進行了一番仔細檢查,在沒有發現什么問題之后,將支票放到了他隨身攜帶的一本小冊子中。然后,他朝局長先生很詭異地一笑,用十分細致的動作打開了一個被鎖著的抽屜,從中拿出了一封信件,他看了一眼之后,便將這封信件遞給了局長先生。局長先生顯然是覺得被杜賓耍了,但是仍然難掩自己的興奮,在接過杜賓遞過來的信之后,他雙手都顫抖起來。在打開此信之后,用充滿欲望的眼睛迅速掃了一遍信件,之后,沒有留下任何話,便顯得有些狼狽地站起身來急忙離開了。
當局長先生離開之后,杜賓才開始向對這一切都不了解的我進行了一番解釋,杜賓把所有的事都告訴了我:“我們不能不承認,巴黎警方是有著很多優點的,最起碼他們在辦案的時候是非常認真的,而且也足夠聰明,除此之外,他們也非常熟悉辦案方法的使用,知道什么案子該選擇什么方法。所以,在局長先生把所有搜查的細節都告訴給我們的時候,我已經知道他們在自己的能力范圍內已經對D大臣的住所進行了不能再仔細的搜查了。”
“你說的‘在自己的能力范圍內已經對D大臣的住所進行了不能再仔細的搜查了’是什么意思?似乎還有什么別的意思啊?”我問杜賓。
“對。可以說,警方在D大臣的住所中進行的搜查已經將搜查的方法用到了極致,這的確是非常巧妙且完美的偵破手法。”杜賓語速很慢地說,“而且,他們能夠非常堅決地執行這些方法。如果信件確實藏在警方已經搜查過的范圍中,那么在警方這樣細致的工作中,信件是一定能夠找到的,我們任何人都無法懷疑這一點。”
我對杜賓的話仍然不很明白,只是想到杜賓整局長的那一幕和他剛才對警方的肯定實在反差太大,于是竟然笑了起來,但是我更想知道杜賓是怎樣找到這封信件的。可是杜賓沒有直奔主題而是用非常認真的神情在表揚警方,只聽杜賓繼續說道:“不過,警方雖然在搜查D大臣住所時所用的手法非常巧妙,并且也能夠很完善地執行這些方法,可是他們犯了一個根本性的錯誤。他們的問題就是,在這個案子中,他們的對手是一個非常狡猾、有著高智商的人,面對這樣的對手,他們的細致手法從根本上就不對。我是說,如果想將這封信找回來,就不能用這種方法。非常可惜的是,局長先生像平常一樣完全不反思這個問題,根本沒有將問題的歸根之處弄明白,就想通過以往的經驗,企圖靠搜查物證的辦法找到他想要的東西,說起來局長先生還真是一個頑固又不知變通的人。我們兩個應該都很清楚,局長先生并不了解思維訓練的意義,所以在思考方式上他當然不會像我們這樣能夠收放自如,他的思維總會有一些局限。所以,像局長先生這樣的人總會出現兩個問題,要么將一個普通的案子想得過于復雜,要么將一個復雜的案子想得過于簡單。雖然局長先生人很正直,可是從思維上來說,你不得不承認,他是一個死腦筋。請原諒我說話太過火了,我有時覺得一個小學生的頭腦靈活度恐怕也好過局長先生。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知道一種‘猜彈珠’的游戲,我經常和一個八歲的小男孩玩這個游戲。在玩的兩個人手中各放一些彈珠,一方可以在每個回合中自由地變換其手中的彈珠數,然后讓另一方去猜在自己手中一共有幾顆彈珠:其數量是奇數還是偶數。如果猜的人猜對了,就能贏對方一顆彈珠,猜錯了,就輸給對方一顆彈珠。經常和我玩的那個小男孩,雖然才八歲,可是卻能夠將他周圍所有小朋友的彈珠贏光!我曾經研究過他為什么總能在游戲中獲勝,后來我發現他贏得游戲的原因是他自己有一套‘猜測邏輯’。其實這也不是什么高深的邏輯,其本質就是通過在游戲中的觀察和猜測,評估一下自己的對手到底有多聰明,然后根據對手的聰明程度讓他們上‘自以為是’的鉤,最終被自己的聰明誤導,從而讓自己獲利。舉個例子,假如和這個男孩玩的是一個有些笨的人,那么這個小男孩就會開始自己預謀好的策略。在游戲剛開始的時候,笨男孩讓小男孩猜手中的彈珠是奇數還是偶數,如果男孩回答‘奇數’時回答錯了。那么在第二回合的時候,男孩心中就想:‘第一回合中我猜奇數輸了,那么他就會認為我第二回合會猜偶數,但是他不會讓我贏,所以其手里的彈珠數量肯定會是奇數,那我這次就繼續猜奇數。’結果果然像小男孩想的一樣,他用逆向思考猜中了對手的心態,贏了游戲中的第二回合。假如他的對手是一個稍微機靈一些的小朋友,那么他還會根據第一回合的輸贏情況深入分析第二回合及其以后的思維邏輯,然后進行自己的猜測。到游戲的第二回合時,小男孩會想:‘這是一個更為機靈的對手,我的對手肯定會想,我第一回合猜奇數錯了,那么第二回合中我可能會再猜偶數試試,可是這樣一來我就覺得太簡單了,因此我可能會猜想他這回還是奇數,所以我在第二回合的時候很可能還猜奇數。基于這個想法為了不讓我贏,他這次會準備一個偶數,那我這次就猜偶數。’結果又被他算準了。這個小男孩就是靠這種邏輯分析,總比對手多思考一步,所以,他才成了他同齡玩伴中的大贏家。表面上看,雖然只是奇數偶數的簡單答案,可背后卻是已經很復雜的邏輯分析和思維分析了,如果不然,完全靠運氣,他怎么會贏得這個游戲呢?”
“你說得對,”當我聽杜賓講完這個故事,也將自己的意見說了一下,“這個游戲其實就是考驗雙方看誰思考得更深一步,看誰才能將對方的思路進行正確的把握。”
“是的,”杜賓說,“我還真問過這個小男孩,是怎樣知道對方是怎么想的。他的答案讓我非常吃驚,他告訴我,在弄清楚對方到底是一個較遲鈍的人還是一個較機靈的人之后,然后通過這么一個辦法來判斷對方到底在想什么,這個辦法就是將自己的表情,盡量調整得與對方的一樣,然后,再想想那時的自己在腦海或心里到底想什么就知道對方的想法了。我們不能說這種方法是科學的,可這個孩子能夠想到站在對方的角度思考問題就已經是很了不起了,我想就算是福柯、馬基雅維利也未必一定比這個男孩的天分高很多吧!”
“你是說,”我似乎也為小男孩而感到震驚,“要想在這個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游戲中獲勝,首先還得了解對方到底是個什么狀態!我的意思是,要先弄明白對方到底是多聰明,聰明到了什么程度之類的問題,然后再進行對對方思路或思考邏輯的分析與推測?”
“沒錯兒,不然怎樣贏對手?”杜賓說,“從這個角度來說,局長先生和巴黎警察真該好好向這個小男孩學習一下。他們為什么常常遇到難以破解的案子?除了案子本身或許很復雜之外,還有兩個非常重要的原因:一是,他們根本沒有考慮過嫌疑人的思考邏輯,對于這一點,他們甚至是根本沒有任何了解;二是,完全沒有弄清楚嫌疑人的聰明程度,或者雖然想到了這一點,卻錯估對手。總之,他們辦案的時候更多的是從自己習慣的思考邏輯著手,然后用自己的想法去推測對手的想法或目的,而不去了解對手到底在想什么,只靠這樣當然會遇到一些根本無法解決的案子。比如這個案子中關于信件失竊的問題,我就很奇怪警察們為什么沒有仔細研究一下他們所面對的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小偷,是一個聰明的人還是一個笨蛋?完全就是在憑著自己的想法,盲目自信地覺得對手既然偷走了東西就一定會把東西藏在某個地方,所以,只要進行嚴密的搜查就能夠找到被盜取的信件,達到完成任務的目的,可是這種普通的手法和以前太為人熟悉的辦案的經驗對于特別的對手來說實在很難達到目的。”
杜賓說:“說起來,巴黎警方用的是跟普通大眾差不多的思維方式,所以,一旦碰上那種稍微狡猾一些的罪犯,就很可能讓他們自己陷入思維的困境,而難以將案子偵破。警察總是對于罪犯的智商估計不足,要么以為罪犯太狡猾而把自己嚇得不知所措,要么就以為罪犯是些蠢蛋,太輕視他們。在他們偵破案件的過程中,總是缺少不可缺少的變通。所以,光是提高賞金根本就無濟于事,只要是一些不太尋常的案子就容易把警察的思路搞暈,因為他們太相信自己過去的經驗,所以總是抱著舊的思考方式、舊的偵破手法不放,最后的結果當然是只能在狹隘的思維邏輯中轉圈。這一點,我們從這個重要信件的失竊案件中就能看出來。在這個案子里,警察實在沒有什么靈活的變通手段,他們基本上沒有考慮他們的對手D大臣是一個什么樣的人物,沒有在意對手的聰明和才智,而只是企圖從一些先進的工具上,比如放大鏡偵查、地毯式搜索之類的技術手段上取得案件偵查的突破。這也就是我為什么說警察的思維太有限,基本上和普通大眾的思維角度沒什么區別。其實,我們都能看得出來,局長先生對于偵破這一案件的心情非常急切,他并不是不努力,也不是不想偵破這個案子,可是他破案的手段又是什么呢?只不過是陳舊的多年積累的辦案經驗而已。也就是說,從思維的角度來看,其方式方法都只是一套路子。你也清楚,假如是一個一般人,在隱藏一些東西而不欲被他人發現時,肯定會找一些看上去不可能的地方,比如被鑿空的桌子腿,或者很難發現的密穴或密室。你想這些地方是最普通的地方,你我都能想到,我們尊敬的局長先生卻也相信從這些地方中就能找到他想要找到的東西。可是,他的對手是位居高位,在復雜的官場中歷練多年,并且能夠接觸到大人物的一等一的精英人士,以局長先生這種尋常的思維怎么可能找到D大臣藏的東西?我相信警方之所以如此迷信自己的思路,一定是基于其以往的成功經驗,或許在之前一段時間中,他們曾經成功偵破過類似這種物件遺失的案件。可是這些成功不具有代表性,也無法證明這是憑借他們的心智思維而將案件偵破的,他們之所以用這種普通辦法還能將案子偵破,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那種極其認真、努力和細致的辦法態度,因為他們的堅定和耐心而將案子偵破了。可是,破案的前提是罪犯并不是一個杰出的、有著高智商的人物。剛才我也說了,警察總是太迷信自己的方式,從來不知道從自己的思維方面進行一些變通,就算是破案的賞金提高,案子的重要性非常突出,他們也一樣十分堅定地用自己的方法。這雖然聽起來很可笑,但從另一個角度上達到了警察想達到的耐心和堅定的效果。”
杜賓接著說到了本案的問題:“我一直在向局長先生強調,那封信應該就在D大臣的住所中。換句話說,那封信其實沒有出局長先生和警方的搜查范圍!我為什么這樣說?是因為我想告訴局長先生,必須先弄明白D大臣是一個什么樣的思維,然后你才能知道D大臣到底將這封信藏在了什么地方,知道了這些你當然就能夠把那封信找到了,難道思路不該是這樣嗎?但是,讓我感到意外的是,我完全沒有想到局長先生已經完全在自己的思維陷阱中被困住了。他明明知道D大臣是一個足以稱為詩人的博學多才之士,卻輕蔑地認為D大臣是一個笨蛋——雖然局長先生從沒有說過,可是我敢斷定在他的眼里,他肯定把所有的詩人都當成是笨蛋,也正是因為這種看法,他內心中是完全將D大臣的聰明才智置之不顧的。”
“可是,D大臣到底算不算一個詩人呢?”我對于這個說法一直有些疑問,“雖然,我確實聽說過與D大臣有著密切關系的他們家族的另外兩人都已經是文壇中非常有名氣的人,可是還沒有什么證據證明D大臣就是人們常說的其中一位啊!當然,我知道D大臣好像在以前寫過一篇數學領域的和‘微分學’有關的論文,那最多只能算是一個數學家啊,怎么說也不見得是個詩人!”
“其實你的問題不應該糾結于是不是詩人,關鍵是我們應該從各種資料中了解D大臣并非一個笨蛋,而是一個非常有學問的人。另外,我得告訴你,”杜賓說,“有關D大臣,我已經注意他很久了,他確實對于數學方面很有興趣,可是,同時他也算得上一個詩人!所以,一個擁有豐富的數學知識和寫詩才情的人,必然有著非常不凡的推理能力。假如他只是一個數學方面的專家,那對我們來說倒是一個非常好的消息,因為這種只有單一學科知識的人可能無法擁有太高超的推理能力。遺憾的是,我們面對的這個對手正是一個難纏的對手,他遠沒有我們想象中的那么不堪,他是一個非常聰明且非常可怕的對手。”
“照你這么說,我倒真有些害怕了,”我有些驚訝地對杜賓說,“在我眼里,數學家的推理能力應該是各種學科中最為優秀的,可是你竟然不同意這個意見。甚至你認為數學家還比不上一個詩人,我想恐怕沒有人會同意你的這個說法吧?畢竟我相信,像我這種觀念在現在,甚至不僅是現在,歷來人們就是這種觀念!你說,一般人的心目中難道不是認為一個精通數學的人是非常善于推理的嗎?”
杜賓此時沒有正面回答我的問題,而是引用了一段法國劇作家尚福爾的話作為對我的疑問的回應:“‘其實,無須懷疑的,凡是被一般人都認同的或者某些類似約定俗成的觀念,沒有一個不是膚淺和愚蠢的。我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大部分普通人并沒有什么杰出的智慧。’這是尚福爾的一段話。所以,你的這個說法,我其實非常理解。數學家其實是最會制造自己非常‘善于推理思考’假象的人!說他們是假象,是因為他們總是將視聽混淆,把一些與事實有關的真相和推理所涉及的本質統統模糊掉。你或許不信服我的說法,那就讓我告訴你數學家們是如何制造假象的。說到底,他們玩的是一種辭令的技巧,更具體一點說,即他們將‘分析’放到了‘代數’里面,然后,給普通人造成的印象就是這些人有著非凡的分析推理能力。其實這只不過是一種代數運算的能力而已,人們卻把它與分析推理畫上等號。我可以告訴你,法國人是非常善于制造這種假象的,而且可以說法國人就是這一假象的始作俑者。一個道理是我們都清楚的,如果在不同的語言中一個字匯或者語詞發生的演變所代表的含義能夠被廣泛接受,那么得到人們認同的必然是這個詞語的重要性和價值性,而絕非僅僅將這個詞死板地帶進一種新的語言系統中。也就是說,僅僅把‘分析’這個詞套進‘代數’這門語言是遠遠不夠的。讓我以幾個現在英語中的詞匯為例吧,這幾個詞都是由拉丁文演變而來的,但是這種演變絕對不是僅僅將幾個拉丁文詞匯放進英語語言系統中,而是還包含著很多文化意義,比如:ambitus是拉丁文中的一個詞,其原本的意思是:寬廣的、能夠在四處看到的,這個詞后來演變成了英文的ambition,其意思是:野心、抱負;而拉丁文religio,原本的意思是:宗教,英文由此演變的religion,其意思同樣是:宗教;拉丁文中homines honesti表示:一些值得尊敬的人,英文則是a set of honorable men,其意思同樣是:一些值得尊敬的人。”
“在你這么一解釋之后,確實觀點跟普通人理解的不太一樣,”我說,“我想,如果你把自己的這個觀點公開,全巴黎的數學家們一定會視你為仇人,跟你沒完沒了地爭論一番。”
“這個當然,我想只有抽象的邏輯的訓練是個例外,”杜賓接著說,“除此之外,我覺得其他任何推理分析能力都不是從某些特別的學科中訓練出來的,就算可以通過某些學科的知識使自己的推理能力得到提高,我也對這種說法保留自己的意見,這其中我覺得最可疑的就是因為數學而培養出了推理分析的能力。其實數學只是一種規定好了各種特定形式和數量運算的學問,所以,對于數學的熟練掌握并不代表著推理能力的提高,從數學中我們能夠提高的能力是一種對形式的觀察和對數量變化的感知能力,但是這些與真正的推理分析能力其實還相差萬里。不少人對于數學崇拜過度,認為從這門非常抽象的學問中能夠解釋世界所有的真相,好像它就是唯一可信的一切事物的真理一樣。這一點,我個人是非常想不通的。我覺得這個復雜的世界是任何單一的學科都無法進行完全解釋的,所以我覺得抱有這種想法的人非常荒謬和無知,難道不是嗎?當然,在數學運算進行的時候,一個命題或公理確實讓你得到了絕對準確的答案,可是這并不能說明這個命題或公理就可以無限使用,成為解釋世界的真理。讓我遺憾的是,不少從事推理的人竟然也和普通大眾一樣,總是犯這種錯誤,認為一個角度就可以運用到整個事件中。”
杜賓解釋說:“我之所以說這么多和這個案子無關的話題,其實只是想讓你知道:就算是數學這類幾乎無法反駁的學科,也并不能完全取代諸如倫理學、形而上學之類的學科的價值,任何運算都不能代替人的思考——這一點你一定要記清楚。我們的真理在于我們的心智、我們的大腦和心靈,而絕非是通過工具的運算。所以,就算是數學稱得上所有科學的基礎學科,可是它的適用范疇就在數學,而不是當成一種真理延伸到所有事物中。當然,這一點數學家們是沒有想明白的,他們覺得數學可以解釋一切。更讓我覺得有些滑稽的是,竟然還有很多與數學研究無關的人相信這一點,且對此沒有任何懷疑。”
杜賓說:“我想你或許已經讀過布萊恩特的《神話學》,這是一本寫得非常好的巨著。在這本著作中,作者也曾談到了像這樣的認知誤區,如果我記得不錯,它的原文是這么說的:‘那些和異教徒關系非常密切的寓言和神話本來是沒有什么可以信以為真的。遺憾的是,我們總是把這個前提忘得一干二凈,反而大費周折地從中對各種傳疑進行推斷和考證,認為這些神話所講的或許并非空中樓閣。’在我眼里,一些偏執的‘數學家們’就如同布萊恩特所說的‘異教徒’,他們沒有把自己的眼光放到整個學問中間,而只是盯著數學領域不放,把這些領域中一些‘寓言神話’信以為真,然后便花費大量甚至是一生的精力來證明和推廣或許根本不存在的‘神話’。我肯定這些數學家沒有看到布萊恩特的話,所以將自己的一生耗在了毫無意義的事情上,他們的聰明才智這樣被浪費,在我看來是很可惜的。總之,到目前為止,我確實沒有發現任何一個數學家同時還具備了讓我欽佩的推理分析能力,說句可能過分的話,他們在我眼中只不過是一群非常善于運算的人而已。”
顯然杜賓對于數學的不滿是長時間積累下來的,所以在這個話題上他不但振振有詞而且慷慨激昂。雖然他說的未必沒道理,可我還是保留了自己對數學和數學家的那份尊敬,因此對他的長篇大論我只是微笑,完全沒有表示更多的意見。好在,他在發泄完對數學家的不滿之后便又回到了案子本身上,他說:“我嘮嘮叨叨地講了這么多,其實只是要證明,假如D大臣只是一個懂運算的人而并非同時是一個詩人的話,我想他的心智推理能力恐怕是很有限的,如果是這樣,那封信也可能早就被局長先生那種地毯式的搜索給發現了。但是我們的D大臣卻是一個心智能力絕對不可小覷的人,正是他的機智讓我們死板的局長最終沒有識破他的秘密,也正是因為這樣,局長先生才肯沒有什么猶豫地立刻給我開支票,因為他已經被D大臣徹底打敗了,沒有任何更好的辦法了。你肯定覺得奇怪,我是怎么知道D大臣的思維方式的?其實,僅僅是因為他的身份——既是詩人又是數學家,就無法讓我把這個對手等同于一般人。另外,我也借鑒了那個教我玩游戲的小男孩的辦法,即將自己設想成D大臣,站在D大臣的角度上看看他會有什么思路。我推理D大臣的思路應該是:‘我自己應該算得上一個十分大膽的奸臣了,有關巴黎警察那些通常的辦案手法我當然非常熟悉。所以,他們故意設計在大街上對我進行的兩次突擊搜查,完全在我預料之中;至于他們慣用的私闖民宅,更不會對我例外,趁我不在的時候到我的住所進行地毯式的搜索,一定是會發生的。既然他們這么愿意不辭辛勞地搜,我就讓他們搜個夠,我可以每天都夜不歸宿,把所有的空間都留給這些警察。再說正好讓他們辛辛苦苦多找幾回,反正他們也找不到,這反而能讓他們確信這封信根本就沒有藏在我的住所中。我非常清楚巴黎的警察就這么點本事,除了平庸之外,沒有什么特別的辦案思路。因此,一般人通常會隱藏東西的地方我是不能選擇的,因為巴黎警察對這方面的搜查還是很有水準的;除此之外,這封信也不能隱藏在秘密夾層或者凹龕中,因為我非常清楚警方可以通過一些儀器將這種隱藏探測出來。那么,這封信應該藏在什么地方才是最安全的呢?我覺得應該選擇一種十分簡單的辦法,因為這些警察們已經將我設想得太過復雜了,而且他們還動用了各種精密儀器來進行搜查,那么只要我反其道而行之,選擇一種簡單到令他們無法想象的辦法,就一定可以躲過他們那復雜細致的搜查。俗話說,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這是D大臣的思維邏輯。我想你肯定還記得在局長先生第一次到我們這兒來的時候,我在一開始的時候便跟他說——‘可能正是因為這件事情就是一件非常簡單的事,而你們卻把它想得太復雜了,所以才會有所困擾。’可是局長先生并沒有理會我的話,認為我是在賣關子,準備看他的好看。”
“你說得對,這件事我記得很清楚,”我說,“而且當時我記得局長先生還非常夸張地笑了起來!”
杜賓繼續分析這個案子:“我們接下來應該解決的就是有關這個案子的本質的問題,不過在談它的‘本質’時我想說點別的東西。我要說的是,其實在這個宇宙中,一個真實的世界和一個所謂的虛擬的世界并不是像我們想象的那樣之間沒有任何關系,如果你對它們進行一個仔細的觀察,就會發現在這兩者之間還有非常之多的相似之處存在,而且它們之間彼此能夠進行互相的借鑒。在這里是一個案子的問題,在其他地方還可能是另外一件事情的本質問題,但在往往大多數事件中,本質的問題都會被很多表面無關的辭令而掩蓋住了,或者是暗喻的掩蓋或者是明喻的掩蓋,其所起的作用只是將事物進行了美化。當這些東西一一呈現在你的眼前時,很多看上去沒有問題卻遠離事物本質的觀點,便可能進入你的視線,混淆你的視聽,將事物的本質完全模糊,這就牽涉到一個怎樣將事物的本質發現出來的問題。我的觀點是按照‘慣性’進行探索,其實‘慣性’并非只是事物在物理運動時產生的,在一些虛幻的、形而上的思維理念上同樣存在一種‘慣性’,而這種‘慣性’則表明‘本質’在真實和虛擬世界中分別呈現的各種景況。一個非常聰明的人,在自己下決心準備實施一件事之后,往往要比一個才智更為遜色的人更加深思熟慮,同時在他一旦付出實施之后,也不會輕易就放棄自己的行動。當然他更不會有什么輕舉妄動的行為,甚至當行動還沒有開始的時候,或許還會顯得有些猶豫。這就是一種思維的‘慣性’,它不是自己就能控制得了的,而是一種起源于事件發生之后的必然的規律。對了,我正想問你,在你上街的時候有沒有注意哪塊招牌是最吸引你的?”
“這種事我還真是沒有關注過。”我略微回憶了一下自己上街時的情況,對杜賓說。
杜賓接著說:“我不知道你是否知道一種和猜謎有關的游戲,這個游戲叫地圖猜謎,先把一張顏色復雜的地圖擺放在玩家面前,然后說出一個詞讓玩家在地圖上把這個詞代表的地名找出來。一個剛剛玩這個游戲的人往往會讓他的對手找一些字體非常小的詞匯,因為他覺得這樣找起來更難;但如果是一個非常熟悉這種游戲的玩家,一般都會選擇那些很大字體的詞,是那種鋪滿地圖的地名。這就是重點,以我們普通的思維來看,選擇一些較大字體的字豈不是更好辨認,更好找出來?我剛才問你是不是注意過大街上的廣告牌,其實你只要觀察一下就會發現,越是字體印得很大的廣告牌,往往因為它的字體太大、太顯眼反而不被街上的人注意。在這個地圖猜謎的游戲中道理也是一樣的,字體印得很大、很明顯的,往往正是一些新手不太注意的,所以他們往往輸掉游戲。這是一個人們思維的誤區,在很多事情上都會出現類似這個游戲中出現的情況。越是一些線索非常明顯的事情,越可能被很多人忽視,而且這些人常常會把一些簡單的事想成格外復雜的事,這就是所謂的被自己的聰明給誤導了的道理。”
杜賓說:“我之所以要給你講清楚這些,就是想讓你明白人們常常因為一些思維的慣性定律而使思維產生一種誤區,特別是在偵破一件案子中,這種情況經常出現。那些聰明的罪犯便會利用這種誤區讓自己變得更為安全,而那些執著的人則往往陷入自己思維的誤區難以自拔。像在這個案子中,局長先生便犯了這樣的錯誤,他所抱的心態與猜謎游戲中的新手的心態非常類似。其實局長先生太主觀了,他完全沒有考慮D大臣本來就是一個非常善于偽裝并且很擅長深思熟慮的人,而這件案子D大臣正是利用了局長先生的思維慣性,用非常簡單的本質制造了一個看上去難以破解的非常復雜的表面。我非常肯定局長先生一定根本沒有想到他千辛萬苦尋找的東西自始至終就在他的眼前,只是這是一個被人認為太過冒險和顯眼而不可能的地方,但是沒有人想到這反而是最為保險的地方。為什么這么說?因為每個人的思維慣性,人們以為誰都能想到的地方對手肯定也會想到了,所以這樣的地方基本上就是不用考慮的。在這個案子中,局長預計的正是如此,但是D大臣并不是一個一般的人,他不僅聰明而且敢于冒險,他算準了警方的思維誤區,所以將信件放到了最為危險同時又是最安全的地方。”
杜賓對D大臣如何進行信件藏匿也進行了分析,他說:“當我在設想D大臣是如何藏匿信件時,我覺得以他那種遠比常人聰明的才智和本身的大膽以及一向都很灑脫的性格,他一定有著十分精妙的藏匿手法,而且選擇也一定會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我猜,他或許從來就沒打算將這封信藏匿起來,因為我認為他的素質,其思維必然已經跳過了‘把信藏起來然后再被找到’的層面。而且如果他沒有藏起這封信,對他來說,除了警方不會想到這一點之外,還有一個好處就是他可以隨時拿到這封信并及時地利用它。因此,D大臣的選擇只是將信隨意擱在一個警方思維誤區中的地方,實際上這是沒有任何風險的,這一點絕對超出了警方之前的各種假設。”
杜賓此時才向我說明自己去拜訪D大臣的事,這一點我萬萬沒有想到,他把其中的經過告訴了我:“當我確信了剛才所說的那些想法之后,我便戴了一副綠色鏡片的眼鏡,在一個大好天氣的清晨,去拜訪了一下D大臣。我徑直去了他的住所,D大臣果然在家,而且如我預料的一樣,他看上去有些疲憊,我想這是他再次夜不歸宿造成的。從表面上看,D大臣是一副非常無聊的樣子,這自然是他裝出來給我看的。我肯定,他一定會在他人面前憑借自己的演技偽裝、掩飾自己,這樣才不容易被人看出他內心的想法;但是我也很清楚,他其實是一個活力十足、非常機警的人。”
杜賓向我講述了他與D大臣的見面過程:“D大臣既然在我面前裝傻,那我也像他一樣把自己偽裝起來。我說自己這些天來眼睛實在很不舒服,所以才失禮,不能摘下眼鏡。其實,我之所以要戴著這副眼鏡只是不想讓D大臣看清我仔細觀察他的眼神,我用非常熱烈的情緒和他聊著一些無關緊要的話題,但我的根本目的卻是借此近距離地觀察他以便發現什么蛛絲馬跡。”
杜賓談到了他在D大臣家中的收獲:“在他家中,我發現了就在D大臣身邊的那張書桌。這是一張堆滿了各種信件和文件的書桌,在桌子上面還有一些樂器和書籍。我借故仔細檢查了這張書桌上的東西,但是沒有發現什么可疑的物件。”
杜賓又說到了他的另外發現:“除了書桌之外,我又仔細觀察了房間中其他可能存放信件的地方。這時,我發現了一個顏色很俗,樣子卻頗有特色小架子。這是一個卡片分類紙盒的架子,卡片紙盒是懸掛在上面的,在盒子的上頭有一條藍色絲帶,但這條藍絲帶已經很臟了,它連著盒子掛在壁爐下邊的一個黃銅把手上。就在這紙盒中,有很隨意扔在里面的幾張卡片,另外還有一封信。而那封信表面上看同樣很臟,好像完全就是一封一直想扔掉卻總忘掉扔的信。這封信好像是從中間撕開的,看上去幾乎就被撕成了兩半。在這封信上有一個非常大的黑色印章圖案,其中的第一個字母是D——這能夠非常清楚地看到——而收信人也是D大臣的名字,其中的字跡很纖細,似乎是一個女人的筆跡。信就胡亂扔在了紙盒架子的最上方,給人的感覺就是那是一封完全不重要的普通信件。”
杜賓進一步描述了發現這封信之后的情況:“對于這封信,我看到后立刻確定這就是宮廷失竊的那封重要信件。首先,這封信與局長先生之前的描述有著非常大的差別——局長對我們說的是在這封信上有一個非常小的紅色印文圖案,其中有S家族所專用的公爵徽章,可是這封信上卻是一個非常大的黑色印章圖案,而且其中的開頭字母是D,且這封信上所寫的收信人是D大臣的名字,而且字跡是如同女人筆跡的十分纖細的字。如果我沒記錯,局長告訴我們的是這封信的收信人是宮廷中的一位大人物,且寫信人的筆跡是十分剛硬的。表面上看所發現的這封信除了在信件尺寸上符合局長先生所說的情況之外,其他方面都與局長先生所描述的情況有所差距。另外,這封信看上去非常臟非常皺,好像是被隨意扔進紙盒架中的。要知道D大臣可是一個辦事非常細致的人,他一向對生活的要求很高,基本上不可能出現這種隨意的情況。之所以是我所看到的情況,那只有一種可能,即他在故意制造這封信看上去無關緊要的觀感。可是,這正是欲蓋彌彰的失策,更容易引起敏感人的懷疑。”
杜賓向我說明了他當時的心態:“我個人是十分想親自查看一下這封信的。因此,我便想盡辦法與D大臣聊一些他十分有興趣的話題,這樣就能夠讓我有更多的時間思考怎樣拿到這封信。在與D大臣聊天的過程中,我盡自己所有的努力將這封信的各種特征全部記到了心里,除此之外,我甚至發現了其他的新線索,而也正是這些線索讓我心中困惑了很久的問題得到了解決。這些新線索就是這封信的邊緣被磨損的地方看上去和正常情況下出現的不一樣,按理說只有信紙的紙質比較硬才會出現這種磨損,而且造成這種磨損應該是反復折疊過多次。但我發現的情況與這個推理是不符合的,這封信呈現在眾人面前的其實只是把信封翻轉過來之后又重新將收信人姓名填好再蓋上封印的。當我觀察好了所有情況之后,便向D大臣告辭了。當然,我不能就這樣走掉,而是故意把自己的一只黃金鼻煙壺假裝遺忘在他那里。”
杜賓繼續講述他的探險之路,他說:“第二天早上,我再次來到D大臣家,我的理由水到渠成,那就是取回我昨天落在D大臣那里的鼻煙壺。虛與委蛇地聊了一些無聊的話題之后,突然從窗外傳來一聲很大的爆炸聲,之后又是一連串的驚叫聲和不少人的尖叫聲,這顯然不是D大臣意料之中要發生的事。于是,他迅速跑到窗邊,急切地推開了自己的窗戶,試圖看清楚外面到底出現了什么變故。這是我絕好的機會,我毫不猶豫,立刻走到那個壁爐紙盒架旁邊,將那封信迅速扔進自己的口袋,然后迅速拿一封在外觀上和原來的信件幾乎一樣的贗品放在那封信原來所在的位置。這封贗品信件是我頭一天從D大臣家離開之后準備的,我確信我的模仿是惟妙惟肖的,很難被認出來。”
杜賓接著講到了自己是如何脫身的:“原來在街上發生了一件持槍男子胡亂朝街上行人射擊的暴力事件,這件事引起了很大的騷動,但這個瘋子很快就被巴黎警察制服了。D大臣也把自己的注意力轉回到了他自己的房間中和我身上,他非常敏感地向我問道剛才我在做些什么,我說我就待在他的身邊,一起查看窗外究竟發生了什么事。但是我的目的已經完全達到了,多待在這里就多一份危險,所以,很快我便向D大臣告辭離開了。你可能會問我怎么有這么好的運氣,恰好在關鍵的時刻出現了騷亂這個意外?那我要告訴你,好運氣只會為有準備的人而準備,街上那名制造混亂的持槍瘋子,是我事先花錢雇人假扮的。”
“那你怎么不在第一天去D大臣家的時候,”我問杜賓,“便將那封信拿走?為什么還要多花時間和找什么制造混亂的人這么麻煩,再去冒一次險?”
“這個當然有我的理由,”杜賓解釋說,“其實D大臣是一個表面溫文爾雅,但實際上非常瘋狂的人,他什么事情都敢做出來。另外,他的手下也都不是吃閑飯的。如果我在沒有十足把握的情況下草率行事,那我告訴你,我是不是能從他家中活著走出來都成一個問題。當然,我這么做的原因也不完全是出于自身安全的考慮,我還有其他的打算。你很清楚在這件事上我是站在‘女大人物’的一邊的。而在過去這么長的時間里,D大臣總是憑借這封重要信件迫使大人物就范,從而讓自己不少的目的都順利實現。如果我們成功地拿回了這封能夠要挾大人物的信,讓大人物再次占據主動,而我們聰明大膽的D大臣卻一直還蒙在鼓里,用一封假信件去繼續要挾大人物,那么成竹在胸的大人物就可以反告D大臣的誣告之罪,從而一舉將D大臣的政治勢力以一個合理的理由清除掉,這豈不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嗎?要知道D大臣確實是一個聰明絕頂、富有才情的優秀人才,可他也確是一個十足的壞蛋。再說,假如我沒有成功逃脫,完全可以突然拿出這封真信件,讓仍然毫不知情的D大臣措手不及,同樣也是能夠保護自己的最重要,當然也是最后的手段。”
“難道在你制造的那封假信里你還留下了什么其他的話嗎?”我問杜賓。
“你說得不錯,如果我不在假造的信中寫點什么,”杜賓回答說,“豈不是太浪費這次大好的機會?有件事你肯定不知道,在維也納的時候D大臣曾經對我進行過一次羞辱,但當時我實在沒有能力還擊,因此只好看上去很有風度地對D大臣說:‘沒有關系,但我會永遠記得今天所發生的事的。’我的話,恐怕早被位高權重的D大臣給忘記了。可是既然我自己沒有忘記,而且又碰上了這次絕佳的報復機會,我當然不會放過。D大臣可是一個十分喜歡思考和推理的高手,他必然希望能夠找出自己失算的所在,既然如此,我何不在這封少有機會給他寫的信中給他一些偵查的線索提示?我想,憑借他的聰明和睿智,必然能夠推斷出這封信是誰寫的。至于我給他寫了什么,那是一句來自克雷比榮一部和復仇有關的劇本《阿特留斯》中的一句話。”
這句話是:
這個足以導致毀滅的復仇計劃,在阿特留斯眼中或許根本不值得,但是對希斯特斯來說,這已經足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