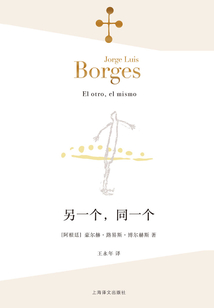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 2評論第1章 序言
我與世無爭,平時漫不經心,有時出于激情,陸陸續續寫了不少詩,在結集出版的書中間,《另一個,同一個》是我偏愛的一本。《關于天賜的詩》(另一首)、《猜測的詩》、《玫瑰與彌爾頓》和《胡寧》都收在這個集子里,如果不算敝帚自珍的話,這幾首詩沒有讓我丟人現眼。集子里還有我熟悉的事物:布宜諾斯艾利斯、對先輩的崇敬、日耳曼語言文化研究、流逝的時間和持久的本體之間的矛盾,以及發現構成我們的物質—時間—可以共有時感到的驚愕。
這本書只是一個匯編,其中的篇章是在不同時刻、不同的情緒下寫成的,沒有整體構思。因此,單調、字眼的重復,甚至整行詩句的重復是意料中事。作家(我們姑且如此稱呼)阿爾韋托·伊達爾戈在他維多利亞街家里的聚會上說我寫作有個習慣,即每一頁要寫兩次,兩次之間只有微不足道的變化。我當時回嘴說,他的二元性不下于我,只不過就他的具體情況而言,第一稿出于別人之手。那時候我們就這樣互相取笑,如今想起來有點抱歉,但也值得懷念。大家都想充當逸聞趣事的主角。其實伊達爾戈的評論是有道理的;《亞歷山大·塞爾扣克》和《〈奧德賽〉第二十三卷》沒有明顯的區別。《匕首》預先展示了我題名為《北區的刀子》的那首米隆加,也許還有題為《遭遇》的那篇小說。我始終弄不明白的是,我第二次寫的東西,好像是不由自主的回聲似的,總是比第一次寫的差勁。在得克薩斯州地處沙漠邊緣的拉伯克,一位身材高挑的姑娘問我寫《假人》時是否打算搞一個《環形廢墟》的變體;我回答她說,我橫穿了整個美洲才得到啟示,那是由衷之言。此外,兩篇東西還是有區別的;一篇寫的是被夢見的做夢人,后一篇寫的是神與人的關系,或許還有詩人與作品的關系。
人的語言包含著某種不可避免的傳統。事實上,個人的試驗是微不足道的,除非創新者甘心制造出一件博物館的藏品,或者像喬伊斯的《芬尼根的守靈夜》,或者像貢戈拉的《孤獨》那樣,供文學史家討論的游戲文章,或者僅僅是驚世駭俗的作品。我有時候躍躍欲試,想把英語或者德語的音樂性移植到西班牙語里來;假如我干了這件幾乎不可能做到的事,我就成了一位偉大的詩人,正如加西拉索把意大利語的音樂性,那位塞維利亞無名氏把羅馬語言的音樂性,魯文·達里奧把法語的音樂性移植到了西班牙語一樣。我的嘗試只限于用音節很少的字寫了一些草稿,然后明智地銷毀了。
作家的命運是很奇特的。開頭往往是巴羅克式,愛虛榮的巴羅克式,多年后,如果吉星高照,他有可能達到的不是簡練(簡練算不了什么),而是謙遜而隱蔽的復雜性。
我從藏書—我父親的藏書—受到的教育比從學校里受到的多;不管時間和地點如何變化無常,我認為我從那些鐘愛的書卷里得益匪淺。在《猜測的詩》里可以看出羅伯特·勃朗寧的戲劇獨白的影響;在別的詩里可以看出盧貢內斯以及我所希望的惠特曼的影響。今天重讀這些篇章時,我覺得更接近的是現代主義,而不是它的敗壞所產生的、如今反過來否定它的那些流派。
佩特[1]說過,一切藝術都傾向于具有音樂的屬性,那也許是因為就音樂而言,實質就是形式,我們能夠敘說一個短篇小說的梗概,卻不能敘說音樂的旋律。如果這個見解可以接受,詩歌就成了一門雜交的藝術:作為抽象的符號體系的語言就服從于音樂目的了。這一錯誤的概念要歸咎于詞典。人們往往忘了詞典是人工匯編的,在語言之后很久才出現。語言的起源是非理性的,具有魔幻性質。丹麥人念出托爾、撒克遜人念出圖諾爾時,并不知道它們代表雷神或者閃電之后的轟響。詩歌要回歸那古老的魔幻。它沒有定規,仿佛在暗中行走一樣,既猶豫又大膽。詩歌是神秘的棋局,棋盤和棋子像是在夢中一樣變化不定,我即使死后也會魂牽夢縈。
豪·路·博爾赫斯
注釋:
[1]Walter Horatio Pater(1839—1894),英國評論家、散文家,倡導一種精美的散文體裁,對唯美主義有較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