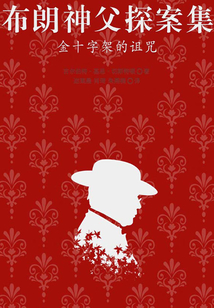最新章節
- 第31章 吉迪恩·懷斯的鬼魂(3)
- 第30章 吉迪恩·懷斯的鬼魂(2)
- 第29章 吉迪恩·懷斯的鬼魂(1)
- 第28章 達納威家族的厄運(4)
- 第27章 達納威家族的厄運(3)
- 第26章 達納威家族的厄運(2)
第1章 布朗神父的復活(1)
有那么一段時間,布朗神父享用著名聲這東西,或者說不堪其擾。他成了名噪一時的新聞人物,甚至成了每周評論里眾人爭議的話題。在數不清的俱樂部和會客廳里,尤其是在美洲,人們熱切而夸張地講述著他的豐功偉績。他當偵探的冒險經歷甚至被寫成短篇小說刊登在雜志上,任何認識他的人讀到這些故事,都會感覺與他太不相稱了,實在難以置信。
說來也怪,這游移不定的聚光燈居然是在神父眾多住所中最隱秘,起碼是最偏遠的一處聚焦到了他身上。當時他被派往南美洲北部沿海的某個地方行使神職,承擔著介乎傳教士和教區神父之間的那種角色。那時的南美列國仍舊若即若離地依附于歐洲列強,或是在門羅總統[1]的巨大陰影下不斷威脅著要成為獨立的共和國。當地人膚色棕紅夾雜粉紅色斑,屬西班牙裔美洲人,而且大多是西班牙-印第安混血,然而數量可觀的英裔、德裔等更具北方特征的美洲人也越來越多地滲透進來。而隨著其中一位此類訪客的到來,麻煩似乎也就此開始了:這位到訪者剛剛登陸,正在為丟了一件手提包而心煩意亂。他走近目光所及的第一棟建筑——偏巧是傳教站及其附屬小教堂。房前有一長溜走廊和一長排木樁,上面纏繞著黑色葡萄藤,方形葉子則已被秋色染紅。成排的柱子后面還坐著一排人,坐姿僵直猶如木樁,色彩搭配仿若葡萄藤。他們頭戴烏黑的寬邊帽,眼睛一眨不眨,眼珠烏黑發亮。許多人面色暗紅,就像是用大西洋彼岸森林里的暗紅色木材雕刻出來的。那些人都吸著細長的黑雪茄,冒出的煙差不多是那一大群里面唯一在動的東西。那位到訪者很可能把他們當成了本地人,雖然他們中的某些人很以自己的西班牙血統為傲。可他無意分辨西班牙后裔和印第安土人的細微差別,一旦認定這些人是土生土長的,他倒更愿意把他們從眼前轟走。
他是一位記者,來自美國堪薩斯城,人精瘦,發色淡黃,長著梅瑞狄斯[2]所謂的愛冒險的鼻子,你很容易聯想到它就像食蟻獸的長鼻那樣聳動著摸索找路。他姓斯奈思,他的父母經過一番深思冥想之后,給他起名掃羅,而他覺得還是盡量把這一事實隱瞞起來為妙。當然,最后他采取了折衷辦法,自稱保羅,不過絕不是出于導致那位外邦人的使徒[3]改名的相同緣故。正相反,以他對這類事的觀點,用那迫害者的名字稱呼他倒更貼切;他對宗教一貫是嗤之以鼻,這種態度從英格索[4]比從伏爾泰[5]那兒更容易學到。巧合的是,他展現給傳教站和走廊前那群人的,恰恰是他的性格中不太重要的這一方面。他是個講究效率的人,而這些人表露出的安逸和冷漠簡直到了厚顏無恥的地步,這令他怒火中燒。他連續發問之后竟然得不到任何明確的回答,他就開始自說自話。
這個衣冠楚楚的人,站在烈日下,頭戴巴拿馬草帽,手里緊攥著手提包,扯起嗓門沖著陰涼里的人嚷開了。他粗聲大氣地指責他們怎么能如此懶惰骯臟,野蠻無知,竟然不如自生自滅、更低等的野獸,就當他們此前曾想過這個問題。在他看來,正是受了教士的毒害,他們才如此窮困潦倒、逆來順受,以致于只能在陰涼地里閑坐吸煙、無所事事。
“你們簡直太軟弱可欺了,”他說,“竟被這些自大的偶像唬住,就因為他們戴著主教法冠和三重冕、穿著金法衣、儀式盛裝招搖過市,視其他人為糞土——你們就像看童話劇的小孩,完全被王冠、華蓋和圣傘迷惑了;就因為一個自命不凡的老主教整天花言巧語,當自己是世間主宰。可你們呢?你們像什么樣,可憐的傻瓜?我告訴你們,這就是為什么你們還遠遠沒開化,不會讀書寫字……”
正在這時,那個“花言巧語”的主教匆匆出了傳教站的門,匆忙得有失尊嚴,看上去并不像世間主宰,倒更像裹在黑色舊衣里的短抱枕,略有人形而已。就算他有三重冕,現在也沒戴,而是戴著一頂破舊的寬邊帽,跟那些西裔印第安人戴的沒太大差別,而且嫌礙事似的把帽子撩到后腦勺去了。他好像正要對呆坐的土人發話,忽然瞥見那個新來的人,便脫口而出:
“噢,我能為你做什么?你要進來嗎?”
保羅·斯奈思進了傳教站;由此,這位記者對很多事情的了解顯著增加。想必他的職業本能強于個人偏見,事實上,精明的記者往往如此。他問了一大堆問題,得到的回答使他既感興趣又覺意外。他發現那些印第安人能讀能寫,原因很簡單,神父教過他們,但僅止于最基本的讀寫,因為他們天生偏愛直接交流。他得知,這些成堆地坐在走廊上紋絲不動的怪人,竟然能在自己的田地里辛勤勞作,尤其是那些有更多西班牙血統的土人;更令他驚訝的是,他們全都擁有真正屬于自己的田地。這多半是源于本地人習以為常的傳統,不過神父也在其中起了一定作用,如果僅從地方政治的角度說的話,這也許是他在政治上的初次也是最后一次作為。
最近,一股無神論和近乎無政府主義的激進浪潮橫掃該地區,這種激進主義熱潮在拉丁文化國家總是周期性爆發,通常發端于一個秘密社團,終結于一場內戰。當地反傳統一派的領導人名叫阿爾瓦雷斯,他是個豐富多彩的葡萄牙冒險家,但據他的政敵透露,他有部分黑人血統,主導著很多秘密據點和神殿里的入會儀式,在這些地方舉行的儀式甚至給無神論都蒙上了神秘色彩。保守派的領導者則平淡無奇,是一個叫門多薩的富翁,他擁有很多工廠,名聲很好,但毫無情趣可言。人們普遍認為,假如沒有采取更得人心的政策以保證耕者有其田,法律和秩序就完全喪失了立足之本。而這場運動的主要策源地就是布朗神父的小傳教站。
神父正跟記者說話的時候,保守派領袖門多薩進來了。他是個膚色黝黑的矮胖子,頭禿得像梨,身材也圓得像梨。他本來抽著一只香氣四溢的雪茄,可一來到神父跟前,就仿佛走進了教堂,連忙丟掉雪茄,動作有些做作。他深深鞠躬,呈現出的弧度對于如此發福的一位紳士來說似乎不可能。他總是分外注重社交儀態,尤其在面對宗教人士的時候——他是那種比神職人員還注重教會禮儀的普通信徒。這讓布朗神父頗為難堪,特別是把這種姿態帶入私人生活的時候。
“我以為我是反教權主義的,”布朗神父訕笑著說,“其實只要把事情都留給教士去做,就不會有這么嚴重的教權主義了。”
“這不是門多薩先生嗎?”記者又來了精神,大聲說,“我想咱們見過面。你去年參加了墨西哥的貿易大會,對吧?”
門多薩先生眨了眨沉重的眼皮,表示認識,然后慢悠悠地綻開笑容:“我記得。”
“在那兒一兩個小時就做成了大買賣,”斯奈思說得津津有味,“對你來說也是意義重大吧,我猜。”
“我十分幸運,”門多薩謙虛道。
“你還別不信!”斯奈思熱切地嚷起來,“好運總是光顧那些知道如何把握時機的人,而你把握得又準又穩。呃,我沒打擾你的正經事吧?”
“哪里的話,”門多薩說,“我時常有幸前來拜訪神父,閑聊一會兒。只是閑聊。”
布朗神父居然與一位功成名就的商人如此熟絡,這似乎讓記者感覺與神父親近了一些。可以看出,務實的斯奈思先生對傳教站及其使命感到一種新的敬意,并不再對那些間或使人聯想到宗教的東西耿耿于懷,而那些東西是小教堂和神父居所難以避免的。他變得十分熱衷于神父的計劃——至少是涉及世俗生活和社會關懷的那一面——并表示隨時準備發揮作用,溝通小站與外界的聯系。就在這一刻布朗神父發覺,這位記者表達關切比流露敵意更讓人反感。
保羅·斯奈思開始大肆宣傳布朗神父。他寫出洋洋灑灑的頌詞,發往位于美國中西部的報社。他抓拍這位倒霉教士埋頭于最尋常事務時的形象,放大成巨幅照片刊登在美國的周日報紙上。他把神父說的話改編成口號,頻頻向眾人獻上來自南美的神父大人的“啟示”。美國人的心理承受能力確實非同一般,換做別國民眾,面對這種連篇累牘的宣傳,早就對布朗神父厭煩至極了。結果,布朗神父收到一大堆懇切的邀請,請他去美國做巡回演講;當他謝絕的時候,對方更是敬佩有加,出人意料地抬高價碼。就像福爾摩斯的故事一樣,有關布朗神父的一系列故事,借助于斯奈思先生的手筆策劃出爐,跟尋求幫助和鼓勵的請求一起擺在這位英雄面前。神父發現故事連載已經開始,但又不知如何應對,只是說應該停止。斯奈思先生便不失時機地提出,布朗神父是否該像福爾摩斯那樣,以墜崖的方式,暫時消失一段時間。對于所有這些要求,神父只能耐心地書面作答,說他接受附加在暫時中斷連載之上的這類條件,同時請求盡可能延后恢復連載。他寫的回信越來越短,寫完最后一則,他舒了口氣。
不用說,這場遍及北美的異常喧鬧也波及到了南美的這座小前哨,他本以為要在這里過一段寂寞的流放生活。已定居南美的英美民眾開始為擁有如此聲名遠播的一位人物而自豪。美國游客,就是那種登陸英倫時吵著要看威斯敏斯特教堂的,現在登上那遠方的海岸,吵著要見布朗神父。眾人乘坐以他名字命名的觀光車,成群結伙地來看他,仿佛他是一座紀念碑。尤其令他煩惱的是,那些活分的野心勃勃的新品貿易商和當地小店主,成天纏著他,要他試用他們賣的貨,給他們做推薦。就算得不到推薦,他們也會為了收集親筆信延長通信時間。神父是個厚道人,給了他們大量他們想要的。有位叫埃克施泰因的法蘭克福酒商提出了特殊要求,神父在一張卡片上匆匆寫下幾個字作為答復,事后證明,正是此舉成了他生命中一個可怕的轉折點。
埃克施泰因是個難纏的小商販,長著毛茸茸的頭發,戴著夾鼻眼鏡,心急火燎地非要神父品嘗他的名牌藥用波特酒,還讓神父在確認收悉的回復中告知他會在何時何地品嘗。神父對這一要求并不感到特別驚訝,因為他早就對廣告宣傳的瘋狂見怪不怪了。于是他草草寫了幾句,就轉頭去忙其它似乎更有意義的事。他再度被打斷,來函的不是別人,正是他的政敵阿爾瓦雷斯,請他出席一個會議,在會上就一項懸而未決的問題達成妥協,并提議當晚在小鎮圍墻外的一間咖啡館里碰頭。對此他也表示接受,并寫了寥寥數語,交給那位衣著花哨、等候回復的軍人信使。碰頭之前還有一兩個小時的空閑,他坐下來準備處理一點自己的正經事。出門前,他給自己倒了一杯埃克施泰因先生的名牌藥酒,帶著滑稽表情瞥了一眼時鐘,喝下藥酒,步入夜色之中。
皎潔的月光灑滿這座西班牙式小鎮,他來到景色優美的鎮入口,洛可可式[6]拱門上方懸著奇形怪狀的棕櫚樹葉,看上去真像西班牙歌劇里的場景。一片長長的棕櫚葉,邊緣呈鋸齒狀,逆著月光呈現黑色,從拱門另一側垂下來,透過門洞依稀可見,好似一條黑鱷魚的下巴。要不是有別的什么吸引了他天生警惕的眼睛,這個幻象恐怕會一直徘徊不去。空氣死寂,沒有一絲風,可他明明看見懸垂的棕櫚葉動了動。
他環顧四周,沒有發現其他人。他已經走過大都門窗緊閉的最后幾所房屋,正走在兩堵長長的禿墻之間。墻是由不成形的大扁石砌成的,這兒一叢那兒一簇地生著那個地區特有的古怪荊棘——兩堵墻平行地一路延伸到拱門。他看不見門外咖啡館的燈光,也許離得太遠了。拱門下方空空蕩蕩,只見一段寬闊的大石板路,在月下顯得蒼白,從中長出零零落落的仙人掌。他感到一股強烈的邪惡氣息襲來,感覺身體也受到一種異常的壓迫,可他沒想到要停下腳步。他有著與生俱來的相當大的勇氣,但與他的好奇心相比,恐怕還稍有遜色。他一生都被求知欲引導著尋求真相,事無巨細。他常常告誡自己,要分清主次,適當加以控制,可是好奇心始終存在。他徑直穿過拱門來到另一側,突然一個人像猴子一樣從樹頂竄出,舉刀向他襲來。與此同時,另一個人敏捷地沿墻爬過來,掄圓了棍子朝他頭部砸下。布朗神父身體打著轉,搖搖晃晃,然后倒在地上癱作一團。在他倒下去的瞬間,圓臉上卻浮現出柔和且極為驚異的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