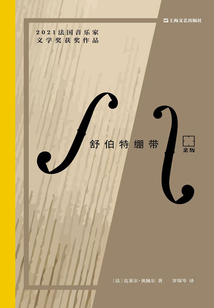
舒伯特繃帶
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序章
舒伯特《降E大調鋼琴三重奏》
op.100,行板,呈示部[1]
2012年4月。巴黎,阿萊西亞科里安花園醫療養老院。
這是一所失能老人養老院(Ehpad),窗戶前有棵高大的橡樹。春日里,樹葉在明亮的陽光中搖曳。
在失智老人居住的樓層,有一間名叫“空間”的公共大廳,始終敞開。
“空間”是個奇特的詞,我在詞典中查詢其定義:囊括宇宙的范圍,行星之間、恒星之間、恒星系之間的虛空。
每周一,我走進“空間”,關上電視機,如同一種儀式。
電視機整天開著,不過無人觀看。關上時,它總是發出一道奇特的響聲,好似機器被吞噬了,在一片寂靜中留下些許灰色的痕跡。
這一層住著二十一位失智老人,特別安裝了防護措施,于是又被稱為“保護生命單元”。電梯設有密碼。每次我走到電梯前,總是想不起來。頗為好笑。
在“空間”一角,一名老太太大聲尖叫,拼命掙扎。兩名女護士圍著她,一邊閃躲她的攻擊,一邊奮力抓住她,以免她摔下椅子。
護士必須為凱斯勒太太[2]替換繃帶。老人手臂上的傷口化膿了。
護士們的身形擋住了老人,我看不清她的臉。她們眉頭緊鎖,動作緊張。凱斯勒太太有時停下尖叫,試圖撕咬護士。
我不知道自己為何在凱斯勒太太面前停下。我一言不發地坐下,在大提琴上為她拉起舒伯特《降E大調鋼琴三重奏》行板樂章的主題。
三秒鐘,又或許是兩小節后,她的手臂放松了,一下子垂了下來。尖叫聲戛然而止,房間恢復平靜。我終于看清她的臉,目光中透露出驚訝,嘴角綻放出微笑。
那天的包扎十分迅速,我甚至沒演奏多久。這已經超越了普通的驚喜,堪稱奇跡。我看到兩位護士也露出微笑,其中一位甚至大笑起來,對我說:“一定要再來啊,帶上舒伯特繃帶!”
說得真好,非常貼切,于是這個說法便誕生了,并沿用至今。
當時離開時,我已經意識到發生了很重要的事。這是我第一次清楚看到病人的痛苦得到根本的緩解。一年后,在巴黎圣佩琳娜醫院姑息治療科,面對一百多名臨終病人,我把在失智樓層“空間”中自發實驗的“舒伯特繃帶”打造成一套規范的護理流程。對此,科室主任的評價極為精辟:“10分鐘的舒伯特相當于5毫克奧諾美[3]。”
不僅有舒伯特,還有巴赫、莫扎特、貝多芬、勃拉姆斯、拉赫瑪尼諾夫、肖斯塔科維奇,有普契尼和威爾第的歌劇音樂,有琵雅芙、克羅克羅[4]、薩爾杜[5]、阿達莫[6]和強尼[7]的歌曲,有華爾茲和探戈舞曲,有猶太、阿拉伯和非洲歌曲,有布列塔尼和愛爾蘭的民謠,有弗拉門戈,有電影配樂,以及福音歌曲、爵士樂、搖滾樂、流行音樂和金屬樂!
那一周,我兩次回到養老院,為凱斯勒太太換藥包扎伴奏,兩次的效果出奇地一致。唯有此法,她的疼痛方能緩解。她筆直地坐在扶手椅中,張開雙臂接受護理,我一遍又一遍地為她演奏舒伯特《降E大調鋼琴三重奏》行板樂章的主題,她容光煥發,照亮了整個房間,照亮了護士和我,甚至照亮了窗外橡樹粗壯的枝丫。至少,在我向她告辭離開時,我如是感覺。
幸福的記敘
今天,我的這份記敘將盡可能緊扣二十多年的切身經歷,并講述音樂在抵至某些特殊人群內心時所走的神秘之路,這些人包括人們所說的重度自閉癥患者、養老院的失能老人、失智人士,以及飽受疼痛折磨的臨終患者。
我的講述并不講究邏輯,只是力圖為我們每個人真正的“核心”留照,我們身上的這一部分至高無瑕,音樂有時能與之相連并令其重振活力。
這是一份幸福的自白。
推動我這樣一個音樂人走向治療,走向“照料”(le prendre-soin)的,不是道德的力量,而是某種天然、本能甚至是野性的力量。
在大提琴圓潤的曲線下,音樂成為我的生命,如同一道抵御荒謬、疾病和死亡的城墻,試圖與頑強抵抗的“下面的東西”交會。那“地下之物”(la sous-terre)。病床邊的音樂。充滿信心,令人煥新的微風。
感受,生命旅程中脆弱的優雅。
感恩,汩汩流淌,化作條條小溪,涌向八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