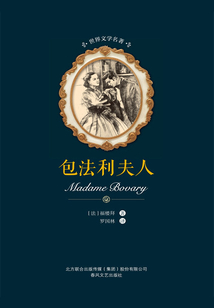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 1評論第1章 譯本序
古今中外,多少真正偉大的文學藝術作品,一經問世,即遭到無情的非難、攻擊、批判,甚至查禁、焚毀,后來僅僅憑仗歷史的公正,才最終獲得其應有的地位,成為人類共享的文化藝術寶庫中的瑰寶,彪炳千古。居斯塔夫·福樓拜的傳世之作《包法利夫人》的遭遇,就是典型的一例。
福樓拜動手寫《包法利夫人》,是1851年9月19日在盧昂近郊的克羅瓦塞別墅。經過將近五年嘔心瀝血的創作,直到1856年5月才完稿。但謄寫人謄得一塌糊涂,他又不得不仔細校正,至5月31日,才寄給《巴黎雜志》他的朋友杜康。《巴黎雜志》是一家半月刊,將手稿擱置了三個月,才決定從10月1日至12月15日,分六期連載《包法利夫人》。但該刊審讀委員會致函福樓拜,認為他的小說需要刪節,請他把刪節的全權交給編輯部。福樓拜未予理睬,僅在來函背面寫了“荒謬透頂”四個字。從10月1日至11月15日發表的幾部分,倒是未作刪節。及至12月1日那一期準備付印之時,編輯部一位負責人對出租馬車里發生的場面(即萊昂與愛瑪從盧昂大教堂里出來后,乘出租馬車瘋跑全城那一段),忽然感到擔心,說:“這一段不合適,我們還是把它去掉吧。”福樓拜對此十分氣憤,但為了不使編輯部為難,便說:“你們要刪節,悉聽尊便,但你們必須說明你們作了刪節。”于是,編輯部加了一條腳注:“審讀委員會認為有必要刪去此處的一段,因為它不符合本刊的編輯方針。特此說明。”事情并未到此止步,接著12月15日那一期,編輯部又決定刪去幾處。福樓拜確實惱怒了,經交涉,在小說正文底下刊出他的抗議:“《巴黎雜志》出于我不贊同的某些考慮,在12月1日那一期里已刪去了一段。在編輯這一期時,他們又顧慮重重,認為必須刪去好幾處。因此,我聲明對后面發表的部分不負責任,讀者看到的僅是片斷,不是整體。”
《包法利夫人》一發表,立刻在文學界和讀者中引起了轟動。當時負責嚴密檢查所有出版物的帝國檢察署,看到這部轟動性小說,《巴黎雜志》在發表時竟“顧慮重重”,多次刪節,該刊審讀委員會還特地聲明,所刪去的部分“不符合本刊的編輯方針”。這還了得!檢察署高度警覺起來,對陸續發表的每一部分仔細研究,很快決定對這本書的作者福樓拜以及《巴黎雜志》發行經理洛朗比沙和印刷商比耶提出公訴。福樓拜等很快收到傳票,審判于1857年1月31日開始。負責宣讀公訴狀的是代理檢察長埃內斯特·皮納爾。此人是帝國政府豢養的一條鷹犬,后來出任內政大臣。他在公訴狀里,指控《包法利夫人》“敗壞公眾道德,誹謗宗教”。其重點打擊對象是作者福樓拜。公訴狀最后要求法庭從輕處理雜志發行經理和印刷商,“至于主犯福樓拜,你們必須嚴懲”。
出庭為福樓拜辯護的是儒勒·塞納爾律師。他在辯護詞中肯定《包法利夫人》是“一本好書”“一本誠實的書”“這本書的思想,從頭至尾是一種非常合乎道德、合乎宗教的思想”“它是通過揭露令人發指的道德敗壞來弘揚道德”。塞納爾是巴黎律師公會成員,曾任國民議會議長,可謂聲譽卓著,而又雄辯機警。他的辯護詞很有特色。當時,他如果不從肯定《包法利夫人》非常合乎道德和宗教這個前提入手,而從維護言論自由和維護藝術之于道德的獨立性入手來進行辯護,那將是非常笨拙的。他不僅論證了《包法利夫人》是一本好書,而且肯定了它的藝術成就,強調它是作者長期深入、細致觀察生活的結晶,贊揚了作者獨特的藝術風格,甚至大膽肯定現實主義的描寫方法。作為一個律師,在當時做到這一點是難能可貴的。
就在開庭前夕,當時影響很大的詩人拉馬丁,約見年輕的作者(福樓拜那時年僅三十五歲),對他表示支持。福樓拜問他:“先生,我因為寫了這部作品,正受到輕罪法庭追究,指控我違背了道德和宗教,這一點你想得通嗎?”拉馬丁斬釘截鐵地回答:“親愛的孩子,在法國沒有一個法庭能給你定罪。有人如此誤解你的作品,并下令對它提出起訴,這非常令人遺憾。不過,為了我們國家和我們時代的榮譽,任何法庭都不能給你定罪。”事實證明,拉馬丁的斷言是真知灼見。面對《包法利夫人》這部杰作,面對德高望重的塞納爾律師邏輯嚴密、雄辯有力的辯護,面對許多著名作家的聲援和抗爭,巴黎第六輕罪法庭在“判決書”里雖然指出,“在本庭受到起訴的這部作品應該受到譴責”,但不得不承認,公訴狀所指控的段落,“無論從它們所闡述的思想還是它們所描寫的情景,仍屬于作者試圖塑造的人物性格的范疇”,因而宣告作者福樓拜以及《巴黎雜志》發行經理和印刷商“無罪”,“不予追究”。
這是一個了不起的勝利。它不僅是福樓拜的勝利,也是整個文學界的勝利。福樓拜本人充分意識到這個勝利的重大意義,他說:“我這場官司是整個當代文學的官司。人們攻擊的不是我的小說,而是所有小說連同創作小說的權利。”[1]統治者的倒行逆施往往產生與其愿望相反的結果。這場官司不僅為《包法利夫人》做了廣告,使它在兩個月內銷售量達一萬五千冊,此后又一版再版,而且進一步確立了這部作品的歷史地位。
《包法利夫人》描寫的是一位小資產階級女性因不滿夫妻生活的平淡無奇而通奸,最后身敗名裂,服毒自殺的故事。這樣一個桃色事件,無論在實際生活中,還是在向來的愛情小說里,都是司空見慣的。何以經福樓拜寫出來,便驚動了帝國政府檢察署,立即對作者提出公訴,給他加上“敗壞道德,誹謗宗教”的罪名,要求法庭“必須嚴懲”呢?這個問題的答案,只要分析一下這部作品的思想內涵便明了。
福樓拜寫包法利夫人,著眼點不在寫她的愛情故事,而在寫她從純真到墮落,從墮落到毀滅的前因后果及當時的社會狀況。
愛瑪出生于外省一個殷實農家。和許多鄉下女孩子一樣,她聰明伶俐,天真純樸。可是,在19世紀上半葉的法國,無論巴黎還是外省的中上層資產階級,都把女孩子送進修道院接受一段教育,培養貴族式的思想感情和言行舉止,為日后進入上流社會打下基礎。愛瑪的父親魯俄老爹愛女心切,也趕時髦,把她送進盧昂的修道院。愛瑪生性敏感,感情熱烈,想象力豐富,在修道院里,“修女們在訓誡時,反復拿未婚夫、丈夫、天國的情人和永恒的婚姻這些概念進行比較,在她的靈魂深處,喚起意想不到的柔情”,而宗教音樂課上所唱的抒情歌曲,全都“格調低下,音調輕浮,使愛瑪窺見了誘人而又變化莫測的感情世界”。在這種情況下,修道院禁欲主義的說教,只能起反作用,越發刺激她受壓抑的情感和對愛情的遐想。不僅如此,1830年前后風靡人心的消極浪漫主義,配合天主教卷土重來的活動,也滲透進了修道院。正是在修道院里,愛瑪接受了浪漫主義傳奇小說的熏陶,成天滿腦子情男、情女、眼淚與吻、月下小舟、林中夜鶯、憑窗盼望白翎騎士前來幽會的女城堡主。這些東西與她出生的環境和她日后的家庭生活格格不入。正是社會提倡的修道院教育,腐蝕了愛瑪稚弱的心靈,在她靈魂深處播下了淫靡的種子,做成了墮落的溫床。試想一想,如果沒有這種教育,日后的愛瑪及其生活道路,必然會是另外一種樣子。由修道院陶鑄出來的愛瑪·魯俄小姐,懷著對愛情的憧憬結了婚,成了包法利夫人。包法利是鄉鎮醫生,按理說在鄉間算得上一個體面人物,可是他平庸無能,感情遲鈍,與愛瑪幻想中的騎士相差十萬八千里。愛瑪所期待的愛情沒有到來。而沃比薩爾的舞會卻向她展示了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的上流社會生活。在這里,她體驗到了奢侈豪華的生活的滋味,看到了養尊處優、浪蕩調情的貴夫人,看到了曾經在王宮里很吃香、在王后娘娘床上睡過覺的老公爵,還同那位風度翩翩、頗有騎士派頭的子爵跳過舞。這次舞會,是涉足社交生活的愛瑪所上的第一課,使她在修道院時期所產生的天花亂墜的幻想,變成了看得見、摸得著的生活方式,在她的心靈深處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后來她的一切渴求和夢想的背后,都浮現出這次舞會的難忘情景。包法利夫人本來并不是個壞女人,盡管受了這些教育和影響,在遷居永維鎮之后,她還是一度發狠躲避萊昂的追求,力圖當一個賢妻良母,甚至試圖幫助丈夫在事業上創造驚人的成就,名揚天下。但是丈夫太無能,太不爭氣,險些斷送一條人命,這使她受到不堪承受的打擊,覺得包法利這個姓氏給她帶來的只有屈辱,因此本已岌岌可危的貞操才徹底崩潰了。她也曾一度試圖到宗教中去尋求抵御情欲誘惑的力量,可是自稱“醫治人類靈魂的醫生”的本堂神甫,對她心靈苦悶的傾吐卻無動于衷,根本不理解,使她的希望歸于徹底幻滅。社會給她造成了墮落的溫床,而在她本能地一再反抗、掙扎時,在社會上卻找不到任何救助。而羅多爾夫、萊昂這類道德敗壞、專門玩弄女性的男人,卻一再勾引她。這樣,她便不可避免地成了他們的虜獲物,最終墮落為不可救藥的淫婦。
包法利夫人的致命錯誤在于,她不懂得豪華淫逸的生活和浪漫傳奇的愛情,需要物質財富作為基礎。她的家庭環境,無論她父親還是她丈夫的家境,都不具備這種物質條件,而她卻偏偏要去追求那種不可能屬于她的生活。在她尋求愛情和幸福,卻淪為別人的玩物的過程中,她不知不覺地將丈夫的薄產揮霍殆盡。這便給高利貸者提供了可乘之機。唯利是圖、精明狡猾的奸商勒樂,看準了包法利夫人的弱點和處境,拿物欲作為誘餌,讓她簽署一張又一張借據,使她積債如山,而一旦發現她身上再也沒有油水可榨時,便串通法院,扣押包法利家的財產去抵債,并且張貼布告宣布拍賣。包法利夫人被逼到了家庭破產、身敗名裂的絕境。她求助于情人,情人們推諉搪塞;她求助于稅吏,稅吏無動于衷;她求助于公證人,公證人花言巧語,企圖乘其危難占有她。這時的人世,對包法利夫人是那樣冷酷無情!在她面前只剩下一條路,就是結束她尚且年輕的生命。作者本人就說過:“就在此刻,我可憐的包法利夫人,正在法國的十二個村莊里受罪、哭泣!”[2]被逼致死的包法利夫人遭到社會唾棄,而引誘她墮落的情人羅多爾夫和萊昂卻逍遙自在,甚至步步高升。作品結尾的這一筆,更飽含了辛辣的諷刺和血淚的控訴。福樓拜說:“任何寫照都是諷刺,歷史是控訴。”[3]這種諷刺和控訴,構成了《包法利夫人》強烈的批判效果。
《包法利夫人》強烈的批判效果,不僅僅體現在對愛瑪的命運的描寫上。這部小說有個副標題,叫作“外省風俗”。除了愛瑪的生活經歷之外,它還給人們提供了什么樣的外省風俗畫呢?給人以鮮明印象的,首先是一幅形形色色的群丑圖。這里有滿嘴“進步”“科學”,實際上不學無術,卻懷著政治野心,欺世盜名的藥店老板奧梅;有自譽為“醫治人類靈魂的醫生”,實際上對人的感情一竅不通,淺薄可笑的本堂神甫布爾尼賢;有道貌岸然,彬彬有禮,卻滿肚子男盜女娼,與奸商暗中勾結,飽肥私囊的公證人紀堯曼;有唯利是圖,奸詐狡猾,重利盤剝,置人于死地的奸商兼高利貸者勒樂;有靈魂骯臟,腐化墮落,隨心所欲玩弄女性,縱情聲色犬馬的地主羅多爾夫;還有生活空虛,百無聊賴,整天擺弄旋床以消磨時光的稅吏兼消防隊長比內,等等。當然,鄉鎮醫生包法利也應算其中一個,這是一個思想平庸,能力低下,感情遲鈍,麻木不仁,做過“名揚天下”的美夢,但終因醫術平庸,只好安于現狀的人。夠了,在一個外省鄉鎮,數得著的有頭有臉的人物,基本上齊全了;要說缺,只缺一個鄉村教師,因為那個時代在鄉間,教師還不受人重視。作者把整個鄉鎮的頭面人物寫得如此周全,幾乎一個不漏,不能不說是一種著意安排。這些人算得上鄉鎮的精英吧,可是他們之中,竟然沒有一個坦蕩君子,沒有一個德才兼備之士,沒有一個有德行的角色!他們全都是蠅營狗茍之輩!一個鄉鎮是如此,推而廣之,整個社會,不是可想而知了嗎?這就是為什么《包法利夫人》雖然寫的是外省一隅,卻具有震動整個社會的力量。
作為外省風俗畫,作品中以濃重的色彩、渲染的筆調,描寫了一個“農業評比會”。這是當局宣揚成就、刺激農業生產發展的一次盛會。會場上張燈結彩,敲鑼打鼓,鳴槍放炮,一派在永維鎮難得見到的節日景象。就在這非凡的熱鬧氣氛中,各種頭面人物,上至省府參事,下至本地鄉紳,粉墨登場。其中,藥店老板奧梅,上躥下跳,出盡風頭;教堂執事賴斯迪布都瓦,趁機向參加會議的農民出租教堂的椅子,大撈外快;省府參事在主席臺上發表演說,大肆吹噓全國農村的進步和政府對農民的關心;而羅多爾夫鉆在二樓,甜言蜜語勾引包法利夫人,兩個人一個慷慨激昂,一個竊竊私語,形成了一曲令人忍俊不禁的二重唱;主席臺下的整個會場,人群吵吵嚷嚷,牛哞羊咩,亂成一片。一個莊嚴隆重的評比會,變成了一幕滑稽可笑的鬧劇。不僅如此,在大會主席宣布的長長一串獲獎者名單中,有一位給地主干了五十四年活的老太太,人又老又瘦,臉上的皺紋比風干的蘋果還多,身上穿著破衣服,兩只手長年接觸谷倉的塵土、洗濯的堿水和羊毛的油脂,粗糙發硬,疙里疙瘩,合也合不攏。而她半個多世紀的辛勞所換來的獎賞,只不過是一枚僅值二十五法郎的獎章!作品中精心安排這樣一位被剝削制度壓榨干的農婦,作為獲獎者的代表,不正是對省府參事所唱的高調,對這次所謂評比會的抗議嗎?會議結束后,頭面人物全都留下來大吃大喝,而群眾散去,“人人回到原來的地位,主子繼續虐待雇工,雇工繼續用鞭子抽打牲口”。這是多么尖刻的諷刺,多么有力的批判。而這種諷刺和批判所針對的,從作品中不難看出,是政府,是最高當局,甚至國君。
《包法利夫人》故事發生的背景是七月王朝,但它所揭露和批判的,主要是第二帝國的社會現實。難怪作品一問世,就立刻掀起軒然大波,“遭到政府攻擊,報紙謾罵,教士仇視”,帝國政府迫不及待地要拿作者問罪。這正是這部作品的巨大成功,正是這部作品繼《紅與黑》和《人間喜劇》之后,成為19世紀批判現實主義又一部杰作的根本原因。
作為繼《紅與黑》和《人間喜劇》之后,19世紀批判現實主義的又一部杰作,《包法利夫人》不僅思想內涵上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和批判效果,而且藝術風格上在繼承現實主義傳統的同時,取得了革新性的突破,在法國甚至世界文壇,獲得了普遍贊譽和高度評價。拉馬丁說這部作品是他“二十年來讀到的最優秀的作品”[4]。波德萊爾贊揚福樓拜“肩負了開辟一條新路的使命”[5]。圣勃夫評論說:“在許多地方,我覺得從不同形式下看到了新文學的標志。”[6]左拉宣稱“新的藝術法典寫出來了”[7]。馬克思的女兒愛琳娜則認為:“完美無缺的《包法利夫人》問世后,在文壇產生了類似革命的效果。”[8]這些評價不約而同地高度肯定了《包法利夫人》的藝術成就。
福樓拜把真實地反映現實生活,當作小說創作的最高原則。他像司湯達和巴爾扎克一樣,把小說喻為“反映現實生活的一面鏡子”。[9]他認為真實和美是不可分割的:“美就意味著真實。雖說真實的東西不一定都美,但美的東西,永遠是真實的。”“喪失了真實性,也就喪失了藝術性。”[10]這些論斷反映了福樓拜的藝術風格的基本傾向。但這種基本傾向并非福樓拜所獨具。人們同樣可以拿這些觀點,去衡量和評價其他現實主義大師們的藝術特點。福樓拜的獨創在于,他通過《包法利夫人》,把小說藝術的真實原則推到了“純客觀”的境界。他主張,作家寫小說,應該像自然科學家搞科學研究一樣,始終保持客觀、冷靜的態度,“作者的想象,即使讓讀者模糊地猜測到,也是不允許的”。作品中“一頁一行,一句一字,都不應該流露出作者的觀點和意圖的絲毫痕跡”[11]。《包法利夫人》以前的小說,無論司湯達的《紅與黑》,還是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在作品中作者處于主宰一切的地位,由作者敘述故事發生的時代背景和社會背景,評價人物和事件;作者還經常借題發揮,抒發感慨或闡發哲理,甚至向讀者進行說教。總之,作者無所不在,無所不能。在《包法利夫人》里,這一切都不見了。作者把自己深深地隱藏起來了。讀完這部小說,甚至很難弄清故事的敘述者究竟是誰。作品上卷第一章寫上中學的夏爾·包法利,其中有一句話:“夏爾當時的情形,現在我們恐怕誰也不記得很清楚了。”由此看出,故事的敘述者似乎是夏爾的一位同學。但僅此而已,后面再也沒露出蛛絲馬跡。寫愛瑪的遭遇和命運,作者自始至終沒有出面發一句感慨;寫“農業評比會”那樣的場面,作者也沒有出面發一句議論。總之,作者把自己徹底從作品中排除了。他只是通過典型事件和典型人物,把現實生活忠實地描寫出來,一切讓讀者去體會,讓讀者去下結論。這種“純客觀”小說,根植于前期批判現實主義的土壤之中,而為19世紀后期的自然主義開辟了道路。左拉就特別推崇《包法利夫人》,稱之為“自然主義的典范之作”,并且通過對《包法利夫人》的評價,闡述了自然主義的藝術觀:“小說家無動于衷是一條基本法則。自然主義小說家使自己徹底消失在自己所敘述的行動背后。他是藏而不露的戲劇導演。”“作家不是說教者,而是解剖學家。他只滿足于講出在人的尸體里所看到的東西,讓讀者自己去下結論。小說家始終保持不偏不倚。福樓拜就是這樣寫小說的。”[12]
前面已經提到,《包法利夫人》以前的小說,作品中故事發生的時代背景和社會背景、主要人物的出身,甚至重要活動或習俗的來龍去脈,無不詳詳細細交代得一清二楚,力圖讓讀者感到,一切都有根有據,天衣無縫。可是,讀完《包法利夫人》,讀者會發現,這本小說根本沒有時代背景和社會背景的交代,人物的出身也沒有專門的交代,更沒有家族譜系式的回顧與敘述。作品的著眼點,是描寫現實的生活,描寫人物現實的活動、遭遇和命運。至于這一切的背景,則是一片虛無。這樣做的目的,是盡可能地把作品的主題思想隱藏起來,讓讀者自己去思考、體會、理解。關于這一點,作者福樓拜說得很明確:“我覺得美的,亦即我想寫的,是一本建立在虛無之上的書。它僅僅靠自己,靠其文筆的內在力量來維持,就像地球沒有任何支撐而維持在空中一樣。這是一本沒有主題,或者盡可能讓主題隱而不露的書。”[13]這種“建立在虛無之上”的小說,正是《包法利夫人》整體風格的又一重要特點。
福樓拜是位語言大師,很注重人物性格化的語言描寫。但是在《包法利夫人》里,他對人物對話的描寫顯得相當節制,作品里幾乎見不到大段大段的直接對話。而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突出地運用了人物內心獨白。不僅愛瑪和夏爾,就是羅多爾夫和萊昂,甚至魯俄老爹,都有大段的內心獨白。雖然從整體上講,內心獨白在這部作品中也是局部的,但可以毫不夸張地稱為“包法利特色”。內心獨白正是人物心理上那個最隱秘的領域、那個夢囈般難以表達的領域的流露,是人物的思想在無意識層次的流動,有助于揭示人物的內心世界,使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性格更加豐富,更加充實,更具有立體感,更真實可信。
福樓拜是一位銳意創新的藝術家,他在《包法利夫人》里為追求藝術的完美所做的嘗試,為革新小說的藝術形式做出了重要貢獻,引起了20世紀的現代派小說家們的普遍注意,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意識流小說大師普魯斯特認為,《包法利夫人》中人物內心獨白和動詞非確指過去時的運用,使得福樓拜“幾乎像康德一樣更新了我們對事物的看法,更新了認識及外部世界現實的理論”[14]。存在主義的代表人物薩特稱福樓拜是“現代小說的創始人”“處于當今所有文學問題的會合處”[15]。而60年代“新小說”的主要作家羅伯-格里耶和娜塔麗·薩洛特,在猛烈抨擊巴爾扎克式小說的同時,卻把福樓拜奉為前驅,全面繼承并大大發展了《包法利夫人》革新性的藝術特色,進而把小說的藝術形式推到了極端。現代派小說家們對福樓拜的崇奉和繼承,充分顯示了福樓拜在法國文學史上獨一無二的地位,而一百多年來人們對《包法利夫人》的研究、評價和借鑒,說明這部作品成了現代小說名副其實的經典。法國當代小說家兼評論家蒙泰朗說得好:“法國當代所有作家,至少像我這種年齡的作家,都從他(福樓拜)那里得到了一點什么。”“人們感激他塑造了一個典型——包法利夫人的典型。”[16]
羅國林
注釋:
[1] 福樓拜:《書信集》第Ⅱ卷第六百七十七頁。
[2] 福樓拜:1853年3月14日給科萊夫人的信。
[3] 福樓拜:1857年2月給普拉迪埃的信。
[4] 拉馬丁:1857年1月30日約見福樓拜的談話。
[5] 《波德萊爾全集》第Ⅱ卷第五百二十三頁。
[6] 圣勃夫:《包法利夫人》,1857年5月4日《世界箴言報》。
[7] 左拉:《居斯塔夫·福樓拜》。
[8] 愛琳娜·馬克思:《包法利夫人》英譯本導言。
[9] 莫泊桑:《居斯塔夫·福樓拜》。
[10] 莫泊桑:《居斯塔夫·福樓拜》。
[11] 莫泊桑:《居斯塔夫·福樓拜》。
[12] 左拉:《自然主義小說》。
[13] 福樓拜:《書信集》第Ⅱ卷第三十一頁。
[14] 普魯斯特:《論福樓拜的風格》,1919年3月《新法蘭西雜志》。
[15] 薩特:《家庭的呆子》第II卷第八頁。
[16] 1983年版《包法利夫人》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