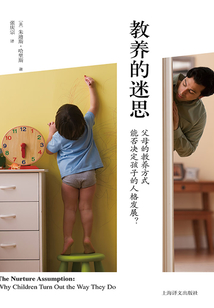
教養的迷思:父母的教養方式能否決定孩子的人格發展?
最新章節
書友吧 1評論第1章 第二版序言
他們叫我“來自新澤西的奶奶”,說我勇氣可大了!十年前,當《教養的迷思》第一版發行時,我住在新澤西,那個時候我已經六十歲了,有一個小外孫女,現在她已到了青春期。目前我四個孫輩中最小的都已上了托兒所。
至于我的勇氣,我得說一點兒都沒變。雖然這是《教養的迷思》的第二版,但它傳遞的信息仍然與第一版相同,即“專家們”是錯誤的。父母的教養并不能決定孩子的成長,孩子的社會化不是家長幫助完成的。教養假設是一個無稽之談,許多支持教養假設的研究都毫無價值。妥協從來不是我的強項。
盡管這本書傳遞了絲毫不妥協的信息,但第一版的面世遭到了激烈的批評,還被召回過一次,我想人們對該書再版的反應不會再那么強烈了吧?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時代已經發生了變化。
我不斷地在超越自己,我的第一個工作是向大家介紹這本修訂版的《教養的迷思》。書中有一個新的介紹,附錄2中“測試兒童發展理論”是全新的。附錄2中描述了一些用來測試我的理論的研究,非常新穎,有的還沒有發表。有趣的是,這些研究不是兒童發展心理學家設計的,而是犯罪學家設計的。
正文中有許多小的變動和一些較大的變動。我修訂了一些錯誤,對有些難懂的、容易引起歧義的段落做了修改。為了讀者能更好地理解后面討論的話題,我對部分章節進行了改寫。但無論是正文部分,還是尾注部分,我沒有做全面的修改,因為這本書的第一版已出版,做大的修改意味著要寫一本新書。
碰巧我寫了一本新書:《基因或教養》(No Two Alike:Human Nature and Human Individuality)。該書除了更新了一些研究之外,還對理論部分進行了更新。這雖然不是大的革新,但新的理論充實了你手頭上這本書的內容。計算機行業人士會說,這不過是又多了一些花里胡哨的東西罷了。原來的理論很好地解釋了社會化的過程,但在解釋人格的個體差異時卻含糊不清,即使在同一個家庭中成長的同卵雙生子身上,人格中的個體差異都十分明顯。《基因或教養》重點討論人格差異,而《教養的迷思》主要討論社會化問題。
我很清楚社會化和人格發展是兩個不同的過程。社會化是讓兒童更加適應自身的文化,使自己的行為與同性別同伴的行為更加相似的過程。而人格發展正相反,它要么保持、要么擴大了個體之間的差異。將這兩個過程混為一談是我的過錯,但自弗洛伊德以來的所有的心理學家都是如此。第一章中談到行為主義者摒棄弗洛伊德心理學,但摒棄得并不徹底。
然而,十年前該書第一版問世時,沒有人指責我背離得不徹底。相反,我被描繪成一個瘋狂的激進分子,一個極端分子。如果說家長對孩子的影響被夸大了,人們可能會打著哈欠接受這個觀點。但我的觀點顯然被視作異端邪說,我認為家長對孩子的人格不會產生持久的影響,也不會對他們走出家門后的行為方式產生影響。這個命題并不是說家長不重要,實際上,他們在孩子生命中扮演了其他的角色。但當媒體把我的論點用簡單的幾個字來表述時,這些細微的差別就已蕩然無存了。《新聞周刊》的封面上赫然出現了“家長重要嗎?”這個大標題。馬爾科姆·格拉德威爾(Malcolm Gladwell)也在《紐約客》上發問“家長重要嗎?”家長看到這個提問后大為光火,這顯然可以理解。一時間,美國幾乎所有的報紙和雜志上都刊登了對這本書的意見,甚至《鄉村遺產》,一個支持馬、騾、牛養殖的雙月刊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
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在《白板說》(The Blank Slate)的第十九章中所描述的發生在《教養的迷思》之后的事情,使他惹火上身。我得設法平息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憤怒。有博士學位的人說我沒有博士學位,不知道我在說什么;發展心理學家們排起隊來告訴記者,說我忽視了所有的證據。有些人指責我,說我允許家長虐待或忽略自己的孩子,說我斷言孩子不需要家長,這些指責都是錯誤的。
但事情也有好的一面。我以前在家里安靜地工作了二十年,除了家人,很少能見到其他人。突然,所有的人都想跟我說話,記者和電視臺的工作人員蜂擁而至,我的家立刻變得門庭若市。當這本書在國外出版后(已被譯成十五種語言),國外的記者也紛紛前來。我收到了來自許多不同國家、不同階層的人寫給我的信和電子郵件,有少數討厭的人,但絕大多數都非常友好。
《教養的迷思》甚至給著名的漫畫家(現在已退休)朱爾斯·費弗(Jules Feiffer)帶來了創作的靈感。他用六幅畫描繪了一個躺在心理分析師診所躺椅上的人。這個人說:“在我這一生中,當我交不到女朋友、找不到工作時,我總是責怪我的母親……就在這個時候這本書出版了。這本書科學地驗證了家長對我們的成長并不起太大的作用,而是我們的同伴在影響我們!……不是我的母親毀了我的人生,而是弗雷迪·阿布拉莫維茨。”
不,不是弗雷迪·阿布拉莫維茨。費弗并不是唯一犯這個錯誤的人。讓我借這個機會消除人們關于同伴影響一個人成長的誤解。
首先,你不能將你的煩惱歸結于你與你母親的關系上,也不能歸結于你與弗雷迪·阿布拉莫維茨的關系上。人際關系的確很重要,他們會產生強大的情感力量,占據我們思維和記憶中的一大部分,但是人際關系對我們的成長并沒有太大的影響。我的理論并不是將社會化歸因為同伴關系或同伴之間的互動。
我用的“同輩群體”(peer group)這個術語也給大家帶來了一些困惑。它讓你想到一群整日在一起閑逛的青少年,當然這些青少年也是同輩群體,但是在該書中,同輩群體的內涵要大得多。我在第七章中解釋過,“群體”是“社會范疇”。所謂社會范疇,例如,“女孩”可以是一群人,也可以不是。如果認同“女孩”的社會范疇,一個小孩就會被社會化為女孩。她要學會孩子的行為方式(而不是成年人的行為方式),還要學會女孩的行為方式(而不是男孩的行為方式)。即使她生活的地方只有兩三個女孩,她仍然會認同“女孩”這個社會范疇。即使其他女孩不喜歡她,不愿意跟她玩,她還是將自己歸類為女孩,哪怕她也不喜歡她們。
對“同輩群體”概念的混淆也引起了其他的誤解。該書中提到的群體社會化理論并不是主要關于青少年這個群體的。社會化不是指那些只發生在大孩子、不發生在小孩子身上的事情,也不是指孩子越大、發生越多的事情。我說的是孩子一旦邁出家門,與其他孩子在一起時,社會化過程就開始了。這個過程早在兩歲時就開始了,對大多數孩子來說,從三歲開始。
該理論也沒有描述近來社會上出現的問題,這些所謂由家長造成的問題只不過是人們臆想出來的罷了。盡管文化在發生變化,但如今的孩子與過去的孩子相比,并沒有更多地受到同伴的影響。群體社會化理論關注的是孩子的智力活動,如今孩子的智力活動與早期孩子的智力活動并沒有什么兩樣。
因此,我在該書中提到的理論和觀點并不僅僅適用于生活在當今復雜的都市化社會中的孩子們。人類學家、生態學家和歷史學家發現不同社會、不同歷史時期的父母教養方式存在著顯著差異。盡管如此,全世界的兒童都是一樣的。在每一個社會里,孩子們都強烈地渴望與其他孩子在一起。至于他們在一起做什么,這在世界范圍內、不同歷史時期基本上都是一樣的。
人們對我另外一個誤解是:我對教養假設的摒棄主要基于雙生子研究。雙生子研究提供的證據固然重要,但它不是唯一的證據。雙生子研究的證據很重要,因為它與許多不斷出現的、令人費解的研究發現吻合。例如,獨生子與有兄弟姐妹的孩子沒有太大的差別,上幼兒園的孩子與在家由父母照看的孩子沒有太大的差別,有兩位同性家長的孩子與有兩位異性家長的孩子沒有太大的差別等。在該書中你會發現許多觀察實例與兒童發展的普遍觀點并不一致。我內心深處儲存的觀察實例為第十二章中所描述的頓悟打下了基礎。正如一位聰明的讀者所說:“設法將現存的事實塞進一個過時的理論框架中就像將一個小號的雙人床單套在一個大號的雙人床上,一個角套上了,另一個角就掉下來。”最后人們不勝其煩,只好把舊床單扔掉。
盡管這是一個家庭主婦的比喻,但并不因為我是全職母親,就排斥教養假設,是證據使然。當我做母親時,大腦中關于兒童發展的觀念都是傳統的、約定俗成的。在我開始對那些觀念產生質疑時,我的孩子已長大成人,成功地過上了成年人的生活。遺憾的是,對于他們的成長,我不能給我自己加分。
但我的理論有證據支撐并不意味著它已被證實。朱爾斯·費弗漫畫中的人物說這本書“科學地證明了家長對孩子的成長是不起作用的”。科學地講,“不起作用”這個觀點是不能被證明的,因為人們很難檢驗“零假設”。與其驗證零假設,還不如捍衛它。我的立場是:父母的教養方式對孩子的成長不起作用。現在輪到信奉教養假設的人們去尋找證據來推翻零假設,他們需要具有說服力、值得推敲的證據。
雖然經過數十年的努力,他們仍然一無所獲。至少到2005年他們還沒有找到相關證據。一位非常坦誠的發展心理學家2005年在一個在線雜志《邊緣》中公開承認:“心理學家還沒有向持懷疑態度的人證明父母有強大的影響力。”在一群回答“你自己都無法證明的東西,你相信是真的嗎?”的科學家和技術專家中,波士頓學院的發展心理學家埃倫·溫諾是其中一員。溫諾說她認為“家長的確塑造了自己的孩子”。雖然她不能證明教養假設,但她依然信奉教養假設。她沒有放棄希望,她堅信總有一天會找到證據,到那時朱迪思·哈里斯將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其他心理學教授(知識不是那么淵博,也不是那么直率)聲稱早在1998年他們就找到了證據。我花了很多時間來考察這些證據,有些發現并不令人感到吃驚,只是研究方法上出了一點問題,然而有些研究發現卻令人不安,即使像我這樣一只疲憊的老鳥也感到深深的不安。你會在《基因或教養》的第三章、第四章中找到那個故事。
在序言的開頭,我異常謹慎地說:“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時代發生了變化。”這句話需要解釋一下,在什么程度上,時代發生了哪些改變。
首先,人們更加接受基因影響行為、基因差異影響個體行為差異的看法。人們更愿意承認孩子除了遺傳父母頭發的顏色和鼻子的形狀外,還遺傳了父母的行為習慣和人格特征。這是一個文化上的轉變,是一個漸變的過程,當然,這和我沒有任何關系,然而,這使人們變得更能接受我的觀點了。問題是迄今為止,許多觀察研究都認為父母對孩子的影響緣于父母與孩子基因的相似性。因此,“我從我媽那兒得到的”這句話現在聽起來有一點歧義:你是指從你媽那兒遺傳的,還是說從你媽那兒學的。十年前,人們對這句話的理解差不多都是“我從我媽那兒學的”。
是文化的改變使人們更加接受我的理論嗎?抑或是與我的理論一致的新發現不斷地涌現出來?隨著時間的流逝,無論是在學術圈內還是學術圈外,人們當初對《教養的迷思》憤怒的反應現在有了明顯的緩和。如今,該書廣泛地被教科書和期刊論文引用,被許多高等院校指定為課程學習和討論的內容,甚至還出現在考試題中。
另一方面,許多引用和討論令人不快。我經常被當作稻草人,隨時準備讓學生打翻在地。讓我感到愉快的引用多半不是來自發展心理學領域,而是來自其他領域,如犯罪學領域。盡管有些研究兒童發展的學者被我爭取過來了,但大多數還沒有,他們仍然在做同樣的、在該書中將被無情剖析的研究。我在介紹的開頭就談到這些研究毫無價值,因為研究者們使用的研究方法使他們無法區分是成長環境對孩子有影響,還是基因對孩子有影響。我主要的興趣是研究環境,而不是基因。只有當我們了解孩子能給環境帶來什么時,我們才知道環境對孩子有什么影響。
在斯蒂芬·平克為《教養的迷思》作的序中,他對該書作了一個過于性急的預測:“我預測該書將是心理學史上的一個轉折點。”也許判斷心理學是否繞了一個大圈還為時尚早,也許要等上二三十年,但現在已經有變化的跡象了。在發展心理學中,我已注意到人們對研究步驟和研究結果的描述已開始處于防守的態勢。心理學其他領域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從學生那兒收到的電子郵件讓我看到了年輕一代成長的希望。
但學術圈外幾乎沒有進步的跡象。雖然人們越來越了解遺傳學,但他們仍然相信教養假設。例如,在最近的一期《時代周刊》上刊登了幾篇關于兒童肥胖的文章。盡管作者承認基因和文化對兒童的肥胖產生影響,但家長依舊要為此負責。“家長如何教孩子控制自己的飲食習慣?”一篇文章問道。“為什么家長為孩子樹立一個良好的飲食習慣如此重要?”問題是沒有任何證據顯示家長教給孩子飲食習慣或家長的榜樣對孩子產生長久的影響。正如第十三章中提到的,養子/女長大成人之后,飲食習慣并不受收養父母的影響。體重不完全由基因決定,超出基因的部分不能怪罪家庭或家長。
我希望我能夠讓撫養孩子這件事變得容易一些,讓家長壓力小一點,但這個愿望并沒有實現。家長仍然沿用他們文化中約定俗成的令人憂心忡忡、勞動強度極大的教養方式。我提出一些善意的忠告,想讓家長們變得輕松起來,但他們卻完全置之不理,甚至連我自己的女兒也是那樣撫養孩子的。
但我為什么指望我能影響自己的女兒呢?
朱迪思·里奇·哈里斯
新澤西中心鎮
2008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