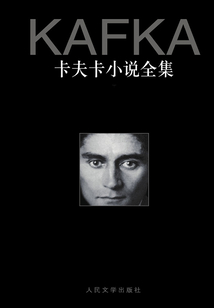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總序
弗蘭茨·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在西方現代文學中有著特殊的地位。他生前在德語文壇上幾乎鮮為人知,但死后卻引起了世人廣泛的注意,成為美學上、哲學上、宗教和社會觀念上激烈爭論的焦點,被譽為西方現代派文學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論年齡和創作年代,卡夫卡屬于表現主義派一代,但他并沒有認同于表現主義。他生活在布拉格德語文學的孤島上,對歌德、克萊斯特、福樓拜、陀思妥耶夫斯基、易卜生、托馬斯·曼等名家的作品懷有濃厚的興趣。在特殊的文學氛圍里,卡夫卡不斷吸收,不斷融化,形成了獨特的“卡夫卡風格”。他作品中別具一格甚至捉摸不透的東西就是那深深地蘊含于簡單平淡的語言之中的、多層次交織的藝術結構。他的一生、他的環境和他的文學偏愛全都網織進那“永恒的謎”里。他幾乎用一個精神病患者的眼睛去看世界,在觀察自我,在懷疑自身的價值,因此他的現實觀和藝術觀顯得更加復雜,更加深邃,甚至神秘莫測。
布拉格是卡夫卡的誕生地,他在這里幾乎度過了一生。到了生命最后的日子,他移居到柏林,試圖擺脫不再是卡夫卡的布拉格。不管怎樣,跟他的同胞里爾克和韋爾弗相比,卡夫卡與布拉格保持著更長時間和更密切的聯系。在這個融匯著捷克、德意志、奧地利和猶太文化的布拉格,卡夫卡發現了他終身無法脫身的迷宮,永遠也無法擺脫的命運。
布拉格是世紀轉折時期奧地利文學一個十分重要的中心。隨著維也納現代派的興起,在二十世紀初,布拉格德語文學進入了一個轉折時期;它打破了迄今為止的區域性影響,在很短的時間里贏得了世界文學的聲望。布拉格也是里爾克和韋爾弗的誕生地。值得注意的是,布拉格德語文學這種突破性的發展正好開始于社會各層講德語的人數日益銳減的時刻。一八八○年,在這個多瑙河王朝北部最重要的都市里,德意志人和德意志猶太人還是一個占總人口百分之十五的少數民族。但到了世紀交替之際,當全市人口增長到四十多萬時,講德語的人僅為三萬左右。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這個比例就變得更小,其中大部分是德意志猶太人。
直到哈布斯堡王朝滅亡前,德意志少數民族的一部分不僅在經濟和文化領域,而且在政治領域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盡管如此,他們越來越陷入孤立的境地。這個以官員、地主和商人為主的階層形成一塊獨立的領地,有自己的大學、德語劇院、報紙和學校等,布拉格德語與捷克語文化之間幾乎就沒有什么共同點。在這個文化大都市里充斥著“一種讓人難以忘懷的、令人眼花繚亂的斯拉夫—德意志—猶太文化的氣氛”[1],各民族的文化意識也不斷地引起激烈的民族沖突,表現了哈布斯堡文化充滿矛盾的危機。
語言問題是造成這種文化氣氛的原因。大約從十九世紀末起,布拉格的德意志人拒絕學習捷克語,捷克人也對講德語的人嗤之以鼻;兩個民族,兩種語言,相互存在,相互排斥,直至敵對。在布拉格,講德語的人只占很小一部分,德語因此也失去了與日常生活的聯系。德意志人和猶太人遭受著與捷克人競爭的折磨。進入二十世紀,德意志人無奈于他們所占比例的銳減,越來越為他們的未來擔心,怕他們有一天會被捷克人吃掉。環境的不穩定決定了布拉格德語知識分子必然產生一種生存危機。對社會矛盾具體的經歷有力地促使他們或者用藝術的手段去表現,或者從理論的角度去闡釋。布拉格是卡夫卡的布拉格:陌生、孤獨、壓抑、痛苦、災難;布拉格是庫賓的小說《那一邊》(1907)中撲朔迷離的夢之國;早期的里爾克也真實地描繪了一個“朦朧的、脆弱的、充滿斯拉夫感傷和沉悶污濁的溫室氣息的”布拉格[2]。這種特殊的生存環境和文化氛圍造就了一批杰出的詩人、小說家、戲劇家、散文家和評論家。在有代表性的作家(卡夫卡、里爾克、布羅德、韋爾弗、基施、柯思費爾德、邁林克、魏斯、貝魯茨、翁卡、烏齊迪爾、魏茨柯夫等)中,絕大多數是猶太人,他們在矛盾日益激化的生存危境中,在理性毀滅的現實里以絢麗多彩的文學藝術形式,道出了對整個現實的危機感。
當時的布拉格作家和評論家烏齊迪爾曾這樣描述說:布拉格的德語作家同時至少根植于四個民族的泉源里:文化和語言上他們理所當然地屬于德意志文化;捷克文化四處包圍著他們;猶太文化在影響著他們,因為它構成了這個城市文化歷史中一個不可分割的主要因素;再就是具有決定性的奧地利文化。[3]
布拉格德語文學是各種文化碰撞交融的結果,但它不是一個統一的文學流派,也沒有任何文學組織,卻共同擁有一個匯聚各種文化的都市與社會傳統,擁有一個危機四伏、風雨飄搖的哈布斯堡王朝。這一切幾乎在所有的布拉格德語作家身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不僅表現在題材和主題上,而且滲透進他們的社會與文學觀念里。在維也納現代派反自然主義潮流的影響下,布拉格德語文學在創作上追求神秘離奇,要么諷刺,要么怪誕。作家們以各自獨有的方式,表現出世紀末日的情感。他們的作品大多以夢幻化的布拉格古城為背景,以異乎尋常的方式,幽默地融朦朧不清的夢幻和對腐朽沒落的現實環境的感受于一體,使現實現象蒙上了一層神秘荒誕的面紗,直至世界毀滅的幻影,既有表現主義的吶喊,又有維也納世紀病的印記,充滿著現實危機感。在表現中,他們打破了傳統的敘述藝術,大多采用了在維也納現代派文學中盛行的小品文敘述風格,追求語言游戲式的描寫,結局的諷喻高潮,突如其來的感染效果,而且往往借用神秘題材和異國色彩的點綴,結合打破幻覺的詼諧更進一步烘托表現效果。
實際上,隨著卡夫卡命運的終結,一個融匯了捷克—德意志—奧地利—猶太文化的布拉格精神也宣告結束。像所有的藝術家一樣,卡夫卡也是他那個時代的產物;社會現實、家庭環境、個人的身體狀況以及其他具體的因素決定了他的命運和創作。他處在一個歷史發展的末期:隨著哈布斯堡王朝日薄西山的掙扎,布拉格的德語文化走向衰敗。但作為藝術家的卡夫卡并沒有去獵取當時時髦的風格,借以表現現實的經歷與感受,而是賦予表現那種末日現象以卡夫卡式的形式,一種并未使他生前發表的為數不多的作品能夠產生廣泛影響的形式。如果卡夫卡在他絕大多數作品和札記里表現了絕望和徒勞的尋求的話,那么這無疑不只是猶太人命運的寫照,而更多溯源于二元王朝面臨衰亡和自我身心的絕望,也就是處于社會精神和文化危機中的現代人的困惑。
卡夫卡的一生是平淡無奇的。他出生在奧匈帝國統治的布拉格,猶太血統,父親是一個百貨批發商。卡夫卡從小受德語文化教育,一九○一年中學畢業后入布拉格大學攻讀德國文學,后迫于父親的意志轉修法學,一九○六年獲得法學博士學位。大學畢業后,先后在法律事務所和法院見習,一九○八年以后一直在一家半官方的工傷事故保險公司供職。一九二二年因肺病嚴重離職,幾度輾轉療養,一九二四年病情惡化,死于維也納近郊的基爾林療養院。
卡夫卡自幼愛好文學。早在中學時代,他就開始大量閱讀世界名著,尤其對歌德的作品、福樓拜的小說和易卜生的戲劇鉆研頗深。與此同時,他還涉獵斯賓諾莎和達爾文的學說。大學時期開始創作,經常和密友馬克斯·布羅德一起參加布拉格的文學活動,并發表一些短小作品。供職以后,文學成為他惟一的業余愛好。一九○八年發表了題為《觀察》的七篇速寫,此后又陸續出版了《變形記》(1912)、《在流放地》(1914)、《鄉村醫生》(1924)和《饑餓藝術家》(1924)四部中短篇小說集。此外,他還寫了三部長篇小說:《失蹤的人》(1912—1914)、《審判》(1914—1918)和《城堡》(1922),但在生前均未出版。對于自己的作品,作者很少表示滿意,認為大都是涂鴉之作,因此在給知友布羅德的遺言中,要求將其“毫無例外地付之一炬”。但是,布羅德違背了作者的遺愿,陸續整理出版了卡夫卡的全部著作(包括手稿、片斷、日記和書信)。一九三五至一九三七年出了六卷集,一九五○至一九五八年又擴充為九卷集。這些作品發表后,在世界文壇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從四十年代以來,現代文學史上形成了特有的一章“卡夫卡學”。
無論對卡夫卡的接受模式多么千差萬別,無論有多少現代主義文學流派和卡夫卡攀親結緣,卡夫卡也不是一個思想家,不是一個哲學家,更不是一個宗教寓言家,卡夫卡是一個獨具一格的奧地利作家,一個開拓創新的小說家。其一,在卡夫卡的藝術世界里,沒有了傳統的和諧,貫穿始終的美學模式是悖謬。一個鄉下人來到法的門前(《在法的門前》),守門人卻不讓他進去,于是他長年累月地等著通往法的門開啟,直到生命最后一息,最終卻得知那扇就要關閉的門只是為他開的。與表現主義作家相比,卡夫卡著意描寫的不是令人心醉神迷的情景,而是平淡無奇的現象:在他的筆下,神秘怪誕的世界更多是精心觀察體驗來的生活細節的組合;那樸實無華、深層隱喻的表現所產生的震撼作用則來自那近乎無詩意的、然而卻扣人心弦的冷靜。卡夫卡敘述的素材幾乎毫無例外地取自普普通通的經歷,但這些經歷的一點一滴卻匯聚成與常理相悖的藝術整體,既催人尋味,也令人費解。卡夫卡對他的朋友雅魯赫說過:“那平淡無奇的東西本身是不可思議的。我不過是把它寫下來而已。”[4]其二,卡夫卡的小說以其新穎別致的形式開拓了藝術表現的新視角,以陌生化的手段,表現了具體的生活情景。毫無疑問,卡夫卡的作品往往會讓人看出作者自身經歷的蛛絲馬跡,尤其是那令人窒息的現代官僚世界的影子。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作者在回復他的出版者沃爾夫對小說《在流放地》的評注時指出:不是這篇小說“令人難堪,而更多是我們共同的以及我們特有的時代,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同樣令人難堪”[5]。然而,卡夫卡的藝術感覺絕非傳統意義上的模仿。他所敘述的故事既無貫穿始終的發展主線,也無個性沖突的發展和升華,傳統的時空概念解體,描寫景物、安排故事的束縛被打破。強烈的社會情緒、深深的內心體驗和復雜的變態心理蘊含于矛盾層面的表現中:一方面是自然主義地描寫人間煙火、七情六欲、人情世態,清楚、真切、明晰;另一方面是所描寫的事件與過程不協調,整體卻往往讓人無所適從,甚至讓人覺得荒誕不經。這就是典型的卡夫卡。卡夫卡正是以這種離經叛道的悖謬法和多層含義的隱喻表現了那夢幻般的內心生活,無法逃脫的精神苦痛和所面臨的困惑。恐怕很少有作家在他們的作品中把握世界和再現世界的時候,能把世界上從未出現過的事物的奇異,像他的作品那樣表現得如此強烈。
卡夫卡的世界是荒誕的、非理性的;困惑于矛盾危機中的人物,是人的生存中普遍存在的陌生、孤獨、苦悶、分裂、異化或者絕望的象征。他的全部作品所描寫的真正對象就是人性的不協調,生活的不協調,現實的不協調。從第一篇作品《一場斗爭的描寫》(1903)開始,他那“籠子尋鳥”的悖論思維幾乎無處不在。在早期小說《鄉村婚禮》(1907)中已經得到充分體現。主人公拉班去看望未婚妻,可心理上卻抗拒這種聯系,且又不愿意公開承認。他沉陷于夢幻里,想象自己作為甲蟲留在床上,而他那裝扮得衣冠楚楚的軀體則踏上了旅程。他無所適從,自我分裂,自我異化,因為他面對的是一個昏暗的世界。夢幻里的自我分裂實際上是拉班無法擺脫生存危機的自我感受,人生與現實的沖突是不可克服的。
短篇成名作《判決》(1912)是卡夫卡對自我分裂和自我異化在理解中的判決,是對自身命運的可能抗拒。許多批評家把《判決》與其后來寫的著名長信《致父親》相提并論,視之為卡夫卡審父情結的自白。實際上,《判決》是作者心理矛盾感受的必然,并不是現實的模仿。小說中的人物更多則表現為主人公格奧爾格·本德曼內心分裂的象征。在一個春光明媚的星期天上午,本德曼寫信給一個遠在俄羅斯的朋友,告訴他跟一個富家閨秀訂婚的消息。這個朋友是光棍漢,流落他鄉,與世格格不入,一事無成。訂婚標志著本德曼的幸福和成就,也就是資產階級世界令人尊敬的人生價值。而這位朋友的存在則成為幸福和成就的障礙,就像本德曼的未婚妻所說的:“格奧爾格,如果你有這樣的朋友的話,你就真不該訂婚。”[6]這位異鄉朋友就是異化本身。本德曼有意要或者更多是必須把寫信透露訂婚的事報告給父親。他在一間昏暗的、密不透氣的房間里會見了父親。尋找父親實際上是轉向良知存在的內心世界。《判決》描寫了父親,也就是良知從隨遇而安的成就世界到格格不入的陌生世界的轉變。由于父親出人意料地直立起來,并施以無比強大的力量——卡夫卡顯然在這里采用了詼諧的喜劇手法——,本德曼被從輝煌的成就世界里分離出來。父親稱他既是一個“純真無邪的孩子”,又是一個“卑劣的人”。[7]本來的命運就決定他是一個與現實世界格格不入的、捉弄生活的故事敘述者,因此父親判他去“死”,本德曼欣然接受。接受良知賜予的、與現實世界不相融的生存便意味著隨遇而安的本德曼的死亡。他懷著對父母的愛投河自殺,告別了追求功利的資產階級現實世界,存在的是一個漂流他鄉的陌生人。
卡夫卡于一九一五年發表的《變形記》是中篇小說的代表作。小說主要從主人公的視角出發,描寫了在家庭與社會的壓迫下人的異化現象。如果《判決》中的本德曼是在自我分裂中尋求自身歸宿的話,那么,《變形記》里的主人公在自我異化中感受到的只是災難和孤獨。一天早晨,推銷員格里高爾·薩姆沙從不安的睡夢中醒來,發現自己變成了一只甲蟲。他掙扎著想從床上起來,但是,變形的身體和四肢無論如何也不聽使喚。他擔心失去工作,不能再掙錢養家,感到十分恐懼。他的出現使人們都為之驚倒。前來催促他工作的公司秘書奪門而逃,父親厭惡他,母親很悲傷,妹妹開始時憐憫他,給他送食物和打掃衛生,但后來也厭倦了。格里高爾變成甲蟲之后,他厭惡人類的食物而喜歡吃腐敗的東西;他總是躲在陰暗的角落里或倒掛在天花板上。然而,他仍然保持著人的心理,能夠感覺、觀察、思考和判斷,能夠體會到他的變形使自己陷入無法擺脫的災難與孤獨中,給家庭招來了很大的不幸。生理上和精神上的雙重痛苦日夜折磨著他。一天,格里高爾被妹妹的小提琴聲吸引出來,搞得舉家不寧,家里招來的房客們大為不滿,吵著要退租。他被視為“一切不幸的根源”,連憐憫他的妹妹也要無情地“把他弄走”。[8]自此,他不再進食,被反鎖在堆滿家具的房中,在孤獨中變成了一具干癟的僵尸。格里高爾死后,全家人如釋重負,永遠離開了那座給他們帶來不幸的公寓。在郊外春意盎然的陽光下,父母親突然發現,自己的女兒已經長成一個身材豐滿的美麗少女,他們的心中充滿了夢想和美好的打算。
卡夫卡在這篇小說中用寫實的手法描寫荒誕不經的事物,把現實荒誕化,把所描寫的事物虛妄化。人變甲蟲,從生理現象看,是反常的、虛妄的、荒誕的;而從社會現象上講,又是正常的、可能的、現實的。卡夫卡在這里追求的不是形似而是神似。他以荒誕的想象、真實的細節描寫、冷漠而簡潔的語言表述、深奧莫測的內涵,寓言式地顯示出荒誕的真實、平淡的可怕,使作品的結尾滲透辛辣的諷刺。格里高爾夢幻式的心理感受深刻地暴露了那個社會里人與人之間赤裸裸的利害關系。
無論卡夫卡的創作多么反常,變化多么多端,他的作品越來越趨于象征性,風格越來越富有卡夫卡的特色,他未竟的三部長篇小說體現了“卡夫卡風格”的發展。
寫于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四年間的長篇小說《失蹤的人》(1927年出版)敘述的是一個名叫卡爾·羅斯曼的少年的故事,他十六歲時因被一個女仆引誘而被父母趕出家門,孑然一身流落異鄉美國。卡爾天真、善良、富有同情心,愿意幫助一切人。由于形形色色的利己主義者和陰險的騙子利用卡爾的輕信,他常常上當,被牽連進一些討厭的冒險勾當里。卡爾要尋找賴以生存之地,同時又想得到自由,他與那個社會格格不入,愈來愈陷入卡夫卡的迷宮世界里。從主人公的坎坷行蹤里,可以讓人看到一個比較具體可感的社會現實。作者從未到過美國,因此,他筆下的美國無疑是自身生存環境的映像。《失蹤的人》的創作或多或少地受到狄更斯的影響,但在敘述風格上,卡夫卡已經開始了獨辟蹊徑的嘗試,尤其是采用了主人公的心理視角和敘述者的直敘交替結合的方式,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展露出現代小說多姿多彩的敘述層面,形成分明而渾然的敘述結構,為其小說創作奠定了基礎。
如果說《失蹤的人》還帶有模仿批判現實主義作家的痕跡,那么,《審判》(1914—1918)便完全是“卡夫卡風格”了。后者的內容已遠非前者那么具體,其普遍化的程度已近乎抽象。《審判》是布羅德最先整理出版的卡夫卡作品(1925年),由此西方現代文學也開始了爭論不休的卡夫卡一章。
《審判》的主人公約瑟夫·K是個銀行高級職員。一天早晨,他莫名其妙地被法院逮捕了。奇怪的是,法院既沒有公布他的罪名,也沒有剝奪他的行動自由。K起先非常氣憤,尤其在第一次開庭時,他大聲譴責司法機構的腐敗和法官的貪贓枉法。他決定不去理睬這樁案子。但日益沉重的心理壓力卻使他無法忘掉這件事,他因此慢慢地厭惡起銀行的差事,自動上法院去探聽,對自己的案子越來越關心,并四處為之奔走。但聘請的律師與法院沆瀣一氣,除了用空話敷衍外,一直寫不出抗辯書。K去找法院的畫師,得到的是“法院一經對某人提出起訴,它就認定你有罪”[9]。最后在教堂里一位神甫給他講了“在法的門前”的寓言,曉諭他“法”是有的,但通往法的道路障礙重重,要找到“法”是不可能的,人只能低頭服從命運的安排,一切申訴只是無謂的申訴。小說結尾,K被兩個穿黑禮服的人架到郊外的采石場處死。
《審判》的表現充滿荒誕和悖謬的色彩,無論從結構和內容上都是“卡夫卡風格”成熟的標志。作者運用象征和夸張的手法,寓言式地勾畫出一個既陌生又熟悉的世界。《審判》的藝術結構多線交織,時空倒置,所描寫的事件和過程突如其來,不合邏輯,荒誕不經,讓人感到如陷迷宮。作為受害者,K的反抗使他越來越陷入任人擺布、神秘莫測、似真似幻的天羅地網里,遭受幽靈似的不可抗拒的力量的折磨;但作為上層社會的一員,K又是與他自身相對立的現實的一部分,他覺得自己不干凈,于是產生了強烈的負罪感。他在審視自己的時候,四周的一切顯得那么朦朧模糊,變化莫測,像比喻一樣虛幻,黯淡無光。因此,他除了傲視一切的絕望以外,簡直是什么也沒有了,K成為一個進退維谷的矛盾體。實際上,這部小說通過主人公的內心體驗,也就是審判和自我審判,從頭至尾給人以壓迫感。這種壓迫感來自那無所不在的“法”的力量:“毫無疑問,在這法庭一切活動的背后……,活動著一個龐大的機構。這個機構不僅雇用了貪贓枉法的看守,愚蠢可笑的監督官和養尊處優糟糕透頂的預審法官,而且無論如何還豢養著一個高級的和最高級的判決組織,那里有一群數不勝數、必不可少的追隨者……,甚或還有劊子手……這個龐大的機構存在的意義又何在呢?它的存在不外乎就是濫捕無辜,給他們施加荒唐的和大多數情況下不了了之的審判……既然這一整套都如此的荒唐不堪,又怎樣來禁止官員們惡劣至極的貪贓枉法呢?”[10]既然有這樣一個是非不分、貪贓枉法、藏污納垢的龐大的機構凌駕于一切之上,那么,誰能幸免于無妄之災呢?“像一條狗!他說,仿佛他的死,要把這無盡的恥辱留在人間。”[11]這也是《審判》留給讀者的深思。
與《審判》相比,卡夫卡的最后一部長篇小說《城堡》(1921—1922)更具“卡夫卡風格”。小說主人公K自稱是土地測量員,受城堡伯爵的雇用來到附近的一個村子。城堡雖然近在咫尺,對于K卻可望而不可即,他永遠進不去。他在村子里經歷了一個又一個反常現象,幾乎連棲身之地都不容易找到。據說管K工作的是一個名叫克拉姆的部長,K千方百計要見到克拉姆,但除了得到信差送來的兩封內容矛盾的信以外,始終見不到人。他在村子里一步步陷下去,最后甚至斷絕了與城堡一切聯系的可能性。小說沒有寫完,據布羅德在《城堡》第一版后記中說,卡夫卡計劃的結局是,K將不懈地進行斗爭,直至精疲力竭,在彌留之際,城堡傳諭,準許K在村中居住和工作,但不許進城堡。
《城堡》是卡夫卡象征手法的集中體現。“城堡”既不是具體的城市,又不是具體的國家,而只是一個抽象的象征物。它象征著虛幻的、混亂的世界,象征著給人們帶來災難的、不可捉摸的現實,也是整個國家統治機器的縮影。卡夫卡所著力描寫的,不是這個象征物本身,而是主人公對它的體驗。K來到城堡領地,好像進入了一個魔幻世界,出現在他面前的一切都是朦朧的、突如其來的、不合邏輯的、稀奇古怪的、驚心動魄的。為了進入城堡,他無時無刻不在進行著頑強的斗爭,但是,他無論使用什么辦法都徒勞無益,永遠也達不到目的。他好像落在無形的蛛網上,無所適從,無能為力,城堡似乎很近,卻又很遙遠;官員們的態度含含糊糊,模棱兩可;公文函件似是而非,難以捉摸。像《審判》里的約瑟夫·K一樣,K對“城堡”制造的迷宮一籌莫展,忍受著荒誕的煎熬,其生存的現實發人深思。
“卡夫卡風格”獨成一家,卡夫卡的作品是留給后人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永遠解不盡的謎。正因為如此,世界現代文學史上才形成了一個方興未艾的卡夫卡學。
自《世界文學》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發表卡夫卡的小說《變形記》的中譯本至今,卡夫卡在我國的翻譯介紹和接受走過了二十幾個年頭。特別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以來,各種譯本源源問世。這些譯本中,除了個別作品譯自英文版外,絕大多數選取了卡夫卡的摯友馬克斯·布羅德整理出版的版本。我們這套《卡夫卡小說全集》選自《卡夫卡全集》的校勘本(德國菲舍爾出版社,1994年),包括作者創作的(生前發表和未發表的)全部長篇、中篇和短篇小說。編者之所以選取這個負有盛名的校勘本,是因為它忠實地根據卡夫卡的手稿,既保留了原作無規則的標點符號和異乎尋常的書寫方式,又突出了原作完成和未完成的兩個部分,同時也糾正了布羅德的一些勘誤,尤其對三部未竟的長篇小說在章節和結尾的校勘上不同于布羅德版本,原原本本地再現了作者手稿的風貌,為翻譯和認識卡夫卡的作品提供了很有價值的參考。
《卡夫卡小說全集》力圖為我國的卡夫卡讀者和卡夫卡研究再現一個新的視野范圍。在譯介卡夫卡的探索中,我們在此愿與所有對卡夫卡感興趣的同仁共勉。
編者 韓瑞祥 仝保民
2003年3月1日
注釋
[1] W.M.約斯頓:《奧地利文化史》第275頁,維也納,1992年。
[2] C.馬格里斯:《奧地利文學中的哈布斯堡神話》第78頁,薩爾茨堡,1988年。
[3] F.烏齊迪爾:《卡夫卡在這里》第7頁,慕尼黑,1966年。
[4] 轉引自《十八世紀以來的德國文學史》第464頁(茲邁伽什等著),柯尼希施泰因,1985年。
[5] F.卡夫卡:《1902—1924年的書信》第150頁,法蘭克福,1992年。
[6] 卡夫卡:《判決》,見《中短篇小說集》第20頁,法蘭克福,1990年。
[7] 卡夫卡:《判決》,見《中短篇小說集》第32頁,法蘭克福,1990年。
[8] 同上,第94頁。
[9] 卡夫卡:《審判》第157頁,法蘭克福,1994年。
[10] 卡夫卡:《審判》第56頁,法蘭克福,1994年。
[11] 同上,第241頁。